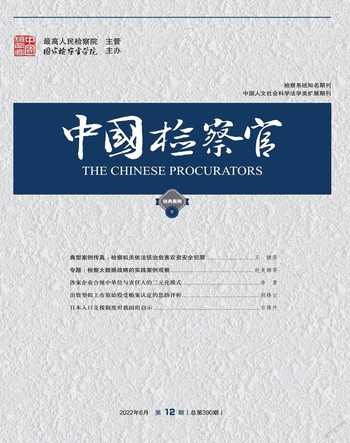獄警違規為服刑人員傳遞款物行為如何定罪
任慶明 王升洲
一、基本案情
2014年至2017年,何某在擔任某監獄監區管教民警期間,多次接收本監區及其他監區服刑人員家屬的匯款及現金共14.69萬元,受托從監獄外代買香煙、茶葉、藥品等生活用品并傳遞現金供24名服刑人員使用,何某從中截留2.9萬元占為己有。
二、分歧意見
對于本案如何處理,主要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是不構成濫用職權罪。根據刑法第397條及“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瀆職案件司法解釋》)第1條,認定濫用職權罪,要求行為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即符合人員傷亡、經濟損失、“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以下簡稱“三種情形”),以及“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四個“重大損失”情形之一。本案沒有因瀆職行為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2.9萬元非違規傳遞行為本身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沒有引發輿情或群訪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不符合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第四種情形是兜底條款,未明確適用條件,不應當適用。
第二種意見是構成濫用職權罪,行為應認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本案雖然沒有因瀆職行為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但多次傳遞物品的行為嚴重破壞監管秩序,損害國家機關的形象和聲譽,在監獄內部影響惡劣,符合“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情形。
第三種意見是構成濫用職權罪,但應適用兜底條款。瀆職行為未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也沒有引發輿情、群訪、社會矛盾糾紛等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但嚴重破壞監獄的監管秩序,威脅監獄的安全穩定,屬于“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本案行為嚴重破壞監管秩序,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應當定罪處罰
實踐中,通常的傳遞情形是為服刑人員傳遞生活用品等普通物品,改善其生活,而比較嚴重的則是傳遞手機、白酒、毒品、現金等違禁品。獄警違規傳遞物品,特別是違禁品供服刑人員使用,會破壞監管秩序,威脅監獄的安全穩定和服刑人員的人身安全。據公開報道,因獄警傳遞違禁品導致服刑人員吸毒或飲酒致死,服刑人員利用傳遞的手機實施詐騙、利用現金行賄、賭博的情況時有發生。[1]法律和相關規定對服刑人員私藏違禁品及獄警傳遞物品或違禁品歷來都是從嚴懲處。司法部《關于切實加強監獄、強制隔離戒毒所違禁物品管理的若干規定》第1條規定,罪犯私藏使用違禁品的,屬于違反改造規定的行為,3年內不得提請減刑假釋;第2條規定,監獄警察違反規定傳遞違禁物品給罪犯的,視為情節嚴重,給予開除處分。《監獄法》第14條規定,監獄民警違反規定,私自為罪犯傳遞信件或者物品,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本案,何某為謀私利,濫用監管職權,在長達4年的時間內為本監區及其他監區的24名服刑人員傳遞物品及現金,主觀惡性深,涉及人員廣,時間跨度大,嚴重破壞監獄監管秩序,威脅監獄安全穩定。雖然行為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社會負面輿論等嚴重后果,但其社會危害性嚴重,應以濫用職權罪定罪處罰。至于依據《瀆職案件司法解釋》中哪種情形入罪,則應在行為社會危害性評價基礎上再對法律條文解釋適用。
第一種觀點沒有從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基本點出發,拋開了基礎事實評價,并機械理解司法解釋的適用條件,筆者并不贊同。
(二)本案濫用職權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不宜以“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評價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獄警”“捎帶”“傳遞”“濫用職權罪”為關鍵詞搜索,發現以“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作為唯一裁判理由認定多次傳遞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的裁判文書共13篇,有罪判決率為100%。其中,一審判決9篇、二審裁定4篇,涉及7個省份,時間跨度為2014年至2019年。從內容來看,除1篇判決依據媒體報道認定“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外,其余12篇判決和裁定對“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證據未列舉,基本是簡單說理。說理邏輯可分兩種:第一種是簡單論述傳遞行為本身的惡劣性,然后直接認定為“損害國家機關形象和聲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第二種是把封閉的監獄解釋為“社會”,將“在監獄造成惡劣影響”代替“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以上裁判文書盡管論證方式不同,但均認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對此,筆者并不贊同。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認定目前雖有分歧,但比較權威的指導性案例和參考刊物已經給出典型含義范疇和證明標準。《刑事審判參考》第1089號案例“楊德林濫用職權、受賄案”對“造成惡劣社會影響”進行了解讀。根據該案例,惡劣社會影響“一般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1)瀆職行為嚴重損害國家機關形象,致使政府公信力下降的;(2)瀆職行為引發新聞媒體廣泛關注,引起強烈社會反響的;(3)瀆職行為造成大規模上訪、暴力沖突等事件,影響國家機關正常職能活動的;(4)瀆職行為誘發民族矛盾糾紛,嚴重影響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5)瀆職行為造成其他惡劣社會影響的”。[2]2012年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羅建華、羅鏡添、朱炳燦、羅錦游濫用職權”(檢例第6號)對“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也做了闡述。該案例認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人員因濫用職權導致大量商販無序占道經營、多次暴力抗法,引起群眾強烈不滿的,應當認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3]綜合上述案例及實踐,筆者認為,認定“造成惡劣社會影響”需要把握兩個方面:一是要有具體表現形式,不能泛化理解。任何瀆職行為都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有負面性或惡劣性,但一般不能因為瀆職行為本身的惡劣性直接認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否則任何瀆職行為都可以套用該條款,而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等作為與“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并列的評價要素就沒有存在意義了。在犯罪構成上,輿情、群訪、社會矛盾糾紛等具體表現形式是瀆職行為引發的后果,不可忽略。案例中的情形,沒有在社會層面上引起不良影響的證據,不應直接認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二是要有社會公開性。特定范圍或系統內的感知并非不特定社會群體的感知,無法在社會層面上造成惡劣影響。有的觀點認為,監獄雖然具有封閉性,但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因此將“在監獄造成惡劣影響”代替“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但這并不合理。結合法律條文的前后語境以及指導性案例的觀點,社會影響應該是公開性的,不能因裁判便利對“社會影響”概念作擴大解釋。
應當說,在認定案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上,司法者大多形成了情感和經驗上的共識,但由于沒有人員傷亡、經濟損失這種量化的標準,對兜底條款更缺乏適用的經驗遵循,于是將此類行為多強行解釋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使“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成為實質上的兜底條款[4],這既模糊了兩種情形之間的法律適用關系,又封閉了法律適用空間,容易對案件辦理造成困擾。筆者認為,在“造成惡劣社會影響”適用愈泛化的情況下,司法者愈要慎重,不應隨意適用,如果不具備“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典型特征,可以考慮適用兜底條款。
綜上,第二種觀點忽略“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具體表現形式及社會公開性特點,強行解釋適用法律,筆者也不贊同。
(三)本案可以考慮適用“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兜底條款
1.相關指導意見和司法解釋表明,有些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導致的“重大損失”并未以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可折算的經濟價值數額)或惡劣社會影響評價。《關于加強查辦危害土地資源瀆職犯罪工作的指導意見》(最高檢原瀆檢廳發,仍具參考指導意義)指出,土地遭破壞的,對損失后果的認定要考慮被破壞土地的性質、地理位置、實際用處等差異所產生的土地價值,受損后無法用經濟價值數額衡量的特殊性,可以采取面積標準認定損失后果。在此,面積標準與經濟價值數額顯然是有區別的。《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規定,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基本農田20畝以上的,屬于“致使國家或者集體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該解釋規定的“特別重大損失”情形將瀆職行為的危害性量化,以審批面積,而非農田損毀的實際后果為標準衡量。再比如,《關于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符合本條款情形之一,致使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的機動車被辦理登記手續,數量達到3輛以上或者價值總額達到30萬元以上的,以濫用職權罪定罪。根據該規定,“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標準之一是機動車被辦理登記手續的數量,這同樣難以用人員傷亡、經濟價值數額或者惡劣社會影響準確評價。以上指導意見和司法解釋以面積、數量認定重大損失,其本質是將瀆職行為或結果量化,這種量化可以體現行為的危害性,但無法用人員傷亡、經濟價值數額或惡劣社會影響評價來準確概括,因此可考慮歸入兜底情形。另需說明的是,很多瀆職罪的后果難以折算為經濟價值數額,不必需也不必要通過經濟價值數額的折算體現危害性。
2.從瀆職類犯罪的相互關系來說,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重大損失”的表現形式難以用人員傷亡、經濟價值數額或惡劣社會影響評價完全概括。《瀆職案件司法解釋》第2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因不具備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則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條至第四百一十九條的規定,但依法構成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犯罪的,以濫用職權罪或者玩忽職守罪定罪處罰”。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與刑法第9章規定的其他瀆職罪是普通法條與特殊法條的關系,其他瀆職罪的重大損失情形是包含于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之中的。經統計,刑法第9章瀆職罪的罪名共有35個,在罪狀中明確將“重大損失”作為入罪或法定刑升格條件的罪名有13個。經對法律和司法解釋進行分析,上述13個罪名涵蓋的“重大損失”情形主要有以下6個種類:人員傷亡、經濟價值數額(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量化的生態環境或公共利益實際損害(環境監管失職罪)[5]、市場或金融秩序被嚴重破壞(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權罪)、量化的瀆職行為(非法批準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6]、引起國際經貿糾紛(商檢失職罪)等。以上類型化的行為或結果都屬于重大損失情形,種類比較靈活具體,都可以納入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重大損失的范圍,但難以用人員傷亡、經濟價值數額和惡劣社會影響完全概括。因此,當遇到三種情形無法準確評價時,就可以考慮適用兜底條款。
3.司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可以適用兜底條款。上述罪名分析可見,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重大損失的表現形式是靈活多樣的,而司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也是如此。《關于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規定,違反刑事訴訟法規定,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羈押,情節嚴重的,對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玩忽職守罪或者濫用職權罪追究刑事責任。根據該《通知》精神,錯誤追訴導致被害人長期被羈押的構成瀆職犯罪,但人身自由權利被侵犯作為瀆職罪后果是無法用人員傷亡及經濟價值數額來衡量的,如果沒有導致社會矛盾糾紛、負面輿論等,也不能抽象地認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因此可考慮以兜底條款入罪。再比如實踐中常見的有案不立、壓案不查、以罰代刑或違規調解刑事案件導致犯罪人不受追訴或繼續犯罪、濫用司法拘留權侵犯人身自由等濫用職權情形,與《通知》規定的情況類似,通常難以用三種情形界定,均可考慮以兜底條款入罪。
4.司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適用兜底條款應當把握“相當社會危害性”的原則。兜底條款的適用邏輯并非是將已有明確情形簡單排除后直接套用,對其適用原則,最高法在“王力軍非法經營再審改判無罪案”(指導案例97號)中已經明確。該案裁判理由認為,非法經營罪“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適用,應當根據行為是否具有與已經明確的非法經營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進行判斷。[7]司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兜底條款的適用同樣要遵循“相當社會危害性”原則,但也要注意變通。相比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等許多犯罪都可以造成的后果,人身自由被侵犯、犯罪被放縱、司法秩序遭破壞等特殊后果往往與司法工作人員職權的不正當行使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社會對自由、正義、秩序等價值被破壞的負面感受很多時候并不亞于有形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例如,張玉環案中,被害人26年的人身自由及精神損耗是難以用某個標準量化的。綜上,兜底條款適用要有實質前提,即在充分考慮司法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特殊性的基礎上把握后果的相當社會危害性。
筆者認為,案例的行為屬于因多次實施而情節嚴重的濫用職權行為(可量化),其危害性在于長期破壞監管秩序,構成對監獄安全穩定的重大威脅,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且難以用三種情形評價,歸入兜底條款較為妥當。當然,舉輕以明重,如果傳遞違禁品的行為導致罪犯又犯罪的,如果不能以三種情形評價的,也可考慮適用兜底條款。
另需說明的是,適用兜底條款并不意味著對法律的恣意選擇,只有從客觀實際出發,正確認識并合理理解運用,才能充分發揮兜底條款的作用,減少案件論證的難度和爭議。司法者在辦案中應準確理解兜底條款,厘清其與三種情形的關系,進而激活該條款,拓展司法工作人員瀆職犯罪法律適用空間,形成豐富的司法判例,為推動出臺更具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釋打下實踐基礎。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副檢察長、二級高級檢察官[300000]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第五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300000]
[1] 參見《獄警帶400斤白酒入監,服刑人發600條朋友圈,特殊待遇的背后》,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20-11-22/doc-iiznezxs3099640.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1月16日。
[2]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3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7-105頁。
[3] 參見《第二批指導性案例》,正義網https://www.spp.gov.cn/jczdal/201608/t20160811_162303.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月13日。
[4] 參見商鳳廷:《瀆職罪中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司法認定》,《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5]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29號)第1條第10款至第17款、第2條。
[6]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林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草原資源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7] 參見《王力軍非法經營再審改判無罪案》,中國法院網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12/id/3614721.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