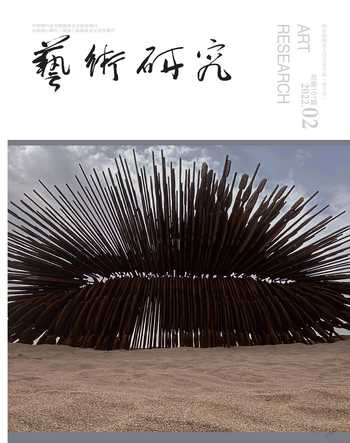歌劇《國之歌》藝術內涵分析
葉勇
摘要:歌劇《國之歌》以聶耳、田漢為主要人物,整部作品充分利用歌劇藝術本真情感的抒發與歌唱抒情表達相結合、假定舞臺空間與情感共鳴營造相結合的藝術手法,講述了聶耳從愛國者走向革命者的發展道路,是利用好歌劇形式講好中國故事的典范之作。
關鍵詞:國之歌 藝術內涵 家國情懷
以人民音樂家聶耳、劇作家田漢為原型創作的大型歌劇《國之歌》,自2019年正式上演以來,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這部匯集了著名導演倪東海、編劇陶國芬、作曲家張昕、朱慧等人創作的作品,圍繞聶耳、田漢等藝術工作者在抗日時期為喚醒民眾而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為主線展開。全劇分為“救亡抗爭”“入黨盟誓”“囚牢言志”“攜手譜曲”“號角長鳴”五個樂章依次展開,在表達劇中人物內心對祖國和人民摯愛之情的同時,也展現了聶耳、田漢的戰友情,特別在《國之歌》的主線索中加入了他們與安娥的革命友誼,以及二人與愛國青年的相知,無疑是為整部歌劇的愛國敘事加入了浪漫主義的色彩。作為一部凝聚了深厚家國情懷的歌劇,《國之歌》的價值由其豐富的藝術內涵得到體現的。
一、本真情感的抒發與歌唱抒情表達的結合
歌劇的突出特征是音樂特征,故而需要以歌唱抒情的方式來表達創作者的感情。但它同時不能違背以本真情感為基本出發點的藝術要求,二者的結合是判斷一部歌劇作品好壞的重要參考標準。大型原創歌劇《國之歌》,在本真情感的抒發與歌唱抒情表達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這是本部歌劇作品取得成功的關鍵之一。主創團隊正是憑借著對歌劇藝術特征的準確把握,為《國之歌》的誕生做好了充分準備。此外,我們還應看到《國之歌》在遵循藝術規律的同時,并沒有讓歌劇的演唱技術手段成為主導作品的因素。后者才是真正引導歌劇藝術形式與表現內容之間完美融合的關鍵所在。
(一)本真情感的抒發
作為20世紀初傳入我國的舶來品,歌劇最早誕生于17世紀的意大利,其歷史則可追溯至古希臘戲劇表演的劇場音樂。應該看到,戲劇與歌劇都屬于依托劇場元素的藝術類型,但二者之間存在著最大差異也不容忽視——即歌劇以音樂、歌唱為主要的表達手段。這就意味著相對于戲曲音樂遵循程式化模式,歌劇更多采用“一曲一用”的模式。這意味著歌劇創作團隊必須根據作品內容,來為每一個章節創作配樂。
研究者也指出:“戲劇作為一種樣式,其內質和外在形式既有穩定的因素,又有變異的成分,因而對它的認識就不能僵化。”1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創作原則,不僅是要在更高的層次上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更是要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創造性發展、創造性轉化中不斷提升。二者的結合帶給《國之歌》的主創團隊更多的啟示,他們從聶耳、田漢的生平經歷入手,將大量的素材加以整理,最后整理出“救亡抗爭”“入黨盟誓”“囚牢言志”“攜手譜曲”“號角長鳴”五個樂章,分別對應整部作品的不同的歷史階段。一方面,為還原歷史場景創造了必要的情感氛圍;另一方面,也為當代觀眾走進歷史、理解歷史提供了必要的藝術鋪墊。
該劇導演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歌劇創作不同于一般音樂作品,必須將本真情感的抒發放在首位。首要的是在歌劇表達手段的詠嘆調和宣敘調之間尋求平衡,不僅要確保以抒情獨唱為主要功能的詠嘆調和以朗誦說明為主要定位的宣敘調之間互不干涉,更要巧妙地借鑒諸如小劇場歌劇的成功經驗。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歌劇舞臺上演的故事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特征,更是由于現代歌劇面對的對象是年輕一代的受眾。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歌劇舞臺營造凝重、象征、悲壯的演劇風格與樣式,強調時代特征與歌劇特性,以象征性、表現性、通雅化演繹故事。探索與嘗試西洋歌劇中國化,古典戲劇通雅化,美聲與民族唱法融合化的新路子。這不僅是《國之歌》的主創團隊試圖探索的發展方向,也是中國歌劇真正走向本土化的一次有
益嘗試。
(二)歌唱抒情的表達
作為一部歌劇作品,《國之歌》在突出自身藝術特征的同時,始終將歌唱抒情作為主要的表現手段加以應用。以第二場的表演為例,劇中田漢對著“小豆苗”展開想象。在這里,“小豆苗”采用了象征的藝術表現手法。所謂象征是指:“通過采取類比聯想的思維方式,以某些客觀存在或想象中的外在事物以及其他可感知到的東西,來反映特定社會人們的觀念意識、心理狀態、抽象概念和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借助于某一具體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藝術家某種深邃的思想,或表達某種富有特殊意義的事理的藝術手法。”2“小豆苗”實則是象征著廣大人民群眾對和平的向往。為了能夠將這種復雜、含蓄、深沉的情感準確地表達出來,主創團隊創作了:
“小苗兒,別害怕,心若安,哪兒都是家”。這是一句飽含著愛國者的深情和革命者眼淚的歌詞,雖表達了現實社會的殘酷,更多則是對必將戰勝侵略者的樂觀主義情懷。正如田漢所作《義勇軍進行曲》中“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起我們新的長城......”作為《風云兒女》的主題歌向中國人民唱響了民族解放的號角,始終昂揚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就歌劇藝術自身而言,本真情感的抒發必須借助一定的手段,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藝術創作原則。《國之歌》的主創團隊敏銳地捕捉到歌劇的創作規律,從而為整部作品藝術內涵的表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演唱手法是歌劇作品的表現手段,而不應該喧賓奪主。僅就這一點而言,《國之歌》無疑很好地在遵循歌劇藝術創作原則和豐富情感表達之間尋找到了平衡點。進一步來說,《國之歌》的成功也為此后原創歌劇的創作樹立了典范,成為運用歌劇藝術踐行“講好中國故事”的最佳詮釋。
二、假定舞臺空間與情感共鳴的營造
《國之歌》以1933年至1935年的中國社會為背景,圍繞聶耳、田漢的戰友情,以及他們和地下工作者安娥、紫姝的情感為主要表現內容。由于采用了歌劇的表現形式,使得整部作品的藝術內涵和表現方式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假定舞臺空間和情感共鳴的營造兩個方面。進而言之,假定舞臺空間為整部作品提供了表現空間(或曰載體),是真正成就一部作品藝術內涵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而情感共鳴的營造則是前者最終試圖達到的目標。在這一點上,我國歌劇工作者已經積累了十分豐富的舞臺實踐經驗。《國之歌》的成功正是建立在既往舞臺表演經驗的基礎上,為歌劇作品本土化探索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一)假定舞臺空間
以抽象的藝術表達取代具象的表現內容是舞臺藝術的重要
手段,其作用不僅在于跨越了舞臺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隔絕,更
在于它作為一種表現手段較好做到了露巧藏拙和揚長避短,從
而為演員在舞臺藝術表演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所謂“抽象”,不是要在舞臺上呈現物質的存在,而是以“虛”的手段讓主創團隊試圖傳遞的信息更為準確、更為強烈。以歌劇《國之歌》為例,在第三場中,聶耳、田漢、安
娥、紫姝四人分別在日本小屋、監獄一角、上海寓所和剪影,導演將其定格在同一空間。然后,聶耳停止讀電影劇本、田漢放下小豆苗、安娥停下筆、紫姝開始思念。四個空間的自由變換雖有對電影中蒙太奇手法的借鑒,實則是將具象世界變換為抽象世界。當觀眾感受到四個空間的變化時,舞臺是對生活中自然狀態的變型,但其目的則是為了能更好地復原生活。對觀眾而言,他們的審美定位不是去考證歷史,而是來欣賞作品。后者直接決定了舞臺空間假定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不是承擔獨立表現功能的人物,而是要在抽象世界中讓自身成為觀眾的審美尺度。
僅就這一點而言,《國之歌》無疑是成功。它綜合運用音樂、歷史、舞臺等多個領域于一體,讓主創團隊人員相輔相成,在假定的舞臺空間中,為觀眾呈現了“真實”的國歌誕生故事。這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生動個案。
(二)情感共鳴的營造
回溯中國現代戲劇的發生,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其實經歷了從單純照搬西方戲劇劇目、嘗試本土化和本土化模式逐漸成熟的發展過程。在外來的影響和刺激下,中國傳統戲劇經過種種動蕩、崩解和調適,才最終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而最終能夠實現戲劇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以講好中國故事原則指導下,在受眾與創作團隊之間實現了情感共鳴。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抽象在推到極端時,都會變成荒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3這一點運用于假定舞臺空間的營造既有必要,以抽象舞臺形象為表現手段的歌劇必須以具象的藝術呈現為輔助,二者的結合方能平衡具象與抽象之間的關系。這不僅是因為舞臺美學的抽象為觀眾提供了凈化了的藝術世界,更在后者營造的形式美空間具有強大的感染力。馬克思在把人的勞動與動物的活動作區別時曾指出,人與動物的差別,關鍵在于人具有按照意識去進行生產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人還能將這種能力遷移到審美對象上去。這種內在的尺度,就包括審美尺度,也即審美標準。
具體到歌劇《國之歌》中,聶耳作為整部作品的靈魂人物。他的青春活力、他的英年早逝,無疑都強化了他本人作為《義勇軍進行曲》作曲者的英雄主義色彩。在《國之歌》的“序幕”中,聶耳眺望著遠處的日本戰艦,他聽到的“從朝搬到夜,從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頭架子都要散了”的哀鳴;同時,漂泊在外灘碼頭的歌女又在唱著:“為了饑寒交迫,我們到處哀歌,嘗盡了人生的滋味。”這是對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最為真實的描繪,它不僅在聶耳的心中徘徊,也在觀眾的心中蕩漾。二者的結合則為聶耳在心中升騰起“一輩子就這樣下去嗎”的質疑。
至此,《義勇軍進行曲》的情感主旨樹立起來,它不僅成為推動整部歌劇不斷前進的動力,也在更為寬泛、更為深遠的層面激蕩著觀眾的心靈世界。因此可見,《國之歌》的藝術內涵不單純局限于情感抒發與演唱技法的配合之中,還在于舞臺藝術空間與情感共鳴營造的適度組合之中。這不僅是《國之歌》創作中積累的經驗,也是指導我國原創歌劇創作的重要原則之一,值得廣大歌劇工作者認真學習。
三、家國情懷的藝術再現
《國之歌》的審美內涵中,家國情懷是整部作品的靈魂所在。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一,家國情懷主要建立在個體對國家共同體的一種精神認同基礎上。它促使人的思想或理念不斷得到升華的同時,也在社會活動中對生命個體的價值選擇提供參考。就中國而言,家國情懷建立在小農經濟和大一統的傳統文化基礎上,并以修齊治平的人生理念得到落實。在本部作品中來說,它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得到呈現。其一,從喚醒民眾到志同道合;其二,從志同道合到踏上革命征途。前者是基礎,也是讓觀眾真正走進人民音樂家、人民藝術家的背景介紹;后者是發展,也是個人情感升華至家國情懷的濃縮。
(一)喚醒民眾與志同道合
《國之歌》以聶耳、田漢及其周邊的革命工作者為中心展開,重點突出了他們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過程。一方面,《義勇軍進行曲》發出了“起來,不愿作奴隸的人們”的吶喊,是要喚醒東方睡獅。另一方面,《國之歌》以“救亡抗爭”“入黨盟誓”“囚牢言志”“攜手譜曲”“號角長鳴”五個樂章為線索,真實而全面地再現了他們試圖以藝術創作為媒介喚醒民眾的艱辛努力。
盡管聶耳、田漢等人的內心沉浸著無盡的愛國熱情,但他們早期的發展中,還只是停留于仁人志士大聲呼喊的層面。真正要讓廣大人民覺醒,就需要借助志同道合者共同的努力。于是,我們在《國之歌》中看到了安娥等人的身影。這是覺醒的先行者在找到了喚醒民眾的共產主義道路之后,進一步發揚革命精神的寫照。本劇賦予聶耳特殊的人格魅力,為現代年輕人理解愛國主義提供了更為全面、立體的精神標桿。聶耳短暫的一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一筆,在民族危亡的時候喚醒大眾起來抗爭!為大眾而謳歌是本劇主人公所具備的獨特藝術氣質,這充分說明聶耳具有其他藝術家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正如《義勇軍進行曲》在短短的104個音符中卻奏響了中華民族危難時刻的最強音。
(二)志同道合與革命征途
作為奠定整部歌劇情感發展主線索,田漢與聶耳之間的革命友誼是推動劇情發展的主要動力。為了更好地呈現二人之間的情感聯系,主創團隊巧妙地涉及了聶耳、田漢二人的對唱:
田漢問:耳朵,你在讀《風云兒女》嗎?
聶耳答:我在讀。
二人的對唱中穿插著抗日的硝煙和烽火,更將風云變幻的時代作為審美要素融入其中。這就為二人的精神交流發展之民族共同心聲的《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創造了藝術誕生的氛圍。隨著劇情的發展,《國之歌》進一步描繪了聶耳、田漢等人在安娥的引導下從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走上革命征途的發展。在歌劇的第一場中,主創團隊采用背景烘托的手法,將田漢和安娥共同看望聶耳,并向對方正式宣布:“你的入黨申請已被批準”。至此,聶耳的愛國之情從個體層面升華至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新高度。
歌劇作為一種西方文化孕育的藝術門類,在傳入我國之后,經過我國歌劇工作者的努力,最終實現了歌劇的中國化。這次公開演出的《國之歌》充分利用了歌劇藝術的表現手法,塑造了聶耳、田漢等革命先行者的光輝形象。就其藝術內涵而言,應從上文所討論的三個方面來界定。首先,本真情感的抒發與歌唱抒情表達的結合是技術基礎,它直接決定了整部歌劇作品必須牢固建立在歌劇的藝術規律之上。其次,假定舞臺空間與情感共鳴的營造,在為技術手段與情感表達之間的融合創造了條件。進一步來說,家國情懷的藝術再現則是整部作品走向成熟的關鍵。《義勇軍進行曲》是聶耳、田漢合作的扛鼎之作,不僅因為人們在歌聲中感受到了二人的革命友誼,更反映了時代的心聲。導演為了更好地營造藝術效果,還創造性地利用了電影拍攝手法。將歷史的既往和革命者的當下相互穿插,從而營造出時而“融入”、時而“融出”的效果。就故事劇情的發展來說,這一手法的價值更在于聶耳、田漢個人的“過去”被融入到中華民族的“過去”中。從喚醒民眾到締結志同道合的友誼、再到共同踏上革命征途,《國之歌》始終圍繞著聶耳、田漢等人以家國情懷投入救亡圖存的斗爭中,是有效踐行家國情懷的真實寫照。與此同時,歌劇《國之歌》的創作也同樣是中國人家國情懷的真實體現,它為當今的年輕人樹立了如何將自己的專業學習與國家需要有效結合的具體方式。
總的來說,原創歌劇《國之歌》的藝術內涵開始于演唱技法與本真情感的結合,借由舞臺空間的假定和情感共鳴的營造得到了有效傳遞,是真正體現華夏兒女家國情懷的新時代文藝佳作,是落實講好中國故事的具體體現,值得廣大歌劇工作者認真學習并加以借鑒。
注釋:
1駱蔓.音樂的價值——評原創歌劇<國之歌>的審美意蘊[J].中國戲劇,2020(6).
2童慶炳.文學理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楊炳編.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和美學[M].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