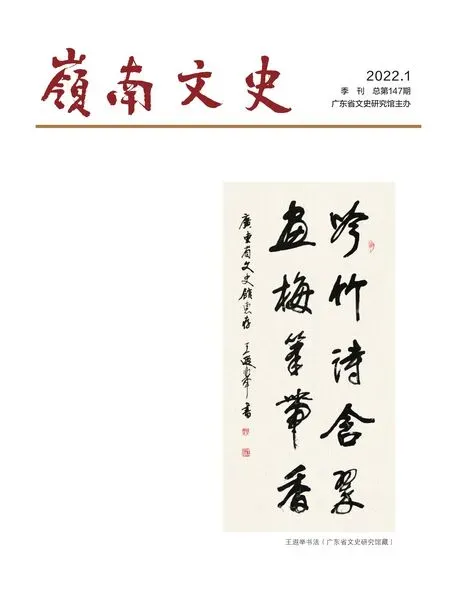香港植物園與廣東早期植物學史研究
向世怡
中國疆域遼闊,自然環境復雜多樣,有豐富的植物資源。在中國五千多年燦爛的文明中,利用植物資源有很長的歷史,這在眾多農書、草本、中藥書籍都有詳細的記載。如《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植物名實圖考》等歷史巨著。在清之后,中國逐漸開始睜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其中博物學、礦物學、動植物學這些對大自然的探索開展進入人們的視野。博物學是近代歐洲構筑帝國體系的重要工具之一,博物學的探索也隨之深入中國各港口城市和內地。
自16世紀開始,不斷有歐美人士到中國采集植物,并將標本帶回國研究,編寫出版關于中國某一區域之植物志書、名錄。如在17世紀中葉,赴華的波蘭籍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ael Boym)就利用中國的本草書籍撰寫了有關中國醫藥的著作。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西文明交匯處,同時也是遭受列強進犯侵擾,接受了現代西方植物學知識和現代植物園的研究。這些可以被視作歐洲列強,尤其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植物學帝國以及科學帝國主義的一部分。
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英國建立的殖民地植物園是延伸世界多處的“神經網絡”,為帝國收集有經濟價值的植物產品和用于欣賞的園藝產品。香港植物園連同英國在華領事機關、中國海關以及新教傳教士一同成為參與博物學研究的在華主要機構。在帝國的背景下,“博物學的活動——制圖、采集、整理、分類、命名等——不止代表探求事實的科學研究,也反映出(某種文化定義下的)認知領域的侵略性擴張。”18世紀西方殖民地對全世界植物考察、收集、鑒定、分類、研究承繼了文藝復興后期自然科學和園林藝術的崛起。
香港植物園(Botanic Garderns, Hong Kong)曾是中國最古老的植物園之一,成立于1871年,也被人稱作中國第一個現代植物園。有學者認為最早的中國植物園是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在北京、南京、江西廬山等地創辦的植物園,而香港植物園雖然是在英國殖民時期由英國人籌劃建立,但也是眾多中國植物園中的一分子。
一、在港植物學的發展與香港植物園
18世紀歐洲探險家帶來許多來自遠方的外來植物,導致植物園的急劇擴張。許多歐洲國家的人第一次看到不尋常的植物,民眾渴望了解所在帝國在海外擴張的領土。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的持續擴張導致植物園概念的延伸源于“英國海外殖民管理者的實用主義”,他們熱衷于擴大他們的商業影響范圍,盡可能利用當地植物產出更大商業利益,著眼于擴大貿易。英國在許多海外領土建立植物園,包括在墨爾本(1846)、阿德萊德(1855)、布里斯班(1855)、牙買加(1857)、新西蘭惠靈頓(1870),以及印度、緬甸、新加坡和非洲。在亞洲先后建成新加坡植物園(1822)、緬甸仰光植物園、印度新德里植物園和馬達拉斯植物園。1919年《自然》(Nature)雜志中一篇文章提到:“在過去的五十年里科學活動的顯著特征,是整個大英帝國都建立了植物園和植物站。”而建立植物園動機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是不同的。在18世紀,隨著邱園(the Royal Gardens,Kew)、西印度群島圣文森特植物園(the Botanic Garden at St.Vincent in the West Indies,1764年成立)的建立,從之前追求美學和經濟學上的新穎和價值基礎上,更加稀有的植物日漸獲得關注。邱園就像范發迪所說的一個“衛星系統”般,牽制著帝國在全球的植物園和研究站。
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被迫開放條約中規定的口岸,致使英國人占據香港,不斷欺凌中國。范發迪論述道,在這些政治劇變的促發下,英國人對中國的博物學研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有更多機會進入中國不同的地區,收集對象從園藝和裝飾植物過渡到有商業價值的植物上。
在一份芬蘭植物學家1907年的記載中,描述了他看到的香港植物園的場景:
“在一座從狹長的海岸陡峭上升的山上,維多利亞市,又稱香港就建在上面,花園則優美地坐落在山頂的斜坡上。從花園露臺上可以欣賞到海港絕美的景色,漫步其中,觀賞中國植物的有趣收藏是一種享受。許多異國的樹木和灌木也生長良好。這里最有趣的樹種之一是翠柏(Libocedrus macrolepis),它是最近從中國大陸引進的。一棵非常大的榕樹(banyan tree)引人注目。樟樹(camphor tree)在這里生長氣候適宜。花園中央矗立著香港前總督的雕像。下面的露臺上有一個噴泉被花壇環繞。一個保存完好的暖房(plant house)里是極好的蕨類植物和蘭花的集合。花園的一個部分是管理員的房子和植物標本館大樓。這些標本是最全的中國植物標本收藏。主管經常遠行到中國大陸,本地收集者也時不時帶來標本。”
同時,植物園第二任總管鄧恩(S.T.Dunn,1868-1938)也在一篇報告中寫道:“標本館、圖書館、以及香港政府的植物和林業部(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of the Hongkong government)都在植物園內的一棟大樓里,其位置可以俯瞰整個園子和海港。”香港植物園在建設之初就不僅是一個參觀游覽的地方,更是進行植物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成為帝國博物學的先驅。當時的殖民擴張和對外貿易使得許多商人、學者癡迷于培育外來植物,隨著“植物獵人”探索世界上更遠的地區,外來植物變得更容易獲得。這一概念的高潮是為渴望了解更多帝國遙遠地區的民眾建立了大型植物園。這一想法還傳播到了英國聯邦的各個地區,植物園很快在仰光、新德里、馬德拉和新加坡興起,當地人第一次能夠熟悉世界其他地區的植物。除公共利益、博物學研究以及城市美化外,植物園還服務于其他更實用的利益,因為植物園可以用來栽培有價值的經濟作物,給英國及其殖民地帶來巨大收益。

圖1:1868年的香港植物園[11]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時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譯官,1848年在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一個集會上提出興建香港植物園的想法。隨后殖民政府提出議案,希望能籌建植物園,并且能在植物學和園藝方面得到英國相關機構的支持。在經過殖民政府和甚至包括一些商業公司的多次商討后,作為一個殖民地,似乎香港也應該跟隨大英帝國其他地區的風尚。1848年時任港督戴維斯(Sir John F.Davis, 1795-1890)有意修建植物園,但因為財政問題一直擱置。1854—1859年的港督寶寧(Sir John Bowring, 1792-1872)對文化事業非常感興趣,還成為在香港的皇家亞洲研究會分會(the local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領頭者之一。他同時也對設立植物園有很高的熱情,并且在皇家亞洲學會上宣傳植物園對傳播中國植物知識的益處。港督夏喬士·羅便臣(Hercules George R.Robinson, 1824-1897)在1861年批準相關議案來成立一個公共花園(public garden),考慮到這樣的花園對于一個快速擴張的城市有極大的吸引力,并且可以花掉稅務的盈余。香港殖民者為改善氣候“決定種植大量綠蔭樹來綠化全島”,同時還想建造一個主要供英國居民休閑的公共花園。1864年,植物園第一期工程竣工并開放給公眾參觀。
1871年,英國植物學家約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 1817-1911)在對他主管下的英國邱園的匯報中,表明未來香港植物園潛在的經濟價值:“(植物園)可以引進大量有價值的但在歐洲完全未知的蔬菜作物。”以香港植物園為代表的一系列19世紀植物園,有了比之前世界各地植物園更多公眾娛樂和教育方面的意義,承載著服務大眾的使命,香港植物園的幾任總管也意識到了植物園在科學教育和作為公共花園的內涵。
在英國本土邱園園長約瑟夫·胡克的認同下,查爾斯·福特(Charles Ford, 1844-1927)于1871年到達香港,成為植物園第一任主管,在他長達三十年的管理下,植物園初見規模。1903年,來自邱園的鄧恩(S.T.Dunn)繼任。1912年,香港植物園出版了《廣東香港植物志》(Flora of Kwangtong and Hongkong)。這是由第二任植物園總管鄧恩和他的助手德邱(W.T.Tutcher)在進行大量研究后而共同完成的。這本書在當時的世界華南植物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1916年植物學家李開定和吳續祖寄了一些廣東植物標本送到日本植物學家Sadahisa Matsuda(1857-1921)處,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方面也依據此書進行研究。
在鄧恩對建立香港植物園標本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來自殖民主義的傲慢:“中國人很適合做這項工作,因為他們喜歡這項任務,通過訓練很快便能上手。目前利用中國人進行工作的困難在于他們不懂得分類學,又不認識植物的拉丁語名字。對于他們來說,外國文字的書寫也難以辨認。”此時的香港植物園與其附屬研究機構具有濃厚的英國對東方殖民統治的現實需要。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植物園受到很大摧殘,許多樹木被毀,進而被日軍占領。抗戰勝利后,在1946年香港殖民政府將之前的植物和林業部改為單獨的林業部和植物館部,植物館部實行對植物園的重建和復蘇計劃。當時標本館的收藏在日占之前于1940年被送到現馬來西亞檳城(Penang),之后又被送到保存尚算完好的新加坡植物園,1948年這批4萬件標本才回到香港。1975年,植物園被重新命名為動植物園(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標本收藏也增加了珍稀動物和鳥類。在20世紀80年代,香港動植物園坐落于城市的黃金位置,是一個受歡迎的戶外活動場所和教育中心。
二、廣州近現代植物學研究及與香港的交流
在中國境內,除香港植物園及其標本室外,美國設立的教會大學,如嶺南大學、金陵大學、福州大學等也都設立了標本室。中山大學的動植物研究也頗有成就。“該校設農科研究所,下分農林植物與土壤二部,同時還擁有國內各大學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園,研究條件較好。”農科所采集大量廣東(包括海南島)地區植物標本,所長陳煥鏞著有《中國經濟樹木學》及《中國植物圖譜》(與胡先骕合著)等,并“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設置的五個科學研究教授席中大學的唯一一席。”
20世紀20年代末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幾年,是中國生物學發展的興旺時期。胡先骕在《中國植物學雜志》發刊辭上有一段精辟的話足以證明:“專研植物分類學之研究所有四,此外尚有各大學之研究標本室,遂使斯學之進步,有一日千里之勢,分類學專家已有多人,皆能獨立研究,不徒賴國外專家之臂助。關于中國蕨類植物之研究,且駕多數歐美學者而上之。在具普遍性之形態學、生理學、細胞學諸學科,亦有卓越之貢獻。此種長足之進步,殆非20年前所能夢見者也。”南京當時是中國植物學發祥地,中國科學社于1922年在南京成立。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32年第一次十年報告中提到:“而胡步曾博士又嘗遣人遠旅青藏,以搜求奇花異卉。所獲動植物標本,蓋已蔚然爛然矣。乃謀于科學社曰:海通以還,外人竟派遣遠征隊深入國土,以采集生物,雖曰致志于學術,而借以探察形勢,圖有不利于我國者,亦頗有其人。……則生物學之研究,不容或緩焉。”科學文明的進步日漸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構成部分,為了搶先做出研究,不給外國侵略分子可乘之機,中國科學家付出了艱辛努力。
1928年中山大學興建農林植物研究所,在1954年歸中國科學院管理之前,這里是華南植物學研究重地,長期致力于廣東、廣西、海南等地植物考察和標本收集。陳煥鏞(1890-1971)作為中國植物學發軔時期主要專家之一,一開始也集聚在南京,后來成為華南地區植物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中國著名植物分類學家,曾前往美國留學,1919年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獲科學碩士學位,1920年回國后曾在金陵大學、東南大學、中山大學等校任教。
1927年他擔任中山大學理學院教授兼植物系主任,“多次到香港、廣州、北江、鼎湖山等地采集植物標本,在短短一年內采集了標本二千余號。”1928年,中山大學農學院接受陳煥鏞設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議。1930年,該所從事廣東植物分布狀況調查以及“擔負起促進廣東農林經濟事業發展的使命”。該所為發展中國植物分類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之后以該所為基礎擴建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陳煥鏞為第一任所長。
胡先骕(1894-1968)與陳煥鏞有密切的工作關系,也為華南植物學和中國科學教育作出重大貢獻。胡先骕1914年先赴美留學,學習森林植物學;1923年再次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博士。1929-1933與陳煥鏞編纂并出版《中國植物圖譜》第二、第三卷。后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主持云南農林植物所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33年,在胡先骕倡導下,原有的北京靜生生物調查所與江西農業院合作創辦廬山森林植物園,由中國蕨類植物學奠基人秦仁昌(1898-1986)承擔建園工作。
在民國時期(包括抗日戰爭時期),廣州和香港就植物知識和研究有密切交流。1926年陳煥鏞曾前往香港植物園標本室工作,還親自帶領秦仁昌到香港植物園標本室查閱有關標本和搜集材料。1929年,胡先骕也曾偕馮澄如前往香港研究,尤其是前往香港植物園訪問研究。馮澄如作為靜生所繪圖員,前往香港植物園繪制所藏植物標本之圖,作刊印《中國植物圖譜》第三、第四冊之用。當年還隨即從香港赴爪哇參加太平洋科學會議,匯集眾多中國所派科學家代表,足見當時中國科學家積極參與世界科學界的各項活動。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1938年日軍南進并轟炸廣州。為保存文化教育事業,若干大中小學走上搬遷的道路。廣州由于臨近香港,所以,香港成為遷移學校的首選地,先后有嶺南大學、南華大學、廣東國民大學和廣州大學遷往香港復課。國立中山大學遷往廣東羅定,而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往香港。該所擁有“當時國內最齊全的設備儀器”,研究專刊——英文《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專刊》(Sunyatsenia)科研水平得到國際公認,這也是中國首次發行的英文版植物學學報。
國內的植物研究中心轉移到香港。“該所幸先機搬走,材料設備,均獲保存,研究工作,遂得繼續,因此內遷之各研究機關均與該所聯絡,遂造成該所為現今植物研究機關之中心地位,且有欲派遣人員來該所借助材料圖書,以供研究者。”陳煥鏞作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所長,1938年春自行將標本、圖書、儀器等遷移到香港九龍,本人也不得不放棄精心耕作的石牌植物標本園,而前往香港繼續主持植物所研究工作,在香港與日軍周旋。1942年香港淪陷后,植物所克服困難,幾經波折,將標本、圖書運回廣州。在這些標本中,尤以海南島地區的為珍貴。
《陳煥鏞紀念文集》也記錄了1945年農學院院長鄧植儀給中大校長王星拱的報告:“該員(指陳煥鏞)忍辱負重,歷盡艱危,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保存該所全部文物,使我國之植物學研究得以不墜,且成為我國植物研究機關唯一復興基礎,厥功甚偉。其心良苦。其志堪嘉。”在這段融合廣州與香港兩地辛勞、奔波的為保全中國植物學發展火種的歷史中,陳煥鏞立下了汗馬功勞,為中國植物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6年中山大學植物所改隸中國科學院后,改名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當年另選北郊龍眼洞開辟植物園和設立鼎湖山樹木園。華南植物所遷到此處,現名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它是“開發華南熱帶、亞熱帶植物資源,研究植物的引種馴化和普及植物學知識”的寶貴園地。迄今,中國植物園總數達 162 家,已步入快速建設和穩步發展階段,為“中國植物科學研究、資源利用、多樣性保護及環境教育作出了重要貢獻,已發展成為國際植物園體系的中堅力量和發展主流。”
三、今日粵港植物園發展與生態文明
香港植物園在1975年更名為香港動植物公園(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在香港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并回歸祖國之后,是著名旅游景點之一。在廣東省,1956年建立了鼎湖山樹木園,1983年建立了深圳市仙湖植物園。從民國時期,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學包括植物學得以建立,到如今21世紀中國科學文化的全面高水平、高速度發展,這期間植物園成為中國現代科學文化的一個縮影,也體現了粵港跨區交流與中西文化交流的豐富歷史。
植物園與當今生態文明的發展息息相關。至21世紀,植物園不再是博物學時代的帝國科學主義下的產品,而是一個涉及多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體。它兼有“物種保護、科研、科普、旅游的內容,又涉及資源開發和商品化”,其核心和靈魂是生物多樣性。在建設粵港澳人文灣區的大背景下,植物園可以稱為大灣區生態文明的一張名片,成為市民科普教育的一個重要基地。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把生態文明建設置于突出位置、納入總體布局,正是順應了人民的新期待,也是深入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題中之義。”
植物園作為城市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民眾提高科學素養的重要場所。植物園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力軍”,是野生戰略性植物資源保護的主體。粵港澳大灣區中植物園也是科學文化、生態文明的代表性場所,對推動植物學新思想新方法、基礎和應用研究依然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將助力大灣區生態文明建設與創新發展。
[1]王楠:《帝國之術與地方知識——近代博物學研究在中國》。《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第236-244頁。
[2]范發迪著,袁劍譯:《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63頁,2011。
[3]李猛:《班克斯的帝國博物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第12頁,2019。
[4]此處garden用復數表示。
[5][6][34]許霖慶:《中國第一個現代植物園——香港植物園(1871—2009)》。《中國植物園》2009年第12期。
[7]104,263–264 (1919).
[8]邱園1759年建立,1841年成為英國國家植物園,如今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和國際最著名的植物學研究機構之一。見林恩·帕克、基里·羅斯–瓊斯著,陳瑩婷譯《邱完的故事》,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9]Pehr Olsson-Seffer, “Visits to Some Botanic Gardens Abroad,” The Plant World, vol.10, no.3,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07, pp.58–62.
[10]S.T.Dunn.“The Hongkong Herbarium.”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vol.1910,no.6,[Royal Botanic Gardens,Kew,Springer],1910,pp.188–92.
[11]Griffiths,D.A.,and S.P.Lau.“ The Hong Kong Botanical Gardens, A Historical Overview.”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26,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1986,pp.56.
[12]李猛:《班克斯的帝國博物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第68頁,2019。
[13]“The Public Botanic Garden of Hong Kong.”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17,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1977,pp.234–35.
[14]Robert Peckham,“Hygienic Nature:Afforestation and the greening of colonial Hong Kong,”Modern Asian Studies 49,4 (2015) pp.1177–120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Jos.D.Hooker, “Report on the Progress and Condition of the Royal Gardens at Kew, During the Year 1871.” Report on the Progress and Condition of the Royal Gardens at Kew, 1871, pp.7.
[16]Stephen Troyte Dunn, William James Tutcher,, London:Published by Stationery Office, 1912.
[17]A List of Plants from Kwangtung,植物學雜志/30 卷 (1916) 359 號/書志,370。
[18]S.T.Dunn.“The Hongkong Herbarium.”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vol.1910,no.6,[Royal Botanic Gardens,Kew,Springer],1910,pp.188–92,https://doi.org/10.2307/4113302.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李新總主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第十一章:國民政府的教育和學術研究?第二節學術研究的奠基與發展?三高校學術研究的開展及社會各界對學術的促進。中華書局,第1版,第1頁,2011。
[20]錢迎倩等:《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 生物學》。福建教育出版社,第5-7頁,2004。
[21]胡宗剛:《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引言”,第1頁,2013。
[22]林麗成、章立言、張劍編注:《中國科學社檔案整理與研究 發展歷程史料》。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第248頁,2015。胡布曾(1893-1968),文學評論家、生物學家。
[23]見胡宗剛:《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
[24]《華南農業大學百年校慶叢書》編委會:《稻花香:華南農業大學校友業績特集》,廣東科技出版社,“中國現代植物分類學奠基人——記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陳煥鏞教授”,2009。
[25][27]胡宗剛:《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江西教育出版社,第665、141頁,2008。
[26]胡先骕、陳煥鏞編:《中國植物圖譜(第三卷)》。靜生生物調查所1933年1月出版。本卷收有植物50種,分述每種植物的外部形態特征和產地,并附有形態圖版50幅(從101圖至150圖)。
胡先骕、陳煥鏞編:《中國植物圖譜》(第四卷)。靜生生物調查所1935年3月出版。本卷收有植物圖版50幅(從第151圖至第200圖),并分述每種植物的分類特征和產地等。
胡先骕、陳煥鏞編:《中國植物圖譜》(第五卷)。靜生生物調查所1937年3月出版。本卷記述植物50種的形態、分布和生態等。附有形態特征插圖50幅。見盛廣智等主編:《中國古今工具書大辭典》,吉林人民出版社,第785頁,1990。
[28]李志軍:《抗戰初期廣東高校遷港的歷史意義》。《重慶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第798頁。
[29]葉華:《抗戰以來的中大農林植物研究所》。《教育雜志》第31卷第4號,1941年第28期。轉引自李志軍:《抗戰初期廣東高校遷港的歷史意義》。
[30]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編:《陳煥鏞紀念文集》,第308頁,1990。
[31]胡宗剛:《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第191頁。
[32]黎盛臣主編,中國植物學會植物園協會編:《中國植物園參觀指南》。金盾出版社,第183頁,1991。
[33]焦陽、邵云云、廖景平、黃宏文、胡華斌、張全發、任海、陳進:《中國植物園現狀及未來發展策略》。《中國科學院院刊》,2019年34(12):第1351-1358頁。
[35]賀善安、顧姻、褚瑞芝等:《植物園與植物園學》。《植物資源與環境學報》,2001年10(4):第48-51頁。
[36]黃勤:《生態文明建設在“五位一體”中的特殊功能》。《光明日報》2014年2月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01/c40531-24272856.html。
[37]周薇:《為什么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布局?》。《南方日報》,2013年1月18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118/c159301-20244128.html。
[38]焦陽、邵云云、廖景平、黃宏文、胡華斌、張全發、任海、陳進:《中國植物園現狀及未來發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