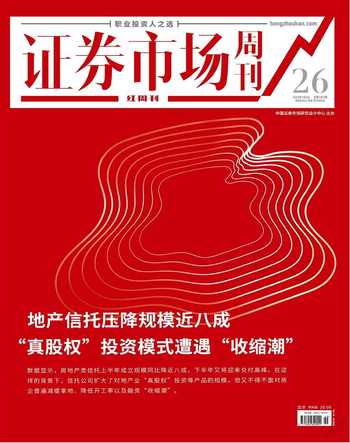信托公司的地產業務收入貢獻預計將打7 折“脫鉤說”浮出水面
熊穎 惠凱
伴隨房企的頻繁爆雷,地產和信托之間的長期穩固關系遭遇挑戰,用業內人士的話來形容,信托和地產正在脫鉤。
“地產信托為主的融資時代可以說基本結束了。”華南某信托公司資深員工感慨說。
《紅周刊》就此詢問了多位信托地產業務一線人員和房地產業內人士,發現信托、地產兩大行業都在各自的焦慮中掙扎。
自2021年以來,房地產企業爆雷不斷,而且“多米諾骨牌”效應正在倒向信托。今年以來,地產信托產品爆雷同樣接二連三,而近期這一趨勢愈發明顯,其中,中信信托、五礦信托、民生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踩雷”。
不過,從事地產信托業務多年的張理(化名)向《紅周刊》表示,雖然地產爆雷所波及的信托公司較多,但由于公司屬性不同,他們受影響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其中,民營背景的信托公司受影響更嚴重,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們本身在做項目時就不太規范,募集給房企的資金幾經周轉,難以找到去向;另一方面,受地產信托產品爆雷影響,投資者信心不足,其他產品的銷售也會受到影響。而一旦一個信托公司募資能力大打折扣,它的業務基本上也會受到很大影響。
張理認為,出于維護自身的融資能力等方面考量,信托公司的剛兌意愿還是比較強的。他以某民營背景信托公司舉例,為了剛兌產品,這家公司將自己往年積累的利潤以及股東的部分利潤都拿出來用于到期產品兌付。
不過,張理同時提醒,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信托公司剛兌太多,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公司利潤,帶來經營不善的風險,后續若旗下地產產品持續爆雷且數量較大,還有可能影響募資能力以致整體業務停滯。
張理表示,過去的很多地產業務現在都做不了了,而這也會直接體現在信托公司今年的業績表現上。他估算,今年信托公司的地產業務收入貢獻預計將打7折。
華南某信托公司資深員工也表示,“地產信托為主的融資時代可以說基本結束了。”據其介紹,“以往主流的地產信托業務無論產品結構、形式如何,都是‘影子銀行’時代的孑遺。”他解釋說,這種模式的核心邏輯就是為了滿足地產商的短期融資需求,盡管投資人能獲得較高收益、但處于業務鏈條中的次要地位,期間信托公司的跨業經營特色也得到了充分發揮,一定程度上避開了監管。“這就是典型的‘影子銀行’,違背了后資管新規時代標準化、凈值化的轉型大方向。”
據上述人員介紹,過去兩年間不少風險抵御能力較弱的信托公司已爆雷或發行能力接近冰凍,增量業務的主力是央企系信托或江浙滬等地的中小型特色信托公司。因為今年是資管新規實施年,退出壓力較大,在2020~2021年上半年發行了大量地產信托產品的信托公司遭遇較大壓力。
張理告訴《紅周刊》,在整個房地產融資領域,幾乎很少有融資渠道可以和信托競爭,因為過去信托主要干的非標融資,和銀行貸款差不多,但銀行對房企的融資主要針對房企拿地之后的開發貸。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操作中,房企通常會先辦理前融,等到銀行開發貸獲批,再進行置換。不難看出,前融資金對房地產開發的重要程度。
張理表示,開發商拿地之前的土地配資,資金來源往往來自信托機構、資管和私募基金等渠道,但隨著配資計劃被叫停、私募基金受P2P爆雷影響很難募資,信托渠道的優勢地位得以顯現。
而得益于信托對房地產的大規模融資,對大部分信托公司來說,房地產業務都是他們過去收入占比較高的一個行業。以地產業務較為出名的五礦信托為例,據其年報,2020年,公司投向房地產的信托資金1054.99 億元,占總信托資金的15.01%;2021 年,公司投向房地產的信托資金也有759.04 億元,占比9.29%。
不過,出于規避風險等因素考量,信托公司內部也在調整他們對房地產資產的篩選標準。張理向《紅周刊》表示,以前的篩選邏輯就是看是否屬于百強房企;而現在更傾向于做一些央企的地產業務,比如保利發展、中國海外發展等;或者一些地方國企,比如說某省、市AAA級平臺、AA+平臺的下屬地產公司。
“但這種業務,現在也沒有什么流量,所以信托公司也在尋求轉型。”張理進一步解釋,之所以說沒什么流量是因為符合要求的企業畢竟是少數,舉例來說,像地方國企的下屬地產公司,一年的銷售額可能就幾十億的規模,再加上它平臺本身的融資能力就很強,能夠通過其他板塊把資金拆借過來,不太迫切需要信托公司去做介入,所以它的融資資金量較小,不能和過去信托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相匹配。
不少業內人士對信托公司的地產業務持悲觀態度。張理告訴《紅周刊》,我們有一部分業內人員覺得,信托給房企做土地款配資的業務以后很有可能就沒了。而這一業務,恰恰是以往信托公司向房企發放融資款的主力業務。“過去信托、地產兩個行業捆綁較深,但現在來看,兩行業正在脫鉤。”
尋求轉型已經成為當下信托公司的必經之路。比如,五礦信托就表示,公司將堅定推進“二次轉型”,將地產、政信、基建、消金和固有等業務作為成熟型業務,按照“順應監管導向、持續改進完善、穩定收入貢獻”的思路優化開展。
張理告訴《紅周刊》,實際上,不少信托轉型還是做的配資業務,以賺息差價為盈利模式,只不過是換了一個行業而已,其中,做的比較多的業務有,基金的基金FOF、政府平臺業務、基建融資等。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小眾的信托轉型方向,做服務類信托、不良資產等。
而房地產信托金融行情的不樂觀也在同步影響著張理的職業選擇,自2017 年畢業后就一直從事信托地產業務的張理,在2021年下半年選擇轉投向基建項目融資。
不過,信托地產也存在“創新”空間,一是“真投資”股權模式;另一種是信托產品與地產周期匹配的“新產品”。
華南某信托公司資深員工表示,以往地產信托的存續期普遍為兩年,“這也和房企‘高周轉’的風格相契合。”站在房企的角度,拉長信托產品的存續期、一定程度上能緩解“短債長投”的壓力。因此未來不排除會出現長期限的信托產品。
《紅周刊》就是否會買長期限產品征詢了北京的資深信托產品投資人小磊,他表示,“以往可以接受兩年期、三年期的產品,但2020年后只投一年期的信托產品,而且會選擇在債券兌付高點前結束的信托產品。”在這樣的投資邏輯下,他購買的多款地產信托均無違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