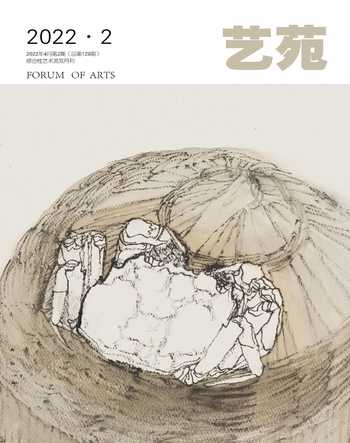“十七年”期間戰爭電影與當代戰爭電影的對比研究
曲德煊 趙文心
摘 要: “十七年”時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戰爭題材電影,體現了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充滿了濃郁的詩意。當代戰爭電影承襲了“十七年”戰爭電影的優點,并在其基礎上做出了新的突破,體現了大片化和人文化的新特點。論文對“十七年”期間戰爭電影與當代國產戰爭電影的美學特征進行了對比研究,以期發現戰爭片的發展規律。
關鍵詞:“十七年”戰爭電影;“兩結合”文藝思想;當代戰爭電影;大片化;人文化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基金項目:2017 年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中國電影中的江西蘇區影像研究”(17YS07)。
一、“十七年”時期戰爭電影
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這十七年間拍攝的電影,簡稱“十七年”電影,該時期中國電影在風格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體現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藝思想。該時期“一掃過去中國電影側重文藝片的傳統,側重細膩溫婉哀怨的美學風格,重新樹立起一種樂觀、明快、激昂,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電影形態”[1]。該時期強調政治性,尤其是反映戰爭生涯的電影。“十七年”期間的戰爭電影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形成了政治與美學的高度統一,通過影片的情節、人物和電影語言,直接抒發出創作者的革命情懷,對觀眾產生認識、教育或審美作用。該時期能創作許多優秀的戰爭電影,一方面因戰爭剛過去不久,人們還保留著對戰爭鮮活的記憶,在這時期拍出的電影格外生動、深刻、準確;另一方面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均以正義者的勝利告終,這使得國家、民族充滿十足底氣,是值得被記錄的光榮歷史;最后,建國初期的喜慶氛圍,造就了彌漫整個社會的革命浪漫主義激情,并將其投影到電影中,以寄托情感,為英雄人物和光輝勝利高唱贊歌,形成了激情四射的時代精神。
(一)革命的現實主義:對革命戰爭的真實描繪
“十七年”戰爭電影主要是以革命歷史題材和革命斗爭題材為主,該年代的電影作品就像是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我們可以了解中國的戰爭歷史,了解中國的傳奇英雄。《上甘嶺》《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董存瑞》等影片都拍攝得非常成功。在該時期的電影作品中,內容勝于形式,形象地展現了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的革命斗爭史,高度的真實感是那些花里胡哨的電影技巧所不能取代的,真實的戰斗場面,有血有肉的戰爭英雄,這樣的現實性與時代感消除了觀眾與銀幕的隔閡,感染、同化觀眾,從而達到鞏固意識形態的作用。
《南征北戰》是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的戰爭片,由成蔭、湯曉丹聯合指導,講述了解放戰爭時,在華東戰場上,人民解放軍正確運用毛澤東運動戰的戰略思想,通過解放軍的精密部署以及工農群眾的全力配合,最后切斷敵軍后路,殲滅敵人的真實戰斗歷程。該影片在1952年春天開始拍攝,為了真實再現戰斗的場景,攝制組去往青州,“幾場重要的戰斗均采用實地拍攝,如將軍廟車站爭奪戰、大沙河阻擊戰,分別是以益都火車站和彌河為拍攝點”“為配合攝制,還調動了步兵騎兵炮兵等各種軍種部隊。多位青州籍的志愿老戰士,當時剛從朝鮮戰場撤回國內,直到現在還記得參加電影拍攝的場景。”[2]無論是場景的布置還是角色的選擇,都盡可能地還原真實,將戰爭中的英雄人物的氣質、戰爭場面的宏偉氣勢、戰役規模以及戰略部署等都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上甘嶺》《地道戰》《中華兒女》等“十七年”優秀戰爭電影的創作中,導演們幾乎都是盡可能地還原戰爭場面,真實歌頌時代精神,體現出革命現實主義。
(二)革命的浪漫主義:大無畏的革命情懷與革命理想
“兩結合思想”正式的提出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倡導“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創作理念。其實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提起過革命的浪漫主義思想,將“革命浪漫主義的文藝觀與政治上的共產主義理想緊密聯系在一起,把文學的浪漫主義與當時的抗日斗爭的革命形式結合在一起,不得不說,革命浪漫主義為現實主義接受是當時的歷史條件對文學發展的一個必然要求也是當時的現實主義必然要走的一條文學道路”[3]。這是最早提出革命浪漫主義,同時也是當時藝術作品創作的要求。到了“十七年”期間,革命的浪漫主義在當時拍攝的戰爭電影中得到了發展,創作者們總結了早期的革命浪漫主義思想,同時也為結合當時毛澤東明確提出的“兩結合”理念,將革命浪漫主義滲入到影片當中。
從美學特征上來看,戰爭電影中革命的浪漫主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十七年”戰爭電影像是一幅記載英雄的畫卷,許許多多的英雄形象呈現在觀眾面前。他們視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具有為了革命的勝利英勇斗爭、不怕困難、勇于犧牲自我的英雄主義精神。趙一曼因傷被俘,面對敵人的嚴刑逼供,她沒有透露半個字,在臨刑前還不忘跟小韓說:“明天是七一,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日子,出去后,千萬不要忘了革命。”她整理衣衫,昂首闊步地走向刑場,嘴里念著: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萬歲!”《趙一曼》將這位英勇無畏的女共產黨員體現得淋漓盡致,激起觀眾們的革命情懷。《董存瑞》講述了董存瑞從一名見習小八路軍開始,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槍火的洗禮,逐漸蛻變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的故事。在1948年的隆化戰斗中,身為突擊爆破隊長的董存瑞為了拖延時間,減少戰友的傷亡,用手托起炸藥包,高喊著:“為了新中國,前進!”他毅然拉開導火線,舍身炸掉了碉堡。
第二,理想主義化的革命敘事。在戰場上面對敵人,不光要憑借堅強的意志,同時還需要革命理想,這是一種精神的寄托。在“十七年”期間的戰爭電影中,表現出很多理想化的情節:《平原游擊隊》中的雙槍李向陽威震敵膽、《鐵道游擊隊》中的游擊隊員們神出鬼沒、《金玉姬》電影中金玉姬忍著病痛依然繼續工作等。電影中將英雄們理想化的設定,激起觀眾內心無限的敬仰與贊頌,雖說真實的戰爭生活有著揮之不去的悲劇色彩,但革命的浪漫主義卻成為一代人的精神寄托。
第三,浪漫大氣的詩意情懷。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場推翻舊社會、改天換日、煥然一新的艱難運動,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遭受很多的苦難,因此困厄中的人往往需要一點詩意,要從精神上先戰勝反動派,這樣才能迎來光明。就像有革命者所認為的:面對敵人的飛機大炮,我們需要浪漫一點。戰爭的勝利需要浪漫的鼓舞,在電影中,導演塑造了許多身處困境但意志力依然頑強的英雄形象,人物身上的信念、毅力是觀眾能感受到的力量。“這種力量的傳達是與一定電影手法聯系在一起的,它不是表現為一種抽象的理念說教,或是一般化的場景呈現,而是被具體化為一種充滿激情和詩意的生動可感的聲畫形象。”[4]《英雄兒女》中王成獨守四號陣地,被敵軍包圍后喊道:“為了勝利,向我開炮!”說完,他手持最后一根爆破筒,眼神堅定,沖向敵人;《平原游擊隊》中李向陽擊敗敵人后說:“中國的土地豈能讓你們橫行霸道!”還有《黨的女兒》《鋼鐵戰士》等影片中都滲透著濃濃的詩意,譜寫了一首首革命的史詩。
(三)“兩結合”思想下傳奇英雄的群像塑造
“十七年”戰爭電影是一個譜寫“神話”的時代,縱觀這一時期的優秀電影作品就可以發現,里面的英雄人物單純、勇敢且極具傳奇色彩。該時期的戰爭片繼承了中國電影的“影戲”敘事方法,線索明晰,干凈明快,利于大眾的觀賞和吸收。“十七年”期間拍攝的戰爭電影,每部影片中塑造的人物都較多,同時在性格上也趨于相似,都有著偉大的革命斗爭精神。而一些電影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導演們往往還會賦予他們傳奇色彩,《平原游擊隊》中李向陽隊長,在接到牽制日軍駐守某縣城的松井部隊的任務后,機智地與敵人周旋,最終克敵制勝。《上甘嶺》中八連連長張忠發,率領軍隊堅守陣地,與敵人浴血奮戰,最終取得勝利。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更加突出地展現了以集體主義為核心、英勇無畏、奮不顧身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英雄的本質就是人類面對死亡、自然、面對社會的各種異己之力的侵害、壓迫、扭曲時所產生的一種積極抗爭、勇于突破而永不退縮、決不屈服的強力生命意志。”[5]“十七年”戰爭電影對英雄人物的傳奇塑造,深深地植入每一位觀影者的心中,激發出他們的崇拜與敬仰之情。
二、當代戰爭電影:大片化和人文化
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漸完善,及在國內外市場資本的推動下,中國電影市場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當代戰爭電影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方面,帶有一定的反思精神,從重視戰爭本身轉而重視戰爭中的人性;另一方面,戰爭電影是國家的政治需求,是紅色文化傳播的需要;三方面,因時代的變化,人們對以往的戰爭有了新的看法,能冷靜地分析戰爭片背后所要表達的真正含義。當代戰爭電影既要滿足國家的政治需要,同時也要增加電影的觀賞性,滿足觀眾的視覺需求,運用精良的電影制作技術,實現藝術和商業雙贏。《集結號》《南京!南京!》《血戰湘江》以及近年來創作的《八佰》《金剛川》《長津湖》《狙擊手》等優秀影片,導演通過對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重要戰役的描寫,用影像的方式回憶歷史,講述戰場的殘酷,讓后代銘記歷史、反思戰爭、致敬先烈。
(一)大片化
2002年,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問世,標志著中國電影進入“大片時代”。國產電影走向“大片化”,一方面,在經濟的推動下,中國電影有機會學習到好萊塢大片的技術經驗和商業美學原則,使中國電影在技術上作出了較大的突破,實現了電影藝術與技術的兩結合;另一方面,“大片”始終離不開“大”這個字,大導演、大明星、大制作、大場面等。國產大片遵循“大”的原則,電影的制作和宣傳方面做到了高額的投入,豪華的明星陣容為電影帶來了輿論熱潮,使電影更具影響力。三方面,國產大片要在學習好萊塢大片模式的基礎上,了解中國的本土文化、本土價值以及本土觀眾的心理結構,創作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大片”,如古裝武俠動作大片、主流大片以及國產魔幻大片等。這些本土化的電影敘事風格使國產大片取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重肯定。
當代戰爭電影在“大片化”的推動下,也創作了許多的“戰爭大片”。“2007年《集結號》的上映,成為了戰爭電影真正在市場票房意義上的破冰之作” [6]《集結號》累計票房高達2.10億,在同年僅次于《變形金剛1》的票房。該電影獲得的成功離不開獨特的敘事視角與藝術風格,也離不開后期得力的商業宣傳。馮小剛導演在拍攝方面有較高的要求,電影中場景的布置、煙火、道具等都聘請了國外較為成熟的制作團隊,真實地還原戰爭場面,包括演員的面部妝容,以及受傷的特效妝都繪制得惟妙惟肖,表現出戰爭的殘酷,讓觀眾身臨其境并進行反思。當代戰爭題材的電影大部分是對歷史真實事件進行改編,這樣的主流無疑是觀眾喜歡的,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國產大片“不能完全照搬好萊塢的模式,而應該要大力發展主流大片,以適應中國特色電影的產業道路,并實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崇高目標”[7]。“戰爭大片”是對歷史戰爭敘述的基礎上,利用先進的制片技術,輔助影片敘事,實現藝術與商業之間互利共贏。戰爭電影“大片化”的轉變是一個良性的循環,依靠“大導演+大投資”的保障,才能制作出場面宏偉、視覺刺激的“大片”,達到完美的藝術表現效果。如《八佰》由管虎導演,黃志忠、姜武、張譯主演,票房累計31.11億;《金剛川》由管虎、郭帆導演,張譯、吳京、魏晨主演,票房累計11.27億;《長津湖》由陳凱歌、徐克導演,吳京、易烊千璽主演,票房累計57.75億等。
(二)風格多元化
當代戰爭電影在以戰爭為主的敘事中,加入了愛情、喜劇、荒誕等元素,使戰爭電影在風格上達到多元化的效果,拓展了戰爭電影想要表達的真實含義,使觀眾更好地從電影的故事中進行反思。管虎拍攝的《斗牛》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風格的戰爭電影,講述了抗戰時期,一頭共產黨留下的奶牛與一名照看奶牛的農民牛二共生死的故事。牛二在亂世中拼死保護奶牛,可到了最后奶牛并沒有還回去,一人一牛又重新回到了后山“相依為命”。這樣的結局,展現荒誕性的同時也從側面烘托了戰爭的殘酷。張藝謀導演的《狙擊手》是一部有著文藝片風格的戰爭電影。影片以人為本,講述了中國志愿軍在敵我軍備力量懸殊的境地下,與美軍狙擊小隊展開殊死較量的故事。電影通過對五班狙擊小隊人物之間敘事的描繪,展現了戰友之間的默契與情意,凸顯了中國軍人的智慧和勇氣。從當代多部戰爭電影中可以看到,多元化的類型設置,使戰爭電影在情節的設置上變得更加豐滿,在更受觀眾喜愛的同時,將觀眾帶入歷史的長河中,感受一場真實且極具教化意義的“戰爭之旅”。
(三)人文主義情懷
新世紀戰爭電影中,將英雄人物設置為普通戰士的形象,突出其平民化。他們是獨立的個體,都有作為“人”的屬性,既要積極戰斗也要珍惜生命。與早期戰爭電影中的人物刻畫不同,當代戰爭電影會為電影中無畏死去的生命惋惜,展現出濃厚的人文主義情懷。如在 《八佰》中,戰士們拿著炸藥包往下跳與敵人同歸于盡,犧牲前,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報出自己的姓名、親人的名字和出生的家鄉,然后縱身躍下。筆者相信,看過《八佰》的觀眾一定會被這段情節所感動。在敵人面前,他們是英勇的戰士,而在家人面前他們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狙擊手》中的大永,面對擁有先進武器的美國狙擊手們,他會緊張,也會害怕;在看到隊友一個個犧牲時,會很悲傷地為他們流淚,突出他感性的性格;同時他又擦干眼淚與敵人奮戰到底,最后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打敗了敵方的狙擊手,拿到情報。當代戰爭電影將人物圓形化,將人物身處戰場上內心的變化體現得淋漓盡致,表現了深刻的人文情懷,更好地展現了戰爭片的藝術張力。
(四)戰爭背后的政治意義
我們說一部電影最難得的是理解其背后真實的含義,戰爭電影也不例外,除了電影語言給觀眾帶來的戰場上壯烈壯美的視覺沖擊外,戰爭背后的政治意義是最重要的。在2013年8月19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當代戰爭電影的拍攝上映是響應國家政策,傳播正能量,呼吁大眾樹立正確的戰爭觀,同時也具備很高的票房價值。
2021年9月30日《長津湖》上映,累計票房57.75億,思想教育功能和市場價值得到了完美的統一。所有觀眾都被電影里志愿軍們鋼鐵般的意志打動。該片以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講述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抗美援朝戰爭是立國之戰,它的勝利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這才是《長津湖》槍林彈雨的背后想要向觀眾傳達的政治意義。
三、當代戰爭電影對“十七年”戰爭電影的發展進化
通過對“十七年”戰爭電影與當代戰爭電影美學特征的分析和梳理可以發現,當代戰爭電影是在承襲“十七年”期間優秀戰爭電影特征的基礎上,運用新的電影制作技術以及新的美學思想,對“十七年”戰爭電影的發展進化。
(一)技術上的革新
當代戰爭電影在畫面的特技制作上相較于“十七年”期間的戰爭電影更為先進。受到國外電影特效技術的影響,中國在新世紀后也對電影后期技術進行了學習與研究。“實地取景+后期特效”能更真實地還原歷史戰爭場面,滿足大眾的感官性和直觀性需求,提升電影的真實感。電影《金剛川》里面的美國飛機,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劇組先在棚內用模型拍攝,再用CG技術進行優化,這才做出了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F4U型號飛機。而“十七年”期間的戰爭電影受限于資金和技術,“再現戰爭場面的煙火特技鏡頭不能滿足大銀幕再現戰爭的需要”[8]。影片里大規模戰爭場面難以進行影像化表達,降低了戰爭片的影像魅力。
“十七年”戰爭電影不能真實地展現戰爭的殘酷,一方面因為技術水平落后,不能通過特效還原戰場;另一方面是為了迎合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影片要努力地避免拍攝中國軍人受傷的場景,必須保持革命的樂觀精神,為觀眾呈現出戰無不勝的軍隊形象,展現勝利的一面比展現失敗多。而當代戰爭電影因觀眾欣賞水平的變化,對大場面的需求,促使戰爭電影在制作上越來越精良,達到技術與藝術的高度融合。
(二)電影美學與思想上的多元化
“十七年”期間的戰爭電影在表現形式和美學特征上與當代戰爭電影相比較為固化。“‘十七年’電影和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在政治和藝術的夾縫中生存,導致電影未能擺脫歷史局限”[9],使該時期電影形成了敵遠我近、敵暗我明、敵俯我仰、敵小我大的美學風格。沒有正視歷史,反而將戰爭浪漫化,稀釋了戰場的殘酷、人性的復雜以及戰爭對人民帶來的痛苦,過于理想化。
當代戰爭電影創作者能正視歷史,表現出一定的反思精神。“優秀的戰爭電影應該具有一種直面戰爭創傷的勇氣和一種真正能講述和再現戰爭歷史的勇氣。”[8]當代戰爭電影擺脫以往的政治束縛,在表現形式與美學上更加多元化。如《血戰湘江》敢于表現失敗的戰役,拓寬了戰爭電影的表現范圍,其目的是吸取經驗教訓,為觀眾樹立正確的戰爭觀,起到教育意義。該片講述的是1934年紅軍在湘江上游與國民黨軍苦戰,最終強渡湘江,在突破了國民黨第四道封鎖線的同時,中央紅軍也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影片真實地還原了歷史,血腥殘酷的戰爭場面警醒著每一位觀眾,不是每場戰爭最后的結果都是好的,只有從慘痛的教訓中不斷尋找正確的方向,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八佰》講述的是一支國民黨軍隊固守四平倉庫,在與日軍人數懸殊較大的情況下,頑強阻擊日軍數日的故事。像《八佰》這類以國民黨軍隊為正面表現對象的戰爭電影,在“十七年”期間的政治意識形態下是不可能出現的。而當代戰爭電影進行了題材突破與美學轉變,更加表現出正視歷史的勇氣和視野。
四、結語
繼承紅色文化傳統是我們思想領域舉足輕重的大事,而革命戰爭題材的影片是重要的承載者。無論是“十七年”戰爭電影還是當代戰爭電影,都展現了真實的戰爭場面,同時對英雄人物的刻畫也充滿著激情與詩意。隨著時代的進步,新世紀的人們對戰爭電影的感受不再像往常那樣“理想化”,而是有了更加真切、敏銳的思考,技術上的進步也彌補了“十七年”戰爭電影缺失的觀賞性。因此,“十七年”期間的戰爭電影與當代戰爭從整體上看,既一脈相承又各有千秋。
“十七年”戰爭電影與當代戰爭電影的主題都是為了呼吁人民群眾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惜當下,展望未來。筆者相信,在未來的電影市場的推動下,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優秀的戰爭題材電影出現在大熒幕上,呈現革命的主旋律。
參考文獻:
[1]曲德煊.“十七年”的傳記意識與傳記電影[J].當代電影,2013(10).
[2]劉珍實,張超.憶《南征北戰》在青州拍攝[J].春秋,2017(5).
[3]卜凌云.英雄時代的詩學理想——毛澤東革命浪漫主義革命觀的嬗變[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5).
[4]石川.政治·影像·詩意——1949—1966年的中國電影[D].中國藝術研究院,2002.
[5]李啟軍.英雄崇拜與電影敘事中的“英雄情結”[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3).
[6]索亞斌,姜鵬亮.沙場秋點兵——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檢視[J].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6(3).
[7]劉帆.中國式大片的發生與發展研究[D].上海大學,2014.
[8]梁桂軍.記憶碎片化及去歷史化——新世紀中國戰爭電影反思[J].當代電影,2018(4).
[9]焦素娥.神話·史詩·傳奇——新中國戰爭電影回眸和反思[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
(責任編輯:萬書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