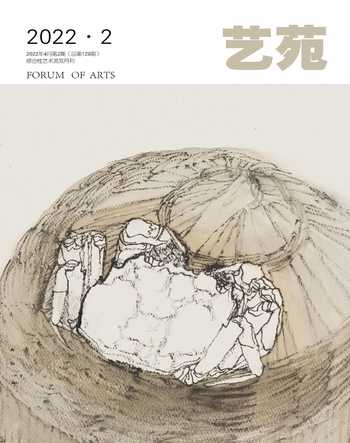中原畫風視域下河南油畫藝術中的族群意識論
閆慶來 李欣原
摘 要: 河南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受自然環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族群意識。河南美術文化以特有的地域族群意識為基礎,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原畫風。河南油畫家群體,以其敏銳的感知力和純熟的表現技巧,通過生命意識、厚土意識、家國意識的不同視角構建出河南油畫藝術中特有的中原畫風。
關鍵詞:中原畫風;河南油畫;生命意識;厚土意識;家國意識
中圖分類號:J22 文獻標識碼:A
基金項目: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河南油畫創作現狀及其傳播研究”(項目編號:2020BYS014)階段性成果。
具有社會屬性的人,一生中會生活在由許多人組成的群體中,有時甚至會在不同的階段生活在不同的群體中,費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來形容這種社會現象。在社會學語境中,這些群體被稱為“族群”。族群的規模有大有小,可以小到一個家庭,也可以擴大到整個社會。由于地域、文化、宗教等的不同,人們可以劃分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群間存在差異,且具備各自的特質。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受自然環境、戰亂、貿易往來等因素影響,河南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內涵,表現出獨特的族群意識。河南油畫家群體(1)以其敏銳的感知力和純熟的表現技巧,通過生命意識、厚土意識、家國意識的不同視角描繪出河南油畫藝術中所特有的族群意識,并以此豐富中原畫風的內涵,促進中原畫風研究的深化。
一、生命意識:族群存在的前提
族群延續的前提是生命的存在,沒有生命就無法形成族群。因此,生命意識是族群意識之根本。當殘酷的自然災害來臨時,為了保護家園和生命,中原人民不屈不撓、奮勇抵抗的精神,彰顯了他們對于個人生命的珍視。自古以來,黃河不僅帶來了生產資料,也帶來了水患災難。中原人民骨子里對黃河存在著深深的敬畏之情,這種敬畏,是對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對生命的敬畏。
(一)生命狀態的多樣化呈現
在許多人心目中,憨厚是中原族群的一種生命氣質的展現。而在河南油畫家筆下,人民的生命狀態卻有著多樣化的呈現。形成這種多樣化的原因,其一是藝術家本身性格及審美取向的差異,其二則在于畫面技巧呈現的差異。除此之外,還有社會變遷下時代政策的引導因素。綜合河南油畫藝術作品分析歸納可知,河南油畫中所描繪的生命狀態主要包含樂觀剛強的勤勞之態、內斂樸實的單純之態、粗獷堅韌的豪邁之態、凝重緘默的苦澀之態、超然脫俗的自在之態。
1.樂觀剛強的勤勞之態
在幾千年文化的積淀過程中,中原人民依仗著勤勞的雙手與惡劣的自然環境長期博弈,才得以繁衍生息。因此,樂觀剛強成為中原人民性格的標簽之一。在河南油畫創作中,對中原人民樂觀剛強的勤勞之態進行描繪的作品較為普遍。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田零等藝術家筆下的民兵剛毅勇敢,農民勤勞且充滿智慧。在《海防女民兵》中,女兵頭戴花色方巾,斜挎布包,端著步槍,其剛毅之氣不遜于男兵。《堅持敵后武裝隊》中,蘆葦叢里的女兵,與置于畫面中央的男兵一樣機警地注視著橋洞前方。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中原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中原人民樂觀剛強的性格和勤勞的優秀品格依然存在。王宏劍創作于1998年的《陽關三疊》,畫面描繪了農民工們剛過小年,為了討生活,在黎明的鄭州火車站露天廣場上等待著開往城市的火車的到來。此畫采用寫實語言,極其真實地描繪了候車的農民工群體的勤勞與樂觀,地平線上的人群與車牌共同形成長城的形狀,象征著眾志成城,反襯出這群“遠征者”的自信與勇氣。王宏劍的《奠基者》更是以太行山開山背石的村民為原型,背景的絕壁增強了山脈的壓迫感,而被圍困在畫面下方的五個形態各異,背著石塊的男男女女,在石頭的世界里開山鑿石,艱難謀生。人物的負重感,堅定的步履,果決的眼神,以及五人的形體組成山一樣綿延的形態,讓人由衷地感受到一種力量之美、信念之美。
2.內斂樸實的單純之態
中原文化中生命狀態的另一特征則為內斂與樸實,單純而樂于滿足。對于這一特質有突出表現的畫家是段建偉。比起情感激昂熱烈的事物,段建偉更容易被平淡的日常生活圖景和捉摸不透的模糊含義所吸引。“我看重這些平淡,世俗生活中的日常景色和幾乎無法辨認的表情。被它的捉摸不定和模糊的含意吸引。”[1]15段建偉多選取中原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性場景進行描繪,表現人們純真的本性,他刻畫的人物面對生命疾苦并無夸張的面部表情,體現了中原人民內斂且樸實的性格特質。楊海峰的《何處塵埃》系列作品以新農村建設背景下中原人民的生活進行創作,延續了對于中原人民內斂樸實性格的描繪。
3.粗獷堅韌的豪邁之態
除了內斂樸實的單純之態以外,中原人民同樣具有粗獷堅韌的豪邁之態。段正渠的作品,充滿激昂炙熱的畫面情緒,表達了中原人民血性十足的豪邁之態。1995年創作的《七月黃河》描繪了光著膀子的陜北漢子在烈日與怒潮中搖櫓奔流,大有移山填海之勢。這一繪畫風格的形成,首先來源于段正渠本身外靜內熱、充滿激情的性格。“我希望自己是個梁山好漢,百折不撓,所向無敵,冥冥之中殺他個痛快淋漓。”[2]198李佩甫說段正渠“一副恭順的小學生模樣。然而那畫中的目光卻是熾熱的,是噴涂的巖漿。”[3]2其次,來源于兒時對武俠小說的熱愛,以及陜北激昂凄美的“酸曲曲”給予段正渠的靈感。“我理解的‘歌’,是悅耳的,委婉吟唱出來的,而酸曲曲兒則是情感的噴發和靈魂的訴說。”[4]73如《山歌》《東方紅》所映射出的精神內涵擴大到了整個中華民族對于生命的豪邁粗獷的歌唱,凄厲高昂的聲音如劈開青天的利刃,唱出了人民對于命運的不屈以及對未來的憧憬。
4.凝重緘默的苦澀之態
中原地區的人民自農耕時代起,飽受自然災害的苦難。對外交流頻繁的當下,與沿海地區相比,中原地區經濟的發展依然存在地域的弱勢,因此當今依然有較大基數的中原人民從事傳統農業生產。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部分農民尷尬地處在城與鄉、傳統與現代、農民與城市身份認同的夾縫當中。因此凝重緘默的中原人民呈現出了苦澀的生命狀態。曹新林早期的油畫,無論技法多么出眾,構圖多么靈動,在視覺感受上總讓人感到壓抑和無奈。畫家張宇認為:“曹新林出身湖南農村,由于家庭成分太高,一入世就受人歧視。特別是進城工作以后,城里人看不起他這個農村人,革命同志又看不起他這個地富子弟,他就受著雙重歧視。這使他從年輕時候開始,就沒敢高聲說話和大聲笑過,什么時候都是怯怯地小心著。我想這種特殊的長期的生活積累,逐漸構成了社會環境、生存意識和自卑心理的一種合力,一直壓迫著曹新林的成長。”[5]2這種特殊的生活經歷也為曹新林提供著特殊的營養,從而滋潤推動著他的創作。煙是愁苦解悶的代表道具,早期曹新林刻畫的最為經典的農民形象,即是頭系羊白肚子手巾,脖子上掛著旱煙管子和煙絲袋子,如《戴煙斗的老人》和《老前輩》。進入20世紀以后,旱煙逐漸被香煙取代,曹新林筆下老農脖子上懸掛的煙袋也逐漸被指縫夾著的香煙取代,如《暖冬》《起五更》《裝修工》等,但是對于這一群體苦澀生命狀態的描繪依然是作品精神內涵的重點。侯震的《城市的補色》通過城鄉差異化呈現的方式來表達農民工形象,通過象征現代城市的建筑、帶有城市符號的物品反襯農民工群體,以輝煌的建筑與黯淡的農民工形成強烈反差。王宏劍的 《思鄉曲》則描繪了一個農民工在建筑工地席地而睡的景象,黑乎乎的腳板和胳膊折射出他工作的艱辛,睡姿宛如襁褓中的嬰兒一樣柔弱,題目已道出了他必然是夢到了故鄉,以及故鄉中苦苦等待他歸去的妻兒老小。
5.超然脫俗的自在之態
擺脫生活世俗的束縛,呈現出自在的生命狀態,這是一種超然的精神追求。受中國道家思想和西方現代哲學的影響,一些藝術家在油畫創作方面對于人的存在問題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例如女性藝術家趙夢歌,她作品中人物自在超脫的氣質,主要源于藝術家自身不受性別框架限制的獨立性格和其本人對于存在主義哲學的思考。從趙夢歌的自述來看,她的字里行間展示了她對世俗超然曠達的態度,她似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冷靜地觀察著這個世界的喜怒哀樂。同時,她又不是帶有自我放逐色彩的虛無主義者。在趙夢歌看來,海德格爾所認為的憂慮和恐懼才揭示人的真實存在的思想過于悲觀和感傷,她將自由存在的渴望寄托于自己的“理想國”,并通過創作使她的內心世界詩意地棲居其中。“在我的‘自·在’系列作品里表現的‘自在’不是‘自在菩薩’,而是強調自我、個性以及自我的存在狀態;自由自在、從容包容、悲天憫人、關照世界,同時又擁有無窮的能量。”[6]12
(二)對繁衍意識和長壽永生愿景的表達
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勞動產品的增多和存活希望的增強,因此,原始先民借助神明信仰和圖騰崇拜來寄托對于生存和種族繁衍的渴望。《道德經》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經》中的“男女精構,萬物化生”,都是對生命繁衍意識的闡釋。仰韶文化中的動物紋樣——蛙、魚、鳥、鹿,傳遞著生命永存和子孫繁衍的巫術寓意。在民間藝術中,也有以象征男女的抽象符號“嫁接”在一個完整的形體中,如民間藝術中“喜陶蓮”“雁戲蓮”“鸞鸞臥蓮”等組合圖像,就是以象征男性的鳥與象征女性的蓮所組合,成為男女合歡、交購的重要表征。黃河流域的民間剪紙藝術中,“雙魚娃娃”圖案、鳥銜魚圖案都象征著陰陽相合、萬物相生的繁衍思想。現代人類的繁衍行為并非機械化的,男女通常彼此心生愛慕,繼而產生生命的交合,繁衍便有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實現。河南油畫創作中主要通過贊美愛情來表達繁衍的原始本能。段正渠在文集《陜北聽歌》中,共引用了五首酸曲曲的歌詞,其中四首都是情歌,與其說他被山鄉男女的率真愛情觸動,不如說他是被那“活著很難,愛得痛苦,但依然遵循著求愛本能”的生命狀態所觸動。其作品《親嘴》就描繪了生長在中原大地之上炙熱的生命交合。《鏡子(之二)》描繪了一個背對著觀者的裸身女子手持鏡子,她的丈夫在一旁為她照著油燈,眼中充滿著愛慕情思。段建偉的《花鞋墊》描繪了男子因意外地得到心上人贈送的花鞋墊而欣喜若狂。在中國農村,繡花鞋墊自古就是愛情的信物。河南油畫家通過這些樸素原始又直白的愛情故事,展現了中原文化對于繁衍生殖的重視和家丁興旺的祝福。陰陽相交為福,通天通地為壽,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對于長壽永生充滿愿景。中原人民通過傳統習俗事項來表達長壽永生的觀念。用于民俗剪紙中的“壽”字,有著長壽之意;而用于喪俗中的“壽”字,則帶有永生之意。王宏劍的《冬之祭》描繪了一場葬禮的民俗儀式實錄,作品“取材于多年前我豫西老家親人的一個葬禮,畫面上幾乎每個人物均為我的親戚,并為我熟知”。[7]66作品使觀眾直接面對人生的終極命題——生存與死亡。
二、厚土意識:建立物質家園過程中所形成的土地崇拜
中國從古至今都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黃河流域適宜農耕的土壤和氣候促使先民們總結出了關于農耕的自然規律。先民們在長期的農耕實踐中,深切體會到土地耕種與黃河泥土之間存在著既依存又對立的關系。中原人民的文化信仰有多種形式,但沒有一樣如土地信仰更具有本色。對土地神和谷神的崇拜,是地地道道的農耕文化的本色信仰。厚土意識,就是中原人民在建設物質家園過程中所形成的土地崇拜。
(一)豐收的土地
河南作為產糧大省,主產小麥、玉米,面條、饅頭一類的面食也就成為河南人的主食。厚土意識的第一種表達形式是通過描繪中原人民的生活經歷和飲食習慣,反映土地給予河南人民的文化烙印。對于河南老一輩畫家來說,饑餓的記憶伴隨著他們的大半生,而對于青年一代畫家,饑餓的記憶伴隨著他們的童年。比如段建偉就曾對段正渠的饑餓童年有過描述:“他吃過玉米芯面、榆樹皮湯和紅薯蒂湯。有一年母親因為漿線打了一大盆面湯,正渠抱住母親的腿不讓漿線要讓做成面條。”“對這段饑餓的歲月正渠有著很深的記憶,1990年他有一張小畫,名字就叫‘吃飯’,畫中一家三口,每人都端著一只大碗,很忙活地吃著。”[2]199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生命得以生存的基本活動。因饑腸轆轆所帶來的痛苦會使人有著更為清晰的“存在感”,這種存在感是生命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時,生理所發出的強烈的抗議信號。河南藝術家把這種情感轉化為對土地的崇拜,通過描繪豐收的土地來療愈饑餓的記憶。如段建偉農村題材的作品多具有食材符號的痕跡,《餃子》《換面》《麥子》《送饃》《玉米》《燒餅》《油條》等作品,運用直白的敘事結構和符號化的隱喻來表達,這是藝術家對他生長的黃土大地的熟捻與審美的無意識表現。曹新林的《羊肉湯》、段正渠的《油潑面》和《回家》,都從飲食的視角投射出中原人民對于大地豐收地向往,凝練了中原文化中對于土地的崇拜觀念。
(二)神秘的土地
厚土意識的另一個表達,是對這片承載著厚重歷史與燦爛文化的黃土地的神秘感描繪。正所謂土生萬物而不語,承載萬物而不怨,那一層層黃土,記載的是源遠流長的悠久歲月,埋葬的是林林總總的萬物生命,反映出的是冷暖干濕的多次旋回。段正渠早年在書刊上看到陜西畫家蔡亮、張自嶷針對陜北的畫作,加上以“大漠”“邊塞”“古道長風”“金戈鐵甲”一類的字眼描寫的陜北高原,使他深深地著迷于那種神秘蒼涼感的描繪。“當我越來越多地想到幾十年前陜北的夜路, 想起漸遠的歌聲, 就越覺得有某種神秘的東西圍繞在周圍。出自對神秘之物的天然興趣, 總奢想把那種感覺畫出來。”[8]34段正渠的《英雄遠去》系列作品正是代表,“1994年, 我畫了《英雄遠去》組畫, 其中一幅就表現了這個場景。據說, 晚上在城里面走, 能聽到嚶嚶的鬼哭聲。兩年前的正月十五晚上十二點,我和一個朋友在廢城墻上走了一圈, 四周空曠無人, 剎那間似乎回到了古代……我特別喜歡這種感覺。這幾年我老沿著絲綢之路往西北跑, 還是尋覓這種感覺”[8]34。為突出表現黃土高原的這種神秘厚重感,段正渠擅于使用大面積的暗色,他認為真正能代表黃土高原的顏色, 應該是一種肅穆、莊重而又純粹的顏色,而黑色往往能使人聯想到時光的流逝和生命的輪替,恰好能表達那種神秘、厚重、蒼茫的感覺。“黑色帶有一種神秘和不確定性,而黃土高原的土地上本身就凝聚著巨大的力量,包含著無限的可能。這種可能性,最集中的體現就是陜北農民的執著、不屈和樂觀。在我眼里,黃土高原是一片孕育希望的土地,所以我用黑色隱喻這種內在的生命力。”[9]35-422000年至2014年間,長期的西北考察和風景寫生使段正渠的創作并不局限于陜北地區,而是擴大到整個北方地區,由此發展出全景式的風景畫,黃河流域本土文化元素的植入和傳統繪畫中書寫性的筆觸運用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較為常見。如《麻黃梁》《北草地》《白城子》《劉家坬》《孫家岔》《陜北長城》等。畫家著力呈現西北地區的千山萬壑、壁立千仞,試圖還原這些滄桑神秘的古代遺跡所呈現出的廣闊而又深刻的歷史圖景。
(三)異化的土地
河南油畫家的厚土意識還體現在基于新時代工業化背景下,對農村土地異化現象的關注。面對這個問題,有的藝術家通過對記憶中淳樸生活的描繪來隱喻現代科技對于生態平衡的破壞。而有的藝術家,則將這種擔憂鮮明地表達了出來。比如于會見,其作品關注的是從偃師老家到洛陽的這31公里的地方。2008年所作《世界在我背上》,2011年所作《遠行》,2012年所作《遠水》《為大地輸液》《故土》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藝術家對異化土地的擔憂。于會見說:“他老家縣城下面是盆地,稍微走幾步路就是山坡,就是首陽山,小時候在山上往下望,看到的就是開闊、遼遠。”[10]簡單的語言中,隱隱地流露出藝術家不僅記錄中原大地的風景變遷,同時也表達了個體對大地異相的憂慮。
三、家國意識:和諧家園的重要內涵
國家的建立可以集中資源去抵御外部的侵害,其本質還是為了人們生存在一個穩定和諧的家園的需要。經歷“大一統”思想與宗法制度幾千年的發展,黃河流域的人們形成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意識和同根同源的家國情懷。家國意識的形成一方面來源于秦始皇構建的“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大一統思想,另一方面來源于以血緣關系維系的家族制度。血緣關系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的基礎,而整個國家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蓋起的高樓大廈,家是小國,國是大家。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觀念讓古代文人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常將自身的榮辱得失與國家興盛成敗密切結合起來。中原地區在“以農為本”的經濟體制下,逐步形成了以村落為基本單位的鄉土社會,具有了鄉村的社區文化、宗法制度、道德觀念、社會規范、權力結構的本色特點。可見,家國意識是族群意識的重要內涵之一。河南油畫藝術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緊貼人民的現實生活,表現人們的事業和生活、順境和逆境、夢想和期望。曹新林在其文集中多次展現出藝術必須與人民公眾的命運緊緊相依的創作態度。他認為:“我們偉大的祖國和民族,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邁著艱難沉重的步伐。作為一個公民,藝術家應具有較強的歷史感、現實感和使命感,使自己的勞動有一定的社會價值。換句話說,藝術要肩負起對社會的預言和為人民代言的使命。”[5]152謝瑞階在1982年80歲大壽時與學生們的即席談話時講到:“我認為人是社會的人,他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那個‘從’字就倆人,那個‘眾’字就是三人。所以我認為凡干一件事情,一定要想想社會。”[11]244這種深具社會責任感的創作觀,使藝術家們遠離脫離大眾和現實的一己悲歡,傾向于為族群思考、為集體思考、為家國命運而思考。
(一)繪畫題材:情系國家命運,表現民族精神
河南油畫家群體情系國家命運,表現民族精神并傳承至今。一代代的河南油畫家滋養著黃河文化精神,凝練出家國意識,這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有學者指出:“至始至終,中國油畫中對于黃河的描繪仍然是依著它所代表的民族精神而展開的。”[12]5謝瑞階的黃河系列繪畫始終以表現民族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精神為特點。應鄭州火車站布置外賓接待室之邀,謝瑞階創作了《黃河在前進》。他用梯田、水田、林木來概括治理黃河的新景象,并在遠景上畫了工廠,近景描繪幾個勘探人員,以示社會主義建設在不斷發展。年逾八旬之際,謝瑞階表示要為祖國的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又創作完成了《黃河組畫》。謝瑞階濃濃的愛國意識寄托在滔滔黃河之中,與其說他想讓全世界人民都熱愛黃河,不如說,他想讓中華民族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段正渠作為中國表現性油畫的代表畫家,在其藝術創作中描繪了大量體現民族精神的黃河系列作品,他對于中華民族百折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把握成就了其作品的內涵。此外,也有藝術家通過英雄人物的描繪來表現民族精神。毛本華與王剛、鮑璐、郝米嘉共同創作的4米大幅油畫作品 《焦裕祿》,描繪的正是焦裕祿與群眾在蘭考一起植樹治沙的場景,表現了焦裕祿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建設家園的內涵精神,象征著他永遠地扎根在人民群眾心中。牛紅巖的《子弟兵之二》、孫平的《救援行動》、石二軍的《躍-1》等作品展現了洪災發生時,戰斗在一線的防汛工作者們淌過過膝的洪水,拯救被洪水淹沒的家園,體現了河南人民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的強烈的家國意識。
(二)繪畫技巧:堅持民族特色,洋為中用
河南油畫藝術在繪畫技巧上融合傳統中國畫的筆墨方式,堅持民族特色,洋為中用。謝瑞階的人物作品嘗試以中國畫的筆墨,借鑒油畫的人體解剖運用于人物造型。他畫黃河之水,擺脫了中國畫單純用線去表現水的方法,運用油畫的透視、光線因素,既重寫水之形,又重表現水之勢。曹新林的《陽光·白墻》《徽州古橋》等風景作品運用了國畫水墨寫意與油畫技法的結合,畫面傳達的潤燥交疊、意境清幽正是水墨大寫意的表達方法。此外,河南油畫家們在注重技法的同時,深入理解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并融入創作中。王宏劍將中國傳統的審美精神和法則注入西方經典繪畫的寫實技巧之中,他運用中國畫的布白和中國畫的全景式構圖,畫面留有一個寬廣而宏大的空間。《陽關三疊》中,王宏劍做到了將中國傳統的審美精神與西方傳統油畫表現視覺空間的技巧相融合。《奠基者》中,他將五個人的形態設計成山峰一樣的輪廓,他們的后面則是山崖絕壁,山與人的融合,體現了老莊道法自然、物我兩忘、無我之境的美學核心。
(三)畫面元素:植入民俗符號,展現民族文化
丹納說, 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傳統工藝匯聚了中華民族的造物智慧,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表征。段正渠的陜北題材作品《窯洞》描繪了一戶陜西人家的家中場景。窯洞是中國北部黃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男人在黃土地上刨挖,女人則在土窯洞里操持家務、生兒育女。作品集聚了民間藝術元素,門簾上有窗花剪紙、衣柜上有成對童子的木版年畫,表達著畫家對民俗文化強烈的感受。段正渠所創作的《吹嗩吶》《吞劍》《噴火》《扭秧歌》《北方》等都反映了北方傳統的街頭民俗民藝。作品《新年》《鞭炮》,通過手拿噼里啪啦作響的鞭炮符號以及畫面一片喜慶的紅色符號來表達春節期間的民風民俗。《臘月里》《玩火少年》等作品,展示了千百年來,黃河流域的農民在冬天烤火取暖、祭祀過節的傳統習俗。《年貨》描繪了一個手提豬肉、腋下夾著春聯的中年男子,表現了北方人民過春節時置辦年貨的畫面。《新娘》中一群男子圍著一襲紅衣的女子,描繪了傳統嫁娶儀式的場景。靜物作品《古陶》《有陶燕的靜物》《書與古陶》《有牽馬俑的靜物》中,描繪了三彩陶馬、牽馬陶俑、陶燕、陶碗等一系列古陶器。曹新林創作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現民俗符號,如《拉二胡的老人》突出表現了二胡這一民間樂器。《剪窗花》描繪了兩名女性拿著剪刀剪著紅紅綠綠的窗花。此外還有《春雪》中的窗花,《又一春》《臘八——實際的記憶》中的對聯,《本命年》中描繪男性人物系著一個大紅色腰帶。這些畫面元素實質就是民俗和民間工藝符號的植入,反映了河南油畫家對中原人民生活內容的細致入微的觀察,不僅傳達了他們對傳統民間藝術的熱愛,也表現出他們重視現代化進程下日益消逝的民俗民藝,同時也通過民俗符號來傳達家國意識以及族群認同感。
四、結語
生命意識、厚土意識、家國意識是層層遞進的關系:生命是萬物借以生存的根本條件;中原人民為保存族群與血脈積極投身于農業生產,在此基礎上誕生了以土地崇拜為核心的厚土意識;長期的合作生產過程中,中原特定的鄉土社會結構孕育了中原人民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故土難移的家國意識。三者更是互為融合的關系:厚土意識中對于中原土地的敬畏也正是體現了對生命的敬畏;家國意識從本質上講,也是維系穩定家園、延續族群血脈的價值要求。因此,這三種意識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建設穩定和諧的家園,促進族群的發展變遷。河南油畫藝術中的族群意識,體現了河南油畫家與黃土地血脈相連的親近感,他們通過作品傳達著對世代繁衍生存在這片中原大地上的人民的關愛。他們在意的是被遮掩在歷史褶皺中的這些平凡勞作者的生命尊嚴,正是因為一個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使生命如燭光般燃燒,才使得族群安定和諧、世代繁衍生息。
注釋:
(1)河南油畫家群體,指在地域劃分方式下,長期浸潤河南文化并以中原文化作為主要創作資源的油畫藝術家群體,主要包括長期生活在河南的河南籍油畫家、早年生活在河南后期調出河南的河南籍油畫家、非河南籍但長期生活在河南的油畫家。文中所列舉藝術家是河南油畫家群體的典型個案。除此之外,還有眾多河南油畫家為河南油畫做出了重要貢獻。限于文章篇幅,文中不再一一列舉。
參考文獻:
[1]段建偉.畫家畫語·回望鄉土[M].沈陽: 遼寧美術出版社,2000.
[2]段正渠.二段·段正渠[M].沈陽: 吉林美術出版社,2008.
[3]水中天.中國現代藝術品評叢書·段正渠[M].南寧: 廣西美術出版社,1998.
[4]段正渠.畫家畫語·陜北聽歌[M].沈陽: 遼寧美術出版社,2000.
[5]曹新林.敞開的壁爐——曹新林美術文集[M].鄭州: 河南美術出版社,2005.
[6]趙夢歌.自·在——趙夢歌藝術作品集[M].濟南: 山東美術出版社,2018.
[7]易英.最后的鄉土現實主義詩人——評八屆美展的獲獎作品《冬之祭》[J].工會博覽(藝苑版),2007(07).
[8]張榮東,王鳳娟,景敏.黃土高原的夜行者——對話段正渠先生[J].愛尚美術,2017(01).
[9]段正渠,殷雙喜.生命的底色——殷雙喜對話段正渠[J].油畫藝術,2015(01).
[10]于會見.用畫筆,畫出我對故鄉濃濃的愛[DB/OL].(2017-08-01).https:// www.sohu.com1/a/161405921_99901948.
[11]何彧,張海.黃河魂——謝瑞階書畫評論集[M].鄭州: 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
[12]王宏亮.論中國油畫中的黃河形象[D].西北師范大學,2012.
(責任編輯:萬書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