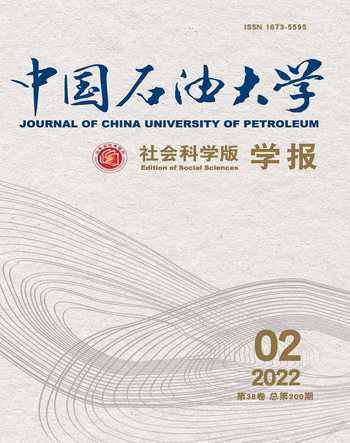人類世的能源書寫:論阿特伍德的“瘋癲亞當”三部曲
唐建南
摘要:隨著能源人文學的興起,能源成為文學研究的嶄新領域。從人類世框架探討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瘋癲亞當”三部曲,考察其中三種能源形式的書寫,可以發現:以石油為主要代表的化石能源是跨國石油資本主義實現全球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其廣泛使用導致了全球變暖、人口劇增、食物匱乏等人類世危機;以垃圾油和太陽能為代表的清潔新能源有望緩解石油枯竭和環境污染問題,但是,建立在舊能源文化基礎上的消費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導致社會變本加厲地揮霍其他資源,加劇了人類世危機;面對社會生態困境,人力與畜力等生命能源的回歸不僅肯定了身體的主體性,抵制了消費主義,也推動了自給自足的多元再棲居社區的建構,人類、非人類自然與后人類組成的異質聯盟構成了再棲居敘事的典范。
關鍵詞:阿特伍德;石油;新能源;生命能源;消費型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22)03003907
一、引言
隨著生態危機的惡化與環境人文學(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的崛起,人文學領域的能源研究也在20世紀末悄然萌芽。2014年,加拿大學者伊姆雷·子曼(Imre Szeman)和美國學者多米尼克·博耶(Dominick Boyer)首次將這個新興的跨學科領域冠名為能源人文學(energy humanities)①,它“力圖打破已有的能源缺席的學術和文化書寫現狀,突破定勢思維,尋求和推動能源研究的‘文化轉向’、‘倫理轉向’和‘話語轉向’”[1]。而能源也由此成為文學文化研究的嶄新視角,幫助人們洞察能源與權力政治、環境變化、文化理念等之間的緊密聯系。具體在文學領域,人們探討文學作品中人類與能源關系的書寫,揭示能源在塑造人類自然史與世界發展趨勢中的重要作用,聚焦能源想象(energy imaginary)如何闡釋當前的地緣政治沖突、人類世危機和消費型社會的形成,思考文學創作如何幫助世界建構擺脫化石燃料的后石油時代(post-oil age)。目前,相比國外的能源人文學研究,國內的能源文學批評還大有發展空間,核能文學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2-3],石油文學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開始,雖然時間跨度較長,但是也僅停留在介紹性階段,并未引起學界的重視 [4-5]。
能源書寫是“加拿大文學女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關注點,但是眾多針對阿特伍德作品的研究很少關注其作品中的能源書寫,比如其“瘋癲亞當”三部曲傳達了作家對能源的關注,可是對其研究的焦點主要局限于作品的題材特點 [6-8]、科技倫理 [9-10]、生態觀念 [11-14]、權力政治關系與跨國資本主義 [15-16]等。有鑒于此,本文將以人類世為框架分析阿特伍德的“瘋癲亞當”三部曲:《羚羊與秧雞》(Oryx and Crake)[17]、《洪疫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18]、《瘋癲亞當》(MaddAddam)[19],探討三大能源形式在作品中的書寫,論證以石油為主要代表的化石能源與人類世危機的內在關聯,討論新能源技術與舊能源文化共存狀態下的困境,思考生命能源的回歸對于建構再棲居社區的重要意義。
二、石油與人類世危機
斯坦芬妮·拉美娜杰(Stephanie LeMenager)曾經指出現代人類“深陷”石油時代,“與石油共存”,我們的衣食住行與石油息息相關,甚至呼吸的空氣中也彌漫著石油分子,20世紀作為美國崛起并主宰世界的世紀就是一個“石油現代階段”,其現代文化就是一部石油影響文化的歷史。[20]6但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正是人類摧毀環境、導致人類世危機的重要原因,而21世紀我們正面臨“石油峰值與全球變暖交匯”的問題,石油資源正在枯竭,人類如何超越當前嚴重依賴廉價石油的文化,如何應對化石燃料帶來的氣候變化,是決定人類未來走向的關鍵問題。[20]68拉美娜杰指出的這些問題也是阿特伍德在“瘋癲亞當”三部曲中所思考的,而且,她利用推理小說形式將這些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即使人類超越了廉價石油,是否可以超越當前石油文化的遺留影響,是否可以擺脫人類世的陰影呢。對于這些問題,阿特伍德并不樂觀,在其筆下,廉價石油已經成為過去,但是石油帝國尚未瓦解,人類世危機正將世界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也正因為如此,阿特伍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不盡如人意的石油書寫。
印度著名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是首位揭示文學領域石油缺席問題的學者。在他看來,石油是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但是國際上普遍對其保持 “緘默”,這不僅出于政治原因,還因為我們“尚未掌握展現石油經歷的文學形式”,石油是驅動現代社會的關鍵能源,卻又是難以再現的抽象存在,書寫石油很容易落入支離破碎的語言困境,所以這塊領域也成為現代文學不敢觸及的禁地。[21]為避免這一書寫困境,阿特伍德回避了文學現實主義的寫法,未將石油公司和權力沖突具象化,而是有機結合了象征、反諷和白描的寫作手法,將化石能源問題融入到其推理小說的科幻語境中,以此披露跨國石油資本對人類世危機惡化的巨大影響。
象征手法主要運用于塑造《瘋癲亞當》中的神父和其主持的石油教堂上:神父的虛偽、貪婪和殘忍暴露了石油資本的陰暗血腥,而其教堂就是石油帝國的象征。神父用《圣經》的宏大敘事為其石油崇拜正名,將石油開采號稱為神圣使命。他借用《馬太福音》中耶穌所說語句。“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19]112根據神父的邏輯,在拉丁語中,“Peter”指代“石頭”,而“oleum”表示“油”,所以石頭下沉積上億年的石油就是耶穌授予圣彼得建立信仰的基石,而這也是上帝“預測石油時代到來的預言” [19]112。神父通過引經據典力求證明其教義是神性的表達,石油就是上帝賜予的“光”,而開采石油就是將上帝豐厚的“饋贈品”傳播到 “人類主宰的星球上”,否則就是違背“神道” [19]112。在此基礎上,神父也用實用主義說服他人理解石油的重大作用。他指出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石油,食物的整個生產過程就是典型案例,從耕地到運輸,從購買到烹飪,保障人類生存的食物與天然氣在內的石油產品密不可分。可是,宗教只是神父粉飾其貪婪殘酷的謊言。盡管石油已經匱乏,油價急劇攀升,神父卻依舊富可敵國,他恬不知恥地接受石油教徒奉獻的不義之財,瘋狂地購買石油股票,享受著高耗能的豪車別墅。表面上他宣揚上帝的寬厚仁愛之心,實則是一個恃強凌弱的“施虐狂”[19]114,他秘密謀殺前妻,將其掩埋在自家庭院;他謾罵侮辱孩子,用語言暴力肆意地傷害其自尊。當精通黑客技術的大兒子澤布發現了父親謀財害命的秘密,選擇離家出走后,神父利用其強大的國際勢力,對澤布暗中進行為期多年的追殺。神父背后的國際勢力就是跨國石油資本,而他的虛偽、貪婪和殘忍就是石油資本的真實寫照。
在一定意義上,跨國石油資本是導致人類世危機的一大根源,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將這種以瘋狂資本積累為目的攫取全球石油資源、導致人類世環境危機的主體稱之為“能源帝國主義”[22]77。在三部曲中,阿特伍德更多采用白描的手法展現石油資本給全球環境帶來的巨大破壞。在石油開采過程中,海上鉆井平臺將垃圾直接排放到海水中,導致了水污染。依賴石油的工廠和汽車是廢氣和毒物的排放源,雖然石油的繁榮期已成為歷史,但是正在轉向清潔新能源的世界依然被石油使用留下的嚴重霧霾所困。人們到城市里需要佩戴可過濾污染顆粒的鼻罩,居住在城市的低收入邊緣人群更是空氣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對于石油工人而言,環境污染甚至危及其生命,他們可能吸入有毒空氣患上不治之癥,在氣候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工作可能會導致身體變異,比如皮膚像盔甲一樣堅硬。當一個地方的石油資源枯竭后,留下的就是荒涼的“鬼城”,本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北極也已經被洗劫一空,散落的空油桶、生銹的汽車和冰川融化后演變而成的荒漠就是20世紀石油文化留給后代的創傷記憶。[19]71石油資本也是反生態的。學校給石油子弟提供的《石油生物學》課程并非鼓勵學生真正推動節能環保,在澤布看來,其宗旨在于鼓勵學生“學習生物學后再推翻它” [19]120。這實際也是石油資本對環保的一貫態度。當清潔替代能源開發出來后,跨國石油企業竭盡所能地進行抵制,以保障石油的能源格局主導地位和石油帝國的霸主身份。他們將新能源稱之為“上帝神圣石油的敵人”,認為太陽能光板就是“撒旦的作品”,“生態等于變態”[19]117,如果采用這些新能源,人類將陷入黑暗,而只有那些無惡不赦的人才會相信全球變暖的謊言。但是,阿特伍德的三部小說不僅證明全球變暖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已經成為困擾物種生存的嚴重問題,它就是跨國石油資本帶來的一系列人類世問題之一。
炎熱天氣貫穿于三部小說之中,雖然它并非作者聚焦的主題,卻是該末日小說系列中揮之不去的黑暗氛圍。三月的室外已經如同煉獄一般酷熱,即使在“秧雞”制造的瘟疫病毒消滅了人類之后,幸存者還是需要戴墨鏡、涂抹防曬霜,用床單包裹全身,尋找蔭蔽處躲避炙熱的陽光。全球變暖也在導致全球地質環境發生巨變。在《洪疫之年》中,地中海南邊曾經肥沃的農田變成了沙漠,曾經物種豐富的亞馬遜熱帶雨林遭受了滅頂之災。在《羚羊與秧雞》中,吉米的母親談到火山爆發引起的海嘯吞沒了多個海邊城市,出生于佛羅里達的她感傷地提及家鄉的殘酷變化:受干旱影響,葡萄園土地干裂,美國第三大淡水湖——奧基喬比湖變成了臭水坑,著名的大沼澤國家公園整整焚燒了三個星期。盡管化石燃料的廣泛使用引發了全球變暖,生活在高科技世界、進入后石油時代的人們卻依然將石油驅動的生活視為過去的美好時光:人們可以驅車自由馳騁,可以乘坐飛機周游世界,可以在連鎖店吃到夾著真正牛肉的漢堡包……對于“真正牛肉”的向往也是整個小說系列中人們表達對真正食物的向往,而這背后卻是更為復雜的人類世問題:一方面,隨著醫療科技的高速發展和廉價石油的出現,世界人口出現了飛速增長,人口劇增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撐,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作為保障,也意味著會釋放更多的二氧化碳,這就會加速氣候變化;另一方面,全球變暖會毀滅無數生命的棲息地,人類的食物來源更難以得到保障,就需要從自然中攫取更多的資源以滿足生存需求。如此以往形成了難以化解的惡性循環,已有技術生產的食物已經難以滿足人類的需求,石油在內的化石資源以更快的速度枯竭,全球變暖問題不斷升級。在《瘋癲亞當》中,北極冰川融化就是人類世危機的典型案例。由于冰川融化,北極熊或饑餓而死,或向南遷徙,它們與南方的灰熊交配,而這兩種動物在過去20萬年中是不可能在大自然中相見的。人類世存在的各種危機讓技術天才“秧雞”絕望至極,這也成為他滅絕人類、重啟世界的動機。對他而言,高科技才能幫助他實現這一愿望,在小說中高科技也的確在化解石油枯竭的危機,新能源技術正成為人類社會繼續前進的驅動力。
三、新能源技術與舊能源文化
阿特伍德在“瘋癲亞當”三部曲中創造了一個高科技世界,如果說新能源技術正在創造一個人類擺脫石油的后石油時代,那么人類世的環境危機是否就能因此迎刃而解呢?在作者筆下,雖然技術實現了新能源的開發,但是因為依戀舊能源文化,人們不愿意擺脫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面臨的只能是生態末日。
在小說中,阿特伍德主要以垃圾油(garboil)和太陽能為例想象未來的能源格局。垃圾油是“garbage”和“oil”的混合詞,人們將飯店的泔水、屠宰場的廢棄物、塑料制品等投入大鍋爐內煮沸,分離出油和水,前者就可以轉化為能源。垃圾油企業在石油匱乏之后開始蓬勃發展,主要是對垃圾進行循環利用,而這種廢物利用的新能源在實質上既是應對人類世垃圾問題的技術經濟策略,又是社會矛盾和生態危機惡化的潛在原因。一定意義上,“垃圾是人類世的能指,而人類世是唯一以人類為中心的時代” [23]123。垃圾油的制作原材料——垃圾,是人類世高能耗社會的產物,人口劇增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撐其衣食住行,過去廉價石油已經讓人類習慣了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從而導致垃圾巨幅增長,大量的能源又需要消耗在垃圾處理上。《瘋癲亞當》中提到,在垃圾油出現之前,人類需將大量垃圾運送到北極,以此解決垃圾的存放處理問題。可是,垃圾油的制作隱藏著殘酷的社會機制和更大的生態風險。首先,小說中垃圾油的處理總是與社會中的邊緣群體關聯,毒氣彌漫的廢市群居著大量社會底層人士,而他們的生活空間描述總是離不開散落在城市之中的垃圾桶。這些底層人士就是蘇珊·西涅·莫里森(Susan Signe Morrison)所談的“垃圾人”(wasted humans),他們被視為無用的累贅,一旦成為主流階級的統治障礙,當權者就會像垃圾清理者一樣將垃圾人變為“無施事能力、無身份、無主體性的物件” [23]102。《洪疫之年》中,“垃圾人”的尸體經常被拋棄到垃圾桶中,成為垃圾油制造公司的原材料,這揭示了垃圾油制作后面隱藏的殘酷社會機制。其次,垃圾油技術的成功開發讓人們誤認為科技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人們可以繼續高能耗的消費型生活。這種技術烏托邦的想象方式也是當前廣受追捧的能源危機解決方案,科技萬能的理念只會導致人們變本加厲地消耗已有資源,也因此加劇了人類世的生態危機,在這一點上,太陽能的開發利用有相似之處。
在小說中,太陽能作為可再生能源是后石油時代的能源拯救者。阿特伍德在聚焦故事情節時,并不刻意講述太陽能本身,而是將其演變為石油一樣的抽象存在,無時無刻不存在于我們的生活背景之中,我們雖然對其視而不見,但是卻深陷其中。在這個新能源世界中,人們無法割舍以石油為代表的舊能源文化,傳統的能源消費觀念依舊根深蒂固,通過能源消耗,可以獲得出行的自由、購買使用商品的愉悅。在三部小說中,太陽能驅動的自行車、汽車、房子、玩具比比皆是,而新人類“秧雞人”的孵化器也依賴太陽能。以研發高科技盈利的大院具有最新的太陽能開發技術,人們生活在太陽能膜覆蓋的房子中,享受著該能源驅動的各種便捷電氣設備。在提倡節能環保的伊甸崖,人們嚴格遵守淋浴用水的規定,《洪疫之年》中的盧瑟恩從伊甸崖回到大院后,認為終于可以隨便使用熱水淋浴是件幸福的事。盧瑟恩的想法隱藏著消費型社會對高能耗生活的欲望,而太陽能就可以滿足人們的欲望。可是,雖然太陽能是清潔的可再生能源,人們不用擔心其資源枯竭和污染環境的問題,但是在無止境地利用該能源時,卻會導致其他資源的巨大浪費,比如水資源,由此加重人類世的危機。因此,這種技術烏托邦在阿特伍德小說中只是一種虛幻的解救人類危機理念,在其生態末日敘事中,如果不從根本上瓦解子曼所提到的“消費型資本主義體系” [24],人類最終只能走向湮滅。在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等人看來,這種資本主義體系最具體、最致命的形式就“帝國主義世界體系”[22]86。即使太陽能可以從技術上解決人類能源的使用問題,但是以爭奪資源、攫取利益來實現霸權統治的跨國資本主義還是會大肆鼓吹消費型社會給予人類的自由與幸福,慫恿普通大眾在消耗大量能源的同時揮霍其他資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跨國資本可以源源不斷地在全球進行資本積累。鑒于當前的生存危機,福斯特等人提出“真正的生態革命必須是反帝國主義的” [22]86。
不過,在阿特伍德筆下,“秧雞”所進行的革命是反人類主義的,他一廂情愿地使用瘟疫病毒消滅了人類,在他所創造的后人類世界中,生命能源再度成為生存的主要來源。
四、生命能源與再棲居敘事
馬丁·伍爾夫(Martin Wolf)曾經指出:“技術上關鍵的轉折在于從人力與畜力等在內的生命能源向風能、水力、化石能源等無生命能源的過渡。” [25]這種能源轉向也象征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不過,在阿特伍德的三部曲中,隨著人類世危機的加劇,以綠色宗教伊甸崖為典范,出現了一股回歸生命能源的力量,而這種生命能源也成為后人類時代賴以生存的能源形式,它與新能源太陽能的利用相結合,成為后人類時代建設再棲居社區的驅動能源。
在三部小說中,由亞當一號創建的伊甸崖是一個致力于節能環保的宗教組織,它號召人們自力更生,提倡自給自足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力支撐,而這種對生命能源的呼喚也是釋放身體能量(energy有“能源”和“能量”兩種含義)、實現身體主體化的過程,與社會上貶低身體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小說中所描繪的消費型資本主義社會致力于將身體客體化,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家鼓吹可以幫助人們采用各種手段管理身體,通過服用藥物或進行生化治療使人體抗擊衰老、抵制病毒,或者將身體商品化,讓身體淪為縱欲的工具,讓罪犯在互相屠戮中滿足觀眾嗜血的欲望,甚至將人肉制作成賴以充饑的漢堡包。與此相反,伊甸崖將身體視為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充分運用人力這一生命能源保障生存。人們親手種植蔬菜、養蜂釀蜜、烹飪食物、調制藥劑、加工肥皂,等等。這不僅能保障大家自給自足的生活,而且能幫助人們建立與內心、與非人類自然的密切關系,以此解構西方傳統意識形態中心智—身體、人類—自然的二元對立關系。以小說中的托比為例,她原來在廢市過著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被亞當一號拯救后來到伊甸崖,初時非常懷疑這里的教義,她機械般地和眾人勞作,認為自己隨時都可能逃離。而在人類毀滅、后人類時代開啟后,托比已經深受伊甸崖教義的影響,在利用生命能源勞作時她將其他物種視為親人摯友,將自我托付于自然的呵護與指引:養蜂時,她像對待親密朋友一樣與蜜蜂交談;為了生存,她殺豬取肉之后懷著愧疚之心祈禱得到動物的寬恕;播種時,她會默念伊甸崖有關“種子圣人”的教義;當疑惑時,她來到愛戴的指引人皮拉的墳冢,嘗試與其靈魂進行心靈交談。托比的系列變化是生命能源得到充分應用的過程,也是分裂的心智與身體重建聯系、重構完整獨立自我的過程,也是她與非人類自然建立密切關系的過程。通過釋放生命能源,托比與他人一起戰勝各種生存困境,也由此告別了過去廢市中忍辱負重的分裂身份,在自強自立中感受到身心融合的巨大力量。
生命能源也幫助人們擺脫了消費型社會的欲望,對他們而言,繼續已有的舊能源文化所支撐的高能耗生活無疑會最終導致毀滅,只有重新依靠身體本身的巨大能量,才能獲得生存保障。就像亞當一號所說:“當無水洪疫降臨,所有的買賣都將停止,我們只能在上帝的伊甸園中自食其力。” [18]126這里所指的自食其力的關鍵內容就是生命能源,與高能效的非生命能源相比,利用生命能源的產出過程更漫長、更復雜、更辛苦,因此人們往往會珍惜所得產品或擁有的資源,而不會像廉價石油所支撐的消費型社會一樣揮霍已有資源。所以伊甸崖的人們非常珍惜自己種植的蔬菜、釀制的蜂蜜,他們簡單生活、敬畏生命,與整個社會的消費主義主流形成了鮮明對比。當人類滅絕后,幸存者更是珍惜有限的資源,并利用身體內在的生命能源保障自己的生存。在一定意義上,伊甸崖的生活模式也是巴特·威靈(Bart Welling)關于“再棲居敘事”的構想,為了抵制石油驅動的消費型資本主義社會,威靈認為有必要建構一種立足生態區域的再棲居模式,“在這個生機勃勃、自給自足的多元社區,人們與非人類鄰居互惠互利、親密相處……重新棲居生命之地” [26]445。
在《瘋癲亞當》中,這種再棲居模式更為凸顯。在這個平等、自足的多元社區,人力與畜力兩種生命能源得以充分利用。為了追殺十惡不赦的逃犯,保證自身生存不受到威脅,幸存者與轉基因豬在后人類代表“黑胡子”的協助下建立了聯盟。轉基因豬本是食物匱乏的幸存者獵殺的對象,也是人類中心主義占據上風時的受害者,但是轉基因豬具有人類的基因,其智慧也能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而當逃犯已經威脅到大家的生命安全時,轉基因豬主動找到友好的幸存者,具有通靈能力的“黑胡子”斡旋其中負責語言的翻譯溝通,最終制定了合力追殺逃犯的計劃。追捕過程中,吉米無法行進,轉基因豬主動提出背著吉米前進,他們共同抵達目的地后,幸存者、轉基因豬和“黑胡子”完美配合,對逃犯圍追堵截,最終成功將其捕獲。在整個過程中,人類與自然的二元對立關系不攻自破,人類、非人類自然與后人類一起利用內在的生命能源共同完成生存任務,并在處理逃犯后,人類與轉基因豬達成了協議,即前者不再將后者作為食物,而后者也不再威脅前者。這種協作的過程也推進了人類“生成—動物”的進程。在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Felix Guattari)看來,生成動物并不是指人類要變成某種動物,而是不同物種之間實現“異質共生”或“異質聯盟”。[27]而這種由人類、非人類自然與后人類組成的異質聯盟就是小說中再棲居社區的建構基礎,驅動該社區的就是生命能源。在一定意義上,生命能源體現為對生命的尊重、對生命力的呼喚,這也是再棲居敘事建構“生命之地”的根本所在。梅麗莎·海恩斯 (Melissa Haynes)將人力與畜力統稱為“動物能源/能量” [28]。由于“動物”(animal)與“生命”(animate)來自于拉丁語的同一詞根“anima”,表示“給予生命”,因此生命能源與動物能源可以說一脈相承,都與“生命”緊密相連。在阿特伍德構建的后人類時代,隨著人類的滅絕,消費型資本主義體系崩潰瓦解,人類、非人類自然與后人類和諧相處,人們不再奢望利用更多能源滿足自身貪婪的物質欲望,而是發揮其內在的“動物能源”保障基本的生存,他們不再需要非生命能源準備食物、制作工具等,僅需要利用內在的生命能源食草果腹或交配生子。“秧雞人”還與人類幸存者交配,他們所孕育的新新人類加入了這個告別石油及舊能源文化的社會,以此進一步豐富了再棲居社區的多元性。
五、結語
在“瘋癲亞當”三部曲中,阿特伍德建構了一個由生命能源驅動的再棲居社區,這有利于修正現有的消費型能源文化,緩解人類世的生態社會危機。可是,如此以來,阿特伍德也從毀滅人類的生態末日想象轉向了生態烏托邦的建構,而烏托邦總是因為過于美好而偏離現實:讓人類放棄高科技,回歸沒有欲望、無需化石能源的農耕生活,總會被詬病為逆轉歷史的簡化做法。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對于沉浸在 “石油烏托邦”[20]74中的現代人類,告別便捷交通工具、大型購物場所、遠郊舒適房屋等主要由石油驅動的現代生活方式,卻是一種噩夢般的未來,再現這種景觀的能源書寫則可以達到警醒世人、反思當前能源文化的目的。換而言之,阿特伍德用文學作品證明“人類與石油的關系已經讓這個世界糟糕透頂”,而我們所有人都將陷入這“一團糟”之中。[26]456從這層意義上講,“瘋癲亞當”三部曲證明科幻小說也許是思考當下和未來能源危機的“最佳體裁”[29]111,因為它用壓縮的時空尺度預示了當前能源文化理念指導下人類文明的發展軌道,揭示了人類期待以“永恒動力”驅動現代世界欲望的虛妄性[13]141。當然,在未來的能源文學研究之中,也有待不同體裁的作品重構能源觀的現實價值。另外,不管是重讀經典,還是分析當下越來越多自覺建構的能源文學作品,都可以發現能源已經嵌入文學想象之中,而建構能源批評、從能源視角“全面重塑已有話語和已有研究對象”是人類認同自己的“能源主體”身份,加深理解能源、權力、文化、環境等內在聯系的關鍵使命。[30]有鑒于此,能源文學創作和能源文學批評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透過文學建構的能源景觀,如阿特伍德小說中建構的想象空間,沉浸在石油文化中的讀者可以發現建立在石油資源上的社會如同流沙上建造的世界,人類有必要理性地看待當前的人類世生態困境,有必要“理智地追憶石油現代階段與全球變暖之前的世界” [26]456,并開始“重新棲居世界與重構文化的任務” [26]456,只有這樣,人類與其他物種才能真正享有源源不斷的生命能源。
注釋:
① 尼克·博耶與伊姆雷·子曼在石油敘事研究的基礎上于2014年首次提出“能源人文學”的概念,并在后期出版的論文集或專著中進一步闡釋該概念,比如子曼與博耶合編的論文集《能源人文學選集》(Energy Humanities: An Anthology)、子曼與其他學者合編的論文集《能源驅動文化:能源環境101條關鍵詞》(Fueling Culture: 101 Words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子曼于2019年出版的專著《石油文化:全球化、文化與能源》(On Petrocultures: Globlization, Culture, and Energy)。
參考文獻:
[1] 趙秀鳳,曹春華.能源人文: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 36(3): 32.
[2] 楊曉輝.日本作家非“被爆”體驗下的“核”書寫[J].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 2015 (5): 35-39.
[3]劉霞.日本核文學研究述評[J]. 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 (4): 59-65.
[4]王勇,馮達,任金鳳.新潮小說對大慶石油文學的影響[J].大慶社會科學, 2013(6):142-144.
[5] 范豫魯.論中國石油文學的演變[J].西安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25(2): 91-96.
[6] Hicks H. The Post-Apocalyptic Nove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rnity Beyond Savage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6.
[7] 方紅.《奧蕾克斯與克雷克》:一部后現代科幻小說[J].外國文學研究, 2006(5): 105-112.
[8] 高彩霞.生態預警小說的科學性與文學性——兼評阿特伍德的小說《“羚羊”與“秧雞”》[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8(4): 37-40.
[9] 蔡奐.技術統治與生態災難:試析反烏托邦生態小說《羚羊與秧雞》[J].世界文學評論, 2007(1):126-129.
[10] 丁林棚. 技術、消費與超現實:《羚羊與秧雞》中的人文批判[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7, 40(2):113-120.
[11] 薛小惠.科學·人性·未來——《羚羊與秧雞》的生態主義解讀[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1,19(3):49-52.
[12] Nazry Bahrawi. Hope of a Hopeless World: Eco-teleology in Margaret Atwood’s Oryx and Crake and The Year of the Flood [J].Green Letters: Studies in Ecocriticism, 2013,17(3): 251-263.
[13] Bouson J Brooks. A “Joke-filled Romp”through End Times: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Deep Ecology, and Human Extinction in Margaret Atwood’s Eco-apocalyptic MaddAddam Trilogy [J].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016,51(3): 341-357.
[14] Richard Alan Northover. Ecological Apocalypse in Margaret Atwood’s MaddAddam Trilogy [J]. Studia Neophilologica, 2016 (1): 81-95.
[15] Sarah A Appleton. Corp(se)ocracy: Marketing Death in Margaret Atwood’s Oryx and Crake and The Year of the Flood [J]. LATCH 4,2011(4):63-73.
[16] 袁霞.論《羚羊與秧雞》中的全球化危機 [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7,40(4):132-138.
[17] Margaret Atwood. Oryx and Crak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18] Margaret Atwood. The Year of the Flood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19] Margare Atwood . MaddAddam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20] Stephanie LeMenager. Living Oil: Petroleum Cultur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 Amitav Ghosh. The Oil Encounter and the Novel: Petrofiction [J]. The New Republic, 1992: 30.
[22]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eman, Brett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J]. Monthly Review, 2019,71(3): 70-88.
[23] Morrison Susan Signe. The Literature of Waste: Material Ecopoetics and Ethical Matter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24] Imre Szeman. System Failure: Oil, Futurity,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Disaster [J].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07,106 (4): 805-823.
[25] Martin Wolf.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M]. Bolt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41.
[26] Bart H Welling. Petronarratology: A Bioregional Approach to Oil Stories [J]. English Studies, 2018,99(4): 442-457.
[27] 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28] Melissa Haynes. Animal [C]//Imre Szeman, et all. Fueling Culture: 101 Words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37.
[29] Graeme Macdonald. Improbability Drives: The Energy of SF[J]. Paradoxa, 2014 (26): 111-144.
[30] Imre Szema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Energy [C]// Matú Miík,Nada Kujundi’c. Energy Humanities.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Directions. Springer, 2020:29.
The Energy Writing in the AnthropoceneOn Margaret Atwood’s MaddAddam Trilogy
Tang Jian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energy humanities, energy has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literatu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nthropocene, an energyoriented analysis of the MaddAddam Trilogy by the Canadia writer Margaret Atwood will b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ree forms of energy illustrated in the series. First, oil as the dominant fossil fuel is a key sourc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for the oil imperialism. The widespread use of oil results in global warming, population explosion, and food shortage etc., which prove that the transnational oil capitalism is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aggravation of the Anthropocene crisis. Second, though the clean new energy sources such as garboil and solar energy can ameliorate the problems of oil depletion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consumerist capitalist system based on the old energy culture prompts the society to waste more resources. Last, to counteract the overwhelming Anthropocene crisis, the return of animate energy such as human and animal labor can acknowledg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body, resist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ism,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lfsufficient and diversified reinhabitary community. The alliance of humanity, nonhuman nature, and posthuman serves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reinhabitary narrative.
Key words: Margaret Atwood; oil; new energy; animate energy; consumerist capi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