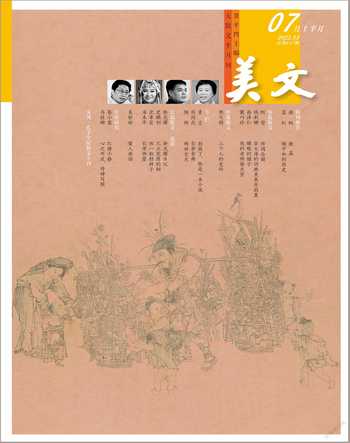我的老師謝光賢

戴巧珍
一直喜歡當老師,如愿以償考上師范,去學校報到時,心中的興奮難以言表,我提著重重的行李從車站一直走到學校,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濡濕了。
到校門口時,突然一群“活雷鋒”圍住了我,給我提包的提包,遞水的遞水,帶路的帶路。其中一位男同學還從口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遞給我,笑盈盈地示意我把汗擦擦。我心中無限暖意,對這所學校的親切感油然而生。
這些“活雷鋒”都是高我一級的學長。這位“男同學”就是謝光賢老師。他剛從浙師大畢業,最近還被任命為團委書記,這些讓新生們感動的“迎新”活動就是他推出的。只一面,我就記住了謝老師,下巴勾勾的,笑起來上嘴唇就不見了,讓他年紀輕輕看上去有一種年長者的慈祥感。
過了幾天,校團委又組織社團活動,校門口琳瑯滿目的小黑板上寫滿了二胡、吉他、籃球、乒乓球等活動,其中還有一堂題為《未來的老師,你準備好了嗎》的輔導講座。我選擇了后者。
進階梯教室時,里面已坐滿了人。講課人正是謝老師,他站在高高的講臺桌前,長長的米色風衣襯得他身形高大偉岸。他躊躇滿志地向我們點頭示意,一派大家風范。
我在教室里找了一圈,沒有一個空位子,只好站在門口聽,心里盤算著聽一會兒就撤。
但我聽了一個開頭就被深深吸引住了。講座像膠水一樣牢牢地把我粘在教室門口。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么精彩的講座!哪怕時隔30多年,我回首往事,依然能捕捉到這個講座帶給我的震撼——原來老師上課可以這樣上,原來一堂課可以出神入化到這樣的境地!
在那堂課里,我第一次聽到一位老師這么深入地談到讀書。他說,要讓每天的閱讀像一日三餐一樣營養你……不要以為很多書看過了就成了過眼煙云,它們其實是換了一種形式在陪伴你,在你的氣質里,在你的談吐上,在你無涯的胸襟里,當然也會顯露在生活和文字里……
其間,謝老師談到了很多學者、作家的觀點以及他們的著作,他像跟我們聊天一樣隨意、輕松、有趣,但他的每一句話都讓我在心里睜開了眼睛。我站著聽完兩個多小時的課,沒有一絲走神,也沒感覺一點酸累。講座太厚重、太豐富、太深刻了,我趴在門框上不停地記筆記,做好回去反芻的準備。
除了震憾,我還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恐慌。
初中三年,每科老師都讓我們強記知識點、機器人一樣拼命刷題,我從來不曾去打量這個世界,打量自己。謝老師突然向我打開了一扇門,但門里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那些著作我一本也沒看過。我感覺自己孤身進入了蒼茫大海,身邊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我不擅長的。
那堂課之后,我常陷在自卑的情緒里,平時也不敢與同學多交流話題,生怕他們看穿我。同時,我開始瘋狂地跑圖書館。師范三年,我不知道奉化的電影院、錄像廳、小吃一條街在哪兒,我幾乎把所有的課余時間都花在了看書上。
有一次吃完晚飯,我從食堂走向教學樓。謝老師和幾位青年老師站在教學樓前的天井里聊天。他叫住我:
“這位同學,你過來——你說說看,你那天聽了講座有什么收獲?”
旁邊的老師挺詫異,說:“學校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這個學生聽過你的講座。”謝老師笑著說:“這個學生是唯一一個站著聽完我講課的人,也是整堂課都在做筆記的人。”
謝老師聽完我的回答,笑了,說:“嗯,挺好,想得挺多的,你好像專門想好等我提問一樣!那我以后要多問問你了——明天有學生會競選活動,你報名了嗎?”
“沒有沒有,我不行的,我不去。”我緊張得臉都發燙了。
“你去都沒去過,怎么知道不行?去吧,我覺得你可以的!”謝老師笑瞇瞇的。
我還想推卻,謝老師收了笑容,正色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學生會工作很能鍛煉人,我們只在普一新生中吸收,入職以后可以做三年,你們可只有一次競選機會,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你好好考慮一下。”
聽謝老師這么一說,我只好應允。當天晚上連夜準備競選稿,一晚上翻來覆去地在床上背“臺詞”。
第二天走進團委活動室,里面黑壓壓的都是人頭,我又氣餒了,幾次想打退堂鼓,但想到謝老師的話,只好咬咬牙坐回競選席,同時快速調整好心態。開始演講時,因為準備得挺認真,“臺詞”又背得熟,意外地講得很順。我竟然入選了。
入職學生會后,謝老師讓我編校團委唯一的刊物《團訊》。編了兩期,恰逢普三的主編有事,謝老師跳過普二的副主編,直接讓我當主編。這樣的信任讓我誠惶誠恐。我不敢怠慢,除了學習,大部分精力都在研究怎樣辦好《團訊》上。寫稿子更是勤得很,白天沒空,晚上打著手電筒寫。
謝老師每次組織團委、學生會干部開會,總會表揚《團訊》,有時讓我在全體學生會干部面前談編輯心得,有時還拿我寫的文章作范例講解。我學習和工作的勁頭更足了,也變得自信而勇敢,逢著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積極向上級媒體投稿。發表后拿去跟謝老師分享,謝老師總會指著刊物編輯改動過的地方——“嗯,這兩處改得很好,你自己多體會體會。繼續寫,不要辜負自己。”
到普三時,謝老師已和我們這些學生干部打成了一片。我們經常在一起組織活動,交流讀書心得。因為這樣的情誼,我們還有幸見識了謝老師“有趣”的一面。
有一次校團委組織我們外出采訪,采訪完畢準備返程時,謝老師叫住我和另一位男同學說:“其他人先回去,你們兩個留一下。”
原來謝老師是要我們兩人陪他相親!
女方是位長發飄飄的大美女,長得太漂亮了,很像1986版《西游記》里演嫦娥的演員,一貫自信的謝老師走進去跟她握手時,人有點愣,說話也有些詞不達意。后來一起去吃飯,席間,都是那位美女姐姐主動給謝老師及我們夾菜。謝老師一直懵懵的,好在有我們跟美女姐姐說笑逗樂,不至于太冷場。我在心里暗暗發笑,原來謝老師也有怯場的時候。
一晃三年過去了,離校前我們去跟謝老師道別。謝老師笑著看著我說:“畢業了,一件作品就完成了。工作以后還是要多看書,多寫寫。寫作也許不能成為我們的事業,但它可以充實心靈,滋養生活。”
我用力地點點頭。走很遠了,回過頭,發現謝老師還在校門口站著……
畢業以后,我一直跟謝老師保持著書信聯系。
我起初分在一個完小,一個班才8個學生,工作悠閑得很,我寫信跟謝老師調侃說一個月就可以把一年的課上好了。謝老師回信鞭策我,工作輕松就多讀讀書,這兩年就把大學文憑考來,以后成家了事情就多了。我覺得很有道理,于是業余時間埋頭苦讀,兩年內就把大專自考六門課都拿了下來,之后緊接著讀了專升本。
兩年后我調到鎮里的中心校工作,工作壓力一下子增大,晚上經常加班。寫信給謝老師訴苦,他回信說,工作忙就借工作好好磨煉自己 ,同時也要擠時間多讀書,書讓我們受益終身。
謝老師的那些信像春風一樣吹散我心中的霧霾,給我力量,催我警醒。師范三年,我最大的變化就是,我自信了,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底氣。我相信,只要努力,人生沒有不可能。
有了微信以后,我們互加了微信好友。在微信里,謝老師告訴我,他有“小棉襖”了,他離開奉化師范,調入奉化市府辦了,他升職當市府辦副主任了……我也告訴他,我開始寫書了,我女兒上幼兒園了……工作以后,我們從師生變成了朋友,分享工作和生活的喜怒哀樂,時時互勉。我以為生活會一直這樣下去,一直到老。
2013年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謝老師的音訊,發微信給他也沒有反應。我找同學打聽,一個霹靂當空炸下——謝老師竟然患了肝癌!發現時已是晚期,現在剛做好換肝手術。還算好,手術是成功的。
我忙不迭地約了同學去看他。見我們來了,他堅持從病床上起來,在客廳會見我們,一邊走一邊把撫住腹部的手移開,緩緩抬上去,拉正衣服的領子,就像以前他給我們上課時,必然把衣服理得筆挺,頭發整得清清爽爽一樣。病成這樣了,他還始終維持一個老師得體的形象。
我們圍著他,仿佛又回到了當年。他顯得頗興奮,聊了很多舊事,連把他發病的情景和手術后的痛苦都講得生動而傳神,仿佛在講別人的故事。我聽得滿臉是淚,他反而安慰我——“我也許是太順了,所以老天要損損我,但我要讓老天失望,我會好起來的。現在換肝后成功的案例非常多。”
謝老師到底是謝老師。謝老師終會回到從前。
2015年,我母親病重,我忙得一直沒工夫聯系謝老師。次年3月,動了手術的母親在重癥監護室20多天沒有蘇醒,而且情形一天差似一天。我每一天都在火上煎熬。
4月15日早上,謝老師突然發微信給我,勸我堅強,要我挺起來照顧好父親和家里的人。還說他又一次從鬼門關回來,現在人還在醫院。原來從去年起,他的病就開始反復,昨天他又昏迷了,搶救回來后,人還發著39度的高燒。他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我痛苦的樣子,忍著病痛給我發微信。
吃晚飯的時候,同學鄭科瑩打電話給我說“明天我們一起去送送吧,謝老師走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跌跌撞撞地趕到奉化殯儀館——
謝老師靜靜地躺在花叢中,臉色蒼白而平和,嘴唇輕輕地抿著,仿佛叫他一聲,他就會把上嘴唇藏起,露出年長者一般慈祥的笑容。
我輕聲地喚他“謝老師——”
這一次,他沒有應我。
(責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