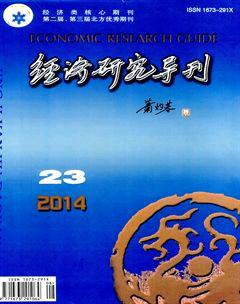基于協(xié)同理論的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發(fā)展策略
張洪雙+寧巖
摘 要:隨著人類旅游活動的延伸,無居民海島旅游正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旅游發(fā)展的趨勢之一。基于協(xié)同理論,研究分析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的三個層次:核心產(chǎn)業(yè)鏈的企業(yè)系統(tǒng)、產(chǎn)業(yè)集群協(xié)同、產(chǎn)業(yè)集群與環(huán)境協(xié)同。實現(xiàn)協(xié)同發(fā)展應從目標協(xié)同、制度協(xié)同、組織協(xié)同、利益協(xié)同、創(chuàng)新協(xié)同、信息協(xié)同等方面入手。以海南省為例進行實證分析,提出發(fā)展思路和策略。
關(guān)鍵詞: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理論;協(xié)同發(fā)展;海南
中圖分類號:F5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3-0145-03
多年來,海南省旅游業(yè)側(cè)重島內(nèi)旅游和產(chǎn)品組合開發(fā),使海南省旅游產(chǎn)品過于單一和低價,海南省旅游業(yè)陷入低價觀光的泥潭,海洋旅游產(chǎn)品升級和轉(zhuǎn)型正在經(jīng)歷瓶頸階段,海南省旅游業(yè)的市場動力系統(tǒng)在逐漸失衡。無居民海島是海洋旅游產(chǎn)品鏈條和價值鏈條的延伸、拉伸的重組形態(tài),應以創(chuàng)新和變革的方式將其進一步調(diào)適旅游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整體性變革。2010年1月4日國務院公布的《國務院公布關(guān)于推進海南省國際旅游島建設發(fā)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建設“富有海南省特色的旅游產(chǎn)品體系”,要“有序發(fā)展無居民島嶼旅游”,為海南省旅游產(chǎn)業(yè)的聯(lián)動升級進一步明確了發(fā)展方向。
無居民海島是指在中國管轄海域內(nèi)不作為常住戶口居住地的島嶼、巖礁和低潮高地等。海南省擁有500平方米以上的無居民島嶼200多個。2011年4月12日,中國公布首批無居民海島開發(fā)名錄共計176個,其中海南省有6個(東鑼島、西鼓島、蜈支洲島、小青洲、加井島、洲仔島)。如何進一步完善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模式,塑造高品質(zhì)旅游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和市場格局,迫在眉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部分無居民海島已經(jīng)進入或完成初期開發(fā)階段,但由于缺乏科學規(guī)劃和統(tǒng)一管理,國有資源意識淡薄,保護意識缺失,造成了海島資源浪費和環(huán)境破壞,尤其是周圍海域生態(tài)結(jié)構(gòu)的破壞。海南省打造國際旅游島高端旅游目的地,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與陸地旅游、有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本文在借鑒國內(nèi)外有關(guān)理論研究的基礎上,以協(xié)同理論視角嘗試架構(gòu)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模式和實現(xiàn)路徑,為業(yè)界和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一、無居民海島旅游發(fā)展理性梳理
(一)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與發(fā)展理論
1.國外相關(guān)理論研究綜述
國外對于“無居民海島旅游”為核心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相對匱乏,在Else-vier SDOL數(shù)據(jù)庫上檢索2000年以來的文獻,總計145篇,其中關(guān)于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模型的研究僅為16篇,基本研究的重點為三個方向。
(1)無居民海島旅游經(jīng)濟問題研究。瑞典學者Girlish(2007)從企業(yè)經(jīng)營者角度分析海島開發(fā)對企業(yè)的影響.劍橋大學Martina(2009)認為,結(jié)構(gòu)變化是眾多無人海島旅游經(jīng)濟保持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英國學者Shareef(2007)通過對比20個無人海島經(jīng)濟發(fā)展情況,發(fā)現(xiàn)旅游發(fā)展加劇了不同產(chǎn)業(yè)的競爭。巴塞羅那大學Schistose教授(2008)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旅游業(yè)在合理開發(fā)和良好管理的前提下,污染較少的旅游業(yè)更有利于海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海上交通和海上乘船觀光,特別是豪華郵輪旅游是近年來國外海島旅游研究的一個熱點。
(2)無居民海島環(huán)境問題的研究.很多學者都運用加拿大學者Buttlar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來分析不同旅游地的演化特征:牛津大學Charles教授(2004)確定了目前海島旅游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要面臨的風險,為無人海島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進行優(yōu)化設計。西班牙學者Eugenie(2005)對進入衰退階段的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島的研究,補充了Buttlar的生命周期理論,指出旅游地的演化還要經(jīng)過“質(zhì)量”、“環(huán)境”和“當?shù)乜沙掷m(xù)發(fā)展”為準則的發(fā)展階段。法國學者Rachel(2006)以泰國皮皮島(Koh Phi Phi)為例進行3年實地調(diào)研,比較論證,探討研究了海島利益相關(guān)者對實現(xiàn)一個海島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實踐的影響,認為利益相關(guān)者(政府、工業(yè)界、非政府組織、地方社區(qū))可以共同參與海島旅游業(yè),實現(xiàn)可持續(xù)性發(fā)展。
(3)無居民海島市場開發(fā)和管理問題的研究。新西蘭壞卡托大學Gunnar教授(2009)分析冰島旅游發(fā)展歷史和面臨危機,丹麥學者Morgan選擇開發(fā)程度、自然、生物、人文四類共五十個影響因子,對海島旅游質(zhì)量進行評價。美國學者Yusuf(2004)研究認為,海島旅游是眾多小的海島經(jīng)濟的重要收入來源,也面臨著自身脆弱性的影響。美國學者Diaz(2010)指出,必須對無人海島旅游產(chǎn)品進行持續(xù)性市場細分。悉尼大學Kannapa教授(2008)通過實證分析,證明政府和社區(qū)的參與對于海島旅游的影響。
2.國內(nèi)相關(guān)理論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無居民海島旅游已有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但從文獻的時間分段來看,2000年之前,對于海島旅游研究的文獻極度匱乏。在中國知網(wǎng)上以“無居民海島”、“海島旅游”為關(guān)鍵詞檢索出2004年以來的相關(guān)文獻總計63篇,而對于無人海島旅游模式和方法的文獻僅2篇。
遼寧師范大學宮元慧(2008)指出目前我國海島旅游業(yè)存在的問題;劉志軍分析海島旅游業(yè)開發(fā)的瓶頸因素,強調(diào)以保護為核心,注重生態(tài)保護;中山大學陳烈教授、李悅增教授(2004)以放雞島為例,研究探索海島旅游戰(zhàn)略發(fā)展模式;中國地質(zhì)大學吳克寧教授(2006)對無人海島旅游開發(fā)進行初步嘗試性探討。學者盧靜怡(2009)實地調(diào)研大鹿島發(fā)展模式,提出產(chǎn)品創(chuàng)新、加強基礎設施配套、制定環(huán)保策略、管理體制創(chuàng)新、突出競合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青島大學孫兆明博士(2009)通過對經(jīng)濟脆弱性、環(huán)境脆弱性和社會脆弱性的解讀,分析海島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支撐體系;河南大學陳金華博士(2008)以南海諸島為例,探討海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相關(guān)因素。淮海工學院張德利(2009)以連云港為例,提出海島旅游組合和規(guī)劃思路;遼寧大學王躍偉博士(2008)以舟山群島為例,綜合和歸納海島旅游開發(fā)的特點;河南大學陳金華和周靈飛(2008)以福建東山島為例研究社區(qū)參與與海島旅游發(fā)展的關(guān)系;華僑大學何巧華(2007)研究了構(gòu)建海島旅游安全系統(tǒng);河南大學陳金華(2007)依托平潭島分析海島旅游預警系統(tǒng)。endprint
總體來看,國內(nèi)外對無居民海島旅游的研究大部分都基于實證分析和案例解讀上,理論上的研究都不充分,對海島旅游實踐不成系統(tǒng),思路局限于各關(guān)聯(lián)節(jié)點上,對于無居民海島協(xié)同發(fā)展的闡釋還是空白。
(二)協(xié)同理論與旅游應用
協(xié)同理論,又稱協(xié)同論或協(xié)同學,是1971年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哈肯教授提出的,成為20世紀70年代在多學科研究基礎上新興的一門學科。協(xié)同理論主要研究非平衡態(tài)系統(tǒng)與外界置換過程中,自身借助內(nèi)部協(xié)同作用,形成時間、空間和功能上的有序。重點在于任何系統(tǒng)都是由子系統(tǒng)構(gòu)成的一種有序運行結(jié)構(gòu),各子系統(tǒng)雖然功能上存在不同,但是在運行中都會通過內(nèi)部整合,形成有序運行的一般規(guī)律。協(xié)同理論以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突變論為基礎,并兼容結(jié)構(gòu)耗散理論,通過動力學和系統(tǒng)學結(jié)合方法,提出多維相空間理論,建立一整套的數(shù)學模型和處理系統(tǒng),描述各種關(guān)聯(lián)和結(jié)構(gòu)從無序到有序的規(guī)律。協(xié)同理論模型的建立旨在引導簡單視角觀察和闡釋復雜系統(tǒng)和結(jié)構(gòu),以發(fā)現(xiàn)相互影響和相互協(xié)作的各關(guān)聯(lián)環(huán)節(jié)間的統(tǒng)一。
協(xié)同理論主要內(nèi)容包括協(xié)同效應、伺服原理和自組織原理。運用協(xié)同理論相關(guān)內(nèi)容,通過開放系統(tǒng)中各子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而產(chǎn)生的整體效應,引導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的有序發(fā)展。對于無居民海島旅游而言,雖然由政府主導,其間也存在自組織的模型,因此運用協(xié)同理論處理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戰(zhàn)略發(fā)展問題,會引起有序良性的連帶反應,對合理開發(fā)、有效利用和科學管理資源體系勢必會起到積極的意義。
二、無居民海島旅游發(fā)展思路
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是前提。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系統(tǒng)包括政府主體和旅游產(chǎn)業(yè)鏈上的企業(yè)、服務企業(yè)機構(gòu)、旅游者以及環(huán)境要素,其中各子系統(tǒng)之間互為依托,相互作用,同時又相互制約和影響。依照協(xié)同理論的技術(shù)模型,必然會形成有序運行的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反射出強大的整體性功效[1]。
1.旅游產(chǎn)業(yè)鏈上企業(yè)間協(xié)同
旅游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運行過程中,依據(jù)經(jīng)濟指標導向,構(gòu)成其核心環(huán)節(jié):資源整合、產(chǎn)品設計、產(chǎn)品生產(chǎn)、產(chǎn)品流動。前三個環(huán)節(jié)的企業(yè)間協(xié)同配合,實現(xiàn)第四個環(huán)節(jié)的共贏是當下市場競爭格局的整體性運行趨勢,而且已產(chǎn)生巨大市場反映。企業(yè)間的協(xié)同是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的基礎,為后續(xù)的結(jié)構(gòu)和層級奠定堅實的基礎。
2.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系統(tǒng)間協(xié)同
旅游開發(fā)商、政府、服務機構(gòu)、科研教育機構(gòu)、供應商、市場推廣機構(gòu)以及勞務市場之間的有序協(xié)同,成為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系統(tǒng)的核心環(huán)節(jié)。各項評估指標和運行指標的結(jié)構(gòu)化和生態(tài)化,對于系統(tǒng)的運行和生命力的延伸都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3.無居民海島旅游系統(tǒng)與環(huán)境的置換協(xié)同
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是在宏觀規(guī)劃前提下,系統(tǒng)內(nèi)各層次要素之間,各子系統(tǒng)間的作用和配置,在競合效應模式下,彼此支持和包容,形成共贏格局。無居民海島旅游系統(tǒng)的建設與持續(xù)發(fā)展,在輸入與輸出環(huán)節(jié)的生態(tài)指數(shù)需要控制標準,通過指標測控協(xié)同發(fā)展,使無居民海島持續(xù)發(fā)展,保持穩(wěn)健、良性、有序的推進旅游系統(tǒng)的內(nèi)外置換生態(tài)化,從而實現(xiàn)收益最大化的戰(zhàn)略目標[2]。
三、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策略
(一)海南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障礙
1.缺乏戰(zhàn)略指導,不均衡發(fā)展
海南省剛剛進入戰(zhàn)略發(fā)展實質(zhì)階段,積累不夠充分,導致目前基礎設施相對不足,資金、設備、交通相關(guān)環(huán)節(jié)尚在完善之中,這直接導致海島旅游開發(fā)的基礎和前提存在缺陷。對于無居民海島規(guī)劃雖然已提到戰(zhàn)略高度,但技術(shù)路線仍模糊,整體性協(xié)同水平較低。
2.旅游產(chǎn)品同質(zhì),無創(chuàng)新表現(xiàn)
目前海南省旅游業(yè)發(fā)展進入瓶頸階段,產(chǎn)品單一,市場格局混亂,形成低價格、無品質(zhì)產(chǎn)品運行范式,低價競爭、惡性競爭和負向競爭導致市場惡化,雖然政府在積極主導,但企業(yè)間缺乏協(xié)同,產(chǎn)品沒有形成吸引力和市場競爭力。
3.協(xié)同規(guī)劃缺失,制度不規(guī)范
目前,海南省旅游業(yè)集群發(fā)展模式在重點推進,但由于規(guī)劃不充分,將集群效應弱化,旅游、海島旅游、無居民海島旅游發(fā)展未能得到合理保障,出現(xiàn)較大的資源浪費,大部分旅游企業(yè)和旅游集群發(fā)展無總體規(guī)劃導向,景區(qū)和產(chǎn)品詳細規(guī)劃甚至偏離和違背了總體規(guī)劃要求,開發(fā)商和投資商受發(fā)展戰(zhàn)略和資金的影響,規(guī)劃設計標準偏低,背離了集約的戰(zhàn)略主旨。配套運行制度系統(tǒng)未能體現(xiàn)功能,各環(huán)節(jié)各自為戰(zhàn)、自相殘殺時有發(fā)生,導致系統(tǒng)運行低效。
4.利益分享機制尚未形成
惡性競爭勢必造成無序后果,為求得生存,旅游產(chǎn)業(yè)鏈上的企業(yè)彼此傾軋,低價競爭泥潭深陷,服務質(zhì)量無法保證,旅游者利益受損,協(xié)同無從談及。因此,對于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來說,利益相關(guān)者的協(xié)調(diào)是基本保障。在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過程中,由于對政府、企業(yè)、旅游者和環(huán)境的相互協(xié)作關(guān)注不高,未充分考量利益相關(guān)問題,因此不能形成良性利益分享機制,也就無法促進旅游業(yè)系統(tǒng)協(xié)同運行[3]。
(二)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對策
1.政府主導,戰(zhàn)略規(guī)劃,縣域協(xié)作
充分發(fā)揮政府職能,統(tǒng)一進行宏觀調(diào)控和科學指導,搭建經(jīng)濟運行平臺,使得企業(yè)通過平臺進行微觀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和處理,由政府戰(zhàn)略規(guī)劃的導向,進行無居民海島旅游區(qū)域協(xié)同發(fā)展格局。
海南省進行無居民海島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需要關(guān)注目前海口、三亞、萬寧等地市的資源結(jié)構(gòu)和產(chǎn)品形態(tài),充分考量三地的旅游業(yè)發(fā)展狀態(tài),評估指標,形成標準,戰(zhàn)略規(guī)劃,合理布控,系統(tǒng)發(fā)展,協(xié)調(diào)運行,以保證海南省旅游產(chǎn)業(yè)格局的生態(tài)結(jié)構(gòu)。同時,將三亞市的東鑼島、西鼓島、蜈支洲島、小青洲四島與大東海區(qū)、三亞灣區(qū)、海棠灣區(qū)、亞龍灣區(qū)四區(qū)進行合理設計,以促進陸地旅游、海島旅游和無居民海島旅游的陸海聯(lián)動發(fā)展效應;將萬寧的加井島、洲仔島兩島與三亞市現(xiàn)有的旅游資源和產(chǎn)品進行整合,并注意生態(tài)效應,與中遠期產(chǎn)品設計進行配套,以保證海南省旅游業(yè)的整體性運行機制和性能長效,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endprint
2.利益相關(guān)者分配協(xié)調(diào),強化動力系統(tǒng)
政府宏觀規(guī)劃,細化區(qū)域運行模型,強化總體規(guī)劃的導向能力,分解各詳細規(guī)劃的指標,保證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同時注重產(chǎn)業(yè)內(nèi)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互動和配合,保證市場運營收益效果。
可以借鑒馬爾代夫的“一島一店”模式、廣東省橫琴島的“俱樂部”模式、三亞市西島的“海上游樂世界”模式以及舟山群島、放雞島成功開發(fā)模式,注重生態(tài)旅游交通、旅游參與性項目、生態(tài)景觀系統(tǒng),細化系統(tǒng)規(guī)劃、宣傳跟進、有序開發(fā)和強化管理,通過科學發(fā)展和銳意變革,以創(chuàng)新求發(fā)展,以結(jié)構(gòu)保穩(wěn)定,保證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分配相對合理,子系統(tǒng)的協(xié)調(diào)和有序自然會提升競爭能力,實現(xiàn)海南旅游業(yè)發(fā)展和國際旅游島建設的需要。
3.塑造品牌,文化引導,強化內(nèi)生系統(tǒng)
品牌的形成意義重大,增加產(chǎn)品的附加值,構(gòu)成市場的沖擊效應和競爭能力,產(chǎn)業(yè)格局的內(nèi)在動力機制問題也會得到強化。需要海南旅游產(chǎn)業(yè)內(nèi)子系統(tǒng)間更為有效的協(xié)同,彼此相互支撐和包容,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引導下,系統(tǒng)搭建塑造品牌的文化效應。
海南是中國最南端的省份,擁有的資源極大豐富。海南省旅游產(chǎn)業(yè)要協(xié)同發(fā)展,以無居民海島聯(lián)動旅游效應,突破瓶頸,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型與變革,完成升級程序,重塑海南作為旅游目的地的消費心理影響。海南的旅游業(yè)轉(zhuǎn)型與升級、打造國際旅游島、實現(xiàn)黃金海岸的戰(zhàn)略目標,都會得到耦合驅(qū)動效應。
4.生態(tài)環(huán)境模式整體性協(xié)同,強化聯(lián)動系統(tǒng)
開發(fā)無居民海島,對環(huán)境影響務必降低到最小。自然和人文資源是先輩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需要我們精心呵護。要將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約束在自然承受能力范圍內(nèi),將海島建設約束在生態(tài)系統(tǒng)承受的范圍內(nèi),將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和設計約束在旅游者可接受的范圍內(nèi)。同時,關(guān)注、加大投入力度,保證設施設備的應用、淡水資源的補給、(海上)交通環(huán)境的改善、排污(廢)能力的提升、基礎服務的配備、社會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等等,以生態(tài)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為視角,以協(xié)同機制為戰(zhàn)略指導,合理規(guī)劃,生態(tài)開發(fā),保證收益,通過產(chǎn)業(yè)融合,形成產(chǎn)業(yè)集聚,形成海南省旅游業(yè)發(fā)展格局的整體性協(xié)同。
四、 結(jié)論
通過對于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模式和發(fā)展策略的分析,探索性提出相應的發(fā)展策略,以協(xié)同理論為依托,引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各子系統(tǒng)間的有序運行,實現(xiàn)共贏局面,對于國際旅游島建設、海南旅游品牌和文化的形成意義重大。同時,在陸地旅游、有居民海島旅游和無居民海島旅游之間,構(gòu)筑聯(lián)動開發(fā)效應,補充了無居民海島協(xié)同發(fā)展模式的空白。海南省旅游業(yè)整體性協(xié)同發(fā)展,有助于國際旅游島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與升級,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進而深化無居民海島旅游的深層次開發(fā)及戰(zhàn)略影響。
參考文獻:
[1] 徐海軍,等.海島旅游研究新進展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的啟示[J].旅游學刊,2011,(4).
[2] 馬麗娜.論我國無人島嶼旅游資源的開發(fā)與保護[J].商業(yè)經(jīng)濟與管理,2009,(2).
[3] 羅美雪,等.福建省無居民海島開發(fā)利用現(xiàn)狀及存在問題[J].臺灣海峽,2007,(5).
[責任編輯 杜 娟]endprint
2.利益相關(guān)者分配協(xié)調(diào),強化動力系統(tǒng)
政府宏觀規(guī)劃,細化區(qū)域運行模型,強化總體規(guī)劃的導向能力,分解各詳細規(guī)劃的指標,保證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同時注重產(chǎn)業(yè)內(nèi)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互動和配合,保證市場運營收益效果。
可以借鑒馬爾代夫的“一島一店”模式、廣東省橫琴島的“俱樂部”模式、三亞市西島的“海上游樂世界”模式以及舟山群島、放雞島成功開發(fā)模式,注重生態(tài)旅游交通、旅游參與性項目、生態(tài)景觀系統(tǒng),細化系統(tǒng)規(guī)劃、宣傳跟進、有序開發(fā)和強化管理,通過科學發(fā)展和銳意變革,以創(chuàng)新求發(fā)展,以結(jié)構(gòu)保穩(wěn)定,保證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分配相對合理,子系統(tǒng)的協(xié)調(diào)和有序自然會提升競爭能力,實現(xiàn)海南旅游業(yè)發(fā)展和國際旅游島建設的需要。
3.塑造品牌,文化引導,強化內(nèi)生系統(tǒng)
品牌的形成意義重大,增加產(chǎn)品的附加值,構(gòu)成市場的沖擊效應和競爭能力,產(chǎn)業(yè)格局的內(nèi)在動力機制問題也會得到強化。需要海南旅游產(chǎn)業(yè)內(nèi)子系統(tǒng)間更為有效的協(xié)同,彼此相互支撐和包容,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引導下,系統(tǒng)搭建塑造品牌的文化效應。
海南是中國最南端的省份,擁有的資源極大豐富。海南省旅游產(chǎn)業(yè)要協(xié)同發(fā)展,以無居民海島聯(lián)動旅游效應,突破瓶頸,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型與變革,完成升級程序,重塑海南作為旅游目的地的消費心理影響。海南的旅游業(yè)轉(zhuǎn)型與升級、打造國際旅游島、實現(xiàn)黃金海岸的戰(zhàn)略目標,都會得到耦合驅(qū)動效應。
4.生態(tài)環(huán)境模式整體性協(xié)同,強化聯(lián)動系統(tǒng)
開發(fā)無居民海島,對環(huán)境影響務必降低到最小。自然和人文資源是先輩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需要我們精心呵護。要將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約束在自然承受能力范圍內(nèi),將海島建設約束在生態(tài)系統(tǒng)承受的范圍內(nèi),將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和設計約束在旅游者可接受的范圍內(nèi)。同時,關(guān)注、加大投入力度,保證設施設備的應用、淡水資源的補給、(海上)交通環(huán)境的改善、排污(廢)能力的提升、基礎服務的配備、社會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等等,以生態(tài)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為視角,以協(xié)同機制為戰(zhàn)略指導,合理規(guī)劃,生態(tài)開發(fā),保證收益,通過產(chǎn)業(yè)融合,形成產(chǎn)業(yè)集聚,形成海南省旅游業(yè)發(fā)展格局的整體性協(xié)同。
四、 結(jié)論
通過對于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模式和發(fā)展策略的分析,探索性提出相應的發(fā)展策略,以協(xié)同理論為依托,引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各子系統(tǒng)間的有序運行,實現(xiàn)共贏局面,對于國際旅游島建設、海南旅游品牌和文化的形成意義重大。同時,在陸地旅游、有居民海島旅游和無居民海島旅游之間,構(gòu)筑聯(lián)動開發(fā)效應,補充了無居民海島協(xié)同發(fā)展模式的空白。海南省旅游業(yè)整體性協(xié)同發(fā)展,有助于國際旅游島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與升級,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進而深化無居民海島旅游的深層次開發(fā)及戰(zhàn)略影響。
參考文獻:
[1] 徐海軍,等.海島旅游研究新進展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的啟示[J].旅游學刊,2011,(4).
[2] 馬麗娜.論我國無人島嶼旅游資源的開發(fā)與保護[J].商業(yè)經(jīng)濟與管理,2009,(2).
[3] 羅美雪,等.福建省無居民海島開發(fā)利用現(xiàn)狀及存在問題[J].臺灣海峽,2007,(5).
[責任編輯 杜 娟]endprint
2.利益相關(guān)者分配協(xié)調(diào),強化動力系統(tǒng)
政府宏觀規(guī)劃,細化區(qū)域運行模型,強化總體規(guī)劃的導向能力,分解各詳細規(guī)劃的指標,保證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同時注重產(chǎn)業(yè)內(nèi)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互動和配合,保證市場運營收益效果。
可以借鑒馬爾代夫的“一島一店”模式、廣東省橫琴島的“俱樂部”模式、三亞市西島的“海上游樂世界”模式以及舟山群島、放雞島成功開發(fā)模式,注重生態(tài)旅游交通、旅游參與性項目、生態(tài)景觀系統(tǒng),細化系統(tǒng)規(guī)劃、宣傳跟進、有序開發(fā)和強化管理,通過科學發(fā)展和銳意變革,以創(chuàng)新求發(fā)展,以結(jié)構(gòu)保穩(wěn)定,保證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分配相對合理,子系統(tǒng)的協(xié)調(diào)和有序自然會提升競爭能力,實現(xiàn)海南旅游業(yè)發(fā)展和國際旅游島建設的需要。
3.塑造品牌,文化引導,強化內(nèi)生系統(tǒng)
品牌的形成意義重大,增加產(chǎn)品的附加值,構(gòu)成市場的沖擊效應和競爭能力,產(chǎn)業(yè)格局的內(nèi)在動力機制問題也會得到強化。需要海南旅游產(chǎn)業(yè)內(nèi)子系統(tǒng)間更為有效的協(xié)同,彼此相互支撐和包容,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引導下,系統(tǒng)搭建塑造品牌的文化效應。
海南是中國最南端的省份,擁有的資源極大豐富。海南省旅游產(chǎn)業(yè)要協(xié)同發(fā)展,以無居民海島聯(lián)動旅游效應,突破瓶頸,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型與變革,完成升級程序,重塑海南作為旅游目的地的消費心理影響。海南的旅游業(yè)轉(zhuǎn)型與升級、打造國際旅游島、實現(xiàn)黃金海岸的戰(zhàn)略目標,都會得到耦合驅(qū)動效應。
4.生態(tài)環(huán)境模式整體性協(xié)同,強化聯(lián)動系統(tǒng)
開發(fā)無居民海島,對環(huán)境影響務必降低到最小。自然和人文資源是先輩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需要我們精心呵護。要將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約束在自然承受能力范圍內(nèi),將海島建設約束在生態(tài)系統(tǒng)承受的范圍內(nèi),將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和設計約束在旅游者可接受的范圍內(nèi)。同時,關(guān)注、加大投入力度,保證設施設備的應用、淡水資源的補給、(海上)交通環(huán)境的改善、排污(廢)能力的提升、基礎服務的配備、社會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等等,以生態(tài)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為視角,以協(xié)同機制為戰(zhàn)略指導,合理規(guī)劃,生態(tài)開發(fā),保證收益,通過產(chǎn)業(yè)融合,形成產(chǎn)業(yè)集聚,形成海南省旅游業(yè)發(fā)展格局的整體性協(xié)同。
四、 結(jié)論
通過對于海南省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模式和發(fā)展策略的分析,探索性提出相應的發(fā)展策略,以協(xié)同理論為依托,引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各子系統(tǒng)間的有序運行,實現(xiàn)共贏局面,對于國際旅游島建設、海南旅游品牌和文化的形成意義重大。同時,在陸地旅游、有居民海島旅游和無居民海島旅游之間,構(gòu)筑聯(lián)動開發(fā)效應,補充了無居民海島協(xié)同發(fā)展模式的空白。海南省旅游業(yè)整體性協(xié)同發(fā)展,有助于國際旅游島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與升級,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進而深化無居民海島旅游的深層次開發(fā)及戰(zhàn)略影響。
參考文獻:
[1] 徐海軍,等.海島旅游研究新進展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的啟示[J].旅游學刊,2011,(4).
[2] 馬麗娜.論我國無人島嶼旅游資源的開發(fā)與保護[J].商業(yè)經(jīng)濟與管理,2009,(2).
[3] 羅美雪,等.福建省無居民海島開發(fā)利用現(xiàn)狀及存在問題[J].臺灣海峽,2007,(5).
[責任編輯 杜 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