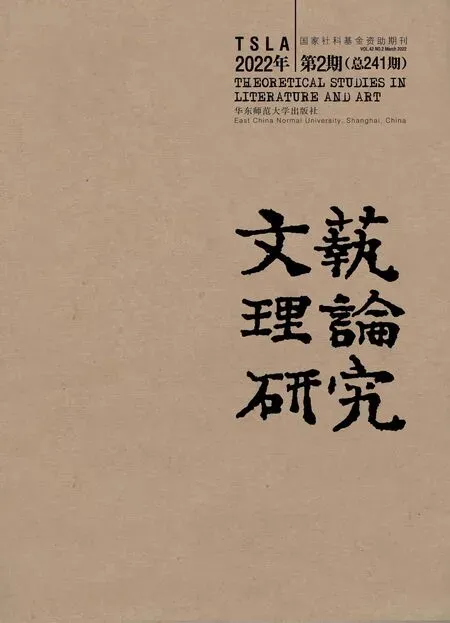審美主義的政治倫理: 王國維早期詩學和思想中的“美”與“德”
蔣浩偉
王國維在早期的文章中對康德、席勒和叔本華等人的思想進行了大量的譯介和運用。這些實踐不僅集中于美學領域,還關系教育學和倫理學的內容。在不同時期,王國維對這些觀點使用和發揮的側重點是不盡相同的。除了對非功利、非政治的審美主義的重視之外,王國維早期的詩學和思想還包涵著中國傳統政治道德的內涵。以往的學者也注意到王國維思想與“儒家心性”的聯系(許宏香194),或認為其詩學呈現了“儒家思想面相”(劉鋒杰152)。但這一儒家心性或面相并不僅限于單純的道德修養方面,還關切到王國維內在整體的思想和價值結構。對于此價值結構的揭示,將有助于加深理解王國維詩學和思想的內涵,并把握其前后期思想學術變化的內在線索。
一、 對群體的重視: 早期論教育文章中的德與美之關系初見
王國維早期的文章以論述國民教育為主。于1903年8月刊登在《教育世界》上的《論教育之宗旨》一文中,王國維把教育分為智育、德育和美育三個方面。在論述德育時,王國維說:“故古今東西之教育,無不以道德為中心點。蓋人之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與福祉實有不可離之關系。”(《王國維全集》第14卷11)這與康德所謂的“至善”需要以幸福相配是一致的。而在論述美育時說:“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發達以達完美之域,一面又為德育與智育之手段。”(11)這則與席勒以審美世界為最完美的,而“美育”為道德世界與自然世界的過渡的觀點相似。
不過,王國維雖然提倡康德、席勒等人的思想,但對他們觀點的擇取各不相同,這在隨后1904年2月刊登的《孔子之美育主義》中尤其明顯:
夫豈獨天然之美而已,人工之美亦有之。宮觀之瑰杰,雕刻之優美雄麗,圖畫之簡淡沖遠,詩歌、音樂之直訴人之肺腑,皆使人達于無欲之境界。故泰西自雅里大德勒以后,皆以美育為德育之助。至近世,謔夫志培利、赫啟孫等皆從之。乃德意志之大詩人希爾列爾出,而大成其說,謂:“人日與美相接,則其感情日益高,而暴慢鄙倍之心自益遠,故美術者,科學與道德之生產地也。”又謂:“審美之境界,乃不關利害之境界,故氣質之欲滅,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審美之境界,乃物質之境界與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物質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勢力;于審美之境界,則遠離之;于道德之境界,則統御之。”(希氏《論人類美育之書簡》。)由上所說,則審美之位置,猶居于道德之次。然希氏后日更進而說美之無上之價值,曰:“如人必以道德之欲克制氣質之欲,則人性之兩部猶未能調和也。于物質之境界及道德之境界中,人性之一部必克制之,以擴充其他部。然人之所以為人,在息此內界之爭斗,而使卑劣之感躋于高尚之感覺,如汗德之《嚴肅論》中,氣質與義務對立,猶非道德上最高之理想也。最高之理想存于美麗之心(Beautiful Soul),其為性質也,高尚純潔,不知有內界之爭斗,而唯樂于守道德之法則,此性質唯可由美育得之。”(芬特爾朋《哲學史》第六百頁。)此希氏最后之說也。顧無論美之與善其位置孰為高下,而美育與德育之不可離,昭昭然矣。(《王國維全集》第14卷15—16)
這一段內容主要取自文德爾班(芬特爾朋)的《哲學史教程》(文德爾班827—828),主要有兩個觀點: 一是美與善高低難分,二是美育與德育不可分離,且美育有助于德育。而接下來在對孔子“始于美育,終于美育”的論點舉了諸多例證后(《王國維全集》第14卷16),王國維對孔子的美育觀進行了發揮:
之人也,之境也,固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光風霽月不足以喻其明,泰山華岳不足以語其高,南溟渤澥不足以比其大。邵子所謂“反觀”者非歟?叔本華所謂“無欲之我”、希爾列爾所謂“美麗之心”者非歟?此時之境界,無希望,無恐怖,無內界之爭斗,無利無害,無人無我,不隨繩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則。一人如此,則優入圣域;社會如此,則成華胥之國。孔子所謂“安而行之”,與希爾列爾所謂“樂于守道德之法則”者,舍美育無由矣。(《王國維全集》第14卷17—18)
王國維介紹叔本華的“無欲之我”時曾說到:“無欲,故無空乏,無希望,無恐怖,其視外物也,不以為與我有利害之關系,而但視為純粹之外物。”(《王國維全集》第14卷14)可見,王國維對此“境界”的理解具體來自叔本華。不過,在叔本華的哲學中,美與德雖同是對意志的解脫之道,卻大不相同。王國維在同年發表的《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中對此說道:“且美之對吾人也,僅一時之救濟,而非永遠之救濟。此其倫理學上之拒絕意志之說,所以不得已也。”(《王國維全集》第1卷40)從叔本華的哲學體系來說,天才對美的直觀屬于表象的層面,而宗教和道德倫理則屬于意志的層面,兩者并沒有王國維所說的“皆以美育為德育之助”。所以,當王國維具體闡述美與德,美育與德育之間關系的時候,就只是借用了康德和席勒的觀點。王國維的觀念雖然是對文德爾班的轉述,但基本涵蓋了康德和席勒觀點的核心和差異。在康德的體系中,美不過是道德的象征,審美判斷力只是為了銜接純粹理性過渡到實踐理性的橋梁。而與此相比,席勒雖也強調美的橋梁作用,但認為所謂“美麗之心”有超出道德和自然世界的地位。所以,王國維說:“顧無論美之與善其位置孰為高下,而美育與德育之不可離,昭昭然矣。”但對于王國維而言,美與善真的是不知高下嗎?
王國維說孔子“始于美育,終于美育”看起來是更加重視“美”本身,但之后他又說“此時之境界”“不隨繩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則”,“孔子所謂‘安而行之’,與希爾列爾所謂‘樂于守道德之法則’者,舍美育無由矣”。可見王國維雖強調美育的重要,但最后邏輯的歸宿點不是叔本華的“無欲之我”,而是更類似席勒的“美麗之心”向“德育”之“道德法則”的通達。而在此文章的結尾,王國維以更加強烈的語氣重申了“美育”對于國內美術、學業發展的重要性,認為國內萬事皆求有用無用的功利態度,“故一切美術皆不能達完全之域”(《王國維全集》第14卷18),“以我國人審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則其朝夕營營,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庸詎知吾國所尊為大圣者,其教育固異于彼賤儒之所為乎?故備舉孔子美育之說,且詮其所以然之理,世之言教育者,可以觀焉”(18)。從他如此重視美育的社會功用而言,王國維的觀點則與康德、叔本華和席勒等人都拉開了距離。如果說,王國維重視美育和德育之間的遞進關系而撇開了叔本華,那么在轉向席勒的審美境界去溝通道德境界時,則又因為側重道德境界而偏向了康德。
因而,《孔子之美育主義》這篇文章中有著雙重的意義與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王國維非常重視美育,認為孔子“始于美育,終于美育”,但另一方面其邏輯落腳點仍將個體之美育引向群體之德育,也就在更大的邏輯框架中把美育引向了更為現實的道德層面。這兩個層面有時并不協調,又因為兩者各自概念的界限不夠清晰明確,容易導致混淆,并一直延續在王國維此后的諸多文章中。
如在同時期的《教育偶感四則》一文中,王國維更加充分地表達了他對國民素質和教育實踐的不滿和構想,其語氣和措辭更加強烈。在文中,王國維認為我國本土之文學、宗教和美術只注重一時之物質價值,而不如西方重視精神文化價值,“則夫蚩蚩之氓,除飲食男女外,非鴉片、賭博之歸而奚歸乎?故我國人之嗜鴉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與西人之細腰、中人之纏足有美學的必然性無以異”(《王國維全集》第1卷139)。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王國維把國人嗜吸鴉片看作是精神心理固有的劣根性表征,而之所以大為提倡文學、美術為主的美育也是有著頗為直接的目的,不是如康德和席勒等人是為了個體精神之啟蒙和自由,而更多著重的是對下層社會群體精神的改造。正如他在1904年執教于江蘇師范學堂的授課講義《教育學》中認為,除了知識、情感、意志種種之現象需要教育之外,“道德者,人之所以為人之要點,教育之力,不可不專注于此,而視為最高之目的”(《王國維全集》第1卷161),“再細察教育之目的。即離人類一般之目的,而自特別之事情觀之。第一,不可不考本國之國體及歷史,而以養成適于國體之良國民為目的(161)”。可見在王國維的心中,道德教育才是教育的根本,而又需特別關注本國國體和歷史。這樣的觀念明顯與康德、席勒等人觀點的內涵和指向相去甚遠。
二、 缺席的上帝: 王國維對西方道德觀念的轉義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1904年上半年開始連載在《教育世界》雜志的,因為其時間與前期論教育的文章相近,仍保留了許多前期論美育促進德育的內容。如在討論《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時,王國維說:“自上章觀之,《紅樓夢》者,悲劇中之悲劇也。其美學上之價值,即存乎此。然使無倫理學上之價值以繼之,則其于美術上之價值尚未可知也。”(《王國維全集》第1卷69)
與此同時期,王國維在《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叔本華哲學的主要內容和特征,認為:“彼之哲學,如上文所述,既以直觀為唯一之根據矣,故其教育學之議論,亦皆以直觀為本。”(《王國維全集》第1卷45)“由此觀之,則叔氏之教育主義,全與其哲學上之方法同,無往而非直觀主義也。”(53)在王國維看來,直觀是叔本華的核心觀點,也是連接美育與德育的中心。但實際上,這并非叔本華觀點的完整表述。
在叔本華看來,對美的直觀與圣人的道德實踐相比,只能帶來一瞬的幸福,而絕非永遠平靜下來:
這時我們可不能以為生命意志的否定,一旦由于那已成為清靜劑的認識而出現了就不會再動搖,人們就可在這上面,猶如在經營得來的財產上一樣高枕無憂了。應該說,生命意志的否定是必須以不斷的斗爭時時重新來爭取的。[……]因此,我們看到圣者們的內心生活史都充滿心靈的斗爭,充滿從天惠方面來的責難和遺棄;而天惠就是使一切動機失去作用的認識方式,作為總的清靜劑而鎮住一切欲求,給人最深的安寧敞開那條自由之門的認識方式。(叔本華536—537)
叔本華的圣人更多指的是宗教人士,而所謂的“天惠”“就是阿斯穆斯對之驚異而稱之為羅馬正教的,超絕的轉變的東西。這也正是在基督教教會里很恰當的被稱為再生的東西,而這所由產生的認識也就是那被稱為‘天惠之功’的東西”(叔本華553)。更具體而言,指的就是“教義又在人化的上帝身上找到了天惠的,意志之否定的,解脫的象征”(555)。上節談到王國維注意到叔本華的“美”只是“一時之救濟”,但這不斷與意志斗爭的圣人道德實踐在王國維的筆下卻是缺席的。
無獨有偶,對于王國維看重的康德來說,其道德概念雖然來自實踐理性的先天立法,但同樣與上帝脫不開關系:
道德原理只有在預設一個具有最高完善性的世界創造者的前提下才允許這一概念是可能的。[……]所以上帝概念是一個從起源上就不屬于物理學的、亦即不是對思辨理性而言的概念,而是一個屬于道德學的概念。(康德191—192)
對此,1906年刊登在《教育世界》上被佛雛考證為王國維的未署名文章《汗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中同樣注意到此點:“彼于實踐理性中往往預想個人之靈魂不死,而視為道德之條件,又說與我相離之上帝之存在,而視為道德之秩序及善人之勝利之保證。[……]夫說道德者自不得不導入于宗教。何則?最高之善乃道德上必然之理想,而此理想,唯由上帝之觀念,決不能為道德之動機故也。”(《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169—170)但這篇未署名的文章帶有“自編撰”(包括撰述、節譯與綜編)的性質(佛雛,《〈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序言》4—11),可能不是王國維的觀點。但在同年6月刊登的《原命》中,王國維同樣認為康德的實踐理性不出因果關系之外,而所謂的自由“在我而不在外物”“大不然者也”(《王國維全集》第14卷61—62),因為“吾人所以從理性之命令,而離身體上之沖動而獨立者,必有種種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現在,必存于過去;不存于個人精神,必存于民族之精神”(62)。可見,王國維對康德這一宗教道德的自由喻示同樣毫無在意,并認為實踐理性或自由僅僅是在個人精神與民族精神之間的事物。
同樣,王國維所在意的席勒也不時充滿了對作為“絕對存在”的上帝的敬重和期望:“我們知道,人的意志所作的規定永遠是偶然的,只有在絕對存在那里物質的必然和道德的必然才能是吻合的。”(席勒218)此外,他還認為:“人在他的人格中無可否認地帶有這種趨向神性的天稟。”(264)而對于人所謂的理性和感性存在如何統一和諧時,席勒又說:“如果我們設想,這兩項任務都盡善盡美地完成了,那就又回到了我原來的出發點上,即關于神性的概念上。”(265)
總之,在康德、席勒和叔本華的哲學中,無論是以美,還是以德為中心,其背后都懸設了一位“絕對存在”或“神性”,而這通通為王國維所忽略。因而,王國維認為叔本華教育學和哲學的根本無非直觀主義,顯然是一種普遍性的誤解。
不僅如此,與美術相比,宗教還是更為低級的存在。在1906年7月刊登在《教育世界》的《去毒篇》一文中,王國維認為:“宗教之說,今世士大夫所斥為迷信者也。自知識上言之,則神之存在、靈魂之不滅,固無人得而證之,然亦不能證其反對之說。何則?以此等問題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故也。”(《王國維全集》第14卷65)這顯然與康德對上帝本體論證明的討論是一致的。但康德并未在此止步,而是于實踐理性的領域內為上帝找到了位置。王國維并沒有如此考量,而僅僅是把宗教當作慰藉下層蚩蚩之氓的“精神鴉片”:“宗教之所以不可廢者,以此故也。人茍無此希望,無此慰藉,則于勞苦之暇、厭倦之余,不歸于雅片,而又奚歸乎?余非不知今日之佛教已達腐敗之極點,而基督教之一部且以擴充勢力、干涉政治為事,然茍有本其教主度世之本意,而能造國民之希望與慰藉者,則其貢獻于國民之功績,雖吾儕之不信宗教者,亦固宜尸祝而社稷之者也。”(65)王國維雖然對宗教的世俗價值給予支持,但這種贊賞其實也是很有限的。相對于宗教而言,王國維對美術的評價則相對較高,認為“而雕刻、繪畫、音樂、文學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則所以慰藉彼者,世固無以過之。何則?吾人對宗教之興味存于未來,而對美術之興味存于現在,故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術之慰藉現實的也”(66)。
無論是對宗教的有限支持,還是對美術的贊賞,王國維在這篇文章里所強調的只是以宗教和美術去滿足和慰藉人在世之嗜好的欲望和痛苦。這與王國維1907年4月刊登在《教育世界》的《人間嗜好之研究》中對高等嗜好的“勢力之欲”的提倡有相通的一面(夏中義106—107),也可能是受到海甫定《心理學概論》的影響(佛雛,《王國維哲學譯稿研究》100),或是谷魯斯的“游戲說”的影響(羅鋼127),亦或是其自身對人生世界的“可愛”一面心有戚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無論王國維所接受的西方理論資源如何變化,康德、席勒和叔本華等人在美與善背后所預設的上帝的那層超越性存在領域在王國維這里至始至終都是被懸擱起來的。
這樣看似對“美”的重視卻引起一個更復雜的問題,即剝離了與個體精神信仰保持著緊密聯系的虛靈和超越的視域,王國維所謂的自足的美和道德法則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就只能在物質世界和道德世界,亦或身體生命的個人情感與群體的國家(民族)精神之間徘徊,也因而有時王國維筆下的“美”只能是“現在現實”而無理想之境地。因此,從上述文章可以看到的是,王國維筆下的“境界”“美”或“直觀主義”總是與現實社會國民群體的道德精神和教育相互關聯,要么如早期論教育文章中由康德、席勒的“美育至德育”逐漸演變成對國民群體性格和道德的強烈質疑和批評,要么由叔本華的“直觀主義”衍化成對個人心理嗜好的補償和滿足,只是一種面對現實世俗無聊痛苦的消遣手段,而絕無超越現實的理想意義了。
三、 審美主義的政治倫理: 王國維詩學與思想的內在價值結構
在1905年5月的《教育世界》上,王國維發表了一篇《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的文章。這篇文章被認為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追求無功利的、獨立自足的審美主義的先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則展現了王國維并沒有完全堅持這種美術獨立觀。
在1906年12月發表的《文學小言》上,王國維雖推崇真正的、非補綴、非文繡的文學,但又寫到:“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王國維全集》第14卷94)又說:“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94)在這里,王國維或許是延續了康德和席勒由美通向德的觀點,認為由高尚人格和德性可反通文學之偉大,因此不覺得“學問”“德性”與“文學者,游戲的事業也”相抵觸。
在1907年1月刊登在《教育世界》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王國又寫道:“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于當日之社會外。”(《王國維全集》第14卷99)在王國維看來:“屈子之自贊曰‘廉貞’,[……]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種之歐穆亞。”(101)王國維最后得出結論說:“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觀后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101—102)
在王國維眼中,屈原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正在于對楚國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偉大之人格”或“德性”。但王國維的理論顯然自我矛盾,因為陶淵明不能被看作“置于當日之社會中”,與社會國家“同累世之休戚”。更重要的是,雖然王國維使用高尚人格等詞匯表面上是借用康德實踐理性的意義,但一旦陷入中國的歷史和詩學對象之中,這些語匯的傳統意義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并逐漸壓縮其中的西學內涵,以至所謂的“德性”不自覺便回到了中國傳統中與家國政治聯系緊密的士大夫道德語境中。這就是王國維“德性”一詞非常含混,而又不自知的地方。正是在此“德性”含混的地方,顯示出了王國維的審美主義背后穩固地站著一個中國傳統政治道德的身影。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有“《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與“有形之社會制度”之論(《王國維全集》第20卷202)。但《白虎通》的“三綱六紀”雖屬“文化”,但不是絕對超越于政治的,其中的秉承于“天”的“陰陽五行”思想才勉強算是(葛兆光234—253)。以此角度來看,王國維對“德性”的理解不完全是基于陳寅恪所言超越政治之上的文化意義的,而是中國傳統中與家國政治緊密綁定的道德觀念。
王國維的這種“德性”政治觀念與席勒的道德國家觀有很大相似,這種相似可能只是平行的偶合。如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席勒認為,所謂道德國家的主要內容和形式是“每個個人按其天稟和規定在自己心中都有一個純粹的、理想的人,他生活的偉大任務,就是在他各種各樣的變換之中同這個理想的人的永不改變的一體性保持一致。這個在任何一個主體中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得到的純粹的人,是由國家所代表,而國家竭力以客觀的,可以說是標準的形式把各個主體的多樣性統一成一體”(席勒219)。這一說法形容王國維看起來也是比較合適的。王國維所謂的“德”并非只是個人道德品格而已,與之相配的最高形式還須由家國政治這一層面來賦予其意義。
可是,對于席勒而言,道德國家雖然是自然國家、審美國家的最終邏輯歸宿點,但其中倫理和法的權威相互壓迫,必須用審美來予以糾正,才能使人分裂的天性和諧一致。席勒認為:“在審美王國中,一切東西,甚至供使用的工具,都是自由的公民,他同最高貴者具有平等的權利;[……]在這里,即在審美的假象王國里,平等的理想得到實現。”(371—372)對于席勒對審美的這種烏托邦設想,哈貝馬斯評價道:“這些書簡成了現代性的審美批判的第一部綱領性文獻。席勒用康德哲學的概念來分析自身內部已經發生分裂的現代性,并設計了一套審美烏托邦,賦予了藝術一種全面的社會-革命作用。”(哈貝馬斯52)當然,席勒也認識到要建構起這樣一個審美的王國近乎理想,“而按照實際,就像純粹的教會或共和國一樣,人們大概只能在個別少數卓越出眾的人當中找到”。(席勒372)但這并不意味著席勒愿意妥協,因為“時代已經啟蒙,就是說,知識已經找到并已交給公眾,這些知識至少說足以能糾正我們的那些實際的原則”(243)。即使那些高雅的藝術理想難以實現,甚至難以被大眾所接受,但“作為已經經過啟蒙和高雅化以后的大眾情感的代言人”會通過自我情感的有效表達來促進下層大眾的進步(574)。在席勒眼中,這些卓越高雅的藝術或思想是人性中共通的東西。
不過,在王國維看來:“吾人之獎勵宗教,為下流社會言之,此由其性質及位置上有不得不如是者。何則?國家固不能令人人受高等之教育,即令能之,其如國民之智力不盡適何?若夫上流社會,則其知識既廣,其希望亦較多,故宗教之對彼,其勢力不能如對下流社會之大,而彼等之慰藉不得不求諸美術。”(《去毒篇》;《王國維全集》第14卷65—66)在上流社會和下流社會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知識阻礙,這知識被王國維理解為傳統意義上的“學問”和“修養”,因而只能配給上流社會的士大夫。進而言之,美術也主要是上流社會的慰藉品,因此席勒所謂“美”本身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倫理意義都全消失殆盡了。這一點絕非一些論者所認為的,王國維后期學術轉向的動機在于借由“古雅”通向席勒“美麗之心”的審美啟蒙動機,后者融合了席勒現代國民主體意識和儒家“無私心”的道德人格(馮慶32)。可以說,王國維無意中將西方哲學和美學中的“知、情、意”具體化為“學問-美術-德性(家國政治)”,并以“德性”為最高歸宿的價值結構,且這個結構只能囤于上流社會,而與下層人數更多的蚩蚩之氓不甚相關。

余 論
縱觀王國維早期的《孔子之美育主義》等文章,他對道家、儒家思想都有承襲,并不局限于對政治道德的重視。例如王國維對孔子教育所顯現的審美境界與邵雍“以物觀物”、叔本華“無欲之我”,以及席勒“美麗之心”之間的互相闡發等,雖不完全具備西方的“超越性”,但多少沾染了超越的色彩。這其中不僅僅是對西方審美觀念的接受,也有源自對孔子學說本身的認識,即個人的內在德性修養與外在宇宙萬物(“天”“道”)的相合,這或可視為中國文化中“內在超越”的體現。
不過,儒家的“內在超越”或“天人觀”大體可分為兩個雖有區別,又難以完全分離的方面,一是以子思、孟子、陸九淵、王陽明一脈的心性儒學,一是以荀子和董仲舒為代表的政治儒學(任劍濤39)。前者的“天人”注重人的內在修養為基底去感悟和順應天命,這個“天”往往只是形式上的,其價值先天依據在人的心性上(孟子的“性善論”),而后者的“天人”則偏靠人的道德和政治實踐,并不在心性上預設價值的先天依據,而往往只作經驗性的描述(荀子的“性惡論”),因此只能與社會政治制度相關聯,特別需要外在的禮樂制度去引導和規范人心(勞思光119—126、251—261)。
總體上來說,儒家上述兩種傾向都不是西方超越性的。不過,心性論因重心在人的內在,特別與西方近現代哲學和美學中的“主體”觀相接近,這也是新儒家偏好以康德的哲學來引渡儒學現代化的原因。王國維將孔子的美育觀與康德、叔本華和席勒的審美觀相聯系,也正是基于這個角度上的。王國維在早期的思想和詩學中主要偏重以儒家的心性論去接洽西方的審美主義,其中也有政治儒學的影子,而直到后期才逐漸將個人的德性修養關聯到政治道德上。換而言之,無論是前期的審美主義,還是后期的對政治道德的關注,都有儒家的德性觀作為基底。也正是由于這一德性基底,王國維由儒家心性論所關聯的西方審美主義轉移到儒家政治實踐論所關聯的政治道德才有了完整的內在邏輯和依據。
以上這兩者都可看作中國文化思想的“內在超越”,只是傾向不同,所引入的理論資源也不同,因此導向的結果和命運也不同。從儒學心性論的層面而言,王國維借此引入的是西方康德、叔本華和席勒的非功利審美觀,因此得以從孔子的德性教育觀念引發出審美主義,而從政治儒學層面而言,王國維借此關聯的多是在《教育世界》上刊登的日本學者儒學研究中對中國傳統道德政治的論述,因此在思想層面未能有實質性的突破,而在現實層面也隨著溥儀小朝廷的覆滅而全盤落空。兩種“內在超越”,兩種不同的命運。換而言之,中國文化的“超越性”不完全是一個事實性的存在,也難以依照某種單一的標準或某一時一地的成敗去判定優劣,但它一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不斷去激發和注入新的活力,才能真正的具備超越性。王國維的個案正提供了這樣一種雙重的歷史視野和經驗。
陳寅恪: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王國維全集》第20卷。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202—204。
[Chen, Yinke. “Elegy and Preface for Wang Guantang.”Vol.20.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2009.202-204.]
馮慶: 《從“古雅”到“美麗之心”——王國維學術轉向的審美啟蒙旨趣》,《文藝研究》1(2021): 32—44。
[Feng, Qing. “From ‘Classical Elegance’ to ‘Beautiful Soul’: The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Purport of Wang Guowei’s Academic Turn.”1(2021): 32-44.]
佛雛: 《王國維哲學譯稿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Fo Ch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
——: 《〈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序言》,《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佛雛校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1—27。
[- - -. Preface.’. Ed. Fo Ch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3.1-27.]
葛兆光: 《中國思想史》第1卷。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Ge, Zhaoguang.. Vol.1.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于爾根·哈貝馬斯: 《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4年。
[Habermas, Jürgen.. Trans. Cao Weido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伊曼努爾·康德: 《實踐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年。
[Kant, Immanuel.. Trans. Deng Xiaomang. Ed. Yang Zut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第1卷。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Lao, Siguang.Vol.1.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劉鋒杰: 《王國維“境界說”的儒家思想面相》,《學習與探索》1(2020): 152—160。
[Liu, Fengjie. “The Confucianist Outlook of Wang Guowei’s ‘Ching-Chieh’.”1(2020): 152-160.]
劉小楓: 《拯救與逍遙》。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Liu, Xiaof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羅鋼: 《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Luo, G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5.]
任劍濤: 《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 宗教信仰、道德信念與秩序問題》,《中國社會科學》7(2012): 26—46。
[Ren, Jiantao.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nscendence: Religious Beliefs, Moral Beliefs and Order.”7(2012): 26-46.]
約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馮·席勒: 《席勒經典美學文論》,范大燦、馮至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Trans. Fan Dacan and Feng Zh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亞瑟·叔本華: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沖白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2年。
[Schopenhauer, Arthur.. Trans. Shi Chong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王國維: 《王國維全集》。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Wang, Guowei.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2009.]
——: 《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佛雛校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
[- - -.’. Ed. Fo Ch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3.]
威廉·文德爾班: 《哲學史教程》下卷,羅達仁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3年。
[Windelband, Wilhelm.. Vol.2. Trans. Luo Dar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3.]
夏中義: 《王國維: 世紀苦魂》。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
[Xia, Zhongyi.:’.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許宏香: 《“尊德性”: 王國維美學思想與儒家心性傳統的價值關聯》,《社會科學輯刊》5(2015): 194—201。
[Xu, Hongxiang. “‘Advocating Virtue’: The Valu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Guowei’s Aesthetic Thought and Confucian Tradition of Mind.”5(2015): 194-201.]
余英時: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余英時文集》第3卷。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1—49。
[Yu, Ying-shih.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System.”-. Vol.3.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