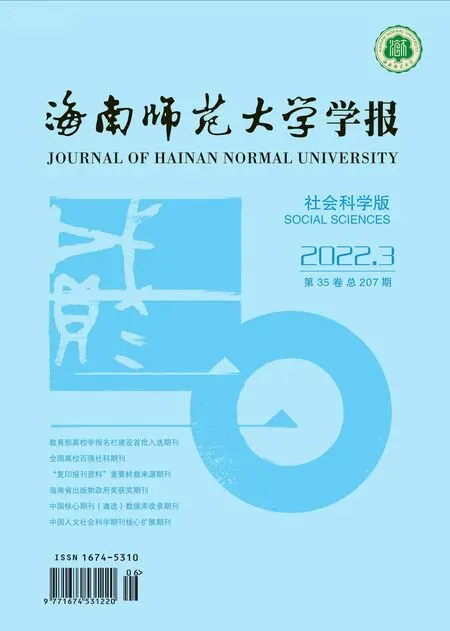以客家話閱讀馬來文:詞書編繤與民謠互譯探討
[新加坡]關瑞發
(英國歐亞高等研究院,倫敦,E16 1AH)
一、前言
中華民族自歷朝帆船航海南下到達馬來亞東岸的土地,商旅在登陸以后,不論要在當地停留,還是想沿著河道和山路走向半島的西岸,他們也都得停留接近半年,方能等到可以吹送帆船回航的季候風。(1)王琛發:《英殖以前彭亨華人歷史紀事》,檳城:韓江傳媒大學,2022年,第2-3頁。這樣一來,中華帆船停泊在當地港口,舟子商旅需上岸居留,或做買賣,或謀取其他生計,生活上總要和當地民眾溝通,學習當地的語言成為最大理由。所以在中華歷朝,都可能曾經有人為著暫居或長留南海諸邦,要解決貿易或異地生活的人際溝通,編寫過各種學習外語用詞的文本。
據宋代《諸蕃志》記載,中華民族那時積累的前人航海經驗,可以書中列舉的五十六個國家或地區為證;古人航行貿易的地點,分布于現在印支半島、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印度,以及遠至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地。(2)[宋]趙汝適撰,楊博文校譯,《諸蕃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27頁。因此,如果說,古人不懂南海各處古代馬來語言,也沒有一種教導和傳承的方式,是說不過去的。更進一步說,古代的航海事業,船上往往乘坐著由中國到南海諸邦求法的僧侶,或者從南海遠赴中國傳法的僧人,他們隨船往來,一路上從事注釋佛經,其中也包括把南海盛行的梵文詞匯翻譯匯整。這些貢獻,當然和現代的詞典編整,有類似的功用。現在重新閱讀這些同時留存在漢傳與日本《大藏經》的許多古代佛教經論,還能發現里頭的音譯梵文詞匯,有些已經演變成為現代馬來語的常用詞。只是,我們現在要尋找古人公開刊行或者方便自備的各種古代“詞典”類型的文獻,已經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清朝嘉慶年間梅州人謝清高少年時隨船航行,晚年居住在澳門靠翻譯為生,留下其口述的《海錄》一書,是一部很好的文字證據。謝清高書中提及各處地方的漢字名稱,以及使用其梅州客家話口音音譯一些馬來文字,稱呼各地的地名和人事。這說明了,不管歷朝海禁,只要民間有絡繹不絕的海上貿易存在,古代絲路沿線各族群互動及互通有無的生存共同體意識,也會依賴著文化和經貿交流作為載體兼推動力量,維系不絕。而語言的互相學習,學習方式的傳承,也就可能繼續下去。
此次撰寫本文,基于從華東南到南洋各地,出現過諸多外文詞典類的文獻,都是以閩南、潮州、廣州等地方言作為媒介語,發揮對譯解義馬來文字的作用。因此,本文決定將討論的內容相對集中在至今唯一可見其清末至民初版本流傳的《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一書,并探討其在廣州發行而后又在新加坡再版供應南洋市場,流行的數十年間,馬來亞客家語社群與馬來文化交流的一些片段。
而討論這本詞典和“客家-馬來”有過的文字互動,不能不重視其讀者群體——來自各地的客語方言社群。客家群體,曾經是清末民初的馬來亞許多地區的“開埠”主力,《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正是在這些地區和社群之間流傳。王琛發的《18—19 世紀南海諸邦客家人海上網絡的思考》,在“摘要”部分總結說:“至遲在18 世紀,客家人沿河海交通分布南海各地,以集體組織的形式開發農礦區并開展對外貿易,各地相互形成海上網絡,這是長期以來‘客家人開埠’說法流傳各地的淵源。各地不同籍貫的客家社會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依靠本籍貫或聯合其他籍貫的群體,以跨海跨境的聲氣相通和實力結盟相互支撐,并且體現為原來客家地區民眾祭祀組織的實踐,承載祖輩文化、禮俗與價值觀,轉化為當地民眾的社會經濟載體,演變出地方社會維持共同福利的公共組織,形成海洋客家的歷史面貌。”(3)王琛發:《18—19 世紀南海諸邦客家人海上網絡的思考》,《龍巖學報》第37卷第6期,2019年11月,第32頁。
二、漢字音譯馬來語詞典的貢獻和局限
古代以漢字翻譯和解說馬來詞匯的詞典,最為人熟知的年代最久文本,應是已故許云樵曾經研究的《滿剌加國譯語》。正如許多南洋研究學者所熟悉的,過去明清文獻常出現“滿剌加”國號,在現代馬來西亞學校課本是另有翻譯,名稱是“馬六甲王國”。而就歷史事實而言,自鄭和下西洋,滿剌加以最初的海港城邦,最后躍升為跨海大國,作為明朝設立官廠之地,也是艦隊集散貨物和駐留補給的所在;由此當然可以推斷,明朝出現“滿剌加國語譯語”,符合明朝的遠洋需要。許云樵譯作《滿剌加國譯語注》(4)許云樵《滿剌加國譯語注》,《南洋學報》第2卷第1集。1941年3月,第63-89頁。時,提及當時明王朝是為了外國交往日漸頻繁,命官設立“四夷館”,負責對外溝通翻譯事宜,并且編撰《各國夷語》(Ko Kwo Yi Yu)(5)許云樵《滿剌加國譯語注》,《南洋學報》第2卷第1集,1941年3月,第63頁。以處理語言溝通的必要。“滿剌加國”的語言,就是“馬六甲”的國語,就是那時當地流行的古代“馬來語”。
再根據楊貴誼的研究,現在流傳的《滿剌加國譯語》,源自明朝通事楊林嘉靖二十八年(1549)校訂的版本,全部只收納了482 個詞條,但已經是采用分類詞格式把詞條分屬17 類,可以視為漢語馬來文詞典最早雛形。此書特點,在于全書是馬來文用詞音譯為發音相近的漢字,再用漢字解說;而且,這其中許多詞條都牽涉宮廷用語,足以讓人懷疑最早版本是由馬六甲王國訪華人員提供,由明朝文人官吏處理書寫。此前百年,鄭和隨員留下多部文獻,詳細記錄南海各處地理位置、生產類屬,以及民情與風俗等。可見那時沒有太多語言障礙。反而在百余年前,這些方言對照馬來語詞典絡繹出現,可能反映華人各民系人口,自1870 年至1930 年間,來往和居住南洋者愈多,華馬日常溝通愈趨頻密。其中可考者包括《嗎黎話》(1847 年)、《通夷新語》(1877 年)、《華夷通語》(1883 年)、《通語津梁》(1889 年)、《巫來油通話》(1926年)、《馬來語粵音譯義》(?)、《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1929 年)、《瓊南音諳摩賴幼話義》等。(6)楊貴誼:《四夷館人編的第一部馬來語詞典〈滿剌加國譯語〉》,《人文雜志》第19 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3年6月,第26-33頁。
筆者于20 世紀1990 年代有幸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東南亞特藏部,處理館藏舊書籍的修繕事務,因此也就有機會見識了《嗎黎話》和《馬來語粵音譯義》這兩本廣東方言馬來詞典,以及閩南人學習馬來語的《華夷通語》和《巫來油通話》,還有分別供海南方言群和客家方言群學習的《瓊南音諳摩賴幼話義》與《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另外,筆者也接觸過林開臻編纂的《福州音馬來語匯編》,大約是在1930 年3-4 月間,在新加坡本土印刷出版的。
《馬來語粵音譯義》由廣東順德馮兆年原創,按粵語音譯漢字速成馬來語詞條約1 300 個,分布在69頁,分為貨物、礦務、船中器皿、人類職事等28 類。正如上邊說的,本書第一頁羅維瀚書寫序言,敘述馮兆年編纂此書的緣起,已經把坊間需要這類詞典的原因說得很清楚:“閩廣之人商賈其間,攘攘不絕,合之各島不下數百萬人焉,誠通商之廣區也。其地均操土音,華人謂之馬拉話,實則巫來由之本音,南洋各島均可通用。履斯土者茍不辨厥言詞,誠有捫舌面墻之慮。”(7)[清]馮兆年編纂:《馬拉話粵音譯義·天文》,廣州:明經閣書局,1890年,頁一。
如果僅根據這些詞典的書名,它們無論是寫成“嗎黎”“巫來油”或“木來由”,都是以不同的方言發音指稱馬來語Melayu,也即反映著彼時中國東南各方言群面向馬來族群溝通的意愿。然而,所有這些詞典的馬來詞匯,畢竟都是依據各種漢字的方言發音,把各種漢字字體拼湊起來,以他們的發音連在一起,形成用中文字寫成、念起來接近馬來原文的馬來詞匯,也就局限了讀者傳播范圍。
例如,《華夷通語》主要是采用福建省廈門、漳州、泉州方言,去對比馬來文字用詞,根據這種對照仿音,馬來人原稱的“下雨”以羅馬字母拼音是“Hujan”,一些地區的口語快念為Ujan,到了《華夷通語》就要讀成閩南語的“羽然”,(8)[清]林衡南編,李清輝校訂:《華夷通語·天文類》,新加坡:古友軒,1883年,頁一。以“羽”音為wu,“然”音為rian,二者合快念才能接近ujan 的發音。但是在《馬拉話粵音譯義》,同樣處理馬來語“下雨”,卻是廣州發音的“烏衍”。(9)[清]馮兆年編纂:《馬拉話粵音譯義·天文》,頁十二。還有就是《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是念作客音“烏煙”。(10)[清]慕陶、阿末:《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天文門》,新加坡:永成書局,1929年,頁三。《福州音馬來語匯編》則作“烏殘”。(11)林開臻編纂:《福州音馬來語匯編》,新加坡:林開臻自費印,1930年,頁22。

圖1 《華夷通語》內頁
另外,不能不說,以方言讀念中文字的發音去對照馬來文的發音,發音也就不一定完全準確。很多時候,用方言發音學習馬來文的發音,是只能假借發音與馬來原文相接近的幾個漢字,互相連接念出。如筆者曾經以馬來文如何形容天上的“星星”為例,討論過現在馬來語羅馬字拼音作“bintang”的文字,如何可以依靠中文方言串字對比發音,一樣正確地念出。但是當年的《巫來由通語》及《華夷通語》,都是以“民冬”對音,(12)[清]林衡南編,李清輝校訂:《華夷通語·天文類》,新加坡:古友軒,1883年,頁一。而在《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則念成客家語“明釘”,(13)[清]慕陶、阿末:《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天文門》,新加坡:永成書局,1929年,頁三。在《馬拉話粵音譯義》就念作“免打”。(14)[清]馮兆年編纂:《馬拉話粵音譯義·天文》,頁十二。而各路方言對照馬來語詞典的使用者,為了發音更準確,還得參照詞典的“例言”或“凡例”,先行閱讀其中建議如何轉借方言的方法指南。
這最終的結果,造成華人真正與馬來群體交談時,是以方言漢字發音模仿的,不等于馬來文原來發音。如此不一定是準確的發音,卻讓對方覺得獲得尊重與親切感,也的確會逐漸影響一些馬來人日常說話時,會隨環境模仿對方的發音方式,形成馬來社會盛行有“市集用語”(Bahasa Pasar)的說法。
三、客家語馬來詞典的交流之道
《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現在可查原版最早是在1909 年印刷發行的,當時是由廣州以文書局出版。而本書在廣州出版后,應是極受南洋客家方言群歡迎,所以1916 年已由新加坡永成書莊再版;而筆者所見所藏的后期新加坡版本有二,現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是可以查詢的。其一是志成書局1927 年的出版,另外是1929 年永成書局的出版,也是“增訂”版本。《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編者署名“游子慕陶”,而它的最大特點,是同時有一個馬來合作者,名為亞末,讓購買者更有學習信心。至今天為止,這是我們在坊間所見,唯一一本在清末完成的使用客家話編纂的馬來語詞典,當然也只用客家話的讀音才能使用它來查閱和學習馬來語文。
現在看《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的編纂方式,它以漢字的客家話發音,把漢字連在一起,形成相同于某個馬來文字的發音,由此教導大眾學會馬來文生字,這其實和當年明政府編寫《滿剌加國譯語》的方法沒兩樣。根據中華傳統的翻譯理念,不是新鮮事情。梁啟超《佛典之翻譯》評論中華古代翻譯佛經,曾說過:“翻譯之事,遣詞既不易,定名尤最難。全采原音,則幾同不譯……”(15)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頁。歷史的佛經翻譯,一些重要的梵文名詞,就是按照古代人自己朝代的發音。南洋閩南人尤其熟悉,一些中文從梵文外借詞匯,用他們淵源自河洛音的方言去念,如中文用的“剎”“剎那”“一剎間”,馬來文Saat 現在繼續專用于形容“一下子”或現代“秒”的觀念。從古代翻譯,到明朝四夷館,然后是各方言群文人學著他們和四夷館的方式采取變通,以漢族方言字體為音譯馬來文詞匯的媒介。明朝四夷館處理《滿剌加國譯語》,或者是后來以方言發音學習馬來文的詞典,包括《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也是如此。
而后人又需要理解,漢語的方塊字是直排的,傳統寫法是根據筆順由上而下直書;馬來語現在流行使用羅馬字拼音,以前是采用從阿拉伯文拼音字演變的爪威(Jawi)字母是從右到左寫作的。古人使用手工編輯和排列文字的技術,要兼容這兩種書寫形式完全不同的文字,排列成對照,匯編成一部雙語詞典,顯得更加復雜。以漢字拼湊在一起的讀音表達馬來語讀音,讀者也不必學習外來拼音方法。那時出現閩南、廣府、潮汕、客家音等方言馬來詞典,是大眾學習馬來語應付溝通的急就章方式。《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不受形式限制,但也很難符合工作與印刷的成本要求。
以《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16)[清]慕陶、阿末:《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新加坡:永成書局,1929年。為主要討論例證,可見華人下南洋,來往馬來亞,像客家人或其他方言群,為了適應海上交通的生活及長期的陸地生活,都必須和南海上通用馬來語的各種馬來民系居民共同相處,長期往來。語言是不可缺乏的溝通工具。因此,客音的馬來話詞典便應運而生。
《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先后在廣州和新加坡出版,而且縱觀詞典里邊31 項分類,詞條牽涉輪船航行的器皿名稱,也特別強調英文的地名,由內容可以直觀地想像,這詞典的出版時有相當大的市場,而且是供應客籍商務人士在海上往來,也在英殖民地本地區日常生活中使用,必須包含很多相關日常生活使用的基本詞條、詞匯。由此推測可知,慕陶氏到了南洋,有感于客籍人士與馬來同胞溝通的迫切需要,因此“游子慕陶”在馬來亞生活期間,便和馬來人士亞末先生合作,編撰了這部詞典。內容包羅了生活、社交活動、商業買賣,衛生等一般民生所用詞匯(見后頁表1)。
現在看《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引導大眾查閱馬來語詞匯和學習馬來語的方式,主要的特點是以單字、詞組引導學習馬來語的入門基礎。本詞典采用的方式,一樣是一本在表面上不需要看見馬來文這種外語的詞典,因為所有“馬來文”都是以同音的漢字方言拼成。例如單字:有(亞撻)、無(撻撻)、多(麻逆)、少(西咭)等;詞組二字:相信(勿揸也)、忘記(魯巴)等。三字相連:保家紙(保險單據,英書練收辣)、住何處(馬那頂間)等等。
而編者也是一再以有關的單字、詞組相互組合,形成所謂“長短句”“路上問答”“雜話”等的日常實用句子,供讀者即學即用,可以打開此書,按照客家發音,在遇上馬來人時即可問答交流。如要“由何條路去某處呢?”在上邊是教讀者用客家話念“馬那夜爛必居某某”,如果要求包裝、或者將事物一分為二,詞典上教導“分開兩份”的馬來文說法是“峇寄路亞”,等等。

表1 《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詞典分類內容

圖2 《正客音譯義木來由話》內頁之一
客籍人士以這類詞典由淺入深地學習,通過自己熟悉的方言注音學習馬來語,事半功倍。各方言群由此詞典,掌握溝通友族的重要工具,無疑是啟開自身對友族了解的窗口,也有機會通過溝通讓對方理解自己。這不只是在此生活經商的一個重要工具,同時也是奠定了華馬族群和諧共處的基本要素。
另一方面,這種詞典,還有能如此學習馬來文,也啟發馬來亞華人舊文人和傳統的知識界,交流馬來文藝。于是便有以馬來文入中文舊體詩的現象,也出現了以嘗試音譯對照中華舊體詩詞介紹馬來民謠,還有全盤以中文字體拼湊馬來詞句而寫成的七律。
吳小保《早期華人馬來語字典》(17)吳小保:《早期華人馬來語字典》,《當今大馬》電子報,2018年10月30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49665.一文曾經舉出新加坡文士邱菽園,在1932 年發表于《星洲日報·游藝場》的一首詩:“馬干馬莫聚餐豪,馬里馬寅任樂陶。幸勿酒狂喧馬己,何妨三馬吃同槽。”他指出說:“詩中混搭了漢語與閩南音譯的馬來語。馬干是‘吃’(makan),馬莫是‘醉’(mabuk),馬里是‘來’(mari),馬寅是‘玩’(main),馬己是‘罵’(maki),三馬是‘一同’(sama)。”并且慨嘆:“不懂馬來語的讀者肯定對這首rojak 舊體詩看得一頭霧水,但即便懂得馬來語,也未必能夠準確地猜想到對應的馬來字詞。一方面因為漢字并無很好的表音功能,另一方面則因為這些對注音用方音(福建、廣東、海南等),如果不懂相關方言讀音,就可能解錯。”邱菽園是康有為的弟子,新加坡文士才子,也曾是聞商。他寫出這種文字,一樣講究中國詩詞押韻平仄,發表在那時陳嘉庚先生初辦的報章上,可見當時很多人都看得懂。誠如吳小保所說,(18)吳小保:《早期華人馬來語字典》,《當今大馬》電子報,2018年10月30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49665.這并非丘菽園獨創的寫法,在更早前的1920 年代,就可找到類似的作品,例如有位賴逋泓便曾經以這種混搭語言,作本土化的舊體詩詞的美學嘗試,寫過:“一年辣咭(lekas)又重陽,粦亦(ringgit)驅人日夜忙。辜負加基(kaki)空夜爛(jalan),阮郎依舊嘆歌商(kosong)。”
華人南來久居馬來屬地,通過交往與學習彼此的生活習俗、文化,潛移默化,文學創作上本土華人文學頗受馬來文化感染。文壇雅士受馬來詩歌影響,以方言創作詩歌饒有趣味。筆者過去發表過的《華譯馬來詩歌發展履程論析》,(19)關瑞發:《華譯馬來詩歌發展族程論析》,《華人文化研究》,2014年第二卷第二期,第127-168頁。可為參考,此不贅言,在此特引陳輔仁1941 年的作品為據,這是兩首以方言音譯的《馬來情歌》,(20)《南洋商報晚版·大眾文化》,1941年8月19日。翻譯者是在認識馬來文后又以中文為基礎再創作的(見表2)。可知如此學習馬來語且主動介紹馬來民謠給華人世界的現象,這樣的文化交流,一直延續至二戰前夕,還在盛行著。

表2 陳輔仁1941年作品《馬來情歌》方言音譯對比
四、向馬來社群介紹客家文化
二戰后,世界局勢急速改變,亞洲政局更天翻地覆。新馬各民族原來就是生存共同體,華人理所當然積極參與馬來亞獨立運動,聯合馬來族群等其他族群,秉承一同抗日衛馬的歷史經驗,轉入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新階段。20 世紀50 年代,隨著馬來語在新馬兩地規定為獨立后的國家語言,當地更是掀起學習馬來語熱潮。這時期,新馬華人也體會著馬來社會處在新興建國過程,也是有著迫切認識華人世界的需要。華人社會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是能體會南洋僅有概念化的中華文化,是由各種地域/方言文化表達著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與豐富多彩的。在1957 年馬來亞獨立前后,馬來亞華人建國初期迫切地同各族群對話,表現在華人以馬來文字書寫的作品中。當初過來人的記憶,一直到1960 年初,以馬來文書寫中華文化的文字逐漸增多,特別重視介紹地方民眾方言文化特色,能反映那時代華人的深切認知,是一再宣示本身自古以來是屬于當地多民族的共同體,多種在地方言文化源于在地開拓主權,由此希冀各族促進更密切的相互認同。
根據上述歷史背景,再結合著馬來亞歷史情況,那時的客家方言與馬來語文之間的翻譯,肯定不可能離開客家山歌。客家人在馬來亞,曾經以拓殖礦區和種植園形成市鎮的主力,其開發區聚落,又常是與馬來人村落犬牙交錯,星羅密布于馬來亞的半島兩岸沿海。華人自明代后,在清朝雍乾嘉時代開發馬來亞的半島,正如謝清高《海錄》記載,是從吉蘭丹北部現屬泰國境內的“太呢”(北大年)開始,一路南下數國,在各地從事采礦與買賣各種貨物。(21)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譯《海錄》,北京:商務印務館,2002年,第35頁。客家山歌在當地,不僅伴隨民眾勞作或者休閑,作為文娛,既能宣泄情緒,又相互敘情,相互感染;那些汕頭或聚落間的對唱、傳歌、接續句子,更有著互相娛樂以外的對話和傳播功能。那個時代,由著上述背景環境,客家山歌翻譯為馬來文必不可少,現在看來也具有反映時代意識的意義。
以筆者淺見,那時的許多文字后來固然難以考據,但是當年南洋大學出版的多語言刊物《南洋文學》,至今傳下許多文字,足以反映上世紀華人民間大眾集資支持創辦的這間大學,校董師生的主流都是面向國內多元民族,而擁有著維護文化多樣性的理想。這其中,便有新加坡前任華裔館館長吳振強博士在少壯時發表的馬來文論述《客家山歌》(Sajak Orang Kek),(22)吳振強:《Sajak Orang Kek》,見《Kesusasteraan Nanyang,南洋文學》第3期,新加坡:南洋大學,1960年10月,第49-53頁。并在其論文中引述親自翻譯客家山歌作為馬來民間“班頓詩”(Pantun)形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吳振強是客家人,他的文字簡單扼要地解釋自己理解的客家民系與習俗文化,說明山歌的來龍去脈,希冀閱讀《南洋文學》的馬來讀者及他們的社群,能初略了解“鄰村”甚至“鄰居”的客家文化。吳振強一共介紹十五首客家山歌,并把屬于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客家山歌,翻譯成馬來人民間傳統盛行的“班頓詩”的格式,且遵從著“班頓詩”所要求的格律,可說是個創舉。如此翻譯,不僅促進了彼此的相互了解與交流,同時也證明民眾的共同心聲,是可以通過互相最熟悉的文化形式相互交心的。此后《馬來語月刊》第13 期,作為推動華文讀者學習馬來語的刊物,曾經摘取了吳振強文中六首客家山歌,還原了客家語的方言版本,以華馬語對譯形式,讓華文讀者從中學習:
(一)
Sikap-mu menyejokkan hati-ku 講起戀妹心系冷
Jauh malam ku-tunggu 夜夜等到四五更
Bunyi kerkokok dengan menyalak, 雞又啼時狗又吠
Suka berchampor takut di-rasa-ku. 一場歡喜一場驚
(二)
Matahari keluar siang terang 日頭一出天大光
Panas lepas padi menguning sakarang 大暑一過禾就黃
Amoi berumor tujoh-delapan belas 阿妹今年十七八
Menjadi itek manila dengan abang. 正好同郎結鴛鴦
(三)
Chantek sakali roman-mu 阿妹人材也系有
Ta'berani keluar perindu 唔奈阿哥唔敢求
Abang berumor tujoh-delapan belas 阿哥今年十七八
Belum berchakap manjadi malu. 唔曾開口先畏羞
(四)
Bergendang di-tengah di-hendaki 打鼓愛打鼓中心
Memukul di-tepi tidak berbunyi 打到鼓邊沒聲音
Belum dapat,jaring di-tarek tidak 打魚唔到不收網
Belum jaya,ta'memuaskan hati. 戀郎唔到不收心
(五)
Limau jatoh ka-dalam perigi 柑子跌落古井心
Sa-tengah timbul sa-tengah di-liputi 一半浮來一半沉
Tenggelam-lah kalau di-hendaki 若是要沉沉下去
Jangan timbul bersedeh hati. 莫來浮起痛郎心
(六)
Masa dahulu emas nampak-nya 先日見妹一團金
Hari ini lain hati-nya 今日見妹兩樣心
Amoi ibarat tali rebab 妹今好比三弦樣
Sa-tiap kali berubah bunyi-nya 下下彈來兩樣音
五、余話
清朝在1904 年“癸卯改制”后,統一“官話”教學,同時在清朝時期的內陸和南洋各地推廣,到20 世紀1913 年代以后的中國國民教育推動“國音”,現在所見各種方言發音的馬來文詞典絕大多數都是清代以前出現的,或是在20 世紀1930 年代以前的翻版,大致反映著當時的演變。大抵讀者只能使用方言讀音對照馬來文發音,接受傳統方言老式教育,不熟悉后來的演變。
1957 年馬來亞獨立以后,以尹景祥編撰的《馬來會話及巫漢漢巫字匯》為例,就可以看到中國新式教育和馬來語言開啟現代拼音模式,及其相互的影響。這本《字匯》大小僅13.5cm × 9.5cm,做成袋子書方便大家攜帶參閱。編者在《例言》指出,《字匯》以1 200 個常用字匯編成兩用小字典,可供漢巫和巫漢相互檢索,并且加了中華“國音”符號注音馬來字,還附有馬來文發音方法及發音練習;此外,它的幾百句會話課文都是以淺白文法分析的,課文內的每個巫文單字,也附有中文直譯字義。(23)尹景祥:《馬來會話及巫漢漢巫字匯》,新加坡:最新出版社,1958年,例言。
此后,許多當年的方言馬來文詞典,包括客家語對照的,可謂是隨著歲月逐漸成為百年文物。但是它們作為見證當年南海族群交流的文化遺產,卻可能反過來,讓我們從中認識一些在現在已經式微的歷史事物原來的名稱,還有一些后人罕用的方言用詞和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