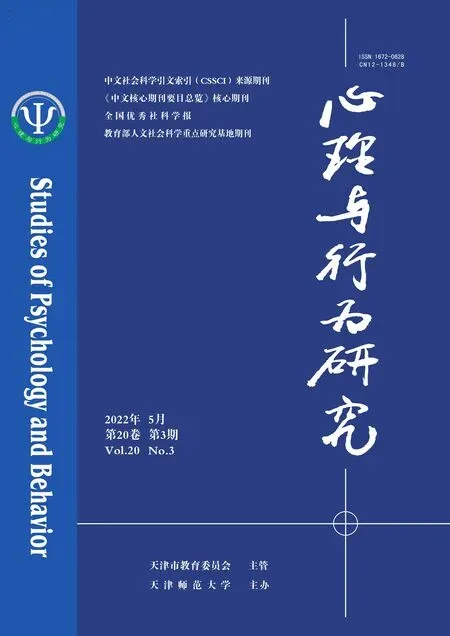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影響:同伴依戀的中介作用 *
譚德琴 謝瑞波 丁 菀 吳 偉 宋省成 李偉健
(浙江師范大學家長教育研究中心,浙江省智能教育技術與應用重點實驗室,金華 321004)
1 引言
留守兒童指的是由于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務工而被留在家鄉,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兒童(王瓊 等, 2019)。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的消極情緒更高(Cheng & Sun, 2015),更容易出現心理適應問題。其中內外化問題尤為突出(范興華, 方曉義, 2010; Wen & Lin, 2012)。內化問題指的是個體心理內部的情緒情感問題,包括孤獨、焦慮、抑郁等(Yap & Jorm, 2015)。與外化問題相比,內化問題不會對別人構成直接威脅,通常不易被覺察(徐夫真 等, 2015),因此,現有研究更多關注外化問題(張永欣 等,2018)或將二者合成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劉廣增等, 2020; 彭源 等, 2018)。個體內化問題的持續發展不僅會給家庭帶來巨大傷害,也會給社會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羅伏生 等, 2009; Costello et al.,2008)。
長期以來,研究者關注的重心集中在內化問題產生的高危期—青春期(侯珂 等, 2017; 彭源等, 2018),而較少關注內化問題萌發和兒童自主性發展的關鍵期—小學階段(韓進之, 魏華忠,1985; 劉廣增 等, 2018)。父母、老師和同伴是小學階段兒童的重要他人,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產生和預防都具有重要作用(金燦燦 等, 2010; 趙金霞, 李振, 2017)。然而,現有研究大多單獨關注其中一種或兩種關系的作用(馬茜芝, 張志杰,2020; 王英芊 等, 2016),鮮有研究從多重依戀關系視角去考察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郭海英 等, 2017;王振宏 等, 2020)。和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父母親情的相對缺失使他們的孤獨、焦慮和抑郁水平更高,更容易出現內化問題(范志宇, 吳巖,2020; 侯珂 等, 2014; 劉正奎 等, 2007)。因此,在親子分離的處境下,從多重依戀關系視角考察小學階段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形成機制和影響因素對于預防留守兒童青春期和成年期內化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1.1 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
影響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因素主要包括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相對于比較穩固的內部因素(如個體人格),外部環境因素(如人際關系)得到改善的可能性更大(張興旭 等, 2019)。多重依戀理論提出兒童會與不同環境里(如家庭和學校)扮演不同角色的成人(如父親、母親和老師)建立依戀關系,不同的依戀關系對兒童有著不同影響(黃桂梅, 張敏強, 2003; 邢淑芬, 王爭艷,2015)。基于此,有必要對其進行考察。
依戀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與身邊的重要他人建立的一種深層、持續的情感聯結(Bowlby,1979)。研究發現,良好的親子依戀能夠有效緩解兒童青少年孤獨、焦慮等內化問題(彭源 等, 2018;趙金霞, 2012; 趙金霞, 李振, 2017);而不良的親子依戀經歷可能使兒童認為世界是冷酷的,在人際交往中保持冷漠、不友好的態度(Bowlby, 1982),產生一系列人際問題和情緒問題。值得關注的是,父親和母親對子女焦慮和抑郁等內化問題的影響機制有所不同(王英芊 等, 2016; 吳慶興, 王美芳, 2014),因此本研究擬分別探討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影響。
小學階段的兒童逐步建構了一種新的人際關系,即師生關系。和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對師生關系更加敏感(謝其利 等, 2020)。良好的師生關系能夠成為留守兒童的保護因素(Liu et al.,2015),對緩解內化問題具有重要作用(Jellesma et al., 2015)。留守兒童父母長期不在身邊,臨時監護人(如祖父母)的照顧往往限于滿足飽暖,缺少對留守兒童學習、行為的監管及心理的有效疏導(范興華, 2011; 戈靜怡 等, 2020),加上大部分時間待在學校,教師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影響可能更大。據此,本研究推測,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可以直接預測留守兒童內化問題,且師生關系的預測作用可能更大。
1.2 同伴依戀在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中的中介作用
根據Hartup(1989)的人際關系理論,與成人間不平等的垂直關系相比,同伴間平等互惠的水平關系對兒童起著更為廣泛和更深刻的作用。進入學校后,校園生活多于家庭生活,兒童與同伴的情感聯結日益深厚,依戀重心逐漸由父母向同伴傾斜(Bodner et al., 2014)。根據依戀理論,親子依戀是最基礎的依戀關系,它會影響留守兒童同伴依戀的建立,起著安全基地和基礎性的作用。有關親子依戀的實證研究表明,親子依戀與同伴依戀存在正相關(Laghi et al., 2016)。親子依戀質量越高,同伴依戀質量也越好(吳慶興, 王美芳, 2014)。
師生關系作為學校環境中另一種重要的人際關系,對留守兒童同伴交往也有重要影響。良好的師生關系有利于引導學生積極參加班級和學校活動,與同學建立積極的情感聯系,促進同伴依戀的形成(馬茜芝, 張志杰, 2020);不良的師生關系可能會使學生在同伴交往中遭到疏離和排斥,不利于同伴依戀的建立。留守兒童進入學校以后,生活環境的改變及其身心的進一步發展會使他們的情感重心逐漸發生轉移,對同伴有更多需求。同伴可以在學業和生活上給予留守兒童更多陪伴,彌補因父母不在身邊而缺失的歸屬感和安全感,使他們體驗到更多積極愉悅的情緒。實證研究也表明,同伴依戀能夠給兒童提供更多情感支持(何燦, 魏華, 2015),緩沖負面情緒,降低內化問題(Healy & Sanders, 2018)。因此,本研究推論同伴依戀可能是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關系的重要中介。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檢驗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直接預測作用及同伴依戀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此外,以往有研究發現男生和女生在抑郁、焦慮等一系列內化問題上存在顯著差異(聶瑞虹 等, 2017; 鄭漢峰 等, 2015),因此本研究在后續分析中將留守兒童的性別納入模型進行控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從安徽省宿州市選取三所小學為取樣學校,以班級為單位對613名三年級留守兒童(在兩次施測間均處于留守狀態,即父親外出/母親外出/父母均外出)進行間隔半年的兩次施測。完成兩次測驗的有效被試共604名,問卷回收率為98.5%。其中男生390人(64.6%),女生214人(35.4%),平均年齡為9.57±1.07歲。父親外出的有303人(50.2%),母親外出的有55人(9.1%),父母均外出的有246人(40.7%)。
2.2 研究工具
2.2.1 親子依戀問卷
選用Armsden和Greenberg(1987)編制,金燦燦等人(2010)修訂的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分問卷。各分問卷包含15個項目,分為信任、溝通與疏離三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其中信任與溝通的分數相加再減去疏離的分數就是最后的依戀總分,分數越高表示依戀狀況越好。在本研究中,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在兩次測驗中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8、0.83和0.85、0.86。
2.2.2 同伴依戀問卷
選用Armsden和Greenberg(1987)編制的同伴依戀問卷,該問卷包含25個項目,分為信任、溝通與疏離三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其中信任與溝通的分數相加再減去疏離的分數就是最后的依戀總分,分數越高表示依戀狀況越好。在本研究中,同伴依戀在兩次測驗中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4和0.93。
2.2.3 師生關系量表
選用Pianta(1994)編制,屈智勇(2002)修訂的師生關系量表,該量表共18個項目。包括親密性、沖突性、支持性和滿意度四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和其他三種依戀關系計分方式保持一致,親密性、支持性與滿意度的分數相加再減去沖突性的分數就是最后的師生關系總分,分數越高表示師生關系越好。在本研究中,師生關系在兩次測驗中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7和0.88。
2.2.4 長處與困難問卷
選用Goodman(1997)編制的長處與困難問卷中的困難部分,該部分包含10個項目,分為情緒問題和同伴交往問題兩個維度。采用3點計分。情緒問題和同伴交往問題的分數相加就是最后的內化問題總分,分數越高表示內化問題越嚴重。在本研究中,內化問題在兩次測驗中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77和0.78。
2.3 施測程序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測試,由經過專業訓練的心理學研究生擔任主試,在班主任的協助下進行。
2.4 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
數據回收以后,采用SPSS20.0對數據進行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采用Mplus8.3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分別檢驗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直接預測作用及同伴依戀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方法對所有變量包含的項目進行未旋轉的主成分因素分析(周浩, 龍立榮, 2004),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26個,第一個公因子的解釋率為23.71%,低于40%的臨界值,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2 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見表1),T1父子依戀、T1母子依戀、T1師生關系與T1同伴依戀兩兩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與T1內化問題、T2內化問題均呈顯著負相關;T1內化問題與T2內化問題呈顯著正相關。

表1 各變量之間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矩陣
3.3 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直接預測作用檢驗
在控制性別和T1留守兒童內化問題后,對直接預測模型進行檢驗。模型整體擬合指標為:
χ2/df=0.000,CFI=1.000,TLI=1.000,SRMR=0.000,RMSEA(90%CI)=0.000[0.00, 0.00],該模型為飽和模型。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師生關系顯著負向預測留守兒童內化問題(β=-0.19,p<0.001),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預測均不顯著(ps>0.05)。見圖1。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以及方杰等人(2012)的建議,無論直接作用是否顯著都需要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進一步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

圖1 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直接預測模型
3.4 同伴依戀在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間的中介作用檢驗
隨后進行中介模型檢驗(見圖2)。模型整體擬合指標為:χ2/df=1.575,CFI=0.997,TLI=0.982,SRMR=0.011,RMSEA(90%CI)=0.034[0.000,0.100],模型擬合良好。對該模型中的各個路徑進行分析,發現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直接預測均不顯著(ps>0.05)。父子依戀和師生關系顯著正向預測同伴依戀(β=0.24,p<0.001; β=0.53,p<0.001),母子依戀顯著負向預測同伴依戀(β=-0.08,p<0.05),同伴依戀顯著負向預測留守兒童內化問題(β=-0.13,p<0.01)。

圖2 同伴依戀在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間的中介模型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Bootstrap檢驗(溫忠麟, 葉寶娟, 2014),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見表2。同伴依戀在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中的中介效應95%的置信區間分別為[-0.06, -0.01]、[0.01, 0.03]、[-0.13, -0.02],均不包含0,表明同伴依戀的中介作用顯著。

表2 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檢驗
3.5 父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影響留守兒童同伴依戀的路徑比較
由中介作用檢驗結果可知,父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均顯著正向預測同伴依戀(β=0.24,p<0.001;β=0.53,p<0.001)。為驗證師生關系對同伴依戀的預測作用是否顯著大于父子依戀,采用嵌套模型比較的方法(張珊珊 等, 2021),限定父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同伴依戀的預測系數相等,得到Wald χ2=12.62,df=1,p<0.01,說明父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同伴依戀的預測作用差異顯著,師生關系對同伴依戀的預測作用更大。
4 討論
本研究發現,師生關系能夠直接預測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對內化問題預測均不顯著。同伴依戀在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間的中介作用均顯著,其中師生關系對同伴依戀的預測作用大于父子依戀;母子依戀質量較低時,留守兒童可能會建立更親密的同伴依戀發揮補償作用。上述結果不僅豐富了多重依戀理論和人際關系理論,也為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預防和干預提供了新視角。
4.1 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師生關系顯著負向預測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這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Jellesma et al.,2015)。師生關系是學生人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內容(白學軍 等, 2022)。老師作為留守兒童生活中的重要成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師生關系良好的兒童擁有老師更多的鼓勵和支持,在課堂活動中也更加投入,能夠體驗到更多積極情緒,減少內化問題;師生關系不良的兒童可能會厭惡和逃避學校,不愿意面對老師又無法跟父母傾訴,進而產生孤獨、壓抑和人際交往困難等內化問題。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對內化問題的預測不顯著,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不一致(Kerns & Brumariu, 2014)。可能由于本研究的對象是留守兒童,與父母情感溝通的缺乏導致親子聯結不夠緊密,遇到問題時父母無法及時與他們溝通,產生情緒問題時也無法立刻幫助他們排解。與留守兒童的父母相比,教師與兒童相處的時間更多,教師不僅在學業上起著“傳道解惑”的作用,在生活上也有著更多的溝通和交流。尤其對于我國學生而言,教師是權威的代表,對兒童的思想和行為都起著重要引導作用,能夠幫助學生形成積極的心理品質,抵御消極情緒等內化問題的侵擾,這一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多重依戀理論,同時強調了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對于減少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重要作用。
4.2 同伴依戀的中介作用
同伴依戀在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關系的中介作用均顯著,但其作用機制不同,影響大小也不同。首先,師生關系對同伴依戀的預測作用大于父子依戀。以往研究證實了父子依戀和師生關系都能促進同伴依戀的形成(王英芊 等, 2016; Jellesma et al., 2015),但尚未探討二者的作用差異。在中國社會中,父親和教師都扮演著權威的角色,對于留守兒童而言,外出務工的父親雖然能夠通過手機與他們保持情感交流,但這種交往具有時空上的特殊性,缺少面對面的直接溝通(趙金霞, 李振, 2017)。與父親相比,教師與兒童相處的時間更多,言傳身教的方式對兒童的影響可能更大,更能引導他們與同伴建立起高質量的依戀關系。其次,父子依戀和師生關系都可以通過促進同伴依戀來減少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當兒童與父親和老師建立起積極正向的關系后可能以同樣的情感態度與同伴交往,從而與同伴建立起高質量的依戀關系。同伴作為留守兒童小學階段的重要依賴對象,能夠給他們提供學業和生活上的雙重幫助,使留守兒童體驗到更多積極情緒,減少孤獨、焦慮、抑郁等內化問題。
最后,本研究發現當母子依戀質量較低時,會促使留守兒童建立高質量的同伴依戀,從同伴那里獲得在母子依戀中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感需求,減少內化問題,這是本研究的新發現。依戀的補償/競爭模型指出兒童會尋求同伴支持,以滿足那些在父母和家庭里無法滿足的需求(Bowlby,1982)。兒童在嬰幼兒時期視主要照顧者(一般是母親)為依戀對象和安全基地。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更多地從同伴那里獲得依戀的接近性尋求和安全基地的功能(Nickerson & Nagle, 2005)。以往有研究發現父母和同伴是兒童交往和依賴的主要對象,二者在為兒童提供情感支持和幫助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Laible et al., 2000)。因此,當一種關系不良時,另一種關系的良好發展可能會起到一定補償作用。在中國家庭里,父親更多扮演著兒童發展的教導者,物質需求的回應者;母親更多扮演著兒童生活的照料者,情感需求的回應者(鄧林園 等, 2013)。同伴是兒童在校園里的主要交往和依賴對象,也是兒童家庭外情感支持的主要來源。相對于父親,同伴和母親對兒童來說可能扮演著更為相似的角色。對于留守兒童而言,母親主要通過電話和網絡視頻與兒童溝通,同伴陪伴兒童的時間更多,能夠給予他們即時的幫助和支持。因此,母子依戀不良可能促使兒童建立起更高質量的同伴依戀,從同伴依戀中汲取情感支持,彌補母子依戀不足導致的情感空缺,保持積極樂觀的生活狀態并進而減少內化問題。
4.3 研究意義與局限
本研究通過兩次追蹤數據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基于多重依戀理論和小學階段留守兒童人際關系的特點將四種主要的依戀關系納入模型中進行考察,更加全面地了解這四種依戀關系對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的不同影響,不僅豐富了多重依戀理論,也為預防和減少留守兒童內化問題提供了新視角。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未對不同留守類型兒童進行區分,年齡及家庭經濟地位等額外變量的控制不完善。第二,被試均來自安徽省,未來研究可以采取隨機取樣的方法從其他省份抽取被試以提高樣本代表性。第三,只對小學三年級兒童進行了兩個時間點的追蹤調查,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對不同年齡段兒童進行更多時間點的數據追蹤,豐富研究的結果。
5 結論
(1)師生關系負向預測留守兒童內化問題,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對內化問題的預測均不顯著。(2)同伴依戀在親子依戀和師生關系與留守兒童內化問題之間均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