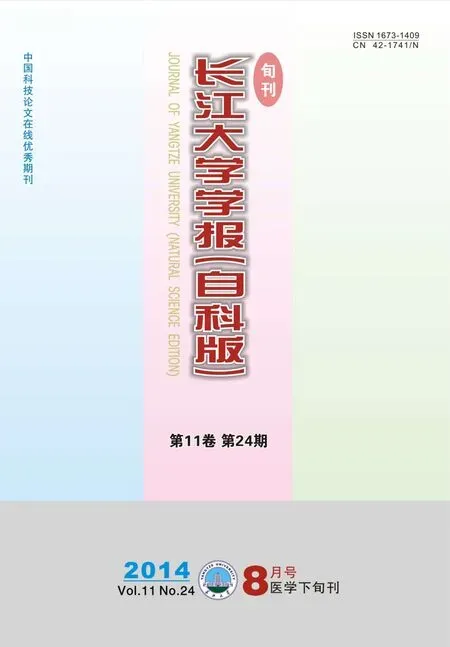長江大學學報(自科版)
- 氟伐他汀、貝那普利單用或聯用對穩定型心絞痛患者血漿同型半胱氨酸的影響
- 腹部非胃手術術后胃癱18例臨床分析
- 肺葉切除術后支氣管胸膜瘺25例臨床診治分析
- 假性靜脈瘤1例及文獻復習
- 彩色多普勒超聲在賁門周圍血管離斷術中的臨床應用
- 骨折重建與人工髖關節置換治療高齡不穩定型股骨粗隆間骨折的療效比較
- 微創鎖定鋼板內固定技術治療脛骨骨折術后非感染性骨不連28例
- 經皮腎鏡氣壓彈道聯合超聲碎石清石系統治療腎結石78例診治體會
- 老年頑固性鼻出血的DSA診斷及選擇性血管栓塞治療
- 手術患者200例預防應激性潰瘍的用藥分析
- 中心靜脈導管胸腔引流聯合滑石粉混懸液治療癌性胸腔積液131例療效分析
- 自擬鼓脹湯治療晚期血吸蟲病肝硬化腹水86例效果觀察
- 多潘立酮聯合復方消化酶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35例
- 以大汗及全身酸痛為主要癥狀的高鉀血癥各1例并文獻復習
- 阿托品肌注聯合利多卡因宮頸旁麻醉在人工流產術中的應用
- 剖宮產術后再次妊娠103例分娩方式探討
- 特發性肺含鐵血黃素沉著癥1例誤診分析
- 非結核分枝桿菌肺病誤診為肺結核8例分析
-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導致猝死35例臨床病理分析
- 液基細胞學檢查在宮頸病變篩查中的應用
- 兒童哮喘發作64例治療分析
- 心理輔導在兒童牙科畏懼癥中應用及效果
- 抑郁、焦慮癥誤診為心血管疾病48例臨床分析
- 金屬支架治療胃癌術后胃食管吻合口狹窄1例
- 髁狀突腫瘤的診斷與治療
- Hawley保持器在腭部良性腫瘤術后的臨床應用
- 成人股骨頭缺血性壞死低場MRI影像學分期與分型的應用分析
- 預激綜合征合并快速房顫同步電復律治療1例報告
- 非典型敗血癥1例
- 惡性腹腔積液引流患者局部換藥敷料的改進
- 腮腺腫瘤摘除術161例圍手術期護理
- 延伸護理服務在支氣管哮喘出院患兒中的應用
- 股骨骨折并發肺脂肪栓塞1例搶救成功的護理體會
- 嚴重多發外傷合并多重耐藥菌株混合感染11例護理
- 手足口病患兒34例護理
- 鼻內鏡下低溫等離子治療鼻出血149例護理體會
- 消化性潰瘍90例心身護理
- 雙硫侖樣反應的護理體會
- 淺談護患關系的影響因素及改進措施
- 下消化道大出血3例急救與護理
- 手術室常見的護理差錯及防范對策
- 優質護理服務落實不足的原因分析與對策
- 健康教育對提高護理人員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作用
- 淺談導診護士綜合素質的培養
- HPLC法測定眼用伏立康唑納米結晶混懸液含量
- 二子菊花飲中紅景天苷的含量測定研究
- 糖化血紅蛋白和BNP檢測在糖尿病合并慢性心衰患者中的臨床意義分析
- ICU獲得性血流感染及病原菌檢出分析
- 某市二級以上醫療機構臨床輸血過程記錄現狀
- 采供血質量記錄的潛在問題分析與干預效果評估
- 輸注異型血小板搶救兒童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1例
- 醫療機構醫務人員職業危害分析與安全管理探索——以荊州市中心醫院為例
- 淺談分區定位法規范管理藥房藥品
- 我院住院部2013年麻醉藥品管理情況分析
- “三位一體”管理手術室循環利用醫用織物的探討
- 二級醫院檢驗科質量內審初探——以監利縣人民醫院為例
- 以病人為中心,創新醫院門診服務
- 云計算及其在醫療信息化管理中的應用
- MAIN ABSTR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