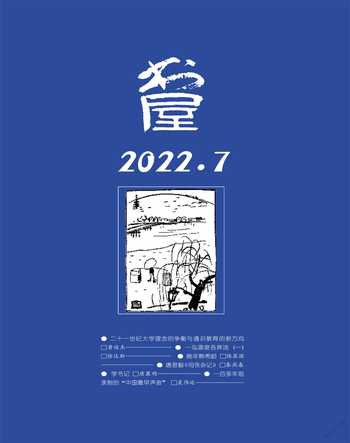佛教對“孝道”的認同
沈棲
兩漢交替之際,佛教傳入中原。佛教以新的觀念、新的教義,形成了新的教派,對儒家學說和道家學說有著直接而重大的影響。在與儒、道的相互交融互動中,最終形成了一種有別于印度佛教的中國化佛教,大大地擴展了中國人的精神領域。
儒家和道家在很多方面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儒家。宋朝時期,名儒朱熹吸收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思想對儒家進行改造,確保了儒家的統治地位。同時,在注重宗法倫理、躬行實踐的中國社會環境中,本來宣傳出世和個人“解脫”的佛教也逐步被改造成為宣傳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的宗教。儒、道、釋三家經過長期的交流、融合,終于導致各自都發生了局部質變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
檢視佛教的“局部質變”,它對儒家“孝道”的認同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孝道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維系家庭關系的道德準則,深入人心,化民成俗,孝行孝德表現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傳入伊始,佛教徒剃度毀形、棄家絕嗣的做法,在講究忠孝的儒家倫理社會環境下,受到儒士們的普遍不滿和強烈責難。為了站住腳跟,佛教開始了自身的“變形”,努力順應本土的倫理理念,從被攻擊最嚴重的一個方面——孝道入手,一方面吸收借鑒了儒家的孝道觀,另一方面構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孝道觀。“報恩”作為佛教的一個基本范疇,同樣體現在其孝道觀念之中。佛教的孝道更多強調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尤其是母親之恩。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就是中國化的過程,為了爭取信眾,獲得發展,佛教采用各種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如俗講變文、變相經變來宣傳佛教義理,尤其是對佛教中國化的核心內容——孝道的宣傳。佛教對于孝道的宣傳大體有兩個路徑:其一,敷演中國本土的傳統典籍中的孝子人物,進行加工改編,然后以這種生動的方式向大眾傳播,如《敦煌變文集》中的《孝子傳》;其二,發掘佛教經典中的孝子和孝行故事,從佛祖到目連再到睒子,從俗講變文到變相再到戲曲,一俟發現且再創造,使這些域外的孝子與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產生特殊的親和力而被著意發揚,深入人心。
從印度傳來的佛教觀念雖說沒有觸動中國封建社會的層序結構,但佛教教義中近似于中國主流價值觀的東西卻被著意發揚,如佛典中某些講孝道的文字就發展成為《父母恩重經》《目連救母變文》等作品。隨著佛教中闡揚孝道的經典如《無量壽經》《地藏菩薩本愿經》《佛說盂蘭盆經》相繼被介紹進入中國,當時的中國人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佛教。誠如南懷瑾云:“佛的這種精神,合于中國《孝經》所說的‘大孝于天下’。”法宣法師將儒家《孝經》“孝乃是上天之常經、大地之常義”與佛陀《戒經》“孝順乃是至道之法”作了比較,得出了如此斷論:“不論是世間或出世間,莫不以孝為根本也。”民國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師的《佛教以孝為本論》則是淋漓盡致地詮釋了佛教中的孝道精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孝”故事的成型和傳播極大地提升了“儒佛合流”的層次。“二十四孝”是中國孝文化登峰造極的產物,它的產生對中國上千年來的民俗影響深遠。隨著佛教宣傳,“二十四孝”日漸深入人心,并在宋元時期廣泛普及開來。元代鄉賢郭居敬主要輯錄西漢文學家劉向《孝子傳》而編成《全相二十四孝詩選》,后印本配上圖畫,通稱《二十四孝圖》,成了“用訓童蒙”、宣傳孝道的通俗讀物,而大法王寺、靈光寺、臥龍寺、青巖寺、圓通寺等佛教場所都以石雕、壁畫的形式廣為宣傳。
高僧太虛認為:“中國即是佛教第二之祖國。”當然,在倫理方面,佛教除了強化了孝道意識外,還彰顯出中國人傳統道德的若干特點諸如仁慈及重視人命,并且使這些特有的德性進一步升華,而力主重視一切有生命之物。總之,自從佛教傳入了中國,中國包括孝道在內的傳統倫理得到了進一步的固化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