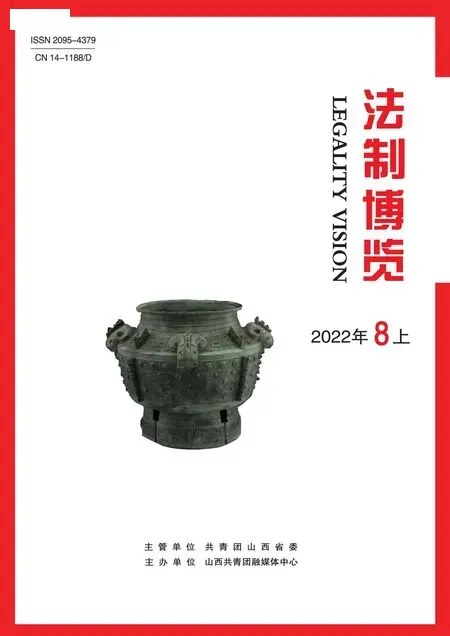流浪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主體認定相關法律問題研究
宋碧波
重慶大學,重慶 400044
一、流浪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主體認定概述
(一)流浪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主體身份界定
我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九條規定,遺棄、逃逸的動物在遺棄、逃逸期間造成他人損害的,由動物原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承擔責任。《民法典》對流浪狀態的動物侵權責任主體規定看似明確,動物的原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作為責任主體無可厚非,但是在司法案件中往往都是無法找到原飼養人或者確定管理人,那么確定責任主體就顯得尤為困難。除此之外并沒有其他法律對動物飼養人、管理人進行明確的定義,這就導致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處理此類案件由于對法律概念不同的理解,運用自由裁量權出現了不同的判決。“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作為我國動物侵權責任承擔的主體頗有特色,但卻忽視了責任主體與動物所有權、占有狀態的聯系。這種定義在法律邏輯上無法準確反映流浪動物與責任承擔主體在物權法上的規范聯系,因此在我國學理上將飼養人或者管理人的概念進行外延,不只是包括所有人還包括占有人。占有人是享有對動物占有的權利,屬于事實上有支配、管理的人。
(二)流浪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主體認定規則
為了解決流浪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主體在我國《民法典》相關規定不明確以及司法實踐中法官審理案件不統一的問題,本文建議引入多維度責任主體認定規則,不可否認的是現階段我國存在具有自己特色的流浪動物侵權責任主體認定規則,但尚未形成體系,無法為法官審理此類案件提供系統、統一的指導規則。多維度責任主體認定規則是指以實際支配管理控制標準為主導、多要素作用的動態責任認定規則。此種動態責任認定規則核心要素為實際控制原則,它要求對流浪動物形成事實上的管領能力,實際管領能力包括意志要素和利益要素。意志要素須責任主體有意識地接受、飼養流浪動物,依據危險控制理論,責任主體對流浪動物占有或者所有,進行支配、管理、控制,由此承擔責任。[1]利益要素不僅是經濟層面的獲利也包括心理上情感滿足和責任感,依據權利義務相一致原理,流浪動物事實上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享受著流浪動物帶來的經濟或者心理上的利益,應承擔動物侵權責任。多要素作用的動態認定是充分考慮形成事實上的管領能力須關注的各個維度,大致分為權屬要素、意志要素、利益要素、時間要素、空間要素。所謂的動態是法院在處理個案時根據不同的案件情況選擇具備的要素使得個案的審理具備開放、多元、多維度的認定規則。
二、我國流浪動物致人損害案例及法律思考
本文選取的8個流浪動物侵權案例中(見表1),景某與郝某一案、楊某與姚某一案、李某一案法院認定被告與流浪動物形成事實上的飼養關系,對流浪動物有管理和約束的義務;在王某與高某一案、崔某與胡某一案、徐某與倪某一案、姜某與何某一案中法院認定被告與流浪動物建立了臨時管理關系,出于無因管理占有流浪動物為合法占有,屬于“管理人”的范疇;在李某與杜某一案法院并未認定被告為流浪動物的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在喬某與肖某一案法院認為被告為流浪動物的保有人。

表1 流浪動物侵權案例
責任承擔者與流浪動物形成事實上的豢養關系不是單純投喂還須有控制能力,法院認定時依據“使該流浪動物對被告投喂的食物產生依賴致流浪動物經常在附近活動引發危險存在”。如何界定流浪動物形成的投喂依賴程度?從大多數案件判決來看多數法官以投喂行為—具有管控能力—形成事實上的豢養關系思路來認定。動物被馴化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投喂人長期的投喂過程中狗逐漸被馴服、安撫,投喂人與流浪動物因此具有社會關系。我國《民法典》規定的“飼養人或者管理人”著重于投喂和管理行為,而非動物處于控制或事實上的管領狀態。“飼養”的時間性—即時性、持續性、長期性三要素對認定主體資格必不可少,此外“飼養”還強調“所有”,物權權屬關系作為認定事實上豢養關系主要要素,當所有人與實際管理控制人二者重合時,在事實上和法律上同時具有正當合理理由作為責任承擔者。
法院認定無因管理普遍適用合法占有人為侵權責任主體,將合法占有人歸屬于“動物管理人”概念范疇。占有側重對動物的實際管控能力,合法占有人對動物享有事實上的管領能力。但是將善意投喂人認定為無因管理人有幾點不妥之處值得思考:第一,善意投喂人主觀上并無為他人管理事務的意思,善意投喂人的投喂行為在不存在重大過失或故意的前提下是值得提倡的。第二,善意投喂人并未從流浪狗身上獲利的主觀意思。第三,如果我們只追求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就會加重善意投喂人的責任,善意投喂人已先行承擔流浪動物管理費用,如果在流浪動物原飼養人、管理人無法確定的情況下要求善意投喂人承擔侵權責任有違公平正義。
三、域外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主體認定司法借鑒
(一)羅馬尼亞民法典
《羅馬尼亞民法典》第一千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了動物侵權責任主體:動物的保管權屬于所有人,或根據法律或合同,甚至僅在事實上獨立地對動物進行控制和監督并為自己的利益使用動物的人。此“民法典”本身并未解釋保管權,但是理論學說和司法實踐認為法律上的保管包括所有人的權利和使用動物的權利,有監督、指導和控制的特權。除此之外《羅馬尼亞民法典》也規定流浪動物致人損害可以援引本法典第一千三百七十五條條的規定,受到動物損害的人可以依照本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條的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對該動物負有物質保管責任的人,即飼養人可以向該動物的所有人要求賠償該動物所造成的損害。
《羅馬尼亞民法典》中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主體認定關鍵在于私人所有權的絕對性,即使是對動物有保管責任的人也可以向動物的所有人要求賠償,物權權屬關系是動物侵權責任主體認定的決定性標準。可將其理解為責任實體化,也就是動物行為的責任是建立在監督保管絕對推定基礎上,不能用相反證據予以反駁。《羅馬尼亞民法典》中還提到有使用動物權利的人和動物的保管人,保管為監督、指導和控制,這種“保管”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害在動物的保管之下存托。羅馬尼亞將所有權人與動物之間事實控制關系基本化即所有的關系體現在權屬規范上,當其他有使用動物權利的人出現時,所有權人與動物之間的基本關系就會發生變化,但變化發生的前提是合法使用權利。
(二)斯普林訴布朗案
查爾斯· 布朗出租房屋給養有名叫喬普犬的主人,在租戶和布朗的女友把喬普放到后院后喬普逃脫了,并咬了斯普林家的兒子。斯普林夫婦起訴了布朗、他的女友和房客,要求根據亞利桑那州修訂法規第11-1020條和第11-1025條嚴格承擔責任。上訴陪審團判決是否支持的決定性問題即對布朗是否為法定所有人產生分歧,是否違背《狗法》中動物侵權責任主體標準—嚴格所有權人主義。上訴陪審團認為判定動物致人損害主體資格應依據“一個所有者以外的任何人保持動物畜牧連續超過6天”。“飼養”術語要求對狗有照顧、監護或控制,而不僅僅是“安置”狗,重點是庇護動物,而不是動物坐、待或翻身的地方。
在本案中亞利桑那州法院以時間要素認定所有者承擔責任,將保持動物的時間界定為連續超過六天。事實上時間跨度并沒有嚴格的標準,其意義在于所屬關系不明確時以動物與保管人在時間維度上的接觸長短來判斷保有人對動物習性了解程度以及對動物危險源防范與控制能力。但時間要素作為對動物管理控制判斷的事實認定輔助因素是出于實踐的需要,或者在個案中以單獨的形式存在,或者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實際控制的認定。上訴陪審團解釋“飼養”包含“庇護”,要求“庇護”對動物照顧、監護和控制,此解釋實際上將責任的判斷標準由對動物的占有和控制轉移為相關空間對動物的管理控制能力。當然在美國的法律實踐中對“庇護”的解讀各不相同,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將庇護定義為:為動物提供住處、保護或避難。
四、我國流浪動物致人損害侵權案主體認定司法破局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流浪動物致人損害責任認定過程中存在立法不完善、主體認定規則不統一、主體責任不明確、流浪動物信息不完善等不同層面的問題。但主體責任認定作為侵權案件首要解決要素,一套系統的、全面的流浪動物致人損害主體責任認定規則不僅可以讓法官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有規則可循,而且對于當事人的利益有更大程度的保護。因此結合了我國近幾年相關案例給出建議,建立主體責任認定規則為以實際管理控制標準主導、多要素作用的動態責任認定。此種動態責任認定規則核心要素為實際管理控制標準,它要求對流浪動物形成事實上的管領能力,實際管理控制標準包括意志要素和利益要素。意志要素要求責任主體有意識地對流浪動物有接受、飼養的意思,這樣才存在事實上的飼養關系。依據危險控制理論,責任主體基于有意識對流浪動物占有或者所有形成的管理、控制狀態,由此承擔責任[2]。利益要素在此不僅是經濟層面的獲利也包括心理上情感的滿足和責任感。依據權利義務相一致原理,流浪動物事實上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一方面享受著流浪動物帶來的經濟或者心理上的利益,理應承擔動物侵權責任。多要素輔助的動態認定是充分考慮形成事實上的管領能力所須考慮的各個維度,大致分為權屬要素、意志要素、利益要素、時間要素、空間要素。所謂的動態是考慮法院在處理各個案件時不同的案件情況沒有哪幾個或者哪一個要素是必須具備的,只是在個案審理時開放、多元、多維度的認定。
五、結語
流浪動物侵權案關鍵一步在于責任主體資格認定,《民法典》的不完善、司法實踐的不統一導致我國類案判決出現差異,我國流浪動物致人損害侵權案主體認定司法破局無疑是一套系統全面的流浪動物致人損害主體責任認定規則——建立以實際管理控制標準主導、多要素作用的動態責任認定。將責任人與流浪動物之間支配、管理、控制的能力與時間要素(長期的投喂行為)、空間要素(固定的投喂)、社會公眾利益影響(流浪動物的危害性)、權屬要素(事實上的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兩階層共同作用,為法官提供可遵循的認定規則體系,保障我國司法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