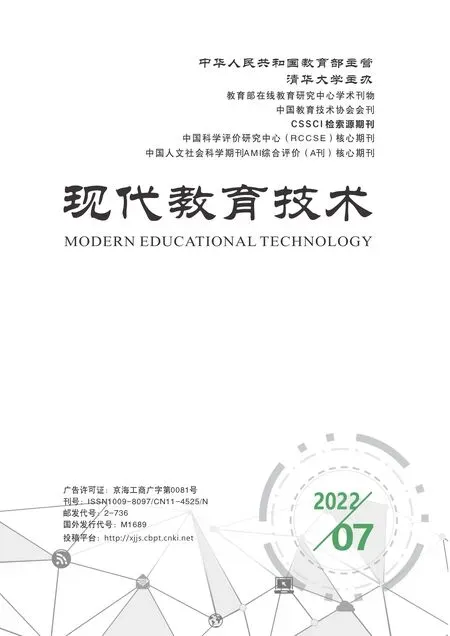基于體驗式學習模型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以“夢回南唐宴”游戲為例
張羽洋 李萬葶 羅雅蘭 聶曉梅
基于體驗式學習模型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以“夢回南唐宴”游戲為例
張羽洋 李萬葶 羅雅蘭 聶曉梅[通訊作者]
(清華大學 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廣東深圳 518055)
現有的數字化文化遺產教育主要依賴于文物的單向展示與外源性資料的補充,其交互性和趣味性逐漸無法滿足人們的學習需求。基于此,文章首先提出了一種融合游戲化設計要素的體驗式學習模型,并分析了此模型與文化遺產教育游戲的關系映射。隨后,文章以古畫《韓熙載夜宴圖》為學習主題,設計了一款基于體驗式學習模型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夢回南唐宴”。最后,文章采用調查問卷、學習效果測試、半結構化訪談等混合研究方法,通過對比實驗對文化遺產教育游戲進行了評價,發現該游戲對于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效果、學習體驗和學習主動性均有積極作用。文章對數字化文化遺產教育的理論與應用研究進行了創新性探索,并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實證參考。
體驗式學習;文化遺產教育;游戲化學習;教育游戲

近年來,數字化文化遺產教育作為公共教育的重要一環,在我國越來越受重視。2021年,國家文物局印發《關于推進博物館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大力發展博物館云教育,構建線上線下相融合的博物館傳播體系[1]。現有的數字化文化遺產教育主要依靠在線數字文物庫、360°全景博物館、VR博物館等,盡管可以起到一定的文物展示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如信息呈現方式以圖文單向展示為主、其交互性與趣味性略顯不足[2],未能提供給學習者參與度更高的沉浸式敘事環境以更好地展現文物背后的內涵等[3]。基于此,本研究設計了一款基于體驗式學習模型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參與者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體驗,通過敘事、交互、音樂等多種媒介了解文物內容。本研究試圖通過改善文化遺產教育的學習體驗,來吸引年輕人更加主動地學習文化遺產,從而達到提升學習效果的目的。
一 體驗式學習模型與文化遺產教育游戲
1 體驗式學習模型的構建
(1)理論基礎
①體驗式學習循環模型。傳統的虛擬博物館大多為用戶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單調且不變的參觀[4],通過遺址重現或者文物重建來展示文化遺產原本的樣貌[5],而無法很好地展現其思想內涵,也不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體驗式學習具有認知、情感、行為等多種學習形態,更關鍵的是能夠獲取意會知識(即從直接經驗中提取的、難以用言語直接表達的程序性知識),這與文化遺產本身的特質相吻合,所以體驗式學習已具備應用于文化遺產教育領域的可行性。
體驗式學習循環模型由組織心理學家Kolb[6]提出,是體驗式學習中較為經典的理論模型。該模型分為四個階段:具體體驗、觀察反思、概念抽象和積極實踐,其本質上是一種綜合學習,具有“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特征[7]。其中,具體體驗是指學習者在真實或模擬情境中活動,習得知識與技能;觀察反思是指學習者在體驗過程中進行反思性的評估與分析;概念抽象是指學習者將感知到的知識進行梳理與歸納,建立結構化的記憶體系;積極實踐則指學習者將習得的知識與技能進行實踐應用。
②游戲化設計理論。游戲化的文化遺產教育有利于激發大眾的文化學習主動意識,提升學習興趣與參與度,對促進文化遺產的傳播起推動作用[8]。20世紀80年代初,教育類嚴肅游戲研究開始出現,其采用寓教于樂的形式,通過對現實事件的模擬,讓用戶在游戲過程中學習[9]。但是,這類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學科教育領域,而在公共教育特別是文化遺產教育領域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10]。
嚴肅游戲是平衡體驗式學習過程中教育性與趣味性的重要途徑[11],具有區別于傳統游戲產品設計的不同特征。Csikszentmihalyi[12]提出的心流理論經過Kiili等[13]的擴展后,逐漸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游戲設計理論,包括清晰目標、即時反饋、挑戰與技能的平衡性三個要素。其中,清晰目標是學習者需要努力達成的結果,可分為一個大目標和若干個小目標;即時反饋主要告知學習者目前距離目標實現還有多遠,包括任務提示反饋、獎勵與懲罰反饋等;挑戰與技能的平衡性則指游戲中任務難度與學習者自身技能的匹配程度。這三個要素反映了嚴肅游戲的主要內容與功能,可為學習者提供目標與動機方面的支持。
(2)融合游戲化設計要素的體驗式學習模型
參考體驗式學習循環模型,融合游戲化設計理論的三個要素,本研究提出了體驗式學習模型,如圖1所示。該模型將學習經歷描述為一個在游戲世界中通過體驗、觀察與實踐構建認知結構的閉環過程,其核心驅動力在于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由清晰的游戲目標來激發;學習者需要在具體體驗游戲的過程中通過觀察反思完成挑戰,從觸發的即時反饋中反思自身的行為,從而對具體體驗中獲得的非結構化知識進行歸納并轉化為結構性記憶,并通過積極實踐將所習得知識與技能進行鞏固。為了保持游戲的平衡性,游戲的挑戰難度會隨學習者技能的提升而升級,從而生成下一輪任務。

圖1 體驗式學習模型

圖2 體驗式學習模型與文化遺產教育游戲的關系映射
2 體驗式學習模型與文化遺產教育游戲的關系映射
文化遺產教育游戲是文化學習的社會語境,這意味著文化遺產教育游戲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向社會傳遞其價值觀,故應有一套與之關聯的學習模型。而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具有藝術品和歷史收藏品的雙重特質,具有“形、意、髓、魂”相結合的特點,其知識體系包含文物的外觀結構、創作理念、歷史文化底蘊等多層內容。基于此,本研究建立了體驗式學習模型與文化遺產教育游戲的關系映射(如圖2所示),以解釋文化遺產的四層知識體系與游戲實現機制之間的聯系:
①感悟文化遺產之“形”。主要依托具體體驗,利用三維重建和動畫技術復現出文物及其所處歷史場景,并通過敘事性設計激發學習者共情,使其感悟文化遺產之“形”,感受文物本身的形體美。
②體悟文化遺產之“意”。主要依托觀察反思,通過以文物歷史知識為背景的關卡挑戰設計和任務反饋機制,引導學習者進行反思性的觀察與思考,使其體悟文化遺產之“意”,體會文化遺產的內在意蘊。
③領悟文化遺產之“髓”。主要依托概念抽象的歸納學習過程,通過知識卡片、導航欄等形式對信息進行模塊化處理,形成意元集群,從而系統梳理文物的相關知識,以助力學習者進行知識歸納并轉化為結構性記憶,使其領悟文化遺產之“髓”,掌握傳統文化的精髓。
④弘揚文化遺產之“魂”。主要依托積極實踐,通過難度調節與技能升級機制保持游戲的平衡性與可玩性,從而提升學習者的學習主動性,形成良性學習循環,使其弘揚文化遺產之“魂”,主動與文化遺產的靈魂產生共鳴。
二 文化遺產教育游戲的設計
基于體驗式學習模型,本研究以古畫《韓熙載夜宴圖》為學習主題,設計了一款名為“夢回南唐宴”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韓熙載夜宴圖》是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畫家顧閎中的繪畫作品,現存宋摹本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畫作長三米有余,描繪了官員韓熙載家設夜宴的場面;整幅作品含有五個場景,描繪了40多位人物,涉及南唐禮儀舞樂等多種知識,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在“夢回南唐宴”游戲中,學習者將成為“穿越者”,以第一人稱視角探索這副古畫的奧秘。游戲按照兩條線索展開:主線為劇情任務,需要玩家與畫中的不同人物進行對話,并結合對話信息完成畫中人物給出的任務;支線為收集任務,需要玩家收集畫中不同人物角色與文物器具的知識卡片。根據體驗式學習模型,“夢回南唐宴”游戲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1 具體體驗
“夢回南唐宴”游戲通過敘事性設計,為學習者提供具體體驗,實現學習者的認知交互:首先,利用三維建模技術對原畫進行情境還原(原畫與游戲的對比如圖3所示);隨后,根據畫作的創作背景進行對話和劇情設計,并通過關卡與任務賦予其邏輯層次;最后,按照對應的歷史年代進行風格一致的音樂音效設計。
“夢回南唐宴”游戲采用交互敘事結構,學習者通過與游戲中的人物發生交互參與推動劇情的發展,其行為與選擇將成為劇情的一部分。交互敘事結構是通過Unity的Fungus引擎插件實現的,此插件將游戲敘事內容以劇情塊(Block)的形式組織起來,每個劇情塊由特定的觸發條件和一組包含對話、變量處理、條件邏輯等操作的指令集組成,其中第一個關卡劇情塊在Fungus中的組織結構如圖4所示。其中,紅色方框代表不同交互任務包含的劇情塊,學習者操作所關聯的劇情內容經指令集處理后被歸入到不同劇情塊中,從而推進劇情的發展。

圖3 原畫(上)與游戲(下)的對比

圖4 第一個關卡劇情塊在Fungus中的組織結構
2 觀察反思
在主線劇情任務中,游戲允許學習者自行選擇與畫中的不同人物進行對話,完成他們給出的任務,從而了解他們的生平和背后故事。部分任務需借助道具完成,學習者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背包”按鈕選擇道具。完成任務后,會有音效和金色粒子特效作為正向反饋激勵,并開放下一個連鎖任務;若任務失敗或長時間無法通關,則會觸發游戲提示,降低游戲的難度等級。
3 概念抽象
游戲中出現的所有角色和文物都有可視化的知識卡片進行相關概念性知識的歸納,并在與場景中的相應對象初次交互后自動解鎖。學習者可以點擊主界面右上角的“畫卷”按鈕打開“博古架”或“人物志”,查看相應文物或人物的信息,如圖5(a)、(b)、(c)、(d)所示。在卡片中,學習者可以對畫中出現的器皿、家具、樂器等高清模型進行拖動旋轉和放大觀察。
4 積極實踐
游戲人物對話中出現的每個文字性知識點都會對應一個交互任務,如行禮、斟酒、彈琵琶等。這種“敘事情節+交互實踐”的形式,有利于加深學習者的記憶。如圖5(e)所示,學習者通過與“李姬”交談獲得琵琶曲的知識,之后在琵琶上彈出對應的旋律;如圖5(f)所示,學習者通過與兩位官員交談了解他們的身份,之后在侍女的詢問中回答對應身份官員的姓名。

圖5 “夢回南唐宴”文化遺產教育游戲截圖
三 文化遺產教育游戲的評價
1 研究工具
本實驗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包括調查問卷、學習效果測試和半結構化訪談,以更好地理解游戲設計機制對學習者學習效果產生的影響,并提升實驗結論的有效性。
(1)調查問卷
本實驗目的是測試“夢回南唐宴”游戲能否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能否優化其學習體驗,以及能否增強其學習動機。基于此,本研究將學習效果、學習體驗、學習主動性三個指標作為游戲的評價指標,并根據這三個指標設計了包含14個題項的調查問卷,如表1所示。

表1 調查問卷題項設計
①學習效果:根據Hooper等[14]提出的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的通用學習成果,調查問卷中設置了6個題項,包括學習者能否理解畫中的文物、人物、創作背景等顯性知識(Q1~Q3)和禮儀、音樂、舞蹈等意會知識(Q4~Q6)。
②學習體驗:根據Mekler等[15]對游戲影響玩家體驗的定量研究,調查問卷中設置了5個題項來測試“夢回南唐宴”游戲能否優化學習者的學習體驗,包括游戲能否獲得學習者的認知和情感欣賞(Q7、Q8),能否提升沉浸感(Q9),是否具備趣味性(Q10)與挑戰性(Q11)。
③學習主動性:根據Fredricks等[16]對學習主動性評價機制的研究,調查問卷從行為(Q12)、情感(Q13)、認知(Q14)三個方面測評學習者的學習主動性。
從問卷可靠性來看,學習效果(Q1~Q6總的Cronbach’s α=0.813,KMO=0.773)、學習體驗(Q7~Q11總的Cronbach’s α=0.871,KMO=0.794)和學習主動性(Q12~Q14總的Cronbach’s α=0.866,KMO=0.711)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分析項的CITC值均大于0.4,相關研究項的KMO值均大于0.7,且Bartlett球形度檢驗結果的值無限接近于零,表明問卷的信效度水平良好。問卷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用1~5分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2)學習效果測試
學習效果測試能夠從客觀角度定量分析學習者的知識習得情況。測試卷由17道封閉式選擇題組成,考察畫作第一個場景中出現的知識點,內容涉及人物辨識與理解(8題)、文物辨識與理解(5題)、故事背景理解(2題)、意會知識理解(2題),滿分為100分。
(3)半結構化訪談
半結構化訪談可以更細致地了解學習者的主觀感受,并起到對其他實驗數據的補充和驗證作用。本次訪談主要從游戲本身的可玩性、享受度、習得性等角度詢問學習者的看法,征得被訪者的同意后,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之后通過“訊飛聽見”語音轉文字服務進行錄音文本整理。
2 研究過程
2021年,本研究通過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啟動實驗,共有97名學生志愿者入選。其中,有55名是來自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志愿者(24~28歲),有42名是來自深圳麗湖中學的初中生志愿者(14~16歲);男生志愿者有56名,女生志愿者有42名。所有入選的志愿者在報名后都接受過先驗背景調查,以確定其并非博物館或歷史文化方面的專家、學者,且都未對畫作《韓熙載夜宴圖》有過預先學習與了解。
所有志愿者被隨機分為兩組:①對照組有48人,通過模擬實地博物館的游覽經歷,來觀察1:1文物仿制品、查看張貼在文物下方的背景信息,并收聽引導者的講解;②實驗組有49人,通過體驗游戲來進行學習。游戲后臺設置數據監聽程序,可以自動記錄每名實驗組學生的游戲時間、交互次數和信息瀏覽時間,以便后續進行更深入的學習者行為研究。考慮到時間成本,兩組學生都只學習《韓熙載夜宴圖》第一個場景“宴罷聆音”中的知識點,且提供給兩組學生的信息量是對等的,學習時間也都約為15分鐘。學習結束后,兩組學生都要填寫調查問卷,并完成學習效果測試。之后,實驗組學生接受一對一訪談,每個學生的訪談時間約為5~10分鐘。
3 數據與錄音文本分析
(1)調查問卷數據分析
不同組別的方差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習效果”上差異性顯著(F=6.058,=0.016),且實驗組平均值(26.08)高于對照組(24.35);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習體驗”上差異性極顯著(F=7.064,=0.009),且實驗組平均值(21.84)高于對照組(19.96);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習主動性”上差異性顯著(F=5.109,=0.026),且實驗組平均值(13.47)高于對照組平均值(12.40)。上述數據說明,通過游戲進行學習的實驗組學生在學習效果、學習體驗和學習主動性上的表現均優于對照組。

表2 不同組別的方差分析結果
注:*<0.05,表示差異性顯著;**<0.01,表示差異性極顯著。下同。
不同組別的非參數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使用MannWhitney檢驗對調查問卷中14個題項的數據統計結果做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Q5、Q6、Q9、Q14四個題項上差異性極顯著(<0.01),在Q7、Q8、Q10、Q12四個題項上差異性顯著(<0.05),而在其他題項上差異性不顯著。具體來說,從學習效果來看,游戲在禮儀、音樂、舞蹈等意會知識的學習上更占優勢,對此類知識習得性的自我評估得分更高;從學習體驗來看,游戲在認知、情感層面的體驗比數字博物館導覽式學習更能獲得學生的欣賞,且在沉浸感、趣味性和挑戰性上的滿意度也更高;從學習主動性來看,實驗組學生在行為、情感、認知上的參與度比對照組學生更高,學習動機也更強烈。

表3 不同組別的非參數檢驗結果
(2)學習效果測試數據分析
不同組別學習效果測試的方差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總分”上差異性極顯著(F=45.857,=0.000),且實驗組的平均得分為73.76,明顯高于對照組的平均得分52.48,這再次證明了游戲對于提升學習效果的作用非常顯著。具體來說,不管是在“人物辨識與理解”(F=31.325,=0.000)、“故事背景理解”(F=12.052,=0.001)還是在“意會知識理解”(F=66.857,=0.000)上,體驗過相關敘事與交互情節的實驗組與沒體驗過的對照組差異性極顯著。唯一的例外是在“文物辨識與理解”上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得分接近,差異性不顯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知識卡片中的內容未引起學習者的重視——游戲中有關文物信息的顯性知識的展示主要依賴于知識卡片,而在訪談中有部分實驗組學生表示他們忽略了游戲界面中進入知識卡片界面的按鈕,故錯過了相關知識點的學習。因此,后續研究需對知識卡片的入口指引方式做進一步優化。

表4 不同組別學習效果測試的方差分析結果
(3)半結構化訪談錄音文本分析
通過對實驗組學生半結構化訪談錄音文本的整理與分析,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對游戲沉浸感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敘事和音樂上,而對游戲趣味性和挑戰性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敘事和關卡設計上。“人物的配音和音樂設計都花了心思,人物形象與性格刻畫很鮮明”,羅同學感嘆道:“很多歷史我之前是不知道的,通過這種對話的形式才理解了這幅畫的背景”;而劉同學認為:“最后故事反轉,原來韓大人是偽裝成了肆意狂放的形象,有一種揭開懸念的感覺。”
此外,超過71%的實驗組學生提到彈奏古琵琶的任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李同學表示:“雖然只有四根弦,但要聽出區別還是比較難,需要一些樂理知識”;王同學則表示“很意外,卡了一會兒才發現這里需要我自己彈琵琶。”感覺“難”“意外”,可能是由于音樂類的互動在文化遺產教育游戲中較為少見而導致。但是,學生對音樂類互動形式的高度關注,也為繼續探索多模態影音交互技術在文化遺產教育游戲中的運用提供了依據。
四 結語
上述數據與錄音文本分析表明,基于體驗式學習模型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對于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效果、學習體驗與學習主動性均有積極作用:游戲所提供的敘事、音樂、交互等多模態交互形式,能夠改善博物館導覽信息呈現方式的單一性,增進學習者對意會知識的理解;游戲提供的浸入式虛擬環境與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能夠有效提升學習者的沉浸感,清晰的任務目標與連環式的關卡設計也大大增加了體驗的趣味性;游戲以寓教于樂的形式開展教育,能夠更好地激發學習者對文化遺產的興趣,使其養成更加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需說明的是,本研究設計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游戲目前僅適用于單人體驗、對學習者的ICT技能有一定要求等。基于此,后續研究將考慮引入動作識別、AR等技術,通過多人協同的交互進一步提升游戲體驗;同時,優化游戲難度調節機制,以減少低齡學習者ICT技能掌握程度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當前的用戶測試場景主要限于校內,以模擬博物館體驗為對照進行研究,在環境真實度上略有不足。因此,后續可與博物館進行合作,在真實的博物館學習場景下進行與游戲體驗的對比實驗,以提高實驗結果的可靠性,進而完善文化遺產教育游戲的設計與應用。
[1]國家文物局.中央宣傳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物局關于推進博物館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OL].
[2]朱曉冬,周明全,耿國華.虛擬博物館開發模式研究[J].計算機應用與軟件,2005,(6):34-35、107.
[3]張斌,李子林.圖檔博機構“數字敘事驅動型”館藏利用模型[J].圖書館論壇,2021,(5):30-39.
[4]Longo F, Nicoletti L, Padovano A, et al. An intelligent serious game for a multi-device cultural heritage experi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and Process Modelling, 2017,(6):498-514.
[5]Malegiannaki I, Daradoumis Τ. Analyzing the educational design, use and effect of spatial games for cultural heritage: A literature review[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7,(5):1-10.
[6]Kolb D.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4:24-25.
[7]王小根,王露露,王心語,等.個性化的體驗式學習活動設計模式的優化[J].現代教育技術,2019,(7):52-58.
[8]楊媛媛,季鐵,張朵朵.文化遺產在嚴肅游戲中的設計與應用[J].包裝工程,2020,(4):312-317.
[9]胡玥,姜友斌,柴惠芳,等.文化傳承視野下博物館電子游戲的設計——以浙江教育博物館電子游戲“文明之旅”為例[J].現代教育技術,2018,(1):52-58.
[10]Bracey G W. The bright future of integrated learning systems[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992,(9):60-62.
[11]魏迎梅.嚴肅游戲在教育中的應用與挑戰[J].電化教育研究,2011,(4):88-90.
[12]Csikszentmihalyi M.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3-4.
[13]Kiili K.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Towards an experiential gaming model[J].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5,(1):13-24.
[14]Hooper G E. Measuring learning outcomes in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The learning impact research Project (LIR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4,(2):151-174.
[15]Mekler E D, Bopp J A, Tuch A N,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the enjoyment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games[A].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C]. New York: ACM, 2014:927-936.
[16]Fredricks J A, Blumenfeld P C, Paris A H. School engagement: Potential of the concept, state of the evidence[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4,(1):59-109.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Game Based 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Taking the Game of “Dream Back to the Banquet in Southern Tang Dynasty” for Example
ZHANG Yu-yang LI Wan-ting LUO Ya-lan NIE Xiao-mei[Corresponding Author]
The exist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mainly relies on the one-way display of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supplement of exogenous materials, and its interactivity and interest cannot meet people’s learning need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ly proposed an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 that integrated gamification design elements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mapping between this model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game. Then, taking the ancient painting of “” as the learning theme, this paper designed a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game named “Dream Back to the Banquet in Southern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is model. Finally, a comparativ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mixed research methods of a questionnaire, a learning effect test, and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evaluate th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game. It was found that the gam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learners’ learning effect,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initiative. This paper made an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and provided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experiential learning;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gamification learning; education game
G40-057
A
1009—8097(2022)07—0048—09
10.3969/j.issn.1009-8097.2022.07.006
張羽洋,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為文化遺產數字化教育與人機交互,郵箱為yuyangz17@foxmail.com。
2021年12月24日
編輯: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