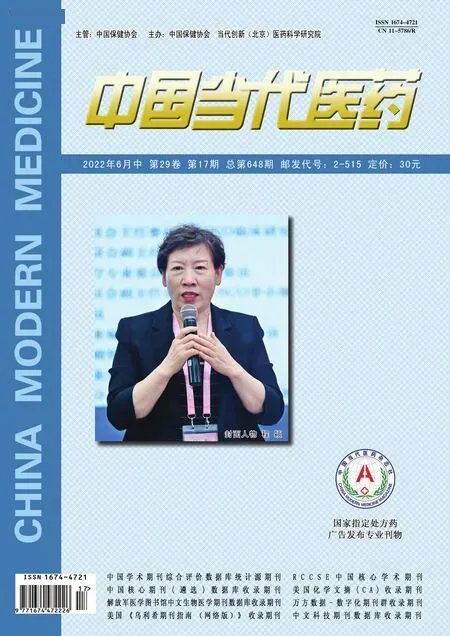音樂干預在老年慢性疾病合并抑郁癥中的應用研究進展
陳 浩 高 原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老年科,重慶 400016
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醫療衛生水平的進步,慢性疾病的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呈上升趨勢[1]。目前我國老年人抑郁癥的患病率較高,2017年的相關調查數據顯示[2],在2180 名≥65 歲的老年人中,抑郁癥狀的檢出率為15.0%,其中男性和女性抑郁癥狀的檢出率分別為11.5%和18.5%。
抑郁癥并非衰老的正常結果,慢性疾病會導致機體功能、認知功能的減退、疼痛及失眠等[3],成為老年抑郁癥的眾多危險因素。抑郁癥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可能會損害患者的機體功能和認知功能,增加死亡率,造成醫療資源與費用的過度消耗等[4]。抑郁癥的特征性表現包括持續情緒低落、失去興趣、負罪感和低自我價值感等,合并抑郁癥的老年慢性疾病患者容易出現以下情況:與治療預期不符的精神或軀體癥狀(食欲減退、睡眠障礙、注意力下降、易激惹等[5]);對標準治療的反應欠佳;參與治療的動機不足;與醫護人員缺乏互動等[6]。抑郁癥的常規治療包括藥物及心理治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抗抑郁藥物接受度低、藥物相關副反應及心理治療較低的依從性等,這些限制在老年人中更加明顯,他們可能會因為對疾病的輕視與病恥感,對以往治療的負面經歷以及機體功能受限而遇到尋求診療的阻礙[7]。關注慢性疾病共病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更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疾病的長程管理,現代音樂干預逐漸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型,音樂干預的積極作用體現在抑郁癥狀的明顯減輕上[8]。本文從音樂干預的定義及類型等方面出發對音樂干預在老年人常見慢性疾病中的應用研究進展作一綜述,期望能為臨床治療提供資料借鑒。
1 音樂干預
音樂具有誘導積極情緒和放松身心的作用,音樂干預的抗抑郁作用可能是通過對中樞神經血清素傳遞和海馬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水平的影響來介導的[9]。基于音樂的干預措施分為兩大類:音樂治療和音樂醫學。音樂治療是一個系統的干預過程,由音樂治療師以循證的方式通過專門設計的音樂形式,以及過程中形成的治療關系作為治療動力來幫助被治療者達到身心健康的目標[8]。音樂醫學是由未取得資質的人員提供的以音樂聆聽為主的干預措施,其成本更低,資源占用更少,主要在非治療性環境中使用,干預后可能會發生精神或生理的變化,但它不是以目標為導向的,也不是基于專業知識和循證依據的[10]。音樂治療主要分為主動型音樂治療和接受型音樂治療。主動型音樂治療中,音樂治療師使用即興、創作或再創作的方法,通過演奏樂器和演唱等形式鼓勵患者積極參與音樂的制作,幫助患者與患者、家屬及治療人員建立社交聯系,利用音樂增加表達和交流而獲得更多改善抑郁癥狀的機會[11]。接受型音樂治療包括音樂聆聽放松、音樂回憶、歌曲討論、音樂引導性想象等,作為一種非語言交流形式,音樂可以幫助患者減輕壓力和焦慮,改善睡眠質量,達到減輕抑郁癥狀的目的[12]。
2 音樂干預在老年慢性疾病中的應用
由于常規藥物治療及心理療法對認知功能的要求較高,而音樂干預對老年人的認知需求相對較小[13],老年人尤其受益于這種非侵入性治療。將音樂治療與標準治療相結合,在減輕老年人的抑郁癥狀及降低五年內死亡的總體風險方面具有統計學意義[14]。一項為期24 周的療養院音樂治療研究結果顯示,音樂治療組成員的老年抑郁量表(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得分明顯下降,對照組沒有顯著變化,且組間差異在治療后8 周持續存在[15]。目前為老年慢性疾病患者探索了多種音樂干預方法,從音樂聆聽到休閑歌唱,再到由受過專門訓練的音樂治療師進行的音樂治療,它們具有無創、高安全性、良好依從性及成本效益比等特點[16],近些年在各種醫療保健環境和各個疾病階段得以迅速發展。
2.1 癡呆癥
癡呆癥的特征是在記憶力、注意力、語言或執行功能等至少兩個認知領域的功能下降。抑郁癥與認知功能障礙有關,2018年一項關于癡呆癥患者的抑郁患病率的薈萃分析發現,25%的癡呆癥患者和16%的輕度認知障礙患者表現出抑郁癥狀[17]。一項對1470名記憶門診患者的調查發現,非癡呆癥患者的抑郁水平低于癡呆癥患者[18]。此外抑郁癥被發現會增加癡呆癥的患病風險[19],因此抑郁癥既可反映癡呆癥的原發階段,也是癡呆癥的獨立危險因素。研究人員發現,阿爾茨海默病患者較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在音樂歌唱和節奏活動中表現更為活躍[20],研究強調音樂對大腦的積極影響,音樂可以通過增強大腦可塑性和誘導大腦中心連接的建立來減少神經元退化。由于受癡呆影響的大腦內側額葉和邊緣區域相對保留,即使在疾病的晚期階段語言功能出現減退時,音樂引起的情緒和記憶也得以保留[21]。音樂提供了與癡呆癥患者聯系的方式,輕度認知障礙到重度癡呆的患者都可以使用基于音樂的治療干預[22]。在臨床實踐提供的各種音樂干預形式中,音樂聆聽和團體歌唱的方法最常用于癡呆癥患者。音樂聆聽加強了患者對聲音、節奏和歌詞的感知與反應,與廣泛的皮層激活相關[21]。團體歌唱能夠以相對較低的門檻使癡呆癥患者參與社交及認知訓練,且參與的積極性高于接受音樂傾聽的癡呆癥患者[23]。有研究觀察結果顯示,中期(6~12 周)音樂干預比長期音樂干預對癡呆癥患者的抑郁癥狀影響更大[21]。音樂干預對癡呆癥患者的情緒、認知、記憶和行為均有積極的影響。Cooke 等[24]將患有癡呆癥的老年人隨機分組后,對試驗組成員以現場演奏音樂的形式進行干預,運用GDS 評估發現試驗組成員抑郁癥狀有所改善;我國臺灣的研究人員選取合適的樂曲作為41 例癡呆癥住院患者用餐的背景音樂播放,8 周后干預組成員的簡明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評分較試驗前顯著降低[25],提示音樂聆聽后認知功能可能得到改善;音樂回憶療法中利用音樂對記憶的刺激作用來引發和改善患者的記憶,延緩記憶力衰退的過程[26];當沒有受過規范培訓的照護人員在日常護理中帶領癡呆癥患者唱歌時,常見的攻擊行為和困惑反應頻率較護理前減少[27]。
2.2 老年衰弱綜合征
老年衰弱綜合征的特征是維持多個生理系統的儲備能力降低超過其實際年齡的水平,表現為無誘因的體重減輕、疲乏感、肌肉量減少、步行速度慢和體力活動下降[28]。它涉及多系統的病理生理改變和精神心理變化,如容易加重機體的退行性改變、增加易損性和抗應激能力減退,易導致焦慮抑郁癥狀和認知功能下降等[29]。這是一個緩慢、動態且可逆的過程,有研究顯示,使用持續12 周、每周120 min 的音樂聆聽聯合體育鍛煉后,與對照組相比,音樂與體育鍛煉治療組的GDS 評分有明顯下降,通過體能測試發現,音樂與體育鍛煉治療組的下肢肌肉耐力有顯著改善[30]。
2.3 腦卒中
腦卒中后抑郁癥(post-stroke depression,PSD)與腦卒中事件后的功能恢復不佳和生活質量低下有關,PSD 可能在急性腦血管事件后發生,也可能在大腦的慢性缺血性改變中發展[31]。PSD 的流行高峰期發生在腦卒中事件后3~6 個月[32],有接近1/4 的腦卒中幸存者經歷了腦卒中后早期的抑郁,而在腦卒中事件發生5年后,這一比例上升到1/3[33]。音樂可以激活額葉系統,促進杏仁核、海馬和伏隔核的邊緣和邊緣旁系統的改變,這些區域的變化與PSD 患者的負面情緒減少相關[34]。音樂促進腦卒中后康復的研究表明,音樂通過促進感覺運動皮層的神經連接和神經元重組,促進運動系統的可塑性變化[35]。關系型主動音樂干預(relational active music therapy approach,RAMT)是一種基于患者和音樂治療師在治療環境中使用有節奏的旋律樂器(即木琴、鐘琴、鼓、小鼓、民族打擊樂器等)的自由互動,樂器的使用增加了患者和音樂治療師之間的交流和共鳴,促進了患者情感的表達和分享;同時樂器的使用刺激了特定的運動功能,特別是上肢大小關節及肌肉得到鍛煉。干預組患者癱瘓的上肢運動及力量(握力)有明顯改善。RAMT 不但改善了腦卒中患者的抑郁癥狀,促進了運動功能的康復,同時腦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質量也得到了提升[36]。
2.4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與抑郁癥是相互影響的,心肌梗死后患者并發抑郁癥較常見[37],抑郁癥的患者發生CVD 的風險明顯增加[38]。音樂作為一種聲波信號,在耳蝸處轉變成神經信號經聽神經上傳至中腦和蝸神經核,最終到達聽覺丘腦、杏仁核,起源于杏仁中央核的神經纖維直接到達腹外側延髓的心血管調節中樞,以上通路的存在可能提供控制心血管反射的作用,從而影響內分泌系統,來發揮生理作用,如可能會影響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的分泌,進一步對局部心臟活動、心率、心率變異性、血壓和呼吸頻率的調節產生影響[39];通過音樂聆聽引導緩慢而有規律地呼吸,可能會影響一氧化氮在血液中的濃度,使高血壓患者的呼吸頻率和血壓有所下降[40]。
2.5 癌癥與慢性疼痛
一項納入94 項訪談研究的薈萃分析[41]顯示,30%~40%的癌癥患者可能會遭受焦慮和抑郁的心理困擾,這些反應與癌癥的診斷和疾病進展等因素密切相關,會進一步影響癌癥患者的治療依從性、生活質量、自愈能力和總體生存率。此外癌癥導致嚴重的疼痛,會極大程度地阻礙抑郁癥狀的改善[42]。在癌癥患者的姑息性治療中,音樂療法是有效且常用的非藥物方法來管理疼痛癥狀,音樂可能上調人體內的血漿內啡肽的水平,內啡肽是一種內源性阿片肽,可產生較強的鎮痛作用[43]。一項納入19 項試驗783 例癌癥患者的薈萃分析發現[44],音樂干預能有效改善癌癥患者的抑郁和疼痛癥狀,并且可以改善癌癥患者的整體生活質量,觀察到的合適干預時間為1~2 個月[41]。
3 總結與討論
音樂治療的總體目標在于減少老年人的行為和心理癥狀,減輕照護人員及醫療系統的負擔。對于老年慢性疾病患者而言,了解抑郁癥狀的改善是否轉化為更現實的結果,如日常生活質量及生活滿意度的改善,這將很有必要[45]。現有的研究結果令人鼓舞,但考慮到我國音樂治療相關的培養及開展整體起步較晚,為了讓醫療保健人員和療養院管理人員更深入地了解并接受音樂干預的理念,并提升國內在未來醫養結合大趨勢下推廣應用的可能性,以下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論證。
3.1 音樂干預標準化
在已發表的原始研究和系統性評價中普遍缺乏有關音樂干預整體框架及實施細節的信息,例如:具體的干預目標;總體時間框架及每次干預的持續時間;干預方法的選擇依據;音樂傳播途徑(現場表演、揚聲器或耳機)以及干預人員的培訓細節等。以上內容的重復與改進,有助于結構化音樂干預形式的形成,提高在臨床研究和實踐中的可復制性,也有助于形成基于音樂有效干預的知識體系及共識指南。需要注意的是,音樂干預不能作為“處方”被提供[46],標準化本身也并不是一個目標,在臨床實踐中,音樂干預人員必須不斷調整治療目標以適應不同疾病的個體,在保留靈活性與標準化治療之間尋得一個平衡點。
3.2 療效評估的一致性及客觀化
用于評估音樂干預療效的方法及選擇是多種多樣的,療效評估一致性的缺乏是回顧性審查研究中的一個常見問題,易導致不同研究之間的結果偏差過大[21],因此需要保證療效評估工具的一致性。音樂干預的結果可能受測試患者即時身體及心理狀態的影響,且大多數研究使用基于自我評估的問卷,未來應該考慮增加基于生理反應的測量,例如血壓、心率和呼吸頻率或利用皮膚電導、腦電圖、血清學指標等監測手段[47],以提高療效評估的客觀性。
3.3 音樂干預研究的規模化及長期化
音樂干預產生的影響并非立竿見影的[21],對于認知功能、記憶功能及機體功能在短時間內難以觀察到顯著的變化,多數音樂干預的受益效果在第6 周甚至第12 周之后方能體現出來[10]。且多數臨床試驗的樣本量均偏小,未來的研究應考慮設計更大樣本、多中心以及漸進持續的干預方案,收集縱向數據并進行更長時間的隨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