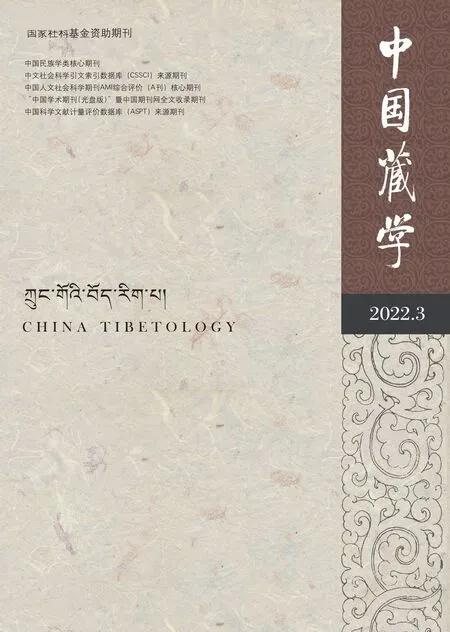大慧法王與明代五臺山漢藏佛教交融①
——以碑刻資料為核心
朱麗霞
五臺山是明代藏傳佛教在內地傳播的核心區(qū)域之一。關于明代五臺山藏傳佛教傳播情況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崔正森《五臺山佛教史》的相關章節(jié)、趙改萍《簡論明代藏傳佛教在五臺山的發(fā)展》①趙改萍:《簡論明代藏傳佛教在五臺山的發(fā)展》,《西藏研究》2005年第4期。、陳楠《釋迦也失在南京、五臺山及其與明成祖關系史實考述》②陳楠:《釋迦也失在南京、五臺山及其與明成祖關系史實考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這些成果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其一,以大寶法王、大慈法王為代表的西藏高層僧侶在五臺山的活動;其二,明代五臺山的藏傳佛教寺廟創(chuàng)建及修復情況;其三,明代五臺山藏傳佛教的發(fā)展特征。通過五臺山的碑刻資料,可以發(fā)現(xiàn)明朝在五臺山還冊封了一位大慧法王,這應是明代五臺山藏傳佛教乃至整個藏傳佛教發(fā)展中值得關注的事件,但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除了杜常順的《明朝宮廷與佛教關系研究》《明代藏僧駐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論教派色彩與法脈傳承》③杜常順:《明朝宮廷與佛教關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21頁;杜常順:《明代藏僧駐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論教派色彩與法脈傳承》,《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但杜常順在《明朝宮廷與佛教關系研究》中認為大慧法王張堅參可能來自河州弘化寺,而在《明代藏僧駐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論教派色彩與法脈傳承》一文中,進行了修訂,認為他有可能是來自燕山以北的漢人。略有提及此人外,其他的論著多未涉及。事實上,以大慧法王為核心,明代五臺山還有部分藏傳佛教僧人擔任了僧錄、僧綱等職務。在捐款修寺、建塔的普通僧眾中,也能看到藏傳佛教僧人的名字。也就是說,以大慧法王為中心,明代五臺山存在著一個數(shù)量較為龐大的藏傳佛教僧團。根據(jù)嘉靖三十六年(1557)所立的《皇明五臺開山歷代傳芳萬古題名記》碑文記載,這其中地位較尊崇的主要有:制授靜覺廣智妙修慈應翊國衍教灌頂贊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桑節(jié)朵而只、欽差提督山西五臺山鈐制番漢一代寺宇兼住大圓照寺誥封萬行通明妙悟大覺宣仁闡教崇禧廣智護國衍梵普濟大慧法王西天弘慈莊嚴大吉祥佛朵而只堅參、欽差提督山西五臺山兼管番漢一代寺宇兼住演教等寺禪師朵而只乳奴、欽差提督山西五臺山兼管番漢一代寺宇僧錄司右覺義亦失堅剉、欽差提督山西五臺山兼管番漢寺宇誥封清修禪師端竹班丹。④秦建新、趙林恩、路寧、徐翠蘭點校:《五臺山碑刻》,太原:山西出版?zhèn)髅郊瘓F·三晉出版社,2017年,第374、377頁。這些人中,又以大慧法王朵而只堅參地位最高。
一、大慧法王受冊封時間
法王作為朝廷封授給藏傳佛教僧人的最高名號,明初都授予了藏傳佛教各派的領袖,使他們在藏地“化導弭患”⑤何孝榮:《明代皇帝崇奉藏傳佛教淺析》,《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3頁。。也就是說,他們本身就是藏地政教領袖,在受冊封后,又進一步成為明朝管理西藏地方事務的重要輔助者。但后來隨著明朝諸帝對藏傳佛教的崇信,留在京城的藏傳佛教僧人不斷地被冊封為法王,這顯然與明初統(tǒng)治者的施政初衷有了距離。新冊封的法王,有的只是基于統(tǒng)治者自身的宗教信仰需求,甚至只是基于個人的好惡,因為在這些法王中,有些完全沒有參與西藏事務的履歷。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長期駐留在京城,去藏遙遠,也難以在西藏事務中發(fā)揮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明憲宗在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84—1486)間,突擊冊封的10位法王⑥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堅剉、乳奴班丹,大能仁寺西天佛子鎖南堅參、結斡領占俱為法王。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舍剌星吉、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著癿領占、朵而只巴為法王。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升西天佛子卜剌加為法王,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領占為法王。,他們中大部分人與西藏地方事務無涉。⑦詳見《明憲宗實錄》卷248—285,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4195—4828頁。但明朝在五臺山冊封的大慧法王則具有特定的職能——管理五臺山的漢藏佛教寺院。
關于大慧法王受冊封的情況,依據(jù)五臺山的碑刻資料,最詳細的記載出現(xiàn)在圓照寺的“明成化皇帝圣旨碑”碑文中:奉天承運……皇帝……萬物……要者,國家必禮遇褒嘉之。爾朵而只堅參□□□之法性,能融□□□□□□,宣如來之妙旨,眷慈善德,宜有褒崇,今特封為萬行通明妙悟大覺宣仁闡教崇僖廣智護國衍梵普濟大慧法王西天弘慈莊嚴感應大吉祥佛。于戲!□□□□,□□清凈之風,贊我鴻圖,茂衍升平之福。允其祗服,用光訓詞……本峰頂蓋造新寺,一□以為本寺院內鐵瓦殿……銅佛,文殊菩薩像百尊,僧房六十余間,并石塔、□墻等具云。欲為服……爾□賜寺額曰演教。仍升剌麻僧朵而只乳奴為禪師兼住,亦室……本山番漢僧眾人等,特命爾領敕提督管理兼住圓照寺,領□□□□,其□□□之。故諭。①《五臺山碑刻》,第211頁。

關于朵而只堅參受封為大慧法王的時間有待考辨。其一,雖然上述圣旨碑被《五臺山碑刻》定名為“明成化皇帝圣旨碑”,其立碑時間也被整理者認定為明憲宗成化七年(1471),但根據(jù)現(xiàn)存拓片,“年九月十四日”之前的內容風化嚴重,難以辨認。③《五臺山碑刻》,第212頁。其二,時人謝蘭撰《重修圓照寺碑記》④此碑是隆慶三年(1569)重立的,第一次立碑時間不詳。提到圓照寺“于嘉靖丁未年欻燃焚之,茍延歲月”⑤《五臺山碑刻》,第216頁。,于是“自京城堅參師法王張”⑥此處指的就是朵而只堅參。等人參與重建,重建始于嘉靖丁未年,即嘉靖二十六年(1547)。如果朵而只堅參是在1471年被封為法王的,那么到1547年,時間過去將近80年了。即便以他在二十幾歲便被封為法王計算,這時他也超過百歲之齡了。一位百歲老人登塔實地勘察、參與寺院重建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朵而只堅參冊封時間應該晚于成化七年。實際上,參照明代的其他文史資料,也可以證實這一點。
除了碑銘,在《明實錄》《明史》等官方資料中,雖然并沒有關于朵而只堅參被封為法王的記載,但《明實錄》中有兩條關于他的其他記載。第一條是正德四年(1509)八月,他被任命為左覺義:
癸亥,司禮監(jiān)傳旨升大隆善護國寺國師著肖藏卜為法王,剌麻羅竹班卓、班丹端竹、班卓羅竹、朵而只堅參俱為左覺義。
第二條是正德五年(1510)七月,他被升為國師:
令大隆善護國寺國師星吉班丹、禪師班卓羅竹俱升佛子,禪師羅竹班卓、班丹端竹、朵而只堅參升國師。⑦《明武宗實錄》卷53,第1203頁;《明武宗實錄》卷65,第1429頁。
此處需要說明的是,朵而只堅參出家于北京大隆善護國寺,后入五臺山管理僧眾,因此明朝官方將其視為大隆善護國寺僧人。明朝藏傳佛教僧人封號遞進遵循的是“禪師—國師—佛子—法王”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他被封為法王一定在正德五年之后。而在正德七年(1512)十月所立的修建大隆善寺的“僧眾職名”碑中,朵而只堅參的身份是國師(弘慈翊教國師)。①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3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9頁。所以,可以將朵而只堅參被封為法王的時間,進一步確定在正德七年十月之后。如果再結合鎮(zhèn)澄《清涼山志》所說的“正德間,封張堅參為法王,賜銀印,兼有都綱印”②[明]鎮(zhèn)澄撰:《清涼山志》,載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9冊,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第69頁。,則他被封法王,必定在正德年間。如此,朵而只堅參被封為大慧法王,只能是在正德七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間。
另外,在冊封朵而只堅參為大慧法王的圣旨碑③《一 明成化皇帝圣旨碑》,載《五臺山碑刻》,第211頁。中,還有其他的線索可以佐證這一時間。這份圣旨的后半部分提到了當時新建的、有鐵瓦殿的、被賜寺額的演教寺。《清涼山志》中關于演教寺有這樣一條記載,即正德七年春季,又“敕梵僧朵而只堅,于中臺頂,建寺一區(qū),鑄鐵為瓦,賜額曰演教,并敕旨護持”④《清涼山志》,第215頁。。這里的“朵而只堅”,應當是朵而只堅參漏寫了“參”字。演教寺建成后,曾有“敕旨”,這與敕封朵而只堅參的圣旨后半部分內容相符合。演教寺從正德七年春季開始建造,建成時間缺乏記載,但應該是在正德七年十月以后。因為按照前面“僧眾職名”碑記載,十月份時,朵而只堅參還是國師身份。但演教寺建成后,他被封為法王,這兩件事出現(xiàn)在同一份圣旨里。藉此,順帶可以確定的是冊封朵而只堅參為大慧法王的圣旨碑立于正德年間,而不是《五臺山碑刻》所說的成化七年。
至于朵而只堅參被封為大慧法王的原因,按照圣旨的內容,是因為他能“宣如來之妙旨,眷慈善德”,也就是基于其佛教修為。但實質上,這一類說法基本上屬于明朝圣旨中常見的套話,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正如下文所述,朵而只堅參屬于岷州大崇教寺法系,所以他被封為大慧法王可能與此有關。明代,大崇教寺僧人與中央政府關系密切,深受明統(tǒng)治者的倚重與尊崇,先后有多名僧人被封為法王、國師等,其中有史可查的主要有: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封班丹扎釋為大智法王;景泰七年(1456),封沙加為大善法王;正統(tǒng)元年(1436),封綽竹藏卜為凈覺慈濟大國師;正統(tǒng)十年(1445),封班卓藏卜為清心戒行國師;景泰六年(1455)左右,封鎖南領占襲為慈濟大國師。成化二十二年,封著癿領占為法王,⑤杜常順:《明朝宮廷與佛教關系研究》,第119—120頁。再加上國師西天佛子桑節(jié)朵而只和朵而只堅參師徒,數(shù)量不少。這些僧人大都留京居于大隆善護國寺(朵而只堅參師徒在五臺山也多有活動),互相之間不僅具有法緣關系,部分人還具有血緣關系,例如沙加為班丹扎釋的弟子,綽竹藏卜、班卓藏卜為班丹扎釋的侄子。所以,明代岷州藏傳佛教僧人互為援手,在京城和五臺山形成了龐大的勢力集團。朵而只堅參作為這個團體中的一員,他受封為法王應該與此關系密切。
那么,如何解讀五臺山正德七年之前的碑刻中出現(xiàn)大慧法王的現(xiàn)象呢?在五臺山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碑刻有兩通,其中一通是刻于成化年間的圣旨碑;⑥《二 明成化皇帝圣旨碑》,載《五臺山碑刻》,第213—215頁。另一通是弘治十三年(1500)的“五臺山重建殊祥寺記”碑。第一通立于圓照寺中,此碑分為上中下3欄,上中兩欄分別刻寫了明憲宗成化十七年(1481)的兩份圣旨,下欄是一份成化八年(1472)的圣旨。這3份碑文都與圓照寺的端竹班丹有關,成化八年的圣旨敕命端竹班丹住持圓照寺;成化十七年的兩份都是擢升圓照寺都綱短竹班丹(應為端竹班丹)為清修禪師,并下令軍民人等不得侵擾圓照寺的圣旨。在這3份圣旨的正文之后,陳列了5位具有管理身份的僧人,第一位便是“欽差提督山西五臺山鈐制番漢一帶寺宇兼住大圓照寺誥封萬行通明妙悟大覺宣仁闡教崇僖廣智護國衍梵普濟大慧法王西天弘慈莊嚴感應大吉祥佛”。①《五臺山碑刻》,第215頁。第二通碑——“五臺山重建殊祥寺記”的后面,也列有“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寺宇大慧法王朵而只堅參”。要解讀此類碑刻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大慧法王的現(xiàn)象,就要結合兩個方面的現(xiàn)象進行分析。第一個是五臺山的明代碑刻具有一個普遍性的特征:在立碑之時,無論當時管理五臺山佛教事務的高階僧人是否真正參與過碑刻中所記的事件,他們的名字都會被列在碑文之后,以示尊崇,并彰顯其作為管理者的身份。②例如,弘治元年(1488)所立的《重修旃檀林碑記》,碑末就列出了欽差提督五臺山掌管番漢一代寺宇兼住大圓照文殊寺誥封清修禪師端竹班丹、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寺宇僧錄司左覺義兼大顯通住山沙門旺署庵等管理五臺山佛教的僧人(《五臺山碑刻》第846頁)。就碑文的內容來看,這些人并沒有參與旃檀林的修建工作。弘治十七年(1504)所立的《敕賜普濟禪寺孤月澄禪師行實塔銘》,主要講述了孤月凈澄禪師的生平,但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僧綱司都綱兼廣緣寺主持啰納忙葛剌、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僧綱司都綱兼大吉祥顯通寺主持普顯列在碑末(《五臺山碑刻》第456頁)。這二人雖然與孤月凈澄沒有關系,但作為五臺山僧綱司的都綱,屬于當時五臺山佛教的管理者,所以就名列碑刻之上了。由此可以肯定這兩通碑立于大慧法王在五臺山行使管理權期間。第二個現(xiàn)象是明代五臺山的少數(shù)石碑刻立時間與相應的圣旨頒發(fā)時間并不同步,應該是圣旨下達時所立的石碑損壞,后又重新刻立,但并沒有改變碑刻的內容。對應到成化年間的圣旨碑,也應當是在朵而只堅參被封為法王后的某個時期,重立了石碑。成化八年和十七年的圣旨被刻在同一通碑上,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圣旨頒布時間和立碑時間非同步性。而在這通碑重立時,作為以圓照寺為活動基地的大慧法王,必然要位列眾僧之首。另外,成化年間五臺山樹立的碑刻很多,只有一通碑文中有大慧法王的名號,如果按照《五臺山碑刻》的解讀,朵而只堅參在成化七年被封為法王,③《五臺山碑刻》在碑文湮滅不清的情況下,將冊封大慧法王的圣旨碑樹立時間解讀為成化七年,很可能是根據(jù)三欄圣旨碑中最早的時間——成化八年(這個時間在碑刻上是清晰的)推測出來的。那么,此后的碑刻中應該都列有他的名字,然而其他碑文中都沒有,這就反證了朵而只堅參不可能在成化七年就被封為法王。根據(jù)五臺山的碑刻記載,大慧法王在五臺山集中活動的時間是在嘉靖年間(1522—1565),這個問題下文有詳論。
另外,在聲稱立于弘治十三年的第二通碑——“五臺山重建殊祥寺記”的陰面,所刻的前幾位人物分別為:
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寺宇僧錄司左覺義明玄
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寺宇大慧法王朵而只堅參
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寺宇僧綱司都綱明續(xù)
敕建圓照寺住持圓□ □□④《五臺山碑刻》,第541頁。
居于首位的明玄,其被授予僧錄司左覺義的時間是在正德十年(1515),這個有專門的敕封圣旨碑①即《皇帝敕諭五臺山左覺義明玄碑》,載《五臺山碑刻》,第11頁。以及立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明代卷案碑”②《五臺山碑刻》,第13頁。可以佐證。因此,這通碑的正面與背面的事件、人物存續(xù)時間之間有明顯的出入,即碑陰的人物所擁有相關封號、官職,都是出現(xiàn)于明武宗正德年間。這通碑立碑時間“大明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秋八月 日立時”③同上,第541頁。位于碑陽,說明其碑陰很可能是在正德或嘉靖時期才添加的,或者被磨平重新雕刻了內容,這種現(xiàn)象在碑刻中也屢有出現(xiàn),④參見劉友恒、張永波、梁曉麗:《隆興寺康乾御碑現(xiàn)狀與記載不符原因探考》,《文物春秋》2020年第1期。當時為將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御碑立于寺院顯要位置,督造者周元理將立在大悲閣前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兩通御碑一碑陽、二碑陰進行了改動。目的是為了凸顯當時當權者的地位。具體到上述“五臺山重建殊祥寺記”中,就是為了加入明玄、朵而只堅參等當時五臺山的管理者。
二、大慧法王的族屬及師承
朵而只堅參雖然被封為法王,但他本人并非藏族,而是一位漢人,一位修學藏傳佛教的漢人,這點可從明代各類史料對他的稱呼中得到印證。鎮(zhèn)澄的《清涼山志》中稱其為“張堅參”,甚至在提到法王寺時直接說“明張法王建”。⑤《清涼山志》,第70頁。五臺山的碑刻中也曾稱其為“堅參師法王張”。⑥《五臺山碑刻》,第216頁。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看,他是一位張姓漢人,“朵而只堅參”是他跟隨藏傳佛教僧人學法后所起的法名。
在師承關系上,根據(jù)《明故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大國師張公墓塔記》的記載,朵而只堅參與前面《皇明五臺開山歷代傳芳萬古題名記》提到的西天佛子大國師桑節(jié)朵而只(1445—1512)是師徒關系,桑節(jié)朵而只去世后,正德七年朵而只堅參為其立塔。⑦詳見杜常順:《明代藏僧駐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論教派色彩與法脈傳承》,《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2頁。《明故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大國師張公墓塔記》的碑頭上刻的是《明故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大國師張桑節(jié)墓塔記》,說明朵而只堅參的師父也是一位漢人,因而又被稱為張桑節(jié),或者直接按照漢人的稱呼習慣稱其為“張公”。桑節(jié)朵而只雖為漢人,但他作為朝廷的特使去過西藏,并師從藏族僧人學習藏傳佛教密法,這些都記載于他的《墓塔記》中:
公姓張氏,諱桑節(jié)朵而只,其先世山后人。景泰年未⑧未,疑為“末”——本刊編者。禮清心戒行國師為師。及長,成化庚寅奉敕命差往烏思藏,封闡化王國王,到彼處彰我圣朝及封恩赍之典。當時公之德化番夷,道□殊域,至于乙亥方回京師,蒙賜宴,升國師,封凈慈利濟。弘治乙酉,彰□請公于天寧寺講習觀法。庚戌隱跡于五臺山圓照寺,修習本佛啞曼答葛功課,加持六字真言。逮正德辛未,崇尚秘教,命譯寫各佛修習講說秘密成法,上聞大悅,遂宴賞。壬子加升西天佛子,……賜金印一顆,重三百五十兩,加封清覺廣智妙修慈應翊國衍教灌頂贊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公生于正統(tǒng)乙丑年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八。
長徒國師卜以是年九月十五日葬公于塔,以謹終也。正德七年冬十月十七日立石。⑨參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3冊,第181頁;黃顥:《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15頁。但二者的碑刻文字,在許多地方有明顯出入。
因為朵而只堅參與其師父同為張姓漢人,所以他“很有可能與其師桑節(jié)朵兒只兼有法緣和血緣兩重關系”①杜常順:《明代藏僧駐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論教派色彩與法脈傳承》,《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2頁。,也就有可能同樣來自“山后”,即燕山以北地區(qū)。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曾經(jīng)“徙山后民萬七千戶屯北平”②(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2,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6頁。,朵而只堅參師徒應該就是此次遷到北京的“山后”人后裔。桑節(jié)朵而只之師“清心戒行國師”,就是來自岷州的大崇教寺僧人班卓藏卜,其于景泰四年(1453)被封為“灌頂清心戒行國師”③《明英宗實錄》卷230,《廢帝郕戾王附錄》卷48,第5025頁。,到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被升為灌頂大國師時,前面冠以“大隆善護國寺”的限定語。④《明憲宗實錄》卷159,第2905頁。所以,盡管朵而只堅參師徒是漢人,但在法脈上,則出自正宗的藏傳佛教法系。桑節(jié)朵而只跟隨班卓藏卜學法的地方是在大隆善護國寺,而朵而只堅參跟隨桑節(jié)朵而只修學藏傳佛教的時間,既有可能是桑節(jié)朵而只隱居圓照寺期間,也有可能是二人皆在大隆善寺期間。因為在《明實錄》中,朵而只堅參也被歸在大隆善護國寺僧人之中。
至于朵而只堅參具體修學的藏傳佛教法門,目前不得而知了,只能根據(jù)其師桑節(jié)朵而只所修之法反推一二。在桑節(jié)朵而只《墓塔記》中提到,他所修的是“本佛啞曼答葛”,即本尊大威德金剛(Yamāntaka,閻魔德迦),為文殊菩薩忿怒相,在五臺山修此法門,大約更為相應。除此之外,他還修持六字大明咒。朵而只堅參既然師從桑節(jié)朵而只,其所習應該也以這兩種法門為主。
三、大慧法王在五臺山的活動
在社會活動方面,朵而只堅參不像其師桑節(jié)朵而只那樣具有被派往西藏的功業(yè),他的主要貢獻集中在促進五臺山佛教發(fā)展方面。根據(jù)五臺山碑刻,朵而只堅參被明武宗封為法王后,在五臺山的活動一直持續(xù)到明世宗時期,甚至可以說,他在五臺山活動的活躍期主要就在明世宗時期。這一點從他在五臺山碑刻中的出現(xiàn)情形便可呈現(xiàn)出來:⑤《五臺山碑刻》,第541、465、829、474、428、63、1083、374、217頁。

碑刻名稱 時間 朵而只堅參名號五臺山重建殊祥寺記 1500(?) 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寺宇大慧法王朵而只堅參皇明五臺山敕賜普濟禪寺太空滿禪師重修功德記并系 嘉靖四年(1525) 欽差提督五臺山番漢寺宇圓照住山國師朵而只堅參塔苑溝經(jīng)幢 嘉靖六年(1527) 兼住敕建大圓照寺大慧法王朵而只堅參空禪師靈塔記并銘(碑陰) 嘉靖十六年(1537) 欽差提督五臺兼管番漢寺宇弘慈翊教國師兼大圓照寺住山朵而只堅參五臺山敕賜普濟禪寺開山第三代住持太五臺山金剛窟般若寺重開山第一代住持嗣臨濟二十四世寶山玉公大和尚緣起實行功德碑嘉靖十七年(1538) 欽差提督五臺兼管番漢一帶寺宇弘慈翊教國師大圓照住山堅參佛真身舍利寶塔碑并銘 嘉靖十七年(1538) 欽差提督五臺鈐制番漢一帶寺宇弘慈翊教國師兼大圓照寺住山堅參誥封西天佛子大慧法王五臺山大塔院寺重修阿育王所建釋迦文

碑刻名稱 時間 朵而只堅參名號五臺山紫府廟重修殿廊碑記并銘 嘉靖十九年(1540) 敕建大圓照寺主持堅參皇明五臺開山歷代傳芳萬古題名記 嘉靖三十六年(1557)欽差提督山西五臺山鈐制番漢一代寺宇兼住大圓照寺誥封萬行通明妙悟大覺宣仁闡教崇禧廣智護國衍梵普濟大慧法王西天弘慈莊嚴大吉祥佛朵而只堅參重修圓照寺碑記(重立) 隆慶三年(1569) 堅參師法王張
可見,朵而只堅參在五臺山碑刻中出現(xiàn)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明世宗的嘉靖朝,這也顯示出明朝對五臺山佛教的管理措施是一以貫之的,并沒有隨著明世宗的崇道而發(fā)生改變。至于他在五臺山活動的具體起始時間,史料中并沒有記載。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就是他為桑節(jié)朵而只立碑時,身份雖然還是國師,但稱號前面已經(jīng)有了“敕提督五臺鈐制番漢”①《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3冊,第181頁。的字樣,也就是說他在正德七年以前,就在管理五臺山的佛教事務。至少在政府層面,明代對五臺山的佛教并沒有“番漢”的區(qū)分。在許多圣旨碑里,皇帝給漢藏管理者的權限中都有“提督五臺山”“管理番漢僧寺”的職權,②《皇帝敕諭五臺山左覺義定旺碑》,參見《五臺山碑刻》,第4頁;《塔苑溝經(jīng)幢》,參見《五臺山碑刻》,第829頁。而且,這些名號都不是虛稱,擁有這些名號的僧人都實實在在地參與了五臺山佛教事務的管理。
就朵而只堅參而言,他除了在五臺山修成了前面提及的法王寺和演教寺外,還參與了五臺山許多寺塔的重修工作,以此來維護和推進五臺山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據(jù)嘉靖十七年所立的《五臺山大塔院寺重修阿育王所建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寶塔碑并銘》記錄,朵而只堅參在這次重修舍利塔中親力親為,與欽差提督五臺兼管番漢一帶寺宇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吉祥顯通寺住山明玄、欽差提督五臺兼管番漢一帶寺宇僧綱司都綱兼大吉祥顯通寺住山明續(xù)等人登塔查看,設計重修方案。在塔修成之后,“法王、覺義、徹天、天竺四師”又讓祖印寫了碑銘。③《五臺山碑刻》,第62頁。另外,在“嘉靖丁未年”(1547),圓照寺遭火災之后,他偕同五臺山的僧俗人眾對之進行了重修。④《重修圓照寺碑記》,參見《五臺山碑刻》,第216—217頁。在這之后,五臺山的碑刻中就沒有關于他的記錄了,直到嘉靖三十六年,他出現(xiàn)在具有總結性的《皇明五臺開山歷代傳芳萬古題名記》碑中。所以,朵而只堅參應該在1547—1557年間去世了。
因為大慧法王在五臺山的主要活動以修建寺院為主,導致在他之后,五臺山的僧人將許多寺院的修建都歸功于他,充分說明五臺山僧人對大慧法王的認可。在明人李維楨(1547—1626)的《五臺游記》中,這種現(xiàn)象躍然紙上:
過羅睺寺,初有西域法王,至今奉香火者,多番僧,去來不常,悉能為漢語。問之,則河州弘化寺僧也,巳。過圓教寺,亦以法王建。有銀印,曰清修禪師,后葬山中,巳。過廣宗寺,亦以法王建,有鐵瓦殿,欲置臺上,而難以轉運,遂置諸此……巳。過文殊寺,亦以法王建。永樂時,造六臂文殊像,甚奇。有鼓有柄,人皮冒之,徑可二尺,亦內賜也。番僧精舍修整佛及供給,多西竺物。⑤[明]李維楨撰:《大泌山房集》卷6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2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20頁。
李維楨所說的“西域”即西藏,明代內地僧俗人士,多有不區(qū)分這二者的。《清涼山志》中就將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回到西藏稱為“旋西域焉”。①《清涼山志》,第83頁。
四、小 結
通過大慧法王的生平事跡,我們可以看出明代五臺山漢藏佛教已高度融合,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漢傳佛教僧人和藏傳佛教僧人都成為管理五臺山佛教事務的主體,從封號上看,甚至藏傳佛教僧人的地位要高于漢傳佛教僧人。在1557年所立的《皇明五臺開山歷代傳芳萬古題名記》碑刻中,五臺山被封為國師以及擁有“欽差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一代寺宇”“欽依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一代寺宇”身份的僧人,總共有16人,其中藏傳佛教僧人5人,分別是桑節(jié)朵而只、朵而只堅參、朵而只乳奴、亦失堅剉、端竹班丹;另外還有來自中天竺等地的“西天僧”4人。而在這些具有管理身份的僧人中,朵而只堅參被封為大慧法王,桑節(jié)朵而只被封為西天佛子大國師,所以朵而只堅參屬于16人中地位最尊崇者。由此可見,明朝雖然是一個以漢人為統(tǒng)治主體的王朝,但在五臺山佛教管理與發(fā)展方面,則具有很強的跨民族性。
二是從佛法傳承上看,漢藏民族的界線已經(jīng)突破。在朵而只堅參的佛法師承上,他上承漢人桑節(jié)朵而只,而桑節(jié)朵而只受學于班卓藏卜。班卓藏卜來自岷州大崇教寺,是大智法王班丹扎釋的侄子,為藏族。所以,到了明代,隨著大量西藏僧人留居京城,內地出現(xiàn)了許多漢人、漢僧修學藏傳佛教的現(xiàn)象,由之帶來的不僅是佛教各傳承派系之間的交流與往來,帶來高原地方與平原地區(qū)之間的交流,更促進了漢藏民族甚至各民族間文化的交流與交融。
三是漢僧的藏傳佛教僧人身份得到廣泛認可。從政府層面看,修習藏傳佛教的漢人被政府封為法王、國師,并且被委以重任;從民間層面看,在朵而只堅參被封為國師、大慧法王后,五臺山絕大多數(shù)碑刻,無論所記內容為何,無論與朵而只堅參有無關系,都會將其列在碑文后面或者列在碑陰僧眾之首,顯現(xiàn)出五臺山僧眾對他的尊崇與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