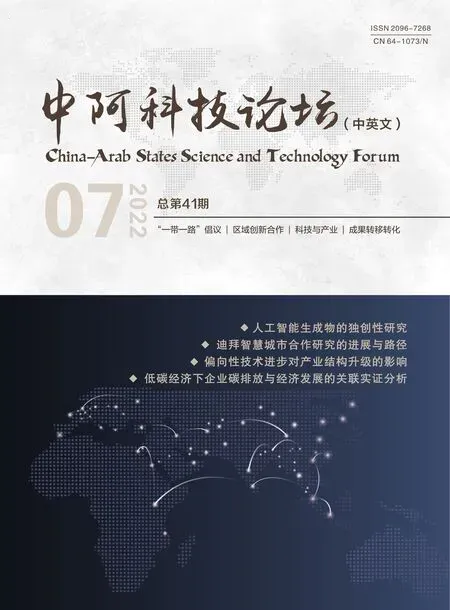知名老中醫經驗數字化傳承熱點可視化及圖譜分析
龔文潔 陳瑋祥 高 園 溫川飆
(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 成都 610072)
知名老中醫是我國寶貴的財富,名醫傳承是推動中醫學術發展與理論創新的重要需求[1],總結知名老中醫經驗傳承方式,有利于提高中醫臨床服務水平[2],也能為該研究領域的進步提供一些參考與思路[3]。近年來,知名老中醫經驗傳承存在著人才培養不足、數據庫不統一、信息孤島現象、缺乏有效方法、大規模推廣難等問題[4]。此前,駱長永等[5](2021)基于CiteSpace軟件對知名老中醫的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進行了可視化分析,得出了知名老中醫經驗傳承研究的前沿熱點,但是對中醫機構與非中醫機構的研究熱點未進行對比分析。本文基于COOC 6.725軟件,分析中醫機構及非中醫機構知名老中醫經驗傳承研究文獻的發布年份、發文作者、發文機構、關鍵詞及投稿期刊等信息,探究目前中醫機構與非中醫機構對知名老中醫經驗數字化傳承的研究重視程度,旨在為研究知名老中醫經驗傳承的學者提供參考與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以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為檢索工具,將檢索條件設置為高級檢索,數據采集時間為2021年11月21日,以“(主題=臨床經驗)OR(主題=學術經驗)OR(主題=辨證論治)OR(主題=師承教育)OR(主題=用藥規律)OR(主題=理法方藥)OR(主題=望聞問切)AND(主題=中醫)”為檢索主題進行精確查詢,再以“(主題=人工智能)OR(主題=數據挖掘)OR(主題=圖像處理)OR(主題=物聯網)OR(主題=互聯網)OR(主題=大數據)OR(主題=關聯規則)OR(主題=聚類分析)OR(主題=算法)”為檢索主題進行二次檢索,檢索文獻的發表時間不限,將資源范圍設置為學術期刊,得到相關文獻2 234篇。
1.2 轉換與篩選
將得到的2 234篇文獻以Refworks格式從CNKI數據庫導出,共形成5個文本文件,利用COOC 6.725軟件進行多文本合并、CNKI綜合提取,將5個文本文件合并轉為1個Excel文件,其中主要包括年份(YR)、全部作者(A1)、期刊(JF)、關鍵詞(K1)、機構(AD)、標題(T1)、摘要(AB)等信息。為提高文獻研究的準確性,對標題欄、全部作者欄等降序排列,進一步刪除無年份的、無作者的、非學術性研究如雜志征稿、新聞報道、會議講座類文獻,經過人工篩查剔除與主題無關的文獻,最終納入2 177篇有效文獻。為了對比中醫機構和非中醫機構對中醫數字化傳承的重視程度,在進行數據處理時,對兩種機構發表的文獻分別分析,其中中醫機構2 038篇,非中醫機構139篇。
2 數據分析
2.1 年發文量分析
研究發文量的年代變化規律有利于把握某一領域的研究變化趨勢。由圖1可知,中醫機構最早研究中醫數字化傳承的論文在1991年發表,為《劉渡舟教授運用經方的專家經驗咨詢系統》,文中系統在當時處于國內領先水平,較早地結合了中醫診斷與人工智能,便于后人的學習和知名老中醫的傳承[6]。中醫機構年發文量總體呈上升趨勢,且在2020年達到頂峰,為418篇。本文數據檢索時間在2021年11月,截至2021年11月發文量已達404篇,該年度發文量有超越2020年的趨勢。根據圖1,可以將知名老中醫經驗數字化傳承分為兩個階段:萌芽期(1991—2010年)和上升期(2011—2019年)。1991—2007年期間,受科學技術的限制,發文量較少,維持在每年2篇左右,大多數傳承方式停留在從傳統文化和中醫思維方面進行傳承;2008—2010年開始出現數據挖掘、關聯規則等科學技術運用到名老中醫經驗傳承中,探究其在名老中醫傳承中的應用前景,文章量開始呈現上升趨勢,對名老中醫經驗傳承起到積極作用。上升期為2011年至今,各大機構開始重視對中醫藥人才的培養和中醫文化的傳承,通過數字化的方式構建中醫傳承輔助平臺傳承知名老中醫經驗。其中從2014年開始,年發文量呈急劇上升的趨勢,中醫傳承輔助平臺得以廣泛應用,出現運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技術傳承知名老中醫。

圖1 1987—2021年名老中醫經驗數字化傳承發文量情況圖
非中醫機構對中醫傳承的研究較少,其最早研究中醫傳承的論文在1987年發表,發文量總體也呈現緩慢波動上升趨勢,在2020年及2021年11月達到峰值27篇,集中表現在通過數據挖掘[7]、中醫輔助診療平臺[8]、互聯網等科學技術傳承發展知名老中醫。
2.2 發文作者分析
經統計,中醫機構共有6 134位作者發表中醫數字化傳承相關文獻,其中發文量排名前十位的作者如圖2A所示,圖2的橫坐標表示作者姓名,縱坐標表示發文量的情況,計量單位為篇。發文量排名第一的作者為吳嘉瑞(北京中醫藥大學,46篇),多運用關聯規則、數據挖掘、聚類算法等技術研究中醫用藥規律,有利于推動中醫信息化的發展及知名老中醫傳承,與發文量排名第二的張冰(北京中醫藥大學,40篇)及排名第三的張曉朦(北京中醫藥大學,26篇)有團隊合作關系。非中醫機構共有452位作者發表中醫信息化傳承相關文獻,其中發文量排名前十位的作者如圖2B所示。發文量排名第一的作者為張天嵩(復旦大學附屬靜安區中心醫院,6篇),研究方向為基于數據挖掘及關聯規則探究知名老中醫治療肝的用藥規律,在知名老中醫傳承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圖2 中醫機構及非中醫機構發文量排名前十的作者情況統計圖
2.3 研究機構分析
對具體機構發文量的統計分析可以展示相關領域研究力量的分布,有利于推動學術創新與學科發展。表1統計結果顯示,中醫機構發文量排名前12位的機構包括北京中醫藥大學、山東中醫藥大學等8所高等院校,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等3所醫院機構和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其中中醫藥高等院校發文量占比較大,是中醫傳承研究的主力軍。非中醫機構發文量較少,大多機構都只發表了2~3篇文章。

表1 中醫機構和非中醫機構發文量比較
2.4 關鍵詞頻次分析
關鍵詞頻次分析能夠展示相關領域研究熱點。去掉主題檢索的關鍵詞進行詞云圖繪制,發現中醫機構和非中醫機構研究關鍵詞中出現頻次最多的都是“中醫傳承輔助平臺”[9]。該平臺系統能夠實現數據的錄入、管理、查詢、分析等操作以輔助中醫傳承工作,對中醫傳承推廣具有重要意義[10]。中醫機構的詞云圖出現了“數據分析”“聚類分析”“關聯規則”“復雜網絡”等非傳統方法傳承中醫的關鍵詞(見圖3A),研究重心在冠心病、潰瘍性結腸炎、糖尿病、慢性萎縮性胃炎上。非中醫機構的詞云圖中出現了“學術傳承”“中醫教育”“師承教育”“名老中醫檔案”等傳統方法傳承中醫的關鍵詞(見圖3B),研究重心同樣出現了冠心病、潰瘍性結腸炎,且在脂肪肝疾病上也有所研究,同時非中醫機構還出現了“古今醫案云平臺”“大數據”“支持向量機”等科技關鍵詞,說明非中醫機構有意向從科學技術方面傳承知名老中醫。

圖3 中醫機構及非中醫機構研究名老中醫經驗傳承關鍵詞詞云譜
2.5 期刊分析
期刊分析能夠幫助快速識別期刊刊文類型,為各領域研究論文投稿提供參考。中醫機構關于中醫信息化傳承的文獻分布在219種期刊上,其中載文量排名第一的是《中醫藥導報》,載文量78篇,排名第二的是《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載文量74篇(圖4A)。非中醫機構文獻分布在80種期刊上,其中載文量排名第一的也是《中醫藥導報》,載文量9篇,排名第二的也是《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載文量6篇(圖4B)。不管是中醫機構還是非中醫機構,關于中醫信息化傳承的研究論文發表期刊,排名前兩位均為《中醫藥導報》和《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

圖4 中醫機構及非中醫機構研究名老中醫經驗傳承論文發表期刊分布
3 建議
3.1 促進中醫機構與非中醫機構合作研究
非中醫機構總體發文量較少,僅139篇,表明非中醫機構在名老中醫經驗傳承上投入的精力還不足,應該提高研究數量,且研究中醫信息化領域的對象大多局限于醫院,高等院校在這方面研究較少,雖然有利用大數據[11]、向量機[12]等科學技術發展中醫信息化的趨勢,但研究都相對分散,缺乏核心技術引領中醫信息化發展,非中醫機構研究數量及深度應進一步提高。在關鍵詞頻次分析方面,中醫機構側重于聚類算法、聚類分析等研究名老中醫經驗傳承,非中醫機構側重于利用大數據、關聯分析等研究名老中醫經驗傳承,兩種機構側重點各有不同,可將研究重心進行融合,以獲得更多的發展借鑒思路。各大高校應注重培養既懂中醫又懂信息技術的復合型人才,建議相關部門完善制定中醫信息化發展機制的政策,加強中醫機構與非中醫機構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密切合作,促進雙方溝通分享研究成果,推動中醫信息化事業向上發展。
3.2 加強新興科學技術與中醫的融合
知名老中醫的傳承重心在于中醫的學術理念及臨床診療經驗的傳承上,如何結合新時代視角與技術繼承與傳承名老中醫經驗是提高臨床診療服務水平的關鍵。此前,王康等(2021)就結合了數據挖掘及統計學方法傳承醫案中的診療經驗,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提供了新思路[14];潘曄等(2021)通過古今醫案云平臺結合數據挖掘方法對新冠肺炎治療方案進行統計分析,探討治療用藥規律,驗證了清肺排毒湯的合理性[15]。從關鍵詞頻次分析可以看出,近幾年來,中醫信息化的研究仍然停留于數據挖掘、關聯分析等技術上,并沒有加強與云計算、物聯網、移動終端等新型技術的融合。中醫信息量大、種類多、涉及學科多而復雜,需要探索出符合當今時代發展的中醫傳承平臺,運用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手段結合傳統方法對推進我國中醫信息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利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可對知名老中醫的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進行數據庫的構建和保存。在結合新技術、新方法的同時應該保持中醫特色,重視知名老中醫傳承教育,加強對年輕醫師的培養,使知名老中醫的寶貴經驗代代相傳。
4 結語
從1991年至今,中醫信息化傳承從萌芽期到穩定期,從傳統方式走向新興科技,各高校機構的研究成果均取得不小的收獲,但中醫信息化的傳承仍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中醫機構研究經驗傳承普遍的方式為師承制、祖傳制、學院制,傳承范圍局限,非中醫機構沒有系統地進行研究,研究成果之間聯系性較弱,但總體來看中醫機構相對于非中醫機構發文量較多,表明其研究力度更大、投入的精力更多、在人才結構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目前,中醫信息化發展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應加強對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加大資金投入,推動各大研究學者團隊合作,大力發展知名老中醫經驗傳承。中醫機構應該繼續從科學技術方面進行突破,加強與人工智能等新型科學技術的融合,為我國中醫信息化的傳承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