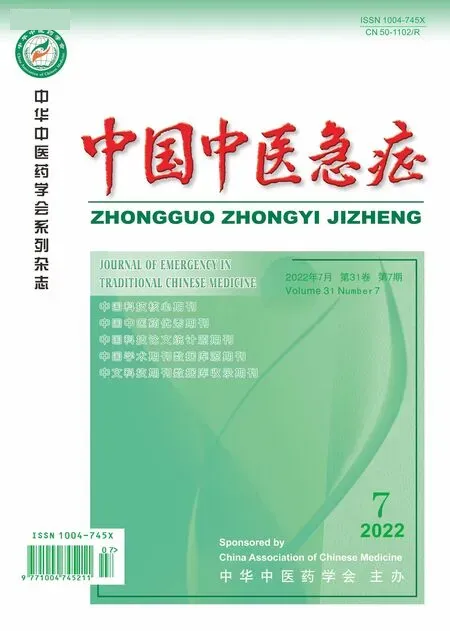關刺扳機點配合頸椎后伸側屈微調法治療頸源性眩暈臨床觀察*
岳建興 翁沁怡 杜 磊 王 飛 孫乃兵 劉雪潔
(蚌埠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安徽 蚌埠 233040)
頸源性眩暈與椎-基底動脈的供血不足和本體感覺傳入紊亂有關,是以體位性或發作性眩暈為主要癥狀的一類疾病。本病發作時多伴有頭頸僵痛、胸悶心慌、惡心嘔吐等多種復合癥狀[1],為康復科的難治、常見、易復發的一種疾病。由于本病在發病期間會嚴重影響到患者的生活、工作和學習,因此受到了醫患雙方的高度重視。目前發病年齡有年輕化趨勢[2],主要與需要長期伏案工作、長期低頭使用手機等不良的生活、工作習慣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對于頸源性眩暈,臨床上治療原則主要以改善微循環、抗眩暈的治療為主,但是存在眩暈得到改善時間相對較長,易復發等不足。近年來筆者采用關刺扳機點配合頸椎后伸側屈微調法治療頸源性眩暈,并與常規針刺組進行臨床療效對比研究,取得較好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1)診斷標準[3]:眩暈或者頭暈;伴有頭頸部不適:如頭頸痛(沿枕寰關節邊緣有明顯壓痛)、項僵(僵硬伴條索狀改變),活動后加重或旋頸誘發試驗(±);影像學顯示頸椎椎體不穩、退變等;多伴有交感癥狀。2)納入標準:符合以上診斷標準;能夠耐受并同意關刺、傳統針刺和頸椎后伸側屈微調法治療;依從性好,能夠堅持治療,配合臨床療效觀察、隨訪;枕后的斜方肌肌腱起點處附近有明顯條索感或壓痛感。3)排除標準:頸椎管狹窄、后縱韌帶骨化、脫位、骨結核及嚴重的骨質疏松者;其他原因引起眩暈者;合并有其他嚴重疾病引起者;精神病者;依從性差者。
1.2 臨床資料 選取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在蚌埠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康復醫學科門診或住院就診的頸源性眩暈患者60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32例與對照組28例。治療組32例,男性14例,女性18例;年齡24~72歲,平均(44.61±10.49)歲;病程6 h至7 d,平均(6.74±4.53)d。對照組28例,男性13例,女性15例;年齡23~68歲,平均(37.54±11.61)歲;病程1~21 d,平均(8.12±6.21)d。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書,本研究經蚌埠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1.3 治療方法 治療組給予關刺扳機點配合頸椎后伸側屈微調。依據扳機點的診斷標準[4]來確定關刺的具體位置:1)后枕部骨骼肌上有明顯的緊張點;2)緊張點的觸壓有疼痛、傳導痛等;3)快速按壓可誘發患肌的“抽搐”反應。取倒騎靠背椅俯伏位。術者押手在后枕部的斜方肌肌腱外緣處附近尋找扳機點、條索狀物或結節并輕按之。常規消毒,將一次性無菌針灸針(佳健牌,規格0.30 mm×25 mm)垂直于肌腱方向、呈15°角平行上項線向正中線方向平刺約0.5寸[5],此時術者自覺刺手針下有明顯沉緊感,患者酸脹感明顯,再以此針為中心上下各刺1針,針尖方向均指向陽性點,針間距約2~3 mm,平刺百會、四神聰安神增加改善眩暈的效果。行平補平瀉,留針30 min,期間行針1次。取針后,休息片刻,舒緩患者的緊張情緒,保持頸肩部自然放松,取坐位。術者立于身后,托住患者頭頸部緩慢的后仰,待覺頸部肌肉完全放松時,術者輕微側身,將與患者同側之拇指頂住患者需要調整的節段之橫突后外側,以對側手掌置于患者對側顳部,將頭向對側旋轉側屈15°左右,順勢兩手反方向用力,幅度約5~10°,推頂病變節段的手指能感覺到關節移動,常可聽到一個節段或多個節段復位時的“咔噠”聲。根據治療需要決定是單側微調及雙側微調。手法要求平穩著實,忌用暴力。每日1次,6次為1療程,休息1 d,繼續下一個療程,共治療2個療程,半年后隨訪。對照組給予常規針刺,以頸夾脊、四神聰、百會、頭維為主穴,根據證型需要酌配太溪、豐隆、血海、太沖、足三里等。操作方法:取俯臥位,常規消毒,選用一次性無菌針灸針(佳健牌,規格0.30 mm×40 mm),直刺頸夾脊,平刺四神聰、頭維、百會,行平補平瀉,留針30 min,期間行針1次。每日1次,6次為1個療程,休息1 d,繼續下1個療程,共治療2個療程,半年后隨訪。
1.4 觀察項目 采用改良《頸性眩暈癥狀與功能評估量表》(ESCV)[6]在治療前和治療2個療程結束后進行量表評價,滿分30分,含眩暈、頸肩痛等5項,每項分5個等級。
1.5 療效標準 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7]擬定。痊愈:頸源性眩暈癥狀、陽性體征消失,頸部活動可,正常工作和生活,隨訪半年以上無復發。顯效:癥狀、陽性體征基本消失,旋頸誘發試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半年以內可復發。有效:癥狀、體征好轉,旋頸誘發試驗(+)。無效:癥狀、體征無減輕,旋頸誘發試驗(+)。
1.6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7.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1。治療組治愈率、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常規針刺組(P<0.05)。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2.2 兩組治療前后ESCV量表積分比較 見表2。治療后兩組的各癥狀積分和總積分均較治療前顯著提高(P<0.01),治療組較對照組提高更為顯著(P<0.05或P<0.01)。
表2 兩組治療前后ESCV量表積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ESCV量表積分比較(分,±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P<0.01;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0.05,△△P<0.01。
組別治療組(n=32)對照組(n=28)總積分13.12±2.02 28.76±4.43**△△11.60±1.31 25.84±6.68**時間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眩暈6.64±1.73 15.42±2.42**△△5.86±1.54 13.56±3.26**頸肩痛1.11±0.37 3.62±0.46**△1.12±0.16 3.53±0.84*頭痛1.12±0.35 1.83±0.26**△1.13±0.72 1.63±0.86**日常生活及工作1.27±0.48 3.92±0.84**△△1.32±1.06 3.47±0.95**心理及社會適應2.98±1.46 3.97±0.59**△△2.47±1.21 3.65±0.98**
2.3 兩組復發率比較 隨訪6個月比較,無失訪病例,治療組3例(10.00%)復發,對照組7例復發(30.43%),對照組復發率顯著高于治療組(P<0.05)。
2.4 不良反應 未見不良反應情況。
3 討論
頸源性眩暈屬中醫學“眩暈”范疇。《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風掉眩,皆屬于肝”。提出了眩暈與肝的密切關系。《靈樞·官針》提出了關刺針法相應于肝的觀點。“關刺者……此肝之應也”。又叫豈刺或淵刺。《靈樞·官針》中提到關刺法多適宜于治療“筋病”,因多用于肌肉起止點的關節處,故曰“關刺”。就針刺手法而言,是復式針刺手法組成的。首先,注重附著在關節周圍的肌腱、韌帶;其次,直達經筋病灶,強調一針多向刺,增強針刺范圍與強度。因此,關刺在舒緩局部筋脈拘攣、散筋結方面有獨特的優勢[8]。
從解剖角度分析,寰樞椎與椎動脈關系密切。頸椎關節一旦失穩,頸部肌肉發生退變或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容易產生肌肉緊張、僵硬及肌肉力量的下降,進一步觸發局部扳機點,阻礙或削弱肌肉的伸展功能,頸椎兩側肌力失去平衡,造成寰樞椎位置紊亂。椎動脈的樞椎橫突孔至枕骨大孔(V3)段雖然行程比較短,但因為該段伴有連續的6~7個彎曲,致頸椎在旋轉時容易發生牽拉、扭曲,供血失常造成眩暈。
Brandt T等認為因上頸部的疼痛引起的前庭和頸感覺傳入不匹配的現象可以誘發眩暈[9]。葉潔等認為頸源性眩暈與周圍軟組織病變、頸椎組織結構的失衡有關,血流動力學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異常[10]。馬明等認為椎動脈上的交感神經纖維因受到神經激惹、炎癥因子刺激或機械壓迫等,導致椎動脈缺血痙攣,引起頸源性眩暈[11]。Melzack等提出中醫的經筋分布與活動性扳機點牽涉痛范圍的重疊程度達80%[12]。因此,本研究認為頸源性眩暈的出現與頸椎小關節紊亂、頸部肌群僵硬(扳機點)致椎動脈(V3為主)受到壓迫或交感神經受刺激引起椎-基底動脈血管收縮引起的供血不足有關。
從解剖學角度看,頭夾肌、頭后大小直肌、頭上斜肌、斜方肌上部等肌腱均附著在上項線附近。已有研究顯示,該部位γ-肌梭中含有豐富的機械感受器[13]。不但控制著頸椎關節的屈伸旋轉,還通過前庭和視覺系統建立了直接的神經生物學上的聯系[14]。項立敏等提出關刺可以促進肌細胞動作電位的形成,起到舒利筋肉、消灶解結的效果[15]。姚芬芬等認為針刺扳機點可糾正經筋痙攣所致的頸部本體感覺紊亂,疏通經絡,改善眩暈癥狀[16]。因此,本研究選取了后枕部上項線風池穴附近的扳機點、條索狀物或痛性結節作為關刺的經筋部位。可以以通為補,直達病灶。通過反射性擴張局部血管,降低扳機點的活性;還可迅速糾正經筋痙攣,使經通筋舒,糾正椎-基底動脈血流動力學的紊亂[17],使治療更徹底。
采用坐位頸椎后伸側屈微調法是根據解剖特征及臨床效果積累而來,認為側向推頂橫突及小關節的方法能夠微調頸椎的小關節的紊亂,使失償后的頸椎解剖結構恢復正常的生理學結構,讓僵硬的頸肌松弛下來,快速解除或緩解對椎動脈及交感神經的壓迫的目的。矯正過程中頸椎的運動幅度僅為10°左右,可有效避免頸部軟組織、內外神經以及血管發生應力性傷害。與借助頸椎的拔伸或旋轉等糾正錯位的小關節的傳統療法相比較,該法操作得法、幅度可控,具有改善頸椎內環境,重建脊柱新的力學平衡的作用,安全性高。同時,避開了“位置性眩暈”的影響,增強了患者的治療感受。
通過上述機理分析及臨床治療效果評價,認為采用關刺扳機點配合頸椎后伸側屈微調法通過調節頸椎失衡的經筋系統,建立了頸椎新的內外平衡關系,恢復椎動脈、椎-基底動脈血流,達到治療眩暈的目的,可靠有效地改善患者眩暈、頸肩痛、頭痛、日常生活及工作、心理及社會適應,操作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