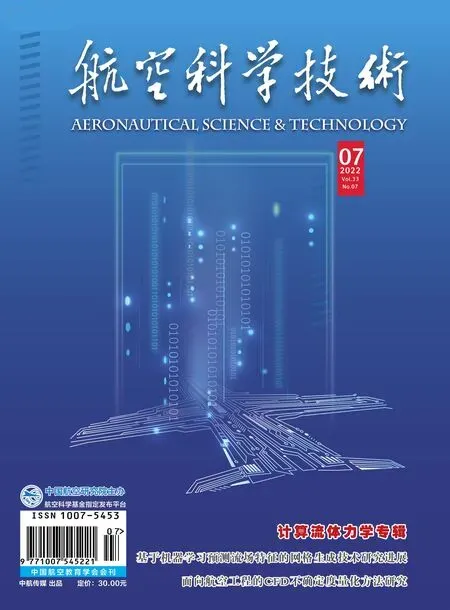機載光電偵察裝備發展現狀分析
張嵐,趙顯宇,熊鐘秀
1.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四川 成都 610091
2.航空工業洛陽電光設備研究所,河南 洛陽 471000
在現代軍事斗爭中,信息的獲取能力成為決定戰爭發展的主要因素。美國等西方國家將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ISR)所涉及的裝備、數據綜合到一起供作戰指揮與決策。后來美國又將ISR 系統與指揮(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和計算機(computer)系統統一到一起,形成C4ISR系統,構成現代軍隊的神經中樞。
機載光電偵察作為C4ISR 系統的重要一環,是指利用光電探測手段,在飛機等航空平臺上獲取敵方目標分布、地形信息、人員及裝備活動的軍事斗爭手段。光電偵察裝備是指利用目標及背景對各類光源的不同反射特性或其自身輻射的差異來進行探測、識別乃至瞄準、跟蹤的軍用儀器或系統。相對雷達、聲學等偵察設備,光電偵察裝備成像效果直觀,利于人員判讀;光電偵察設備大多屬于無源探測設備,隱蔽性好,不容易被敵方探測;并且光電偵察設備抗干擾性能好,可以在強電磁對抗環境中工作,是偵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裝備。機載光電監視偵察系統能夠利用航空平臺快速、靈活的優勢高效地對目標進行大范圍、遠距離偵察,提供實時的戰場態勢情報,數十年來,機載光電偵察裝備的應用為軍事斗爭的形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1]。
從使用上講,機載光電偵察包括光電偵察和光電監視兩種類型,光電偵察主要指在大范圍內對目標區域進行探測、識別等;而光電監視則主要是對已知目標進行觀察,掌握目標隨時間的變化情況。相對雷達等偵察手段,光電偵察可以實現被動探測,降低了被敵方發現的風險。同時得益于可見光及紅外探測技術的發展,光電偵察可以實現高分辨、高幀頻成像,成為提供戰場支援和奪取信息優勢的重要手段。
1 國外主要航空偵察平臺
機載偵察裝備是依托航空偵察平臺而發揮作用的,航空平臺的飛行速度、飛行高度,以及其隱身、氣動要求都會直接影響航空偵察的結構甚至功能。而機載偵察裝備(載荷)的性能與功能又直接影響航空偵察平臺的效能與工作方式。航空偵察平臺與光電偵察裝備如何搭配使用主要取決于航空偵察任務需求與使用場景。不同偵察任務對區域范圍、時效性乃至偵察設備的性能要求都有不同。一般來說,偵察任務是軍事活動的重要前提,是軍事情報獲取的基本手段。在軍事斗爭的早期,一般由專用的大型偵察機平臺攜帶高性能光電偵察裝備對目標作戰區進行廣域搜索,獲得全面完整的戰場態勢信息;在軍事斗爭進行中,戰術偵察任務又成為偵察活動的主要形式,其特點是偵察區域小,時效性要求高。往往采用戰斗機、無人機或直升機等航空戰術平臺加掛光電吊艙等多種形式的偵察裝備對特定目標進行探測、識別及跟蹤。
在分析機載光電偵察裝備之前首先應該對目前主要的航空偵察平臺進行梳理[2-4]。專用偵察機是執行航空偵察任務的重要平臺,典型機型有美國的SR-71偵察機、U-2偵察機、EP-3 偵察機、EP-8 偵察機,以及RC-135 偵察機(見圖1)等。其中SR-71偵察機由洛克希德公司研制,1966年開始在美軍服役,該機實用偵察高度達到24000m,最大飛行速度超過Ma3,裝備有可見光、紅外及合成孔徑雷達等偵察設備。U-2 偵察機同樣由洛克希德公司研制,于1956年進入美軍服役,實用升限同樣超過24000m,但其早期型號有效偵察高度僅為5000~15000m,裝備有8 臺照相偵察用全自動照相機,還可安裝合成孔徑雷達。U-2 偵察機一直服役至今,其航電裝置也在進行不斷升級。而后三種偵察機均是在客機平臺上改造而成,機體空間較大,搭載的偵察設備種類比較多,使用及維護成本較低。

圖1 美國RC-135偵察機Fig.1 The RC-135 reconnaissance plane of U.S.
此外,偵察型直升機也是航空偵察的重要平臺。由于其出動靈活度較高,偵察性直升機可以配屬在海面艦艇上或在一些地面戰場中使用。典型的偵察型直升機有美國RAH-66“科曼奇”直升機,俄羅斯卡-31、卡-52 直升機,法國“地平線”直升機,英國“海王”直升機等。美國陸軍在2018 年提出了“未來攻擊偵察直升機”(FARA)計劃,開啟了下一代軍用直升機的研發。
近些年,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大力發展無人偵察平臺,無人機使用效費比很高,成為當前的局部戰爭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武器之一。典型無人偵察機有“掃描鷹”無人偵察機、RQ-4“全球鷹”無人偵察機、MQ-8 無人直升機(見圖2),以及RQ-170隱身無人偵察機。此外,兼顧偵察與打擊功能的無人機也在國際市場受到大量的關注,如美國的MQ-1、MQ-9 系列無人機(見圖3),以色列“赫爾墨斯”900型無人機以及俄羅斯“獵戶座”無人機,我國的“翼龍”系列無人機在該類機型中處于世界先進水平[5]。

圖2 美國MQ-8“火力偵察兵”無人直升機Fig.2 The MQ-8“Fire Scout”Unmanned helicopter

圖3 美國MQ-9察打一體無人機Fig.3 The MQ-9 reconnaissance and strike integrate UAV
除有人/無人飛機和直升機平臺外,近些年飛艇等浮空平臺再次得到人們的關注。飛艇具有留空時間長、覆蓋面積大、能源消耗低等諸多優點,可作為邊防、海防的空中監測平臺。尤其是一些飛艇還能在平流層內長時間停留,可以進行低空預警。目前,美國軍方將多艘飛艇(見圖4)部署在伊拉克、阿富汗及其他地方,用于執行持久監視任務,這些平臺執行任務的時間可達數周乃至數月。

圖4 美國陸軍混合飛艇Fig.4 The hybrid airship of U.S.army
2 典型機載光電偵察裝備
針對機載平臺與使用需求的不同,機載光電偵察裝備主要有內裝式和吊艙式兩種類型。內裝式光電偵察設備裝載在航空平臺內部,在機身留出光窗,通常在一些對隱身性或氣動要求高的平臺中使用;而吊艙式偵察設備可以掛在機頭、機腹乃至機翼處,使用較為靈活。
不同的機載光電偵察傳感器配置差異也比較大。有的只配置單紅外傳感器,有的只配置單可見光傳感器,有的可以實現紅外/可見光組合偵察。隨著光電探測技術的發展,光電吊艙的傳感器配置也在逐漸豐富,本節對幾類典型的機載偵察裝備進行介紹[6-9]。
2.1 光電偵察吊艙
依據裝機條件、結構外形的不同,常見的光電吊艙主要有轉塔式和吊艙式兩種類型。吊艙型光電偵察系統主要用于戰斗機等機動性強的平臺,其外形必須滿足一定的徑長比以滿足高速氣動要求,通過外掛物掛架與飛機相連,拆裝靈活,通用性較強,但體積較大、重量較重。轉塔型光電吊艙多用于直升機、無人機以及部分巡邏偵察機等相對飛行速度較慢的飛行器,它一般與飛機固連,成為飛機的一個組成部分。
典型的轉塔式光電偵察系統有加拿大L-3 韋斯凱(Wescam)公司生產的MX-20系列吊艙(見圖5)以及美國菲力爾(FLIR)公司研制的Safire 系列吊艙(見圖6)。MX-20 是一款90kg 級的高性能遠距多傳感器成像系統,紅外成像分辨率有640×512或1280×1024可選,支持4個視場切換;可見光可提供720P 和1080P 兩種分辨率,可連續變焦;此外還提供30km測距能力的激光測距器和激光照射器。該系列吊艙在美軍P-8A、HC-130H、德軍P-3C以及部分無人機、直升機和浮空平臺上均有裝備。Safire 系列吊艙同樣提供上述分辨率的紅外及可見光相機,光學鏡頭可120 倍變焦,紅外窄視場為0.25°,寬視場為40°,電視攝像機窄視場為0.25°,寬視場為29°,此外還可提供近紅外微光電視、短波紅外成像、激光測距等功能。該系列吊艙同樣在部分無人機、直升機及運輸機平臺上裝備。

圖5 加拿大L-3 MX-20吊艙Fig.5 L-3 MX-20 pod of Canada

圖6 美軍菲力爾Safire吊艙Fig.6 FLIR Safire pod of U.S.
典型的吊艙式光電偵察系統有美國MS-177 吊艙,法國泰雷茲公司的機載偵察識別系統(airborne reconnaissance observation system,AREOS)及泰勒斯英國公司研制的數字聯合偵察吊艙(digital joint reconnaissance pod, DJRP)。MS-177吊艙(見圖7)是從DB-110吊艙、MS-110吊艙一路升級而來,由原美國聯合技術公司(現雷神技術公司)研制,可提供可見光、近紅外、短波紅外及中波紅外圖像,成像焦距達到了177in(約4496mm),識別距離達到80km。在短波紅外及中波紅外波段內還分出6 個波段實現多光譜成像、每小時偵察覆蓋面積可達37000km2。泰勒斯公司的DJRP吊艙可提供可見光及長波紅外圖像,其中可見光傳感器支持6倍光學變焦。DJRP吊艙(見圖8)工作時光電傳感器處于掃描狀態,以實現對廣域范圍的偵察。

圖7 美國MS-177系統Fig.7 MS-177 system of U.S.

圖8 泰雷茲DJRP吊艙Fig.8 Thales DJRP pod
除傳統的吊艙之外,近些年也有一些特殊外形的機載偵察裝備。如裝備在以色列“赫爾墨斯”900型無人機(見圖9)上的“天空之眼”監視系統。將多孔徑成像系統直接安裝在機腹下,可在臨空狀態下對80km2左右范圍內的地面區域進行持續監視。另外,它可以在實時觀察時以特定分辨率和放大率記錄和顯示圖像,利用不同觀察角和放大率,用戶可以同時分別觀看10個以上感興趣區域,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及時回放”,以分析態勢的發展。

圖9 裝備有“天空之眼”系統的“赫爾墨斯”900型無人機Fig.9 The“SkEye”system in Hermes-900 UAS
2.2 內裝式光電偵察裝備
典型的內裝式光電偵察系統有原美國雷神公司研制的綜合傳感器系統(ISS)以及原美國柯林斯公司研制的“畢業生”電光偵察系統(SYERS),目前上述公司已經合并,組建了新的“雷神技術公司”。ISS 系統主要裝備在美國RQ-4“全球鷹”無人機上,包含一臺1024×1024 像素數可見光傳感器和一臺640×512中波紅外傳感器,對地面進行遠距離、高分辨率、傾斜偵察成像,同時利用飛機的飛行運動將掃描向前遞推,從而獲得廣闊地域內的連續圖像。ISS系統的相關技術已被融合進雷神技術公司下一代“休斯”綜合監視識別系統(HISAR)中。SYERS-2C系統已經應用于美國U-2偵察機中(見圖10),可提供可見光、近紅外、短波紅外、中波紅外10個光譜波段圖像,并且可對移動及靜止目標進行探測、跟蹤與評估。

圖10 美國SYERS-2型偵察系統及其在U-2偵察機上的裝載示意Fig.10 SYERS-2 reconnaissance system and the locad in U-2 plane
3 機載光電偵察技術
光電偵察裝備的能力形成主要依賴光電探測技術的發展。可見光和紅外探測技術已經發展多年,在機載偵察領域,限制可見光和紅外探測性能的主要因素是探測器的性能以及光和熱在大氣傳播過程中的衰減,相關技術的研究資料豐富,本文不再作過多介紹。本節主要介紹多光譜探測、偏振探測和深度學習等新型技術的原理及在機載光電偵察領域的應用[10]。
3.1 多光譜/高光譜探測技術
目前,偽裝技術的發展對目標探測和識別技術提出了挑戰。然而,偽裝目標與真實目標的光譜圖像信息之間存在著細微差異,光譜特性是物質的基本屬性,不同波長的光譜反映原子或分子內能級躍遷的類型,通過分析這些光譜差別可以區分出真實目標與偽裝目標之間的物質特征差異,從而實現反偽裝探測。多光譜/高光譜成像是將傳統光學成像技術和光譜測量技術相結合的一種新型偵察技術,其獲取的信息不僅包括二維空間信息,還包含隨波長分布的光譜輻射信息。我們可以通過多光譜/高光譜成像技術來分析被觀測物體的光譜特征,從而探測、識別和評估表面材料,進而實現目標探測和地形分類。
常用的成像光譜波段主要有可見光波段、近紅外波段、短波紅外波段、中波紅外波段和長波紅外波段。他們分別根據目標的反射光和熱輻射光來進行探測及識別,相同顏色的不同物體在可見光波段可能無法進行區分,但其熱輻射水平會存在差異,據此可以實現目標識別與偽裝揭露。而更精細的波段劃分則能實現更強大的揭偽和識別能力,國外已研制出超過200個波段的航空多光譜相機[11]。圖11為對室外汽車進行中波多光譜成像的效果。
通過圖11對室外汽車的多光譜圖像可以看出,在不同光譜通道內,不同物體反射的光學強度是不同的,在裝備使用中可以利用這一特點來減弱偽裝網、植被等物體對目標的遮蔽效果。

圖11 汽車多光譜圖像[12]Fig.11 Multispectral imaging for automobile
3.2 偏振探測技術
偏振是光的4 個基本特性之一,任何目標都存在一定的偏振特性。通常光電探測器中的圖像信息主要反映視場內各物體到達探測器的光的強度差異。但實際場景中,一些雨霧或水面磷光等干擾因素也被疊加到目標的成像圖上,會對目標的跟蹤與識別有負面影響,甚至直接將有用的目標信號淹沒。不過,水面磷光以及雨霧等干擾信息和目標的偏振特性是不完全相同的,利用不同物體的光學偏振特征差別,可以有效地去除干擾,提升目標的信噪比[13-14]。圖12 和圖13 分別展示利用偏振光學手段在圖像去霧與發現偽裝/隱蔽目標時的應用效果圖。

圖12 偏振去霧Fig.12 Polarization defogging

圖13 偏振發現隱蔽目標Fig.13 Find camouflage targets through polarized light
偏振成像系統結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運動部件,通過旋轉偏振器件等方法來濾除干擾圖像,這種結構簡單靈活、成本較低,不過實時性較差,對于變化場景的目標需要一定的反應和調整時間;另一類是無運動部件,如將不同方向的線偏振器件有規律地直接耦合在焦平面探測器陣列上,這種方法實時性較好,不過會犧牲一定的像素分辨率。
3.3 基于深度學習的目標識別技術
深度學習的思想來自人工神經網絡,神經網絡沒有嚴格的定義,它的特點就是模仿人類大腦神經元之間傳遞信息的模式,是一個對接收到的信號不斷迭代、不斷抽象的過程。在偵察領域,深度學習方法在目標檢測識別領域以其獨有的精度與特征自動提取等優勢,得到迅速發展并廣泛普及。
目前,基于深度學習目標檢測識別技術主要有二階段(two-stage)和一階段(one-stage)兩種架構。二階段結構的深度學習目標檢測識別算法主要分為兩步,首先通過顯著性檢測從圖像中提取一系列候選框,然后通過深度卷積網絡對每個候選框進行進一步的分類和回歸定位以得到識別結果,其代表算法有RCNN、Fast RCNN、Faster RCNN(結構圖見圖14)等。一階段結構的深度學習目標檢測識別算法無須預先提取候選目標區域,而是將目標位置、類別和置信度以回歸的方式求解,而不需要顯著性檢測過程,其代表算法有SSD 系列、YOLO 系列(結構圖見圖15),以及EfficietDet等。

圖14 RCNN結構圖Fig.14 Schematic diagram of RCNN

圖15 YOLO結構圖Fig.15 Schematic diagram of YOLO
對于兩種架構而言,二階段結構需要人工預先提取目標的特征,而一階段結構是將特征提取環節也并入神經網絡中,實現端到端的處理。在面對更多的目標種類,更復雜的應用場景中,一階段效率更高,也逐漸成為深度學習的主流算法。不過一階段發受樣本的影響比較大,如果訓練樣本數量少或樣本種類不夠豐富,容易提取到非正確的目標特征,反而降低目標識別的正確率;另外一階段法計算量比較大,訓練時間長,因此在實際應用中還需根據真實應用場景選擇合適的算法。
正因為深度學習技術的使用能極大地提升對目標的偵察識別效率,很多國家均對其持續投入研究。美國空軍開發了一款“敏捷禿鷹”(agile condor)吊艙,集成了人工智能計算機,目前已在多型飛機上開展了試飛驗證[15-17]。
4 結束語
機載光電偵察裝備在軍事斗爭中的重要作用,在歷次現代戰爭中得到了證明。光電探測技術的持續發展,使光電偵察系統的能力和效率得到了持續提升,也讓各型光電偵察設備得以在越來越多的航空平臺上裝備。
相對于機載光電預警、光電瞄準等光電探測系統,機載光電偵察設備技術主要具有探測范圍廣、目標種類多、工作時間久、處理數據量大等特點。因此大面陣探測器、多光譜目標探測手段、偏振圖像處理手段、深度學習數據處理手段越來越廣泛地在光電偵察系統中得到應用。同時,航空光電偵察能力的發揮是航空平臺與偵察載荷共同作用的結果。如今,各種作戰平臺不斷涌現,其更新換代的頻率也日益加快,尤其是無人化作戰平臺的廣泛應用,使得戰場形態發生進一步轉化。為適應裝備的快速發展,縮短光電偵察載荷的研發周期,減少后勤壓力,機載光電偵察裝備要逐步走上通用化、標準化和模塊化的發展道路。目前,美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偵察載荷的通用化,其MS-110 吊艙不僅可以掛載在多型戰斗機和無人機上,其核心部件也可以作為內裝載荷裝備到一些偵察機及運輸機上;而RQ-4“全球鷹”無人機也設計了可以調整的掛架,既能裝載ISS系統,也能裝載SYERS-2C系統。此外,隨著光電偵察能力的提升,機載光電系統的復雜性也將提高,將帶動航空電子系統的整體擴容,需要更先進的機載任務系統來支撐。
綜合分析目前機載光電偵察系統發展趨勢,我國機載光電偵察設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1)提升我國大面陣探測器、高透過率光學鏡片等一系列基礎材料、基礎器件的研發能力,進而提升偵察系統探測性能參數。(2)提高智能化程度,通過深度學習、大數據等手段提升偵察數據處理效率,快速形成情報信息,縮短戰爭準備時間。(3)提高通用化水平,注重開展型號統型設計和標準化工作,降低研發成本,縮短研發周期,同時可以有效地減輕保障負擔。(4)提高產品集成度與功能復用性,將光電偵察與光電搜索、瞄準、跟蹤等多種功能集成在一個裝備中,提升單一裝備的功能種類,同樣有利于提升裝備使用效率,減輕后勤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