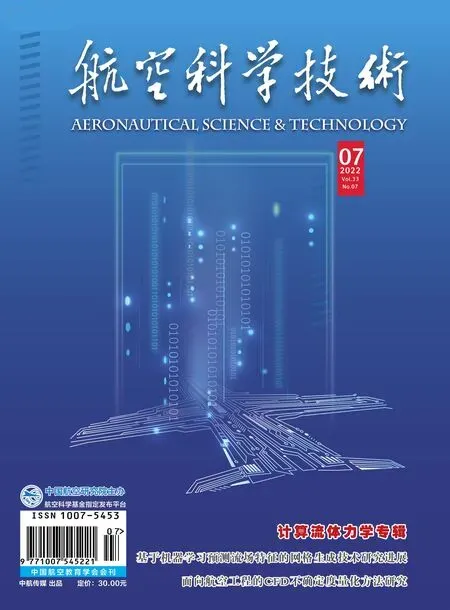高超聲速飛機氣動外形概念設計
劉濟民,顏仙榮,張朝陽,沈伋
海軍研究院,上海 200436
臨近空間高超聲速情報、監視及偵察(ISR)飛行器具有飛行速度快、反應時間短、突防能力強、作戰效能高等優點,可以憑借速度和高度的優勢完成普通飛行器無法完成的高難度情報、監視和偵察任務,在軍事上具有巨大的戰略意義[1-2]。20 世紀初,美國就開展了高超聲速飛機的相關研究,并先后提出了多個概念方案。廖孟豪等[3]對美國軍方和軍工部門提出的4個高超聲速作戰飛機概念方案進行了梳理,對比分析了各個概念方案的氣動布局特點,分析認為,美國高超聲速作戰飛機氣動布局向提升低速特性、降低內外流耦合程度、增加機身容量等方向演變。左林玄等[4]詳細總結了高超聲速飛行器的氣動布局分類,并指出未來高超聲速飛行器的布局將向翼身融合布局和乘波體布局兩個方向發展。李憲開等[5]結合高超聲速飛機的需求,分析了高超聲速飛機氣動布局設計存在的問題、難點和關鍵技術。
氣動布局技術是水平起降高超聲速飛機研制的核心技術之一。崔凱等[6-7]采用前體/發動機一體化設計思想,給出了一種雙旁側進氣翼身融合體概念設計方案。國內對高超聲速飛行器的相關研究日趨活躍,但對高超聲速飛機尤其是氣動布局方面的研究還不多,而且缺乏具體的應用背景和需求指標牽引。劉濟民等對高超聲速ISR平臺的軍事需求進行了分析,并對其在未來海戰中的應用進行了研究[8]。根據軍事需求分析得到的能力需求,目前的技術發展水平和對未來作戰使用的基本構想,對高超聲速ISR 平臺做以下技術想定,見表1。

表1 高超聲速ISR平臺主要技術指標Table 1 Main technology index of hypersonic ISR vehicle
本文以上述高超聲速ISR 平臺目標圖像為需求牽引,擬采用類乘波體氣動布局,對高超聲速ISR平臺的氣動外形進行初步設計與性能分析,并進一步驗證氣動外形概念方案滿足設計需求的程度,找到軍事需求與技術滿足度之間的差距,為高超聲速飛機氣動布局技術研究指明努力的方向。
1 氣動外形設計方法
氣動外形設計包括乘波前體氣動外形優化設計、機翼設計。在此基礎上,進行高超聲速ISR 平臺氣動外形一體化設計,包括乘波前體與機身的集成、機翼與機身的集成,以及后體與機身的集成三部分。
1.1 乘波前體設計
作者前期對高超聲速ISR平臺的乘波前體進行了優化設計和性能分析,優化后的乘波體具有應用于高超聲速ISR 平臺氣動外形設計的潛力。因此,選取參考文獻[9]中優化后的乘波體作為高超聲速ISR平臺的機身前體。
1.2 機翼設計
對于大多數的高超聲速飛行器,機身為主要升力面,利用前機身的壓縮產生主要升力。機翼作為次要升力部件,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也需重點設計。由參考文獻[9]可知,高超聲速ISR 平臺乘波前體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升力(113482N),還有一小半升力需要機翼來提供。另外,為了滿足水平起降設計要求,也需對機翼進行詳細設計。這就是高超聲速機翼的設計目標。
為了保證較好的波阻特性,對于高超聲速飛行器來說,在進行翼型設計選擇時一般會考慮較薄的對稱翼型,通常采用對稱雙弧形翼型、小展弦比大后掠梯形翼面[10]。機翼形狀相對簡單,由翼型參數和翼平面參數控制。對于高超聲速巡航類飛行器,機翼外形既要保證高超聲速ISR 飛行器巡航飛行時的升力和配平特性需求,又必須保證水平著陸時需要的高升力特性,同時機翼的重量還要輕。綜上考慮,確定高超聲速機翼的設計參數值及幾何參數見表2。

表2 機翼幾何參數Table 2 Geometry parameters of wing
采用計算流體力學(CFD)方法來計算機翼的氣動性能,并對機翼升阻比L/D與迎角α進行非線性回歸分析。高超聲速機翼在迎角5° ≤α≤14°范圍內的氣動性能數值計算結果見表3。其中,FL、FD分別為高超聲機翼的升力和阻力。

表3 機翼氣動性能與迎角的關系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wing vs α
圖1 為高超聲速機翼的升力、阻力和升阻比隨飛行迎角的變化關系曲線。由圖1 可知,高超聲速機翼基準構型的升力和阻力均隨迎角α的增大而增大,但阻力的增長幅度大于升力的增長幅度,導致升阻比隨迎角的增大而降低。迎角大于9°以后,阻力急劇增大。升力與迎角α近似為線性關系,阻力和升阻比與迎角α呈二階關系。隨著迎角的增大,升阻比減小,但在小迎角下,升力的絕對值小。因此,在實際應用時,宜采用適當大小的安裝角。

圖1 氣動性能隨迎角的變化曲線Fig.1 Change curve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vs angle of attack
對機翼升阻比L/D與迎角α進行非線性回歸分析。由圖1可知,機翼的升阻比L/D與迎角α呈二階關系。依據表3中的計算結果得到非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回歸方程中迎角α的單位采用角度制。由高超聲速機翼的L/D與迎角α之間的關系,可根據升力需求來合理確定機翼的安裝角,并且可以為高超聲速飛行器氣動模型的建立和控制系統設計提供依據。
1.3 后體設計
高超聲速飛行器后體/尾噴管一體化設計也是機體/發動機一體化設計的一個重要部分。后體/尾噴管一體化設計要求將后體作為發動機噴管膨脹面的組成部分,從而可以減小發動機的重量,降低外部阻力。在高超聲速吸氣式推進系統中,多采用單壁膨脹噴管取代傳統的對稱形式的推進噴管。單壁膨脹噴管能將飛行器后體下表面作為尾噴管的一部分,而且單壁膨脹噴管的非對稱結構設計,使得飛行器在非設計狀態飛行時,噴管具有一定的自適應補償特性。另外,單壁膨脹噴管結構的不對稱性,使整個飛行器產生很大的附加升力和俯仰力矩,從而影響到飛行器的飛行性能和配平特性。
1.4 一體化集成方法
高超聲速ISR平臺的中部機身由前機身尾部截面拉伸得到。對乘波前體的底部順著乘波前緣的方向進行拉伸,水平長度為4m,與1.2節中的翼根弦長一致,也是渦輪基組合循環發動機(TBCC)燃燒室的長度。機翼與機身的集成主要由兩個參數確定:一是機翼在機身的安裝位置,二是機翼安裝角。由于翼根長度與機身中部的長度一致,機翼安裝于機身中部的兩側。由于乘波前體和中部機身都有8.62°的向下傾角,為了使機翼盡可能地不破壞乘波前體和機身中部的流場結構,機翼安裝角確定為8.62°。本文對后體/尾噴管的設計進行了簡化處理,具體方法如下:尾噴管由機身向后等比例縮小產生,尾噴管長度為2m,上表面與機身平齊,下表面向上傾斜。按上述方案一體化集成后的高超聲速ISR平臺氣動外形如圖2所示。

圖2 高超聲速ISR平臺概念外形Fig.2 Aerodynamic shape of hypersonic ISR vehicle
高超聲速ISR平臺概念方案的氣動外形幾何參數見表4。機身體積(不包括機翼)為36.594m3,機身表面積(不包括機翼)為41.117m2。氣動外形的容積率定義為[1-13]

表4 高超聲速ISR平臺幾何參數Table 4 Geometry parameters of hypersonic ISR vehicle

式中:V為機體的體積,Sw為機體的濕面積。由式(2)可算出高超聲速ISR平臺的機身容積率為0.2681。
2 性能分析
計算域為橢圓柱,長為20m,長半徑(Z向)為10m,短半徑(Y向)為5m。采用非結構四面體網格,對壁面附近網格進行了加密處理,壁面上單元大小為1mm,計算域網格總數為1954萬,計算域及網格示意圖如圖3所示。

圖3 三維計算域及網格示意圖Fig.3 3D computation grids and domain
計算域的前面和上下邊界采用壓力遠場邊界條件,其他邊界采用壓力出口條件,壁面處按等溫、無滑移處理,壁面溫度設為1000K[14]。考慮到高超聲速激波分辨和黏性計算精度等問題,數值方法空間采用AUSM+格式[15-18],時間項采用全隱格式。采用RNGk?ε兩方程湍流模型和增強型壁面函數[19]來模擬湍流。計算中采用的自由流條件按標準大氣給出,見表5。

表5 自由流條件Table 5 Freestream conditions for computation
2.1 設計狀態下氣動性能
圖4 為高超聲速ISR 平臺上下表面壓力云圖。由下表面靜壓云圖可知,概念外形不僅乘波前體下表面壓力高,機身中部下表面也處于高壓區,只有尾部由于向上收斂,導致氣流膨脹,壓力減小。概念方案中機身中部向下傾斜,流經乘波前體上表面的氣流流經機身中部時膨脹,壓力降低。從上表面壓力云圖可知,在機翼前緣與機身結合處存在高壓氣體泄漏,機翼前緣與機身的結合處還需進行詳細設計,可以進一步提高全機的升阻比。高超聲速ISR平臺三維基準外形的氣動性能見表6。其中,氣動力系數采用的參考面積為機身橫截面的最大面積,與乘波前體的底部面積Sb相同(Sb=7.388m2)。

表6 三維基準外形氣動性能Table 6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3D benchmark model

圖4 高超聲速ISR平臺機身表面壓力云圖Fig.4 Pressure contours on the surface of hypersonic ISR fuselage
由表6 可知,三維基準外形的升阻比較高,與乘波前體的升阻比4.9028 相比,降低了0.0206,降幅僅為0.42%。計算結果和壓力云圖均表明機身中部也保持了較好的乘波特性。本文設計的高超聲速ISR平臺氣動外形的升阻比高于參考文獻[20]~文獻[22]中設計的高超聲速飛行器氣動外形的升阻比。
下面對高超聲速ISR 平臺各個部位所受的力進行分析,各個部位的受力情況見表7。其中,下標“f”代表機身的乘波前體、下標“c”代表中部機身、下標“a”代表機身的后體、下標“w”代表機翼。由表7 可知,乘波前體是氣動外形的主要升力來源,占總升力的44.19%,與一體化集成前相比,氣動性能基本沒變,仍然保持了較好的升阻比特性。機身中部產生的升力大小僅小于乘波前體,占總升力的33.92%,阻力占總阻力的29.94%。中部機身的升阻比為5.5313,高于乘波前體。由于機翼安裝角為8.62°,相當于有8.62°的迎角,此時機翼的升阻比為4.6786,與機翼升阻比回歸模型(見式(1))的計算結果4.6776基本吻合。

表7 機身各個部位所受的力Table 7 Aerodynamic force of each part
2.2 非設計狀態下氣動性能
高超聲速飛機飛行速度跨越亞聲速、跨聲速、超聲速和高超聲速,這就要求飛機的飛行性能具有寬速域全包線的適應性,氣動布局需要兼顧整個飛行速域進行匹配設計。為了進一步了解高超聲速ISR平臺氣動外形在寬速域和寬高度域條件下的氣動性能,對高超聲速ISR 平臺在非設計狀態下的氣動性能進行了分析。
(1)非設計飛行馬赫數性能分析
保持飛行高度H=30km 不變,采用數值計算方法分析概念外形在Ma5~Ma7 范圍內的氣動性能,計算條件見表8。圖5 為高超聲速ISR 平臺概念外形的升力系數、阻力系數和升阻比隨飛行馬赫數Ma的變化關系曲線。

圖5 氣動性能隨飛行馬赫數的變化曲線Fig.5 Change curve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vs Ma
由圖5可知,在Ma5~Ma7范圍內,高超聲速ISR平臺的升力系數、阻力系數和升阻比均隨Ma的增大而變小。高超聲速ISR平臺的氣動性能隨Ma的變化總體不大,升阻比的變化量在1.03%以內。升阻比均大于4.84,保持了較好的高升阻比特性。當Ma=5.0 時,高超聲速ISR 平臺雖然升阻比較大,但由于此時的動壓(20.948kPa)比設計狀態Ma=6.0 時(30.165kPa)減小了30.56%,升力僅為1.954×105N,但仍能保持巡航飛行的升力需求,此時的飛行阻力為3.96×104N。當Ma=7.0時,高超聲速ISR平臺的飛行阻力為6.6666×104N,遠超超燃沖壓發動機所能提供的推力(4.2×104N)。
(2)非設計飛行高度性能分析
保持飛行馬赫數Ma6.0不變,對飛行高度H=20~40km范圍內的氣動性能進行計算,計算條件見表8[23]。

表8 計算條件Table 8 Freestream conditions for computation
圖6為高超聲速ISR平臺概念外形的升力系數、阻力系數和升阻比隨飛行高度H的變化關系曲線。由圖6 可知,在H=20~40km 的范圍內,高超聲速ISR 平臺的升力系數隨飛行高度H的增大先變小后增大,阻力系數隨飛行高度H的增大而增大,升阻比均隨飛行高度H的增大而變小。高超聲速ISR 平臺的氣動性能隨飛行高度H的變化總體不大,升力系數的變化量在1.52%以內,阻力系數的變化量在4.85%以內。升阻比均大于4.72,保持了較好的高升阻比特性。當H=20km 時,高超聲速ISR平臺雖然升阻比較大,但由于此時的空氣密度較大,導致動壓(139.274kPa)比設計狀態H=30km時(30.165kPa)增大了4.617倍,升力和阻力遠遠超過設計要求。當H=40km時,由于密度很小,此時的動壓僅為7.236kPa,為設計狀態H=30km 時(30.165kPa)的24%,升力太小,也不能滿足飛行要求。

圖6 氣動性能隨飛行高度的變化曲線Fig.6 Change curve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vs H
由圖5、圖6 還可知,飛行高度對高超聲速ISR 平臺氣動性能的影響大于飛行馬赫數對氣動性能的影響。上述研究結果可為高超聲速ISR飛行器的飛行特性分析與飛行軌跡優化設計提供參考。
3 高超聲速ISR平臺概念方案需求驗證
由2.1節計算結果可知,高超聲速ISR平臺氣動外形總的升力超過2.5×105N,即使與推進系統進行一體化設計后有部分升力損失,也能滿足升力需求。總的阻力為52368N,在保持升阻比不變的情況下,當升力為2.0×105N時,對應的阻力為41894N。對超燃沖壓發動機來說,這個推力需求在可接受范圍之內。
當把飛行器的升阻比L/D、巡航速度V和推進系統的比沖Isp視為常數時,航程R可用Breguet公式表示為[24]

式中:m0為飛行器巡航飛行時的滿載質量,mfuel為燃油質量,εm為燃油結構質量比。超燃沖壓發動機的比沖范圍為900~1100m/s[25-26]。概念方案的L/D為4.8822,當設計指標航程R=7000km 時,按推進系統的比沖Isp=1000m/s(中等要求)計算,則燃油結構質量比εm需不小于0.792才可滿足航程需求,即高超聲速ISR 飛行器空重(不算載荷)必須小于7.56×103kg。對于高超聲速飛行器來說,這個指標太高,很難實現。若把燃油結構質量比εm定為可行的目標值εm=0.5(對應空重為10.63×103kg),由式(3)可算得高超聲速ISR平臺可實現的航程為4419km。
目前,高超聲速ISR平臺可實現的航程4419km與需求航程7000km 之間還存在較大的差距(2581km),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途徑有以下兩個方面。
(1)提高技術水平
由Breguet航程公式(3)可知,要想提高航程,可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提高超燃沖壓發動機的比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把超燃沖壓發動機的比沖由1000m/s 提高到1584m/s 即可滿足7000km 的航程要求。二是進一步優化高超聲速ISR 平臺的氣動外形,提高其升阻比。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把升阻比提高到7.7337也能滿足7000km的航程需求。三是加強輕質高強度耐高溫材料的研制,同時優化結構熱防護設計,從而提高飛行器的燃油結構質量比εm,使之達到0.792。若能在上述三個方面同時取得突破,則高超聲速ISR飛行器航程達到7000km是可以實現的。
(2)改變使用方式
在高超聲速ISR 平臺本身性能不變的條件下,通過火箭助推或大型運輸機空中掛載的方式,可以大大擴大其作戰使用范圍。另外,把高超聲速ISR 飛行器作為艦載無人機搭載于航母上也可以使其偵察范圍覆蓋第二島鏈,此時航母需前出1000km。
4 結論
本文對高超聲速ISR平臺概念外形進行了初步設計,并采用數值計算方法對其氣動性能進行了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1)機體和機翼的設計方法對高超聲速ISR 平臺總體氣動性能影響較大。乘波前體雖然給整個高超聲速ISR平臺的高升阻比特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機身中部和機翼的氣動性能依然重要。只有機身各個部分均保持較高的升阻比特性,全機才能獲得較好的氣動性能。
(2)類乘波體飛行器在小于設計馬赫數和設計高度的非設計狀態下具有更高的升阻比。因此,在滿足升力需求和推力限制的條件下,高超聲速ISR 平臺宜在略小于設計馬赫數和高度的條件下進行巡航飛行。
(3)在目前的技術發展水平狀態下,航程要達到7000km還很難實現。高超聲速飛行條件下的升阻比屏障、比沖屏障和熱障都是影響高超聲速飛行器航程的關鍵因素,只有上述技術難點逐步得到解決,高超聲速飛機才能真正走向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