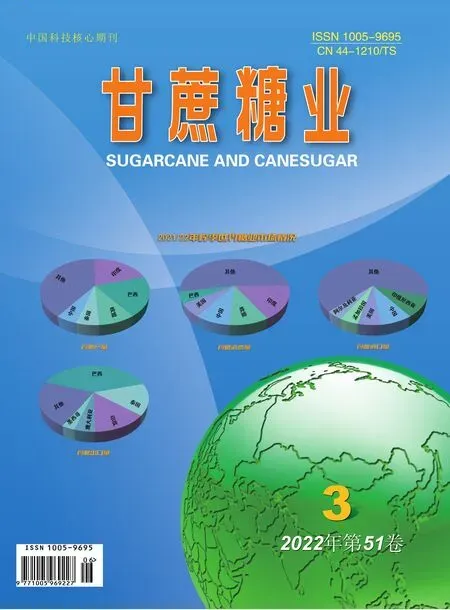代糖產品特性與對人體健康的利弊的評估
周國旺,楊 娜,張宇擎,李雪姚,曹國強
(黑龍江金象生化有限責任公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0 引言
“代糖”通常指替代蔗糖、果糖、葡萄糖、麥芽糖、乳糖發揮甜味作用的甜味劑。由于世界各地的人們日益注重身體健康,減少糖的攝入量已經成為世界關注點。代糖產品的增多,以及適量食糖才有益健康的宣傳影響,將會給制糖企業的生產帶來影響。目前,代糖的安全性仍存在許多爭議,且代糖產品的口感、質地欠佳,因此,難以預計未來10~20年后代糖的發展將會達到什么水平。本綜述通過最常見的合成和天然甜味劑,探討代糖的基本特性與安全性,以及其他國家的代糖應用情況和世界上知名企業的減糖措施,還分析了這些甜味劑對新陳代謝的影響,并給出了消費者對這些甜味劑進行大規模調查得出的意見結果。目的是提供對這些甜味劑與蔗糖的感官特性差異的理解,并以期為制糖企業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1 代糖的感官特性以及對代謝的影響
代糖的種類很多,根據其來源,一般可分為人工合成甜味劑和天然甜味劑。人工甜味劑包括糖精、甜蜜素、安賽蜜、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紐甜和愛德萬甜。天然甜味劑可進一步分為營養型甜味劑和非營養型甜味劑。營養型甜味劑包括糖醇類、稀有糖、楓糖和龍舌蘭;非營養型甜味劑主要包括甜菊糖苷、羅漢果甜苷和甜味蛋白(索馬甜、莫內林、馬檳榔甜蛋白、培它丁、布拉齊因、仙茅甜蛋白、神秘果素),詳見表1[1-2]。

表1 代糖的分類
清潔標簽(clean label)起源于歐盟,就是在產品標簽中盡可能少出現E編碼(歐盟為各種食品添加劑而編訂的食物標簽),保持標簽配料欄中的食品天然的屬性。對健康食品的追求促使人們轉向天然甜味劑。但是,天然或合成甜味劑都不屬于生理代謝惰性物質。如果甜味劑想要替代蔗糖產品,不僅要成功模仿蔗糖的感官特征,而且還要對體重和新陳代謝產生有利的影響。
1.1 感官特性
人工合成甜味劑的甜度很高,感官性質與蔗糖相似,但實際上除了甜味,還會有苦味和金屬味。目前甜味劑市場已擁有多種性質不一、風味各異的產品,然而,雖有如此之多的產品種類,尚無一種能夠真正取代蔗糖。很多甜味劑的甜度取決于濃度、pH值、溫度,以及其他添加劑的應用(如其他甜味劑/風味劑),不同的甜味劑混合也會產生增效和協同效應,有時心理因素也會影響感官結果。不同甜味劑的時間強度曲線差異也很大,例如,糖精與蔗糖都在15 s左右達到峰值,果糖會更早達到峰值,造成甜味短暫沖擊,但持續時間較短;還會造成風味后勁不足略顯寡淡。新橙皮苷二氫查爾酮、索馬甜、甘草甜素等甜味峰值會相對延遲,且甜度持續時間比蔗糖更長,使得余味持久、而清爽不足。混合合成甜味劑已經被用來幫助減少單一甜味劑導致的不良口味。對常見的代糖產品從是否含有苦味、是否具有余甜味,以及是否有額外的味道等3個方面進行感官評價對比,每種代糖的感官評價結果詳見表
2[1]。

表2 常見代糖的感官評價
1.2 對代謝的影響
有研究表明:代糖產品可以減肥,改善反應性低血糖和糖尿病,部分人工合成代糖和部分天然代糖均可促進胰島素正常分泌,這對于糖的代謝是有益的。阿斯巴甜、木糖醇、赤蘚糖醇、阿洛酮糖、塔格糖、索馬甜不會促進胰島素的分泌。大量文獻報道,代糖有可能造成腸道菌群的失調,從而導致腹瀉現象或糖不耐癥。糖精和三氯蔗糖都會對腸道菌群產生消極的影響。常見代糖對人體代謝的影響見表3[1]。

表3 常見代糖對人體代謝的影響
1.3 代糖的熱值、甜度、價格
代糖的第一大優點就是甜度較高,如糖精鈉的甜度比蔗糖甜300~500倍;第二大優點是熱值小、甚至是零熱量,如人工合成代糖和天然代糖(甜菊糖苷、羅漢果甜苷、索馬甜)等,熱值均為零;第三大優點是價格低廉,例如,同樣甜度下,紐甜的價格比蔗糖低數千倍。常見代糖的熱值、甜度、價格詳見表4[1]。

表4 代糖的熱值、甜度、價格
1.4 天然和合成甜味劑的結構、每日容許攝入量和生物效應
一些常見的天然和合成糖的分子結構,每日的安全攝入量的規定,以及生物學效應等信息,詳見表5[3]。從生物學效應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代糖是相對安全的。

表5 天然和合成甜味劑的結構和生物效應
1.5 甜味蛋白的特性
甜味蛋白是一類熱門的天然代糖,包括索馬甜、莫內林、馬檳榔甜蛋白、培它丁、布拉齊因、仙茅甜蛋白、神秘果素。索馬甜是最典型甜味蛋白,它是從非洲的一種竹竽科(Thaumatococcus daniellii)多年生灌木中分離出來的[4]。在中等濃度下,索馬甜會出現甘草味和金屬味[5]。在低濃度下,索馬甜是一種風味增強劑,特別適合與其他高強度甜味劑(除阿斯巴甜)和多元醇混合。雖然索馬甜的投產較早,但受生產成本高的制約,一直未大規模應用。甜味蛋白的安全性相對較高,Joseph等認為索馬甜將成為最有前途的甜味劑之一[2]。其他甜蛋白質,比如布拉齊因和莫內林,由于成本高和高溫不穩定,商業上的應用有限。神秘果素和仙茅甜蛋白可用于食品風味的修飾,有利于提高食品的適口性。不同甜味蛋白的特性比較參見表6[2]。

表6 不同甜味蛋白的特性比較
甜味蛋白氨基酸構成,布拉齊因由54個氨基酸殘基構成,是分子量最小的甜味蛋白,索馬甜由207個氨基酸殘基構成,是分子量最大的甜味蛋白。合成甜味蛋白的基因可以在不同的宿主內進行表達,如細菌、酵母、真菌、轉基因植物。隨著基因工程的不斷發展,為甜味蛋白的商業化生產提供可能研究具有很大的價值。Park等在胡蘿卜愈傷組織中高效表達神秘果素,為神秘果素的工業規模化生產提供了基礎[6]。
2 代糖的潛在風險研究
代糖產品,尤其是人工代糖,從問世之日起就爭議不斷,很多國家的科研人員認為:甜味劑對人體健康造成較大影響,甚至會導致癌癥。糖精和甜蜜素在美國禁用后,現在又恢復使用。此外,代糖在動物體的實驗結果,不能用于衡量和預估及代替其在人體的實驗結果。因此,仍需辯證看待代糖產品,用更為科學的、嚴謹的實驗體系和事實去評估代糖的安全性。
2.1 代糖可能會導致非酒精性脂肪肝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一種以積累為特征的全身性、廣泛性疾病。Emamat等認為低熱量或無熱量甜味劑導致人體“腸道失調”,進而推測,增加人工甜味劑的攝入可進一步提高NAFLD的患病率[7]。Abbas等不贊同Emamat的觀點,他們認為仍需進行前瞻性和干預研究來闡明是否代糖品的代謝會增加肝臟疾病的風險[8]。
2.2 三氯蔗糖高溫時產生有毒物質
三氯蔗糖作為食品添加劑已被全球80多個國家在4000余種產品中使用,也被允許在高溫烹飪如烘焙中使用,全球許多公共衛生權威機構,如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等均認可三氯蔗糖的安全性。然而,近期研究發現三氯蔗糖在高溫下并不穩定,它能夠參與食品加工中的氯化反應,產生有毒物質。當三氯蔗糖或含三氯蔗糖食物在金屬烹飪用具中加熱時,已經具備了生成高毒性的氯代芳香族有害物( 、多氯聯苯和多氯萘)的必要條件(碳源、氯源、催化劑和必需的反應溫度)[9]。
2.3 三氯蔗糖會導致水體污染
三氯蔗糖因其在水環境中被廣泛檢出,且具有高極性、持久性等特點,被US EPA(美國環境保護局)列為新興污染物,相關檢測、降解及毒理學研究逐漸增多。各種各樣的處理過程嘗試驗證水中的三氯蔗糖的降解原理。游離有效氯、臭氧以及高鐵酸鹽對三氯蔗糖的處理效果不明顯。紫外線對三氯蔗糖的光氧化作用也不明顯。然而,具有強氧化性的·OH(羥基自由基)對三氯蔗糖的降解效果最好,其機理是羥基取代三氯蔗糖上的氯原子使其轉化為對環境無害的果糖和糖醇[10]。
2.4 代糖對腸道菌群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只有糖精、三氯蔗糖和甜菊糖改變腸道微生物菌群的組成。根據定義,益生元是一種不可消化的食物成分,但一些多元醇可以被少量吸收,至少部分通過被動擴散在腸道吸收。然而,其中一些如異麥芽糖、麥芽糖醇、乳糖醇、木糖醇,可以到達大腸并增加人類體內雙歧桿菌的數量。進一步研究甜味劑對人體腸道微生物組成的影響是有必要的[11]。Bian研究發現,糖精通過改變腸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謝功能誘導小鼠肝臟炎癥。最近研究發現,攝入安賽蜜的99%作為完整的分子在小腸中被完全吸收,并通過血液分布到不同的組織,而在結腸中微生物群基本不會直接接觸到安賽蜜,但結腸內的厚壁菌門細菌數量卻增加了,益生菌A. muciniphila的數量減少了[12]。
2.5 木糖醇可導致腹瀉
木糖醇工業在中國已經發展了50多年,它的口感最接近天然,與蔗糖甜度比較相近,常用在牙膏、口香糖中。但木糖醇有一個明顯缺點:在人體腸道內吸收率不足20%,易造成腸壁積累,從而出現腹脹、腹瀉等問題。不同糖醇耐受程度的人群腹脹反應不同,因此,木糖醇很少用于飲料。但目前有研究表明,低劑量的木糖醇可刺激胃腸激素的分泌,并引起胃排空速度減慢,從而增加飽腹感,而且對血脂、血糖和胰島素的影響很小[13]。
2.6 非營養性甜味劑可能引發肥胖和II型糖尿病
有證據表明:受到過度食用營養性甜味劑不利于代謝和健康的影響,非營養性甜味劑(NNS)消費逐年增加,特別是在肥胖人群與糖尿病患者中。非營養性甜味劑的特征是具有零或可忽略的熱量負荷,同時具有甜蜜的味道。有人認為用其替代傳統的食用糖,可減少能量攝入。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實際情恰恰與人們所認為的相反,非營養性甜味劑會導致代謝性疾病的發展或惡化,包括代謝綜合征、肥胖、II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14]。
人工甜味劑攝入與糖尿病發生率關系的研究是比較深入的,表7中列舉了6項調查報告,其中3項研究表明:人工甜味劑攝入會導致II型糖尿病發生率的升高,另外3項研究發現:人工甜味劑攝入與糖尿病發生率之間沒有關聯,詳見表6[15]。

表7 人工甜味劑的攝入與糖尿病發生率的關系
3 代糖的應用
3.1 中國批準使用的代糖
我國對代糖的應用一直是比較嚴謹的,GB 2760-2014中批準使用的甜味劑包括:N-[N-(3,3-二甲基丁基)]-L-a-天門冬氨-L-苯丙氨酸1-甲酯(又名紐甜)、糖精鈉、環已基氨基磺酸鈉(甜蜜素)和環己基氨基磺酸鈣、異麥芽酮糖醇(氫化帕拉金糖)、天門冬酰苯丙氨酸甲酯(又名阿斯巴甜)、天門冬酰苯丙氨酸甲酯乙酰磺胺酸、麥芽糖醇和麥芽糖醇液、山梨糖醇和山梨糖醇液、D-甘露糖醇、木糖醇、赤蘚糖醇(生產用菌株:解脂假絲酵母)、甜菊糖甙、甘草和草酸酸一鉀及三鉀、乙酰磺氨酸鉀(安賽蜜)、甘草酸胺、L-a-天冬氨酰-N-(2,2,4,4-四甲基-3-硫化三亞甲基)-D-丙氨酰胺(阿力甜)、乳糖醇(4-β-D-吡喃半乳糖-D-山梨醇)、羅漢果甜甙、三氯蔗糖(蔗糖素)、索馬甜[16]。
3.2 代糖下游應用種類
甜味劑的下游主要應用領域包括飲料、烘焙食品、調味品、個人護理產品、藥品等。其中,飲料占比50%,是甜味劑最大的應用領域。飲料中使用較頻繁的代糖有阿斯巴甜、安賽蜜、三氯蔗糖、甜味菊糖苷和赤蘚糖醇。多種甜味劑的混合使用,一方面,可以有效增加甜度;另一方面,可以規避單一甜味劑導致的不良口味[17]。
3.3 國內外代糖新產品的發展
陸婉瑤等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的代糖新產品數量增長較快,代糖新產品在總甜味產品的比重也較大。美國、韓國、日本代糖新產品所占的比重分別為51.4%、51.3%、52.1%,而中國、印度、巴西的這一比重分別為5.5%、17.9%、31.2%。中國的代糖類產品剛剛處于興起階段,代糖產品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17]。
代糖新產品在國外的流行與一些大公司的推廣和宣傳有一定關系,例如,雀巢(Nestle)在2017~2020年將主要產品中的糖添加量降低5%;百事可樂(Pepsico)到2025年至少67%的飲料每12盎司中添加糖的熱量不超過100 kcal[18]。目前,國內消費者對代糖產品不是十分青睞,主要與民眾認為食用代糖可能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還與代糖產品的口味欠佳有關。
3.4 減少食物含糖量的策略
減少食物含糖量的方法可以分為4種:一是糖替代品;二是多感官整合;三是食品結構技術;四是逐步減少糖[18]。糖的替代品(非營養性甜味劑、糖醇和結構纖維)的優點是可以大幅度的減糖, 缺點是很難復制蔗糖的感官特征。非營養性甜味劑難以促使消化道釋放提升飽腹感的化學信號,讓人“不容易飽”,這也容易增加熱量攝入。利用多感官整合原理(特別是香氣)可以有效地降低糖含量,但糖的還原量很小。食品結構的創新在不顯著改變食品成分的情況下減少了食糖,但在大規模生產的食品中可能很難實施。逐步減少糖,如果消費者接受感官特性的變化,就比較容易制定方案,但逐漸減少食糖會給食品公司帶來困難、銷售額降低,不太可能實施。因此,食品制造商綜合運用一系列技術的整體方法可能會取得最好的進展。然而,在不影響感官特性的情況下,在加工食品中大量減少糖分可能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4 代糖研究展望
代糖產品從出現開始就對其安全性有很多爭議,根據現有研究和國家規定甜味食品的衛生指標執行表明,代糖在規定添加量內使用是安全的。食品企業應清晰標明代糖的名稱及用量,讓消費者根據需求自行選擇。未來在代糖安全性的研究上,應開展有針對性的科研驗證,并建立嚴格的監測體系。Eleonora Moriconi等指出,將來的前瞻性研究旨在解決不同種類代糖在不同臨床環境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各種臨床環境包括肥胖、II型糖尿病、代謝并發癥和不同年齡的人。代糖所引起的中樞神經系統回路反應、腸道激素分泌作用和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19]。Michelle D. Pang等認為,未來的研究應該重點考慮不同人工甜味劑的代謝途徑,長期監測并評估不同人工甜味劑對微生物菌群的影響,進而系統評估代糖對體重控制和葡萄糖體內平衡的影響[20]。
食糖不僅是調味品,給人們帶來愉悅美妙的口感,更是人體5大營養素之一。要科學認識食糖、合理消費食糖[22]。糖是大腦和神經系統的唯一能源,世界衛生組織認為:適量吃糖有益健康,一般不超過45 g/d。隨著“中國政府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國家戰略的確定,倡導人均每日添加糖攝入量不超過25 g,適量食糖已成為行業共識,同時也為糖和甜味劑產業發展指明了大方向[21]。
目前我國代糖市場還屬于起步探索階段,作為功能糖和高倍甜味劑原料的主產國,國內企業發展代糖類產品具有較大的原料優勢。消費者對健康的關注與健康食品的需求,將帶動未來代糖新產品資源的開發圍繞安全可靠、高甜度、易生產、價格便宜、天然、甜味特性好、性質穩定、低熱量或零熱量等方向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