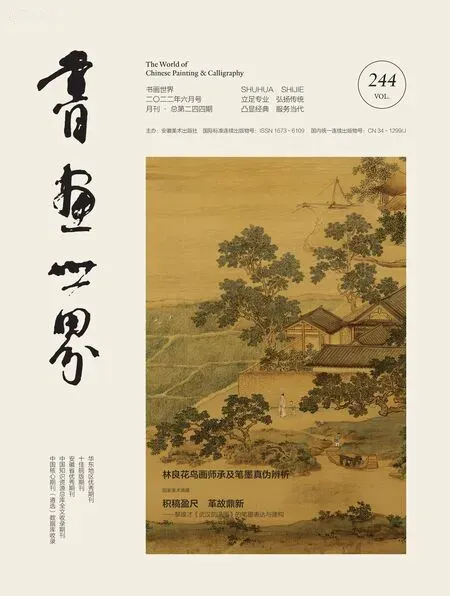明代戲曲小說版刻插圖的“跪拜”圖像研究—以“公堂審訊”圖像為中心
文_劉京晶
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內容提要:戲曲小說版刻插圖作為繪畫藝術的一種,在明代以“公堂審訊”為主題的“跪拜”圖像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本文從審訊場所中的隱喻性、“公堂審訊”的圖文預敘功能,以及審訊中的時空轉換等多角度出發,窺視中華傳統文化中有關“跪拜”圖像的政治空間,從而發掘出明代戲曲小說版刻插圖“跪拜”圖像的深層意蘊。
自古以來,戲曲小說都深受人們的喜愛,中國古代戲曲小說中的大量版刻插圖更是有其獨特的藝術韻味。版刻插圖中 “跪拜”主題種類繁多,最常見的如“日常生活”類的私人空間、“公堂審訊”類的政治空間以及“祈神祭拜”類的神性空間等。其中“公堂審訊”類主題的公堂構圖極具隱喻性,戲曲小說的圖像和文本還具有圖文預敘的功能。此外,在時間和空間的關系上,“公堂審訊”類主題呈現出一種時空的轉換。明代戲曲小說版刻插圖的“跪拜”圖像運用“公堂審訊”主題,展現出一種極具威嚴感的政治空間。
一、審訊場所中的隱喻性
(一)屏風設置
作為中國傳統繪畫的重要題材,公堂官員身后存在的屏風是極具隱喻性的。事實上,屏風有“障”的作用,也就是用屏風的分隔作用來營造一種政治空間;此外,屏風還具有“彰”的功能,為表達“公堂審訊”這一主題的文化韻味,明代戲曲小說版刻插圖的“跪拜”圖像往往以屏風上的繪畫來反映官員所崇尚的思想,呈現出一幅幅“畫中畫”。從公堂審訊中屏風的政治空間的意義上來講,在描繪公堂審訊場景的大量明代戲曲小說圖像中,屏風似乎是司法場域中的重要工具。室內的屏風分隔了公堂中的“暖閣”,而室外的屏風虛擬了公堂審訊的場景。就屏風作為繪畫主題的空間意義而言,屏風的描繪有著多種表現形式。例如,圖1中的屏風進行了留白處理,讓畫面變得更加簡潔,而且突出了審判官員的權威形象。圖2中的屏風再現了公堂上常用的“海水朝日圖”或“指日高升圖”,它象征著官員強烈的政治野心。圖3的屏風則以山水入畫,山水具有遼闊之感,往往有著吉祥的寓意。

圖1 屏風進行留白處理(選自《何文秀玉釵記》)

圖2 屏風中再現“海水朝日圖”或“指日高升圖”(選自《古本小說集成》)

圖3 屏風以山水入畫(選自《靈寶刀》)
(二)人物位置
作為權力的宣示者,審判官員和他們所支配的案件往往處于圖像最核心的位置,是整個公堂審訊畫面中最為關鍵的焦點區域,也是畫面中的主導者。這不僅體現在其往往位于公堂場景的中心位置,還體現在官員的烏紗帽、官袍、腰帶及其特殊的形態特征上。正是借助這些元素,審案官員的權力更大程度地彰顯出來。這也成為戲曲小說圖像的讀者熱衷于關注的焦點。這種處理方式,不僅與科舉制度的社會背景相吻合,而且與中國封建社會所塑造的親民“父母官”形象有關,甚至與宗教傳統也有一定的聯系。
除審案官員這一廳堂審訊的權力核心之外,站在公案旁邊的胥吏是明代廳堂審訊圖像中的聽審襄助者。官與吏之間相互依存且相互敵對,他們之間有著極為微妙的聯系。一方面,由于胥吏對官府的基本事務已經熟知,官員不得不依賴他們的經驗、學識和人力來處理復雜的事務,更不用說那些想要利用胥吏來接受賄賂的腐敗官員;相反,那些平日收入較低的胥吏,需要靠官府才能謀取利益。但是,所謂“清官難逃猾吏手”,如果官員任憑胥吏對百姓進行敲詐,不僅會危害百姓,也會有損官員的名譽。所以,那些清正廉潔的官員,必須盡力去約束和控制胥吏;同時,貪圖利益的胥吏們會想方設法地擺脫官員的束縛。因此,官員與胥吏之間便一直上演著“控制與反控制”的權力博弈。
明代戲曲小說的廳堂審訊圖像中的衙役形象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站在公堂下面拿著手杖的皂隸;另一種是站在廳堂另一邊,與胥吏相對而立的門子。從這兩種人物的形象,可看出他們有著一剛一柔的強烈對比。作為威儀的代表者,他們營造出一種威嚴肅殺的氣氛。
除此之外,兩造是公堂中恩典的祈求者。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公堂審訊圖像中,作為接受審訊的兩造,他們幾乎都跪在公案前面或下面。這與中國古代傳統意識里所謂的“大堂之上,公案之下”相契合。因為他們身體跪拜的姿勢,相比于審案官員而言,形成一種視覺空間中的地位差別。更可措意的是,這不僅是一種肢體上的下跪,也暗示著權力關系中的屈服。也就是說,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展示出對以審案官員所代表的國家權力的屈服,從而體現出傳統中國司法權力的專斷。
二、審訊中的圖文預敘
預敘是敘事學中的一個重要術語。熱奈特指出,故事時序和敘事文時序之間存在著很多形式的不協調,他稱之為“逆時序”。他將關于提前講述以后發生的事件的敘述形式,稱為“預述”。里蒙-凱南提出,“預敘是指在提及先發生的事件之前敘述一個故事事件;可以說,敘述提前進入了故事的未來”。在明代戲曲小說的公堂審訊圖像中,預敘的功能就是在讀者閱讀文本之前提前告知或預示故事的發展方向,以此增強故事的懸念性和趣味性。里蒙-凱南提出,當出現預敘時,它就會使“接下去將發生什么事情”所引起的懸念被另一個懸念代替,也就是圍繞著“這件事將怎樣發生”的懸念,使得讀者有繼續閱讀的興趣。
古代戲曲小說圖像文本的敘事,既不同于純粹的圖像表現,又不同于單純的文本敘事。其不同之處便在于它是圖文敘事或在圖文的互文性中敘事。它在履行敘事職能的時候,一方面表現出一種“逆時序”的特點,具有像文本敘事一樣的“預敘”功能,另一方面還帶有明顯的圖像文本特點。
古代戲曲小說圖像文本敘事由圖像敘事、文本敘事,以及二者之間的互文性共同來完成。明代戲曲小說中的圖像很多都是卷首圖,從圖像和文本的位置關系上來講,常常是圖像在前面,文本在后面。也就是說,在閱讀戲曲小說文本之前,讀者首先看到的是文本之前各種各樣的圖像。因為這些圖像大多概括性地反映出戲曲小說文本中的重要情節與關鍵角色,所以圖像敘事就成為一種“預敘”。作為一種預敘,戲曲小說圖像“提前進入了故事的未來”,既吸引讀者進入戲曲小說一環接一環的故事情節中,又引導著讀者的閱讀行為。這使得讀者從一開始便處于一種閱讀期待中,讀者閱讀的興趣便大大增強。
三、審訊中的時空轉換
(一)在時間程序中獲得空間
從橫組合序列角度而言,可以將戲曲小說圖像看作是為戲曲小說文本所設置的預敘。它既以逆時序的形式提前揭示著故事情節的發展方向,又以“語-圖”互文的形式帶入后面的順時序敘事。此外,從縱聚合角度來講,戲曲小說圖像文本“語-圖”的關系呈現出敘事的時空體,主要表現為在時間程序中獲得空間。
戲曲小說圖像文本敘事性的特別之處是它呈現出圖像敘事和文本敘事的結合。圖像敘事展現的是空間性,而文本敘事凸顯的是時間性。那么,戲曲小說圖像與文本是如何實現完美結合的,這是戲曲小說圖像文本敘事必須回答的問題。首先,文本敘事所呈現的線性時間,表現為故事情節一環接一環地往后進行,或許沒有任何想要結束的苗頭,這會讓讀者一直好奇下面還會發生什么事情,所謂的懸念都是為使這種時間程序充滿好奇和期待。但是,戲曲小說圖像文本中文本敘事的線性時間并不是純粹的,甚至它只是“偽時況”,進而變成了一種時空的結合。
(二)在空間布局中修飾時間
從縱聚合序列的角度來講,戲曲小說圖像文本是運用敘事停頓、隱喻空間營造等方式從時間程序中獲得空間,但只有圖像的隱喻空間,或空間若只是靜止的,還不能夠成為敘事,“敘事就是以事件的轉變為前提,它意味著從一個事件轉變為另一個事件,意味著時間性。……敘事不僅需要記錄時間,尤其需要運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修飾時間”。所以,從橫組合序列來說,戲曲小說圖像文本要實現真正的圖文敘事,必須讓空間化的戲曲小說圖像呈現出時間性,也就是在空間布局中修飾時間。
戲曲小說圖像文本敘事既要有故事的時間程序和線性推演,又要有空間聚合與深層布展,不僅是在時間程序中獲得空間,同時也是在空間布局中修飾時間。所以,這是一種獨特的敘事時空體。
結語
在戲曲小說版刻插圖“跪拜”圖像的創作上,明代藝術家將以“公堂審訊”為主題的“跪拜”圖像的隱喻性、預敘和時空轉換功能展現得淋漓盡致,并將對當時社會的獨特見解融于畫中,為世人留存了一幅幅耐人尋味的版刻插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