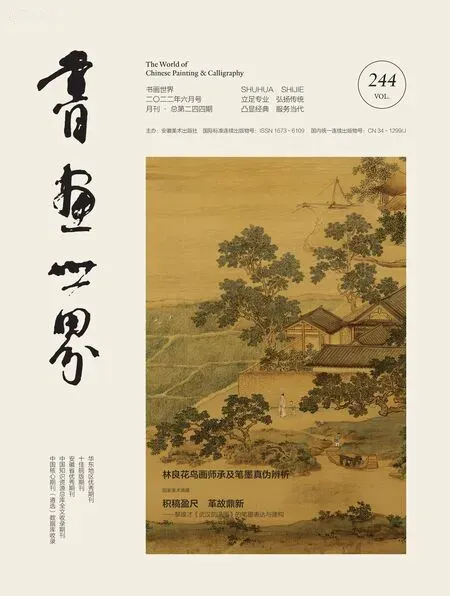年俗中的書法—當代書協春聯活動反思
文_林春衍
湖北美術學院
內容提要:春聯的書寫古已有之,延續至今日,書寫卻變成了“打印”。幸運的是,在中國書協、地方書協,以及一些人士的努力下,手寫春聯傳承了下來。每逢春節前后,“送春聯”活動不僅具有書法傳播意義,更是一種保護文化的舉措。本文結合古代年俗書寫傳統與當代書法環境,綜合考察各地書協每年一度的“送春聯”活動之利弊,探究這一傳統的發展和演變。
一、人們表達美好愿景的“舊方式”
春聯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年俗,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最開始人們在桃木板上刻符或是畫神將以求平安,后來開始書寫文字以祝愿賜福。清代梁章鉅在《楹聯叢話全編》中說:“楹聯之興,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慶’‘長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蓋自宋人始,而見于載籍者寥寥。”后蜀皇帝孟昶創作了可能是中國的第一副春聯“新年納余慶,佳節號長春”。由此,中國人以吉祥詩句書寫春聯來祝福春節的傳統便開始了。宋代王安石《元日》中“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描寫的便是春節時張貼春聯的場景。明代坊間傳聞,明太祖朱元璋號令全國百姓在春節期間掛上對聯,并微服出訪去感受每家每戶的節日氣氛。清代以降,社會上各階層都積極地投入春聯的創作活動中來,“春聯書法”也時常誕生一些書作佳品。
由民俗藝術發展而來的春聯書法,含有特定的內容和節日意義,如今它大多用于表達人們對未來的美好祝愿。譬如“喜居寶地千年旺,福照家門萬事興”祝愿福旺、家興,“金牛開出豐收景,喜鵲銜來幸福春”祈愿來年豐收、幸福,“七旬赴宴三千叟,五代同堂二百家”期盼子孫滿堂、家人長壽。
如此歷史悠久的新年祝愿方式,在當代各地書協的“送春聯”活動中延續了下來。書家們用墨或是金粉在紅紙上書寫,配以吉語,在人海中擺臺揮毫,營造出喜慶、祥和、熱鬧的氛圍。在書家們的筆下,人們仿佛回到了木門楹柱掛紅聯、鞭炮福燈除舊歲的往昔。各地書協的春聯活動不僅是對“舊方式”的繼承,更是對中華文化精粹的保護和傳播,它已成為當今科技時代的“新傳統”。
二、機械復制時代下的“新傳統”
在21世紀的中國,手書春聯更多地被機器復制取代,簽字筆的使用和書法環境的變化使多數人喪失了毛筆書寫能力。書法進入純粹藝術的時代,高效率和低成本誘導著春聯書法走向市場化、商品化。在追逐利益與速度的潮流中,人們降低了對儀式感的需要和對知識文化的需求。在隨處可見的市場上購買一副機制春聯,總是比自己精心書寫或者請某個更有知識文化的人書寫要方便和容易得多。
這不僅改變了以往的風俗和傳統,同時也是對楹聯書法文化傳承的破壞。最初,作為民俗的春聯,在很大程度上培養了民眾對書法的興趣。人們通過善書者所寫的“兩條紅聯”,聯想到書法本身的美感。正是由于家家“各書己聯”,或找宗族里的讀書人書聯,春聯書法在過去呈現出形式豐富的特點。機械復制則是千篇一律的魏碑體、行楷書,板正呆滯,毫無生命力可言,手書春聯的唯一性、藝術性完全消失:效率提高了,“美”卻消失了。這種破壞不僅體現在書法領域,同樣也損害著由春聯內容所傳遞的詩聯文化。明代文震亨于《長物志》中言:“用木為格,以湘妃竹橫斜釘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兩旁用版為春帖,必隨意取唐聯佳者刻于上。”由此可知,在明代書刻春聯,內容必須從唐代佳聯中選,符合格律與法則。而今的復制春聯忽視了這一點,完全由現代人自擬不合格律的聯句,甚至出現許多意思不通、平仄不對的病聯。春聯書法所含有的書法美和詩情被機器和商業湮沒。
當代書協的“送春聯”“書春聯”活動,奮力地抵抗著機械復制時代對春聯書法、春聯文化的破壞。書法家將書寫的習慣與行為帶回人們的視野,喚起民眾對傳統文化的熱情。盡管各個書家的水平風格不一,但書寫的本質是相同的。它傳遞出漢字的魅力與書法的內涵。只有在書寫中春聯才有真正的生命力,書寫的并不只是文字本身,更包括漢字文化的法則與詩句韻律的意境。為何書寫出來的春聯與機械打印的漢字有著本質的區別?誠然,二者皆處于視覺層面,但正如朱良志先生所說:
書法與漢字的根本差異就在于書法擴大了漢字的生命表現力,豐富了漢字所表現的生命內容,從漢字到書法雖是一步之遙,卻完成了從民族共同體的共性符號到展示個體生命的個性符號的轉換。
漢字體現了宇宙人生精神,那只是上古時期造字者的體驗,書法卻直接打通了書家個體和宇宙的聯系;漢字以一種特殊的線條和想象的空間表達了漢民族對世界的看法,書法極盡這線條和空間的變化,賦予它更激烈的沖突,更飄忽的意態,更奇妙的組合,更神秘的空間。
除了在書寫上的功夫,書協會員手書春聯在內容品位上也高于機制的春聯。機制春聯的商家往往審美能力不夠,藝術和文化的品位低下,更懶于尋找佳句好詞。他們所選聯句大都了無新意,藝術性被實用主義碾壓。書協會員一般來說在文化修養和楹聯知識儲備上遠勝于商家,書法美與詩意美在春聯中才實現了相對的統一。
書家們用書法建構起民俗與書法、傳統文化之間的橋梁,既向人們展示了書法的面貌,又傳播著聯句背后的意境與內涵。各地書協已舉辦了幾十年的寫春聯、送春聯系列活動。每逢春節,書家便走鄉串戶,不懼嚴冬寒風,在室外免費給人們書聯。這份溫情和堅守在當今充斥著機械復制的時代尤為珍貴,春聯活動也成為一種新的傳統,它在傳承春聯年俗的同時,也延伸了書法和楹聯文化的邊界。
三、重復和屈才的“兩難境”
因各地情況不同,書協春聯活動所選的場所和舉辦方式依情況而定,基本上會持續一個星期甚至上十天,一個功力深厚而享有名聲的書家往往要連書好幾天。一般情況下(尤其是在“送聯下鄉”的活動中),每人可免費獲得一副由書協書家手寫的春聯。活動從開始到結束,每天都會有大量鄉親來索取對聯。這不僅給書家帶來了過重的負擔,還削弱了春聯書法的藝術性。
作為書協的書家,我們應該大量練習或是創作對聯書法,而春聯書法正是對聯書法的一種。黃惇先生考證道:“在明代嘉靖至萬歷年間,民俗對聯在社會各行各業廣泛傳播,在這一雅俗觀大轉變的時期得到文人書家的接受,大批士大夫、文人參與創作,使原來民俗中的桃符、春帖、春聯逐步演化成在廳堂、書齋懸掛觀賞的書法對聯。”創作一副精彩的對聯是極需要心思和氣力的,要在幾天內不間斷地書寫春聯,可想質量將難以保證。有時一個書家一天要寫50副以上的春聯才能應付眾多的索聯者,如此多的數量意味著書家很大程度上是在做一種機械、重復的“生產”,而不是書法創造。它消磨著書家在此時的書法藝術性和創新性。很多書家為了方便省事,往往來回書寫同樣的聯句,毫無變化,更不愿意去思索和創造新的春聯內容與書法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書寫的意義和書法的功能大打折扣。
還有一種現象,也是值得書協注意和警醒的:書家在春聯活動中的主觀性“屈才”。因為書家面對的大部分是普通的勞動人民,他們并未受過專業的書法訓練和審美教育,在商業打印春聯的影響下,對所謂“俗書”更加青睞。書協書家的風格很難被大眾普遍地接受和欣賞,往往寫了幾副自己認為不錯的春聯作品,卻受到索聯者的質疑和不滿。有些書家便放棄自己所擅長的寫法,為了好評與稱贊轉而迎合大眾的審美。他們大都采用比較圓熟、軟媚的書風,以期符合人們的認識和審美水平。為了使觀眾可以看懂,書家大量地使用行楷書體,在能夠飛揚處停滯,把繁體改成簡體。在內容上,書家從網絡上尋找更貼合商業、世俗的現代聯句。雖然如此選擇聯句并沒有背離對聯書法的本質,卻是一種下下之策。余德泉先生曾經把對聯的內容概括為七個方面:“一、宣示哲理;二、概括人生;三、昭明心志;四、錄載史實;五、寄寓褒貶;六、抒發情感;七、描繪風光。”春聯作為對聯的一種,也理應遵循這七個方面的要求,書家對內容質量的忽視不但降低了春聯的美感,同時也喪失了春聯書法對傳統文化的宣傳和保護功能。如上文所述,文震亨在《長物志》中說“必選唐聯佳者刻于上”,書家從唐詩、唐聯中擇優所書,既保留了春聯書法內容上的高雅和精致,又傳播了唐詩文化,豈不兩全其美?
當然,我們不能過于理想化地看待春聯活動,許多客觀條件(諸如需求量大、大眾欣賞水平低等)迫使書協在舉辦此類活動時出現了上述現象,陷入兩難的境地。所以,有時我們可以允許少部分應酬之作的存在。但一定不能忘記:書協肩負著書法振興和發展的職責,書家應該在主觀上對自己有高標準、高要求,著力化解大眾與書法家之間的審美矛盾,向他們普及更多的書法文化和楹聯知識。

許偉東 得樂長歌五言聯68cm×23cm×2 2017
總的來說,當代各地書協在每年舉辦的春聯系列活動,蘊含著保護、傳承中華文化精粹的深意。它是積極的,是有生命力的“新傳統”。年俗中的書法,不僅書寫著人們長久以往對來日的美好期許,更是中華兒女對傳統風俗和中國文化的一次呼喚。在這個層面上說,春聯書法活動的持續舉辦,是一種有著“衛道”精神的文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