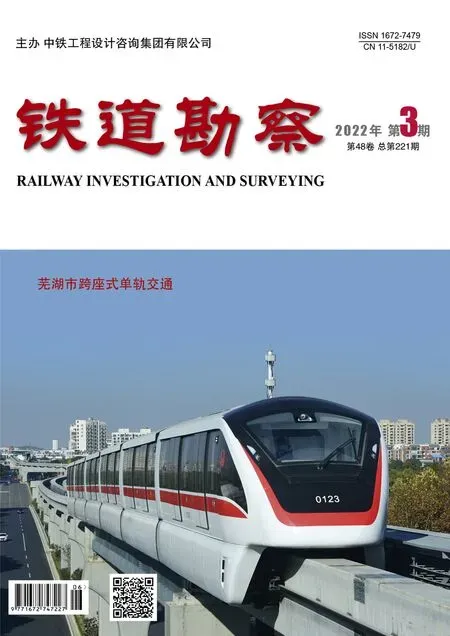高速鐵路隧道間距對巖體變形及應力分布的影響
2022-08-01 05:59:48邱冠豪
鐵道勘察
2022年3期
關鍵詞:裂紋
邱冠豪 王 飛
(1. 中鐵工程設計咨詢集團有限公司鄭州設計院,鄭州 450001; 2. 鄭州大學水利科學與工程學院,鄭州 450001)
工程孔洞在地鐵、隧道、礦山等工程中較為常見,其穩定性對工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1]。 其中,孔洞間距是設計中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隧道間距對于工程穩定性影響的研究具有重要工程指導價值。 已有學者進行相關研究,CAO 采用簡化理論、室內試驗和數值模擬等方法,解決現場原位試驗的操作性差、經濟成本高等問題[2];EXADAKTYLOSA 以彈性理論為基礎,研究孔洞形狀對巖體受力狀態的影響[3];CHAO 進一步將研究擴展到多孔洞的應力分布規律研究,發現孔道間距、形狀對其受力狀態的影響[4];HUO 等以現實為依據,采用室內試驗和數值模擬對不同工程情形下的力學進行研究,探索孔洞形狀、孔洞與缺陷的相對位置、孔洞間距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5-12];FAN 等研究了含有孔洞的試樣在單軸壓縮下的力學性能、應力分布和破壞行為,發現孔洞破壞明顯與試樣強度和裂紋發育有關[13];ZHU等研究含有不同充填物和孔洞的砂巖試樣的力學行為和裂紋演化,發現充填物類型和孔洞形狀都對峰值應力和變形特性有重要影響[14]。
以下基于合理的雙孔間距,針對高鐵雙孔隧道的實際情況,開展含兩孔試樣的力學性質實驗。 先采用類巖材料制作不同孔間距的試樣,進行單軸壓縮力學測試。 試驗過程中,采用聲發射(AE)裝置和DIC 設備監測試樣的加載破壞過程,以便進行裂紋起裂、擴展研究。……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艦船科學技術(2022年20期)2022-11-28 08:19:18
艦船科學技術(2022年13期)2022-08-11 09:29:16
艦船科學技術(2022年6期)2022-04-19 11:01:3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學學報(2021年4期)2021-11-22 07:44:46
山東冶金(2019年6期)2020-01-06 07:45:58
World Journal of Diabetes(2019年7期)2019-07-23 11:52:08
山東冶金(2019年3期)2019-07-10 00:54:06
揚子江(2019年1期)2019-03-08 02:52:34
四川輕化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7年3期)2017-06-29 12:00:57
焊接(2015年2期)2015-07-18 11: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