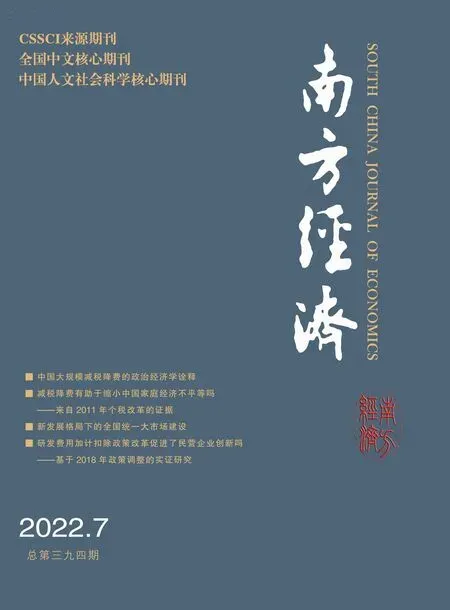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促進了民營企業創新嗎
——基于2018年政策調整的實證研究
李 源 王 陽 羅浩泉 陳斐然
一、引言
2018年中國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進行了重大改革,最主要的改革內容有兩項:一是提高了加計扣除比例,由原先的50%提高到75%;二是擴大了政策適用范圍,由原先僅適用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擴大到所有負面清單之外的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旨在通過為企業創新減稅,降低企業創新成本來激發企業創新積極性。在企業研發投入和企業專利及發明專利申請中,民營企業占比均達到90%以上,是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主要受益群體(1)筆者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數據計算。。但是,在高加計扣除政策激勵之下,部分民營企業存在著操縱會計賬目虛高列支研發費用的可能(楊國超等,2017;萬源星等,2020)。此次改革不僅提高了加計扣除比例,而且進一步增加了政策普惠性,尤其是大量非科技型企業納入到適用范圍后,為辨別是否會出現大范圍虛列研發費用的“偽”創新現象,有必要對其政策實施效果進行細致的評估。
目前對中國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研究文獻主要是基于2016年之前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該時期政策修訂主要集中在調整歸集口徑范圍和適用主體范圍,未涉及加計扣除比例的調整(任海云、宋偉宸,2017;王登禮等,2018;馮澤等,2019;萬源星等,2020;吳秋生、馮藝,2020;劉曄、林陳聃,2021;等)。僅有少量文獻關注到201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石紹賓、李敏(2021)采用標準DID方法研究發現,2018年的政策強度提升能夠激勵制造業企業創新,但研究結論無法排除2015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變化的影響。楊瑞平等(2021)、吳秋生、李官輝(2022)均以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對象,采用標準DID方法,研究發現2018年的政策強度提升顯著降低了高新技術企業創新投入增長率,但研究結論難以有效排除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影響。總體來看,對于201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對企業創新影響的研究還不夠豐富、充分和深入。
綜上,本文以民營企業作為研究對象,選取2016年~2019年A股上市公司相關數據,采用連續DID方法,考察201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對民營企業創新的影響。同時考慮企業的行業、規模、技術類型、生命周期等異質性因素均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任海云、宋偉宸,2017;劉詩源等,2020),實證檢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對民營企業創新的異質性影響。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實證考察2018年的政策改革對民營企業創新的實際激勵效果是否符合預期。二是豐富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影響的研究方法。以201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調升為契機,采用連續DID方法評估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影響,為后續研究提供有益探索。三是深入考察2018年政策改革對民營企業激勵效果的異質性,為后續進行更加精準的政策改革提供實證支持。
本文其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政策改革背景;第三部分是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第四部分是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穩健性檢驗;第六部分是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政策改革背景
我國從1996年開始頒布實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截止到2021年4月,該政策已歷經多輪改革(見表1),而改革表現出了漸進式的特征:

表1 中國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沿革
(1)政策逐漸系統化和體系化。200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被以法律形式予以確認。(2)適用主體范圍逐漸擴大。2003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取消了對企業所有制的限制;2006年,主體范圍從工業企業擴充至財務核算制度健全、實行查賬征稅的內外資企業、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等;2015年,首次提出適用主體范圍的負面清單制。(3)費用扣除口徑逐漸拓寬。2008年首次對研發費用扣除口徑做出詳細規定;2013年和2015年扣除口徑逐步放寬,縮小了與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研發費用歸集口徑的差異。(4)扣除比例逐漸提高。2017年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扣除比例從50%提升至75%,2018年財政部、稅務總局、科技部聯合出臺《關于提高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的通知》(財稅〔2018〕99號),范圍由科技型中小企業推廣至負面清單之外的所有企業,同時扣除比例由50%上調至75%。2021年國家再次調整政策,將制造業扣除比例從75%提升至100%。
近年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已成為我國激勵企業科技創新的最為重要的普惠性政策。數據顯示,全國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數由2015年的5.3萬戶攀升至2019年的33.9萬戶,年均增長59.0%;減稅額由2015年的726億元增加至2019年的3552億元,年均增長48.7%(2)曾金華,制造業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至100%——真金白銀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經濟日報, 2021-03-28(04)。。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視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并且各國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具有對象不同、力度不一和配套其他政策組合實施等特點(Daniel,2021)。例如,英國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主要針對小型企業,而土耳其的政策對象是科技型公司;印度的扣除比例控制在100%~200%之間,而巴西的扣除比例控制在160%~180%之間;愛爾蘭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通常是與其他政策一起配套實施。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尚處于中低水平,因此有必要考察2018年政策實施效果,為后續政策改革方向提供實證支持和啟示,例如可否將2021年的政策改革舉措擴大到所有負面清單之外的企業,可否在此基礎上繼續提升加計扣除比例等。
三、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與民營企業創新投入
關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民營企業創新投入影響的研究結論并不統一。相關研究結論可歸納為三種:(1)政策對民營企業創新投入具有激勵效果。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會通過產生“非債務稅盾”效應降低企業所得稅負擔,增強企業研發意愿(Kemsley and Nissim,2002;林洲鈺等,2013;任海云、宋偉宸,2017)。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還能夠有效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Takalo and Tanayama,2010)。(2)政策對民營企業創新投入具有抑制作用。部分民營企業存在研發活動與其他活動相互交織的現象,使得各項費用難以準確歸集到相應研發項目中,企業存在故意增加非研發費用支出用于“偽裝”研發費用的可能(萬源星等,2020)。(3)政策對民營企業創新投入的影響不明顯。如果企業為了達到滿足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條件所付出的成本過高,則可能導致政策的無效率(Guellec and Bruno,2003)。由于政策執行存在滯后性和不穩定性,導致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創新的長期促進作用并不顯著(James et al.,2017)。楊瑞平等(2021)實證發現201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會顯著降低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投入增長率,政策對企業創新投入的效果在長期可能不那么明顯。我國進入新時代,創新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民營企業只有通過創新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而我國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不斷改革,旨在支持企業不斷創新。根據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投入具有激勵效應。
(二)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與民營企業創新產出
大多數文獻結論支持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顯著提升企業創新產出數量(賀康等,2020;孫自愿等,2020)。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民營企業創新的融資約束,從而激勵民營企業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引進新工藝等。然而,也有部分研究發現,由于民營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可能引發企業采取策略性創新、研發操縱、迎合政策等尋租行為(黎文靖、鄭曼妮,2016;楊國超等,2017)。因此,提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對民營企業創新產出數量可能同時存在正面和負面影響。還有部分研究進一步考慮了政策對企業創新產出質量的影響。陳強遠等(2020)研究發現,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創新產出質量仍存在正面和負面雙重影響的可能。一方面,企業受到政策激勵,可能會將資源投入到前沿創新活動中,從而提高創新質量(Takalo and Tanayama,2010;Czarnitzki et al.,2011)。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無法具體掌握企業創新產出質量情況,部分企業可能存在利用低質量創新產出來攫取政策紅利的動機,從而導致整體創新產出質量下降(孫剛等,2016;張杰等,2016)。民營企業處于相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其市場競爭力離不開創新能力,更多的“真”創新(包括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意味著更高的市場競爭力,民營企業進行“真”創新的動機會更加強烈。據此,分別提出以下假設:
3.2 甘露醇口服后不被腸道吸收,在腸道內形成高滲環境,阻止腸內水分的吸收并使體液中水分向腸腔內轉移,刺激腸壁傳入神經末梢反射性引起腸蠕動,使整段腸腔容積性瀉下,排除腸內糞便,從而達到清潔腸道的目的[5]。由于口服導瀉劑,需要大量飲水,以及導瀉藥本身口感、不良反應等,容易導致腹脹、腹痛、水電解質紊亂、產生爆炸性氣體,嚴重時患者不能耐受,甚至導致腸出血、腸穿孔[6]。甘露醇可在腸道細菌的作用下產生甲烷等氣體,在行高頻電凝、電切時有易引起氣體爆炸的危險[7]。故不宜應用于內鏡下電切手術前腸道準備。
H2: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產出數量具有激勵效應。
H3: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產出質量具有激勵效應。
(三)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效果的異質性特征
1.行業異質性影響
現有研究發現,不同行業的企業在應對政策改革、市場競爭等環境變化時所采取的創新策略具有明顯差異(林洲鈺等,2013;任海云、宋偉宸,2017)。考慮到2021年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主要是針對制造業企業,為更進一步識別2018年的政策改革對負面清單之外民營企業創新的影響,為后續政策改革提供參考,擬將民營企業樣本劃分為制造業和非制造業進行行業異質性分析。目前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不包括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住宿和餐飲業、娛樂業、煙草制造等行業,這些行業大部分屬于低技術服務業,對創新的依賴程度較低,因此能夠享受該政策的大多是以信息服務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而該類服務業研發投入大、創新意識強(劉詩源等,2020)。此外,我國制造業,尤其是生物醫藥、信息通信等高科技產業的創新績效深受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的負面影響(劉薇、張溪,2019)。基于此,提出假設H4。
H4: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非制造業民企創新投入和產出的激勵效果更大。
2.規模異質性影響
不同規模企業的創新資源、創新意愿不同,對政策強度提升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大型企業通常具有更完善的研發管理流程,能負擔巨額研發費用和承擔研發風險,而非大型企業創新資源相對較少,對研發失敗的風險承擔能力相對較弱(Stock et al.,2002;任海云、宋偉宸,2017),同時考慮到當前國家支持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更加強調中小企業的創新性,若中小企業享有優惠政策,會更有動力加大創新投入。基于此,提出假設H5。
H5: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非大型民企創新投入的激勵效果更大。
3.技術類型異質性影響
相對于低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擁有更強的創新意愿和創新能力(陳遠燕,2016;王春元,2017),但同時由于主要承擔著高技術和新技術的研發,具有更高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有助于降低企業創新成本,分擔創新風險,提升政策強度可能更有助于高新技術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力度。此外,2018年前后爆發中美貿易摩擦,歐美發達國家實施關鍵核心技術壟斷,我國高新技術企業開始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攻克關鍵核心技術上,在增加創新投入的同時,短期內創新產出變得更為困難。因此,提升政策強度在短期內對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可能會弱于對非高新技術企業的影響。基于此,提出假設H6。
H6: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高新技術民企創新投入的激勵效果明顯,但對非高新技術民企創新產出的激勵效果更大。
4.生命周期異質性影響
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具有不同的特征。處于成長期的企業具有融資約束較緊、資本性支出較多等特點,首要目標是在行業中站穩腳跟,將資金用于購置機器設備、建設倉庫廠房以實現產能擴大(劉詩源等,2020;楊瑞平等,2021)。而處于成熟期的企業具有經營模式成熟、組織架構較為完善、銷售網絡廣泛、盈利模式穩定等特點,同時為避免進入衰退期,也需要通過不斷創新以謀求企業持續發展。因此對成熟期企業來講,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增加了可自由支配的現金流,更容易提高創新投入積極性(任海云、宋偉宸,2017)。基于此,提出假設H7。
H7: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成熟期民企創新投入的激勵效果更大。
四、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
(一)研究樣本和模型設定
本文選取2016年~2019年的中國A股上市民營企業為研究樣本,該時間段排除了2015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的影響。2017年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扣除比例從50%提升至75%,2018年才開始推廣到負面清單以外的全部企業。由于上市公司樣本中總資產最低的公司超過了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認定標準,故上市公司樣本中不含科技型中小企業,無需考慮2017年試點政策的影響。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額從企業年報中通過手工獲取,其余數據均來源于CSMAR、CNRDS、WIND數據庫。參照既有文獻做法,對原始數據做如下處理:(1)剔除ST、*ST、PT企業;(2)剔除數據缺失的企業;(3)剔除負面清單制行業的企業。最終得到6173個觀測樣本。
在考察評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效果時,最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標準DID(雙重差分)法,但根據本研究的目的,難以為實驗組構造理想有效的對照組是最大的困難。采用標準DID法的理想情況是2018年前后實驗組的加計扣除比例從50%變化為75%,而對照組的變化應是保持50%不變。但由于數據受限,本文的研究樣本是2016年~2019年的A股上市民營企業,2018年及以后的對照組全部變為實驗組。為此,本文借鑒Nunn and Qian(2011)的做法,采用連續DID模型(3)也有文獻稱之為廣義DID、強度DID或“準”DID。:
RDi,t=α+βlnDei,t*Post+∑γXi,t+μi+ωt+εi,t
(1)
其中,RDi,t代表企業i第t年的創新水平;lnDei,t代表企業i第t年所享受的政策強度;Post是政策實施前后虛擬變量,即2018年及以后為1,否則為0;X為一組控制變量;μi和ωt分別表示企業和時間固定效應,分別控制企業層面上的非時變因素和時間層面上不隨企業變化的外部因素;εi,t為隨機誤差項。上述模型與標準DID模型的區別在于,不以虛擬變量來區分處理組和對照組,而是將企業所享受的政策強度作為處理強度。
(二)變量選取
變量選取和定義見表2。因變量分別從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創新產出質量三方面考察。采用企業研發投入強度來衡量創新投入。強度指標是相對指標,與絕對指標相比,可以排除企業規模的影響,能更有效地表征企業研發投入水平(馮澤等,2019)。分別采用專利申請量和發明專利申請量來衡量創新產出的數量和質量。因為相比于專利授權量,專利申請量更能真實反映企業創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專利授權過程的時滯性影響(Griliches,1990;Annamaria et al.,2013)。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更能夠體現創新的質量,屬于實質性創新,而非發明專利申請可能是企業為了達到政策支持條件而開展的策略性創新(黎文靖、鄭曼妮,2016)。

表2 變量指標一覽表
核心解釋變量是政策強度與政策實施時間的交互項,其中政策強度采用企業年報中披露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數額的對數衡量(4)中國證監會于2014年發布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號》文件規定,上市公司必須對研發細節進行公開。此后,中國上市公司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額等具體信息披露有很大改善。。控制變量則選取一系列公司層面的特征變量:(1)企業規模,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2)企業年齡,表征企業所積累的經驗與資源,會影響企業創新(劉詩源等,2020);(3)利潤總額和(4)總資產收益率,衡量企業盈利能力,是企業創新的基本保障;(5)總資產負債率,表征企業負債能力;(6)管理層持股比例,在一定門檻條件下會影響企業創新(陳金勇等,2015);(7)研發人員占比,人才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Bronzini and Piselli,2016)。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表4展示了模型(1)的估計結果。可見,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正,意味著政策強度提升對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創新產出質量均有顯著激勵效果,H1、H2和H3得證。

表4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民營企業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
從控制變量的系數來看:(1)民營企業規模對研發投入強度具有負向效果,但對創新產出有正向效果。因為規模較小的民企更具有創新意愿(Stock et al.,2002),而規模較大的企業具有比較完善的研發體系(George,1996)。(2)民營企業年齡對創新投入有負向影響,而對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有正向影響,但均不顯著。(3)總利潤對民營企業的創新均有顯著的正向效果,符合預期。(4)總資產收益率對創新投入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創新產出有正向影響。(5)總資產負債率對創新投入有顯著的負向效果,因為高負債率給企業帶來較大的資金壓力,導致研發投入降低(陳遠燕,2016),但可能會鞭策民企提高研發資金轉化效率,促進創新產出。(6)管理層持股比例對民企創新具有正向效果。因為管理層持股會激勵管理層為了公司的長遠利益與核心競爭力而更加積極地支持創新活動(陳金勇等,2015)。(7)研發人員占比對民營企業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與Bronzini and Piselli(2016)的結論一致。
(四)異質性分析
1.區分行業特征的回歸結果
為探索2018年政策強度提升對不同行業民營企業創新影響的潛在異質性,將樣本劃分為制造業和非制造業,估計結果見表5。可見,無論是制造業還是非制造業,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均具有顯著的正向激勵作用,且行業間效果差異顯著。具體地,對于制造業民企,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05%、0.178%和0.150%。同理,對于非制造業民企,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14%、0.237%和0.244%。從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和經驗P值來看,相對于制造業民企,2018年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非制造業民企的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創新產出質量的激勵效果更大,H4得證。
2.區分規模特征的回歸結果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將樣本分為大型和非大型兩類,估計結果見表6。結果顯示,政策強度提升對大型和非大型民營企業創新均具有顯著的正向激勵作用。具體地,對于大型民企,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06%、0.242%和0.212%。同理,對于非大型民企,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13%、0.211%和0.214%。從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和經驗P值來看,政策強度提升對非大型民企的創新投入激勵效果較大,而對不同規模民企的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的效果差異不明顯,H5得證。

表6 政策強度提升對不同規模民營企業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
3.區分技術類型的回歸結果
以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認定與否,將樣本劃分為高新技術企業和非高新技術企業兩類,分別進行估計,結果見表7。可以發現,政策強度提升對高新技術民企和非高新技術民企創新均具有顯著的正向激勵作用,且組間效果差異明顯。具體地,對于前者,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高新技術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07%、0.173%和0.158%。同理,對于后者,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非高新技術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06%、0.338%和0.267%。從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和經驗P值來看,政策強度提升對高新技術民企的創新投入激勵效果更大,但對非高新技術民企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的激勵效果更大,H6得證。

表7 政策強度提升對不同技術類型民營企業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
4.區分生命周期的回歸結果
在描述性統計中(見表3),企業年齡均值和中位數都在18年左右,因此以18年為分界線,將樣本分為成熟期和成長期兩類,并進行估計,結果見表8。可以發現,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成熟期民企和成長期民企創新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激勵作用,但組間效果差異部分顯著。具體地,對于成熟期民企,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高新技術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07%、0.2%和0.177%。同理,對于后者,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政策強度每提升1%,成長期民企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分別平均增加約0.006%、0.273%和0.239%。從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和經驗P值來看,政策強度提升對成熟期民企的創新投入激勵效果更大,但組間民企的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的差異不明顯,H7得證。

表8 政策強度提升對不同生命周期民營企業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
五、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模型(1)無法排除同時期其他因素引致的可能,本部分先從其他行業政策變化和國內國際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兩個方面探討,再分別用縮短時間窗口和改變時間點、替換核心解釋變量、Heckman兩步法和標準DID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首先,考慮到可能存在其他行業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我們搜索了2016年~2019年發布的促進產業(行業)發展的支持性政策,發現2018年~2019年間的財政政策不多,主要涉及農業企業,部分關于新能源行業企業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科研基地建設方面,比如技術創新中心建設、試驗區建設等;2016年~2017年間的財政政策較多,也涉及環保、新能源等行業,但這些政策在2018年~2019年間仍然有效。因此,我們認為其他行業政策造成影響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考慮到國內國際宏觀經濟變化等方面,我們重點考察了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根據相關文獻,我們發現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民營企業創新的結論尚存在爭議。一方面,劉薇、張溪(2019)研究發現美國對華實施的出口管制降低了中國企業的創新績效,特別是生物技術、信息通信、電子等高科技產業。Xie et al.(2019)研究發現貿易壁壘顯著降低企業研發投入的強度及持續性,對高科技、單一產品企業的影響尤為顯著。另一方面,馬天月、丁雪辰(2020)通過案例及統計數據,指出我國企業在面對各類貿易壁壘的打壓中反而更注重自主研發。因此,我們認為以中美貿易摩擦為主的國際國內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民營企業創新的影響存在“正負相抵”的可能。
(一)縮短時間窗口和改變時間點
誠然,上述討論仍然不足以排除所有潛在因素影響。下面通過縮短時間窗口和改變政策時間點做穩健性檢驗。具體地,將研究時間段縮短為2016年~2017年,再將政策實施時間提前到2017年,設定新的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NPost,該變量在2017年取1,在2016年取0。結果如表9所示,lnDe1*NPost系數不顯著,意味著政策強度提升對民企創新的效應在2018年之前不存在。

表9 縮小時間窗口和改變時間點后的回歸結果
(二)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除了手工搜集企業年報中披露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額數據,另外采用虛擬變量DE替換原來的lnDe1,即有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時,DE取值為1,否則為0。表10結果表明,新的核心解釋變量符號與前文一致,故結論依然穩健。

表10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
(三)Heckman兩步法
考慮到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問題,即創新水平較好的企業更容易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導致估計結果存在偏誤(陳遠燕,2016;陳強遠等,2020),采用Heckman兩步法處理:第一步,估計出企業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概率,得到IMR(逆米爾斯比例);第二步,將IMR作為控制變量放入第二階段的回歸方程,以控制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選擇偏誤,并控制企業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表11結果顯示,對于民營企業創新投入,IMR系數是顯著的,表明存在自選擇問題,因此使用Heckman兩步法是有必要的。對于企業創新產出,IMR系數不顯著,意味著不存在自選擇問題。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依然顯著為正,故前文結論依然成立。

表11 Heckman兩步法結果
(四)采用標準DID方法
考慮到可能存在的雙向因果問題,仍然嘗試采用標準DID方法。參考錢雪松、方勝(2017)的做法,先計算2016年~2017年各個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額的平均值,再將其按從小到大排序并分成三等分,并且把額度最低的小組定為實驗組,中間的或者最高的小組分別定為對照組Treat1和Treat2,并采用控制雙向固定效應的DID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表12中,Diff系數主要衡量了201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強度提升對民企創新效果。可見,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投入具有顯著的激勵作用,而對民營企業創新產出的激勵效果基本是正向的。因此,前文結論依然成立。

表12 標準DID結果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201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改革對民營企業的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數量和創新產出質量均有顯著的正向激勵效果,并且該結論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之后依然成立。一方面,民營企業處于相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在新發展階段,民營企業能否獲得市場競爭力,越來越依賴于創新能力,所以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上市公司更有動力進行“真”創新。另一方面,政策監管體系日益完善,資本市場監管越來越規范,也迫使民營上市企業必須進行“真”創新。
進一步地,政策改革實施效果存在行業、規模、技術類型、生命周期等方面的異質性:在創新投入方面,對非大型民營企業、高新技術民營企業、成熟期民營企業的創新投入激勵效果更大;在創新產出方面,對非高新技術民營企業的創新產出激勵效果更大。而相對于制造業民營企業,政策改革對非制造業民營企業的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的激勵效果均更大。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后續改革提供如下政策啟示:(1)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政策強度提升對民營企業創新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果,并且政策強度提升對非大型民營企業創新投入激勵效果較大。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扣除比例處于中低水平。在適當的時機,可繼續提高扣除比例,尤其是對中小企業,以促進民營企業釋放更大的創新動能。(2)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政策強度提升對非制造業民營企業創新的激勵效應較大。后續政策改革可考慮將2021年政策的扣除比例適用范圍擴大到負面清單之外的全部企業。(3)本文研究結果顯示,相比于非高新技術民營企業,政策強度提升對高新技術民營企業創新產出的激勵效應較小。后續政策改革可考慮強化對民營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導向性,針對不同類型研發項目費用設置不同扣除比例,規定企業在基礎研究項目中可享受的加計扣除比例最高,應用研究項目其次,試驗發展項目最低。
當然,僅僅依靠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來激勵民營企業創新是遠遠不夠的,政府仍需要繼續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緩解民營企業融資約束,鼓勵人才向民營企業流動,通過不斷提高創新政策的系統性、協調性,使政策對民營企業創新的激勵效果達到最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