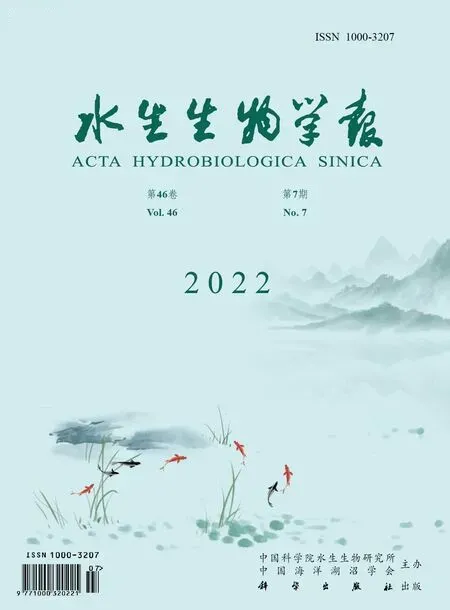甌江口鳳鱭魚卵、仔稚魚的時空分布及其與環境因子關系
孫浩奇 蔣日進 陳峰 芮銀 李霞芳 李振華 印瑞 周永東
(1.浙江海洋大學海洋與漁業研究所,舟山 316021;2.浙江省海洋水產研究所農業農村部重點漁場漁業資源科學觀測實驗站,浙江省海洋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研究重點實驗室,舟山 316021)
鳳鱭(Coilia mystus)隸屬鯡形目(Clupeiformes),鳀科(Engraulidae),鱭屬(Coilia)[1],在我國東南沿海均有分布,根據形態特征差異可大致分為長江型、閩江型和珠江型三種生態類群[2]。鳳鱭作為一種短距離溯河洄游性魚類[3],一般在近海分散生活,繁殖期時成熟的鳳鱭個體集群洄游至河口進行產卵,繁殖活動結束后親體重新回到近海生活[4]。甌江入海河口(以下簡稱“甌江口”)是鳳鱭主要棲息場所之一,位于浙江南部近岸,是甌江徑流和臺灣暖流等多水團共同影響下的咸淡水交匯區[5]。甌江口水域多紊流,潮流較為復雜,其徑流帶來豐富的營養鹽和餌料生物,給魚類提供了多元化的棲息地類型[6]。魚卵仔稚魚等對于棲息環境的變化較為敏感,外部環境的微小變化就可能對早期群體的生存和延續產生較大的影響。鳳鱭作為甌江口海域主要優勢種,其數量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洄游性魚類群落結構對環境適應的波動性[7]。
基于統計回歸分析的廣義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GAM)是一種分析漁業資源數量分布與環境因子間關系的模型方法[8,9]。在實際的資源調查中,早期群體資源豐度等數據可能存在大量0值,資源分布方式不均勻,很難服從某一特定的數據分布方式,若采用常規GAM模型擬合早期群體豐度變化與環境因子間關系,可能導致模型擬合結果與實際情況誤差較大[10]。兩階段廣義加性模型(Two-stage GAM)通過分階段處理0值數據,可以較好地看出豐度變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11],其在生物群體與環境關系的研究中已得到相關應用[12],但在魚卵仔稚魚等早期群體中的研究較少。本研究根據2015年、2018年和2019年的5—8月在甌江口及其鄰近海域進行的鳳鱭資源和環境調查數據,分析鳳鱭早期群體的資源分布,應用Two-stage GAM模型解析鳳鱭魚卵、仔稚魚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探討非生物因子對鳳鱭早期發育階段生境選擇的影響[13],為探明甌江口鳳鱭產卵場和育幼場提供基礎資料[14],同時基于2020年5—7月的環境數據進行模型預測,以期為合理預測甌江口鳳鱭資源的時空變動提供科學參考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調查區域與采樣方法
鳳鱭魚卵和仔稚魚資源和環境數據來源于2015年、2018年、2019年5至8月在甌江口內進行的產卵場選劃項目。共設置11個站位,每月的大潮汛和小潮汛之間,在靈昆島至橋下鎮之間水域(27°53′N—28°51′N、120°35′E—120°58′E)調查采集鳳鱭的魚卵和仔稚魚(圖1),使用淺水I型浮游生物網(網口直徑0.5 m,網目尺寸0.505 mm)進行水平拖網采樣。調查船租用群眾雙拖漁船,單機功率為56 kW,調查拖速為2 kn/h,每站拖網時間10min。每一個調查站位的水深、水溫和水鹽等環境數據通過多功能水質儀同步測定。依據《海洋調查規范第六部分-海洋生物調查》采集、保存樣品,在實驗室根據形態特征和分子鑒定技術對鳳鱭魚卵和仔稚魚進行種類鑒定[15]。根據各個站位鳳鱭魚卵和鳳鱭仔稚魚的數量及濾水量,計算每個站位鳳鱭魚卵和仔稚魚的豐度(ind./m3)。

圖1 甌江口鳳鱭魚卵仔稚魚采樣位點Fig.1 Sampling stations of Coilia mystus eggs and larvae in the Oujiang Estuary
1.2 初始影響因子的篩選
產卵場環境對于魚類早期群體分布具有顯著影響[16],根據鳳鱭產卵孵化等相關研究,在構建GAM模型的初始解釋變量中,選取水深(Depth,DEP)、表層水溫(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ST)、表層水鹽(Surface water salinity,SS)、底層水溫(Bottom water temperature,BT)和底層水鹽(Bottom water salinity,BS)5個環境變量,經度(Lat)和緯度(Lon)2個空間變量以及月份(Month)作為時間變量加入模型進行建模。預測變量的多重共線性會對模型參數回歸的準確性產生干擾,本研究通過Pearson相關分析和方差膨脹因子對環境變量及空間變量進行共線性診斷。Pearson相關性閾值設定為0.7,方差膨脹系數(VIF)閾值設定為4,認為相關性和方差膨脹因子高于閾值的變量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17];通過pearson相關性分析找出存在多重共線性的變量,去除其中VIF值最大的變量,重復此步驟至所有預測變量的VIF值和Pearson相關性值均小于閾值。
1.3 數據處理與分析
棲息地環境對生物的分布有十分顯著的影響。為進一步了解甌江口鳳鱭產卵場和育幼場的分布,本研究利用兩階段廣義加性模型(Two-stage GAM)分別對鳳鱭魚卵、仔稚魚的分布與環境因子的關系進行分析。模型構建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基于二項分布構建GAM1模型,使用logistic鏈接函數模擬鳳鱭魚卵、仔稚魚出現的概率P與環境因子的關系;第二部分,基于高斯分布構建GAM2模型,使用identical鏈接函數模擬鳳鱭魚卵、仔稚魚出現情況下其豐度與環境因子的關系,使用對數函數對豐度進行標準化處理[11]。

式中,P為鳳鱭魚卵、仔稚魚出現概率,Y為鳳鱭魚卵、仔稚魚資源豐度,α為函數的截距,xi為解釋變量,Si(xi)為各解釋變量的單變量樣條平滑函數,表示殘差。
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和解釋率篩選最優模型組合。在模型擬合過程中,采用逐步回歸法依次將解釋變量加入至模型中,至模型的AIC值最小且不再變化,選擇解釋率最高的模型作為最終模型[18]。一般認為AIC值越低,偏差解釋率越高,模型擬合效果越好。

式中,k是參數個數,L是似然函數。
1.4 模型驗證與預測
采用五折交叉驗證分別對GAM1和GAM2的模型預測性能和準確性進行評價[19]。將總數據集隨機等分為5個子數據集,每次隨機選擇4個子數據集作為訓練集,剩余的1個子數據集作為驗證集用于模型預測準確性評估,重復計算100次,對各模型的準確性評估取平均效應。
GAM1模型的預測性能評價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下面積(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AUC作為靈敏度和特異度在不同閾值下的綜合指標,不受二項分布類模型預測所需閾值的影響,其閾值獨立性不需要設定閾值就能對模型作出判斷,可以較好地反映GAM1模型的預測準確性。AUC變化范圍為(0,1),一般認為,AUC值為 0.5—0.7時模型價值較低;0.7—0.9時模型預測力較好;>0.9時預測力極好;<0.5模型擬合差于隨機模型。根據模型預測力,AUC 均值大于0.7的模型可以用于后續的GAM2模型的構建和分析[20]。
體育(physical education)除去外顯的生物性外,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其發展歷程與人類社會的變遷相伴相生。個體的實踐要通過組織化的活動才能構成具有更豐富社會意義的行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對現代體育的發生與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競技體育之外,民眾自發地圍繞運動、健身等展開的社會活動也成為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通過GAM1計算各站位點的出現概率,在0—0.9設定出現概率的閾值(從0開始以0.1間隔遞增),當出現概率低于閾值時其相對資源密度為0,出現概率等于或高于閾值時采用GAM2計算其相對資源豐度,對于出現概率閾值的選擇及GAM2模型的預測性能評價采用回歸分析法,即通過構建驗試集的模型預測值(y)與實際觀測值(y0)間的線性關系來描述二者的近似程度:

a和b的均值反映預測性能,式中,斜率a=1時模型預測無系統偏差,截距b=0時預測值與實際觀測值具有相似的空間特征。同時計算決定系數(R2)作為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21]。
根據2020年5—7月各站點環境調查數據,以0.05°×0.05°網格大小對研究水域進行劃分,獲得每個網格中心點的坐標,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計算網格中心點的環境數據。基于Two-stage GAM對2020年5—7月的相對資源密度分布進行預測,分析不同月份鳳鱭魚卵、仔稚魚的預測結果與實際調查站位的時空分布。
利用Excel2016進行數據整理計算,R 4.0.3軟件和ArcGIS10.2中進行模型構建和繪圖,其中GAM模型利用R4.0.3中gam軟件包完成。
2 結果
2.1 GAM模型構建
Pearson相關性分析和VIF檢驗結果顯示,底溫、底鹽、緯度與其他解釋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逐步舍去超過閾值的解釋變量后,最終選擇水深、表溫、表鹽、經度作為解釋變量,用于魚卵和仔稚魚模型的建立和分析(表1)。在構建GAM模型過程中,以時間變量月份作為分類因子,篩選后的水深等解釋變量作為影響因子進行建模。依據AIC最小原則,構建鳳鱭魚卵、仔稚魚的Two-stage GAM最優模型,結果如下:

表1 模型擬合結果及各因子參數Tab.1 Fitting and parameters of each factor of models

式中,P為鳳鱭魚卵或仔稚魚出現的概率,Y為鳳鱭魚卵或仔稚魚的相對資源量,Month為月份,ST為表層水溫,SS為表層水鹽,ε為相應的GAM模型截距。
l.GAM1模型最佳預測變量組合為Month+ST+SS,模型累積偏差解釋率為23.21%,表溫對仔稚魚的出現概率具有極顯著影響(P<0.01),貢獻率為9.31%,月份具有顯著影響(P<0.05),貢獻率為5.43%,表鹽貢獻率為8.74%。l.GAM2模型結果顯示:影響仔稚魚相對資源密度的變量為表溫和表鹽,模型的累積偏差解釋率為33.3%,其中表溫對于模型的貢獻率最大,為28.12%,表鹽貢獻率僅為5.20%。
2.2 影響因子效應分析
溫州甌江口鳳鱭魚卵、仔稚魚在不同月份其分布有一定差異。根據5—8月各站位平均相對資源密度結果顯示(圖2),鳳鱭魚卵基本分布在江心嶼至七都島附近等低鹽淡水區水域,其中高豐度區主要集中于七都島上游。研究結果顯示鳳鱭主要在甌江口上游產卵,產卵時間主要集中在5—7月,7月甌江水域出現鳳鱭魚卵的概率有明顯下降(圖3a),8月僅部分水域出現魚卵,考慮到實際調查中僅2015年8月采集到兩次鳳鱭,當年的鳳鱭資源量較其他年份明顯偏高,同時2018年、2019年8月均未采集到鳳鱭魚卵,推測甌江口及附近水域的鳳鱭產卵期至8月結束。
鳳鱭仔稚魚5—8月在甌江流域均有分布(圖2),7月仔稚魚出現頻率最高(圖3b)。仔稚魚主要集中分布于江心嶼與靈昆島之間水域,資源重心在七都島北部低鹽區水域;7月與5月、6月相比,低鹽區仔稚魚相對資源量較小,七都島及靈昆島附近水域資源量高于甌江其他水域;8月鳳鱭仔稚魚則圍繞靈昆島高鹽區海域作密集分布,即甌江入海口附近,在甌江中上游低鹽區及七都島高低鹽交匯區相對資源量較低,靈昆島北部水域仔稚魚相對資源量高于南部。

圖2 鳳鱭魚卵、仔稚魚5—8月平均資源密度分布(a.魚卵;b.仔稚魚)Fig.2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resource density of eggs and larvae of Coilia mystus from May to August (a.eggs;b.larvae)

圖3 月份對鳳鱭魚卵仔稚魚出現概率的影響(a.魚卵;b.仔稚魚)Fig.3 Effects of spatiotemporal factors on the eggs and larvae distribution of Coilia mystus (a.eggs;b.larvae)
鳳鱭作為中上層短距離洄游性魚類,表溫鹽度等水環境因子是影響鳳鱭產卵繁殖及仔稚魚的生長、分布最重要的環境因素(圖4)。
鳳鱭魚卵主要出現在表溫20—32℃,26℃時鳳鱭魚卵出現概率最高(圖4a),而魚卵的豐度在20—25℃間呈現先降后升的趨勢,在23℃以后魚卵隨表溫升高而增加(圖4b)。仔稚魚的出現概率隨表溫呈先升后降的趨勢,表溫22℃左右出現率最大(圖4c);豐度隨表溫波動變化,高峰區為24—27℃。綜合來看,魚卵適宜表溫為24—26℃,仔稚魚適宜表溫為22—27℃(圖4d)。
甌江鳳鱭魚卵和仔稚魚的資源變動隨鹽度變化趨勢明顯,魚卵主要集中分布于低鹽淡水區,在低鹽區的出現概率最高(圖4e),其豐度隨鹽度升高而顯著降低(圖4f),出現概率和豐度的高峰區集中在表鹽0—1左右,魚卵的鹽度適宜性在1以下。仔稚魚自低鹽淡水區至入海口咸淡水交匯水域均有分布,表鹽為7時仔稚魚出現概率最高(圖4g),資源豐度峰值在表層鹽度10左右,鳳鱭仔稚魚的出現概率和豐度隨表鹽升高而升高(圖4h),仔稚魚的鹽度適宜性為5—13。

圖4 環境因子對鳳鱭魚卵仔稚魚分布的影響(a、b、e、f .魚卵;c、d、g、h.仔稚魚)Fig.4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eggs and larvae distribution of Coilia mystus (a,b,e,f.eggs;c,d,g,h.larvae)
2.3 模型預測性能
交叉驗證的結果顯示(表2),用于分析魚卵、仔稚魚出現概率的GAM1模型的AUC均值大于0.7,模型預測性能較好,其中分析魚卵出現概率的e.GAM1模型(AUC均值0.83)優于仔稚魚的l.GAM1模型(AUC均值0.71),兩者均可用于后續的GAM2模型分析。根據對GAM2模型的交叉驗證線性回歸結果,e.GAM2模型的線性回歸斜率均值為1.09,截距均值為0.38,決定系數(R2)均值為0.24;l.GAM2模型的線性回歸斜率a均值為0.54,截距b均值為0.72,決定系數(R2)均值為0.15。從整體情況來看,Two-stage GAM模型對于魚卵的擬合效果和預測性能方面均優于仔稚魚。

表2 回歸分析統計結果Tab.2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基于GAM1得到的鳳鱭魚卵、仔稚魚的出現概率,設定不同的出現概率閾值,對于等于或高于閾值的站位點的相對資源密度預測值采用GAM2計算,低于閾值的站位點的相對資源密度定義為0作為其預測值,各站位相對資源密度的預測值與實際值進行線性回歸擬合,以選擇適宜的出現概率閾值進行相對資源密度預測。不同出現概率的閾值下鳳鱭魚卵、仔稚魚線性回歸的決定系數結果顯示(圖5):鳳鱭魚卵出現概率的閾值設定為0.4時,模型的擬合性能優于其他閾值,其線性回歸決定系數R2為0.541,線性回歸的斜率a為0.754,截距b為0.231;仔稚魚出現概率閾值設定為0.6時預測值與實際值的線性回歸決定系數R2最大,為0.214,其斜率a為0.368,截距b為0.95。因此本文中的鳳鱭魚卵出現概率的閾值為0.4,仔稚魚出現概率的閾值為0.6。

圖5 出現概率的閾值選擇結果Fig.5 Threshold selection result of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2.4 空間分布預測
基于Two-stage GAM對2020年5—7月甌江口鳳鱭魚卵和仔稚魚的相對資源密度的預測結果顯示(圖6):2020年6月鳳鱭魚卵和仔稚魚的適宜棲息水域明顯寬于5月和7月,鳳鱭魚卵預測的相對資源密度高值區集中在靈昆島東部附近水域以及江心嶼上游,6月份所采集到的鳳鱭魚卵基本位于江心嶼附近水域。實際調查中魚卵出現站位較多的月份(5月),多位于模型所預測的相對資源密度高值區的上游水域。7月的資源調查未采集到魚卵,模型所預測的7月高值區也基本位于江心嶼上游水域。模型預測的仔稚魚相對資源密度高值區則集中在七度島附近水域,6月仔稚魚的相對資源密度高值區最廣,在設立的11個調查站位中均采集到鳳鱭仔稚魚;除未采集到鳳鱭仔稚魚的5月外,6月和7月的仔稚魚相對資源密度較高站位基本位于預測的高值區內。

圖6 2020年5—7月鳳鱭魚卵、仔稚魚相對資源密度的預測值與實際值疊加圖Fig.6 Overlapping maps of prediction and observations of relative resource density of eggs and larvae of Coilia mystus from May to July 2020
3 討論
3.1 魚卵仔稚魚的時空分布
在長江口鳳鱭早期群體的相關研究中[13,22],認為長江口鳳鱭繁殖期從4月開始至10月結束。甌江口不同月份鳳鱭魚卵和仔稚魚豐度和時空分布差別明顯(圖2),仔稚魚相較魚卵的峰值出現時間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與長江口鳳鱭相比,甌江口鳳鱭繁殖期較短,甌江口鳳鱭的繁殖盛期基本集中在5—7月。鳳鱭繁殖群體從4月開始進行洄游性產卵繁殖,在5—7月進入繁殖盛期,至8月大部分鳳鱭基本結束繁殖并進入近海索餌。鳳鱭魚卵主要分布在甌江上游淡水區至七都島附近咸淡水交匯區,6月魚卵相對資源量最高,集中分布在江心嶼附近。鳳鱭仔稚魚則隨著月份變化從淡水區向靈昆島附近海域聚集。本研究認為造成這種分布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鳳鱭洄游至淡水區進行繁殖產卵,魚卵適應的鹽度生態位寬度較窄,一般魚卵孵化成仔稚魚所需時間較短,而仔稚魚相較魚卵對不同水環境的適應力更強,使得仔稚魚較魚卵分布水域更廣泛[23];第二,鳳鱭卵為浮性卵,魚卵、仔稚魚基本隨水流作用進行移動,其分布主要受河口徑流量影響,同時產卵季節徑流量的變化對河口洄游性魚類的繁殖產生一定的影響。入海河口徑流量的改變會使包括水溫、水鹽、溶解氧、濁度在內的環境因子發生改變,從而影響產卵群體溯河洄游的數量,使甌江水域的鳳鱭魚卵、仔稚魚的數量及分布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24],這也是造成鳳鱭魚卵和仔稚魚年度空間分布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甌江口具有豐富的營養鹽和浮游生物,加上該海域獨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相對平靜的海洋環境,為魚卵、仔稚魚提供了適宜孵化、生長和索餌的生境[25],使鳳鱭仔稚魚7—8月數量最高且主要聚集在甌江口靈昆島附近海域。
3.2 產卵場適宜性的關鍵影響因子
魚類不同發育階段對環境的適應性不同,棲息環境的改變和空間生物動態變化是影響其時空分布的主要因素[26]。研究結果顯示,表溫、表鹽對于鳳鱭魚卵、仔稚魚的出現概率或豐度變化具有顯著影響(P<0.05),不同月份下水溫、水鹽等水環境的變化使鳳鱭早期群體出現明顯的時空變動。
水溫、鹽度對魚類的存活、新陳代謝及洄游分布等有不同程度的影響[27]。研究結果顯示,表溫對于鳳鱭魚卵、仔稚魚的出現率和豐度均有影響。魚類的生長發育具有適溫范圍,當水溫達到一定程度時刺激魚類親體性腺發育成熟并產卵[28],在適溫范圍內,水溫升高可以縮減魚卵孵化所需時間[29],而水溫過高不利于卵孵化和仔稚魚的生長發育,造成魚類早期群體死亡率上升,致使資源量降低。鳳鱭仔稚魚相較魚卵對表層水溫的適宜性更寬[13],魚卵和仔稚魚的最適表溫在25℃左右,表溫在23—27℃時最適宜鳳鱭進行產卵繁殖,也有利于魚卵孵化和仔稚魚生長發育,這與胡麗娟等[13]對長江口鳳鱭仔稚魚的適宜水溫研究結果一致。2015年8水溫(平均26.49℃)處于鳳鱭魚卵的適宜性水溫范圍內,較其他年份(2018年的31.36℃、2019年的30.04℃)更適宜卵的生存和孵化,這可能是當年8月仍采集到魚卵的一個主要原因。
河口地區的鹽度梯度變化十分復雜,魚類早期發育階段對于鹽度的適應范圍較窄[30],鹽度影響魚類的生命活動主要體現在調節體內滲透壓平衡、改變腸道酶活性等方式,鹽度過高或過低會使魚卵孵化率降低,仔稚魚畸形率升高。本研究中鹽度對于魚卵的分布具有顯著影響,鳳鱭卵作為浮性卵,可以避免在低鹽度水環境下卵沉底堆積成塊,出現胚胎氧氣供應不足等問題。甌江口鳳鱭魚卵主要分布在甌江上游淡水區,說明甌江口鳳鱭群體主要洄游至低鹽水域產卵并完成魚卵孵化過程。與長江口鳳鱭的產卵場鹽度生態位寬度相比[13],甌江口海域鳳鱭產卵和孵化的適宜鹽度范圍更窄,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甌江口相比長江口的徑流量小,甌江口鳳鱭洄游至最適繁殖的低鹽水域距離和時間較短。與魚卵相比,鳳鱭仔稚魚對于鹽度的適應范圍廣,魚類早期發育階段對鹽度變化適應能力較弱,仔稚魚的體液滲透壓在低鹽環境容易得到平衡[31],利于鳳鱭早期補充群體的攝食生長。低鹽環境適宜鳳鱭產卵,對于魚卵孵化和仔稚魚的生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比分析甌江口與長江口鳳鱭仔稚魚的資源變化可以看出,兩個不同水域鳳鱭洄游繁殖時間主要集中在5—7月,對于水溫、水鹽的適宜范圍大致相同。早期研究將我國近海洄游性鳳鱭分為珠江型、閩江型和長江型3個生態型,溫州甌江口鳳鱭應隸屬于長江型鳳鱭[6]。而鳳鱭作為短距離河口洄游性魚類,基本在既定的區域進行繁殖發育,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及所處水域環境變化,不同水域的群體在外部環境的長期影響下生態位寬度發生改變[32],使得位于甌江口及近海的鳳鱭群體與其他河口群體之間形態差異逐漸增大,甌江口鳳鱭可能已發生明顯的地理分化[33]。
在本研究中魚卵非零值豐度數據較少,與模型的標準分布類型契合度不高,采用Two-stage GAM模型對于分析魚卵時空分布與環境變量之間關系效果優于仔稚魚模型,在解決零值數據較多引起的模型擬合能力不足等方面有較好的效果。一般認為魚類資源出現概率與密度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高豐度區代表更高的發現率,魚卵和仔稚魚的高頻率出現和高豐度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產卵群體及鳳鱭早期群體所需的適宜環境條件。基于二項分布的GAM1模型可以表達魚卵、仔稚魚的出現概率,從已知數據預測整體分布特點,推斷鳳鱭產卵場和育幼場的理論分布區,基于高斯分布的GAM2模型用于解釋環境變量對于豐度變化的影響,可以更好地表達魚卵、仔稚魚的豐度變化與不同環境因子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魚卵、仔稚魚生長發育的生境適宜性需求。模型的整體解釋率不高,一方面可能是選取的自變量覆蓋范圍不足,另一方面缺乏對生物分布機制性的解釋,在以后的研究中應結合生理學和地理水文動力等因素做進一步分析,了解魚卵、仔稚魚的存活條件,以期準確解析鳳鱭資源的補充過程和種群的動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