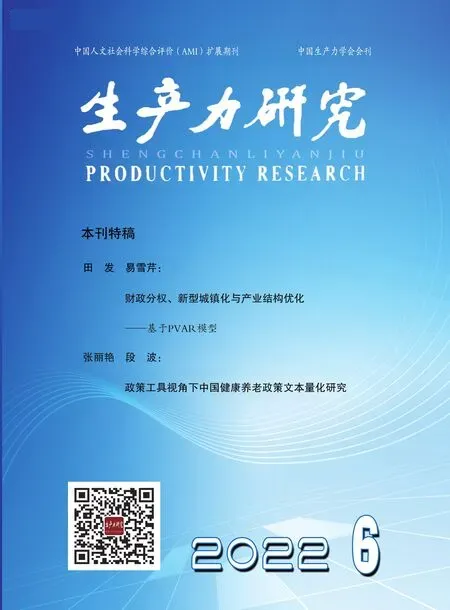長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鎮化質量綜合評價和分析
——基于PSR 模型
黃艷秋,謝定哲
(1.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數理與統計學院,上海 201620;2.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電子電氣工程學院,上海 201620)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新型城鎮化已取得長足進步,當前新型城鎮化主要強調人口與經濟社會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均衡分布,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產業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換;隨著人口和產業資源向我國東部沿海集中,我國形成津京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有力地推動了東部地區發展。目前,長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共27 個市)為國內發展基礎最好、體制環境最優、整體競爭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初步形成了世界級城市群的規模和布局,作為“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地帶,在我國國際化和現代化戰略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19 年底,國務院印發了《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新型城鎮化是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1]。
新型城鎮化相關研究也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問題,研究方向主要有發展現狀分析、城鎮化質量評價、擴展格局及驅動力研究等。早期國內學者首先關注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試著用城市化水平、速度和城市成長力系數構建城鎮化水平測評體系[2-3];從經濟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景觀城市化、生活城市化、科技城市化、環境狀態城市化等維度的發展水平構建評價體系[4]。但新型城鎮化質量指標數據存在復雜性非線性等特點的現實情況,盡管傳統方法較多,得出結果也較為相似[5-6],對于與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創新性存在討論。
壓力—狀態—響應(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模型最初是由加拿大統計學家David J.Rapport 和Tony Friend(1979 年)提出[7],世界經合組織(OECD)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修訂并共同發展PSR(壓力—狀態—響應)模型,當前正廣泛被采用于生態評價,是生態系統健康評價中常用的一種評價模型[8-10]。該模型不僅可以充分反映人與自然發展進程中的相互作用,也能很大程度上體現綠色發展中自然制約的影響因素與人類活動作用的經濟后果。
1995 年由Diakoulaki 等提出的CRITIC 賦權法,充分考慮到指標之間的對比強度與沖突強度進而確定了指標的權重[11]。不同于熵權法[12],CRITIC 賦權法更為全面,不僅在縱向層面考慮到了指標本身的波動性,也在橫向層面考慮到了指標之間的關聯性[13]。考慮到綠色新型城鎮化發展和指標之間的對比強度,本文基于壓力—狀態—響應(PSR)評價模型,從壓力指標、狀態指標、響應指標3 個方面構建新型城鎮化質量的影響因素指標體系;利用CRITIC賦權法計算各項指標的權重,并利用綜合評價得分評價長三角27 個城市的新型城鎮化質量。
二、新型城鎮化質量測度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一)新型城鎮化質量測度指標體系構建
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必然是發生在自然綠色發展進程中的人類活動,因此可以采用PSR 模型進行指標體系的建立。基于PSR 模型構成準則層(壓力、狀態、響應)下對應的要素層(人口壓力、環境壓力、資源狀態、經濟狀態、環境狀態、環境響應、社會響應、經濟響應)及27 個指標組成的指標層,進而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進行評估與優化(見表1)。

表1 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指標體系
(二)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對象是長三角27 個城市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質量,時間窗口選擇為2010—2019 年。相關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臺(https://data.cnki.net/)等。
三、CRITIC 賦權法
基于長三角27 個城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情況,本文研究面板數據在傳統的截面數據中增設一項時間維度的數據,通過CRITIC 賦權法計算不同時間點的權重,并得到長三角27 城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評價得分。CRITIC 賦權法在增設時間維度的數據后,表現形式為標準差的對比強度可反映同一指標不同評價對象之間的差異性,而表現形式為相關系數的沖突強度則反映了不同指標之間的差異性。基于傳統的CRITIC 賦權法,本文引入指標之間差異相對變動的變異系數,在計算中盡可能地包含每個評價對象的信息量,從而使指標權重的賦權更為合理、科學[7-8]。
基于改進的CRITIC 賦權法計算各指標權重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在選取的時間序列Tk(k∈N+)中計算第k 個時間點的第j 個指標的變異系數與沖突系數。
a 個城市,b 項評價指標中,存在經無量綱化處理后的觀測值形成的數據矩陣。
變異系數:

第二步,計算第k 個時間點的第j 個指標歸一化的客觀權重。其中表示第k 個時間的第j 個指標所包含的信息量。若信息量值越大,則表明該指標的重要程度相應的也就越高,也就是說指標的權重也就越大。

第三步,通過指標權重進行加權,可以得到長三角27 個城市在第k 個時間點的綜合評價得分。

并利用python 進行數據計算,即可得到長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得分。
四、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中羅列的上海、江蘇南京、浙江杭州及安徽合肥等27 市為研究區域,通過對PSR 模型構建的指標體系進行數據檢索,并利用CRITIC 賦權法進行計算,可得出長三角27 個城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權重和綜合評價得分(見表1、表2)。

表2 長三角27 城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評價得分
從表1 可知,2019 年利用CRITIC 賦權法計算出城鎮化發展指標權重中,壓力P 系數為0.17,S 狀態系數0.363,R 響應系數0.467,各子系統對新型城鎮化貢獻大小分別為:響應R 子系統>狀態S 子系統>壓力P 子系統,其中,響應R 子系統權重達46.7%,表明其對新型城鎮化質量評價的作用最為顯著。壓力P 子系統中環境壓力占比最大,其次為人口壓力,但整體壓力P 對新型城鎮化具有明顯的負向作用。在狀態S 子系統中,經濟狀態和資源狀態是城市新型城鎮化主要狀態,對新型城鎮化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響應R 子系統中經濟和社會響應占比最大,隨著新型城鎮化人口和環境壓力不斷增大,資源、經濟以及環境系統狀態也會隨之改變,從而響應對經濟社會環境子系統發展,所以長三角新型城鎮化發展總體要依賴于經濟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健全、環境友好等多因素互相影響,促進人和自然和諧相處。
其中,從經濟、人口與資源以及環境等因素考慮,經濟占比32%,人口和資源指標作為基礎指標占比23%,環境占比18%,說明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指標考慮到當前長三角區域發展的區域特點,以經濟、人口、環境、社會綜合因素考慮指標的合理性,綠色發展和以人為本為長三角發展的重要目標,生態環境城鎮化指標和人口指標數保持相對平穩的增長態勢。
從表2 可知,2009—2019 年這十年高質量區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蘇州以及寧波4 市,浙江的嘉興、紹興、江蘇的常州、鎮江等較高質量區域附著于上海、杭州、蘇州高質量區周邊,整體沿海以淡水湖泊、沿海生態為核心的且注重資源協調度與多元化的經濟發展城市,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更高;較低和低質量區則主要分布在各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如江蘇蘇中、蘇北、安徽南部的安慶、池州等地相偏于內陸地區發展,整體產業和經濟發展滯后,加之人口流失以及尚未完全轉型的傳統的經濟、工業化發展方式導致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評價得分偏低。太湖發展的蘇州、無錫、常州、浙江等城市得分較高,淡水、海洋、森林資源對周邊城市新型城鎮化發展輻射效果十分明顯。其中依托于太湖發展的蘇州、無錫、常州、浙江等城市,不難看出,即便是在壓力大于其他城市的情況下,憑借城市周邊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新興經濟的崛起依舊能夠取得良好得分。
五、結論
本文采用通過對PSR 模型構建的指標體系進行數據檢索,并利用CRITIC 賦權法進行計算,可得出長三角27 個城市的新型城鎮化質量的權重和綜合評價得分,得出以下結論:
1.PSR 模型(壓力、狀態、響應)子系統對新型城鎮化貢獻大小分別為:響應R 子系統>狀態S 子系統>壓力P 子系統,長三角新型城鎮化發展總體要依賴于經濟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健全、環境友好等多因素互相影響,以經濟、人口、環境、社會綜合因素考慮指標的合理性,綠色發展和以人為本為長三角發展的重要目標,生態環境城鎮化指標和人口指標數保持相對平穩的增長態勢。
2.長三角27 個城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綜合評價得分,2009—2019 年這十年高質量區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蘇州及以點狀散布的寧波和舟山5 市,以點帶面包括浙江的嘉興、紹興、江蘇的常州、鎮江等較高質量區附著于上海、杭州、蘇州高質量區周邊;江蘇蘇中和蘇北、浙江南部、安徽南部的城市偏于內陸地區發展,整體產業和經濟發展滯后,加之人口流失以及尚未完全轉型的傳統的經濟、工業化發展方式導致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評價得分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