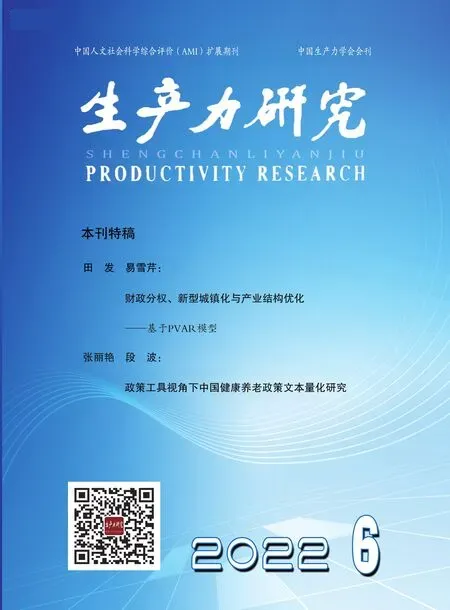長三角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武 戈,張如玉
(江南大學 商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現階段長三角地區力求經濟高質量增長,發展經濟的同時減少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促進長三角區域內資源合理配置、要素適當流動,實現區域協同發展進步。為了能以更少的資源消耗、更低的環境代價實現長三角經濟可持續地發展,必須關注環境因素,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合理評價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本文嘗試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為研究切入點,分析長三角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源,探究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尋求綠色生產率提升的策略。
一、文獻綜述
關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Fare 等(1989)[1]提出的產出角度的方向性距離函數,考慮了“非期望產出”的效率評價,但沒有考慮投入產出的松弛性問題。Tone(2001)[2]提出的SBM 模型可以解決該問題,SBM 模型基于松弛測度,包含“非期望產出”的非徑向、非角度,但是SBM 模型不能解決投入和產出都存在徑向和非徑向關系的情況。Tone 和Tsutsui(2010)[3]提出的EBM 模型同時包含徑向和非徑向兩類距離函數,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傳統DEA 模型和SBM 模型的缺陷。
目前國內外學者在測算全要素生產率時,普遍將以上的模型與生產率指數結合運用。Oh(2010)[4]提出的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數,將全局參比Malmquist 指數與包含壞產出的方向距離函數進行結合測算生產率。郭慶旺等(2005)[5]利用非參數DEA-Malmquist 指數方法估算中國各省份1979—2003 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李斌等(2016)[6]等選用基于SBM 方向距離函數的ML 指數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李斌等(2013)[7]采用非徑向非角度SBM 效率測度模型結合ML 生產率指數來測算分行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朱文濤等(2019)[8]利用SBM 模型及ML 指數測算2003—2015 年中國29 個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郭海紅等(2018)[9]基于EBM 函數和ML 指數測算省際及區域的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劉曉潔和劉洪(2018)[10]結合E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 生產率指數,研究2000—2016年中國30 個省份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大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源于技術進步[11-13],少數學者的研究表明技術效率改進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更大[14]。
關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研究,多數學者從經濟發展水平、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政府干預、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貿易開放、環境規制等角度考察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15-17]。
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方法與模型構建
(一)EBM 模型
EBM 模型同時包含徑向和非徑向兩類距離函數,既考慮了非期望產出,又可以解決傳統DEA 模型和SBM 方向距離函數存在的缺陷。具體如下:

γ* 代表最佳效率值;xik,yrk,bpk為第i 個決策單元的第k 種投入、第r、p 種期望和非期望產出;λ 為線性組合系數;θ 為徑向規劃參數;εx表示非徑向部分的重要程度分別表示第i 種投入要素、r 種期望產出、p 種非期望產出的松弛量和權重。
(二)GML 指數
GML 指數將所有各期的總和作為參考集,可以進行跨期比較。可分解為技術進步指數(TC)和技術效率指數(EC):

三、變量設定
2011 年國務院撤銷了安徽省的地級市巢湖,本研究的決策單元為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除巢湖)在內的三省一市的41 個地級市。
(一)投入指標
1.勞動投入。以各城市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數的總和衡量勞動投入。
2.資本投入。以資本存量來衡量資本投入。資本存量運用永續盤存法進行計算,公式為:

其中,δ 為折舊率,Iit為t 年城市i 現價的固定資產投資,dit為固定資產投資的省級價格指數。參考張軍等(2004)[18]、單豪杰等(2008)[19]的研究,令折舊率等于9.6%。
3.能源投入。城市層面缺少一次能源消費統計數據,采用各城市用電量來衡量生產率產出的能源消耗。
(二)產出指標
1.期望產出:選擇以樣本基期的不變價格計算的各城市地區生產總值。
2.非期望產出:根據環境指標數據的可得性及其經濟含義,非期望產出選擇工業廢水、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粉)塵排放量。
上述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四、測算結果分析
本文運用MaxDEA 軟件采用考慮非參數混合徑向(EBM)與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數結合來測算長三角41 個城市2003—2018 年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分析
表1 為長三角41 個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在2003—2018 年的幾何均值。從長三角地區整體層面看,長三角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2003—2018年幾何平均值為1.013,由于比1 大,說明長三角地區整體處于生產前沿面上,整體的效率在提高,年均上升了1.3 個百分點。由城市GML 指數幾何均值看,長三角地區29 個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大于1,占比達到樣本城市總數的70.73%,說明長三角大部分城市2003—2018 年實現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表1 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2003—2018 年的幾何均值
(二)長三角城市GML 指數增長動力分析
表2 為長三角地區2003—2018 年間總體平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及其分解。由表2 可知,綠色全要素增長率總體呈現增長態勢,但增長率差異較大,且有部分年份出現下降的趨勢。計算可得GML、TC 指數的幾何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33%、1.88%,EC 指數下降0.54%。

表2 長三角地區總體平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指數
具體來說,2003—2006 年GML 指數持續增長,這主要是受到技術進步增長的影響,但技術效率持續下降;2006—2007 年GML 指數為1.016,上升了1.65%,技術效率增加了6.22%,但技術進步下降了4.31%,技術效率是主要影響因素;2007—2018 年GML、TC 和EC 在1 上下小幅波動,但GML 和TC變化方向始終保持一致。2017—2018 年GML 指數為1.095,上升了9.54%,技術效率下降0.20%,技術進步指數增加了9.76%。由此可見樣本期內長三角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技術進步,而技術效率改進的貢獻相對較小。
圖1 所示是2003—2018 年長三角地區GML、TC 和EC 的變化趨勢。從折線圖的變化趨勢看,TC 與GML 的變動趨勢保持大體一致,再次表明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由技術進步所推動。

圖1 2003—2018 年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指數變化趨勢
五、長三角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本文在借鑒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結合長三角地區現狀,選取以下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InPGDP)。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城市有利于經濟增長,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但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消耗大量的能源,加重環境污染,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本文選用人均GDP 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2.人力資本(InEDU)。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正規的學校教育是產生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本文選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即普通高等學校在校人數來衡量各城市的人力資本水平。
3.外商投資(FDI)。外商投資可以提高本地生產效率,也可能加重環境污染,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衡量外商投資水平。
4.產業結構(IS)。產業結構影響資源在經濟系統中的運行效率,對整個經濟體的能源消耗具有強大的調節作用。本文選取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5.環境治理能力(ER)。環境治理一方面可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由于環境治理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產率的提高。本文選用固體廢物利用率來衡量環境治理能力的水平。
6.能源結構(ES)。工業能源的消耗是中國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調整能源結構是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考慮到城市數據的可得性,選取工業用電量占城市總用電量的比例作為能源消費結構的衡量指標。
7.技術進步(InPT)。技術進步可以提高生產率和能源利用率,但如果技術在發展初期為污染性技術,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本文用各城市專利授權數量衡量技術進步水平。
8.政府干預(GOV)。政府的干預也會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本文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與GDP 的比值衡量各地政府的干預程度。
基于以上因素分析,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i=1,2…,41,表示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t 表示年份;CGTFPit、CGECit和CGTCit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代表i 地區在第t 年的累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累積綠色技術效率以及累積綠色技術進步;αit為常數項,β1~β8為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μit表示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本文使用面板數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RE)進行回歸,為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采用全面FGLS 模型進行回歸。表3 顯示RE 模型、全面FGLS模型回歸結果。

表3 RE 模型、全面FGLS 模型回歸結果
(二)實證結果分析
從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大部分變量系數相近、影響相同,個別變量的顯著度有所差異,全面FGLS 模型的回歸結果更加顯著,本文將根據全面FGLS 模型(4)~ 模型(6)的回歸結果分析長三角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
經濟發展水平對CGTFP 具有促進作用,對CGTC具有抑制作用。對綠色技術效率具有正向影響,但影響不顯著。
人力資本對CGTFP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CGEC 和CGTC 具有負向影響,但綠色技術進步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外商投資對CGTC 和CGEC 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影響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總體來看,外商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CGTFP。
產業結構雖然對CGTC 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CGTFP 具有更加顯著的抑制作用。對綠色技術效率也具有負向影響,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總體來看,現行的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還是抑制了CGTFP的提升。
環境治理能力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指標的選取不能很好地反映環境治理能力和CGTFP 之間的關系,仍需深入分析。
能源結構對CGTFP 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CGEC 和CGTC 的影響不顯著。這一結果肯定了當前長三角地區在能源結構方面的調整成效,有效促進了經濟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技術進步對CGEC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CGTFP 和CGTC 的影響不顯著。技術進步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可以大幅提高CGEC。
政府干預對CGTFP 和CGEC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CGTC 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EBM-GML 指數測度長三角地區41個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全面探究長三角地區綠色經濟發展狀況。
從動態演變角度分析,樣本期內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整體層面呈上升趨勢,增長幅度不大。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技術進步,技術效率改進的貢獻相對較小。雖然長三角地區城市的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高,但技術效率增長不足,需要進一步改善。
從影響因素角度分析,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能源結構、政府干預等因素促進長三角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外商投資、產業結構抑制長三角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二)政策啟示
1.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各個城市之間可以加強人才交流和互動,實現人力資本均衡合理分布,以適應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在提升人力資本的同時,要重視高質量人才的引進,提高綠色技術效率。對于在人才流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障礙,從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角度出發,對長三角地區在醫療、教育、住房等基礎方面實施協同發展,促進人才跨城市流動,使人力資本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均衡協調發展。
2.為了實現長三角地區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在建立績效評價體系過程中,不能僅僅考慮經濟增長,還需要重點關注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要建立一定的激勵和適當的懲罰機制,讓各個城市和企業有動力改善環境質量,追求綠色GDP。積極優化調整能源結構,促進能源體系的低碳化,提高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3.長三角各個城市在積極引入外商投資的過程中,不能只追求外商投資帶來的經濟利益,還需要考慮引入的外商投資在環境和能源方面的問題。調整招商引資的工作思路,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更多的流入高新技術產業部門,促進技術進步,對高污染高能耗部門設置一定的環境規制成本,盡可能降低能源消耗和減少污染排放,提高綠色生產率。
4.長三角一些城市目前仍然存在較多的傳統產業,產業結構優化不足。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和合肥等核心城市可以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提升自身產業優勢的同時,還可以與周邊輻射城市形成互補關系,促使各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的進程中實現整體產業分布更優格局,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實現經濟綠色可持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