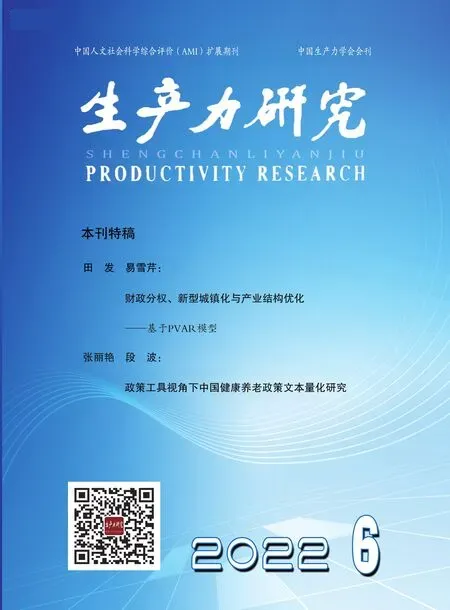互聯網使用強度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
——基于2018CFPS 的實證
王 娟,熊 楊
(南京郵電大學 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3)
2021 中國精神衛生調查顯示,我國成人抑郁障礙終生患病率為6.8%。新冠疫情期間針對患者的治療兼顧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數字時代互聯網已經融入居民生活的不同維度,網絡對居民心理健康已經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現有文獻中,探討互聯網對生理健康的影響較多,主要涉及醫療健康體系和健康知識獲取兩方面。如曹博林(2021)[1]認為,互聯網醫療有利于促進患者的滿意度、疾病治愈效果、健康素養和健康行為;Green 等(2004)[2]發現健康個體更傾向于使用互聯網搜尋健康信息;Shaw 和Gant(2002)[3]較早通過實驗研究發現,通過互聯網交流溝通可以減輕參與者孤獨失落等情緒癥狀;Heo 等(2015)[4]認為老人可以通過互聯網更好地重新融入社會,通過與社會的溝通排遣孤獨感。結合現有文獻,本文首先關注互聯網使用強度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并嘗試通過理論闡述關系形成機制;其次,通過邊際系數探索各因素對不同層次心理狀態的影響規律。
一、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數據采取的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文章使用2018 年CFPS 中的個人數據庫,研究對象是16~64歲的居民,剔除缺失數據樣本后保留11 915 個有效樣本。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心理健康狀況。CFPS 數據中有“我感到情緒低落”和“我感到悲傷難過”兩項問題,答案都是“幾乎沒有”“有些時候”“大多時候有”“經常有”四類,分別賦值為“1”“2”“3”和“4”,然后將二者的賦值相加作為心理健康的代理變量,數值下降表征心理狀態的改善。
2.被解釋變量。互聯網使用強度。選取報告中的“業余上網時間”衡量。
3.控制變量。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因素眾多,結合楊克文和何歡(2020)[5]、Cotten 等(2014)[6]現有文獻的研究,選取控制變量有收入滿意度、性格外向性、對未來信心、工作環境滿意度四項主觀因素;選取性別、年齡、教育水平、認知能力、個人地位、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住院等客觀因素;其他層面選取家庭人數、城鄉差異兩項;省份做省份固定效應。
(三)模型選取
模型中對互聯網使用強度作對數化處理,并加入對數項的二次項。

time 是核心解釋變量,β1是我們最關注的核心系數;xi是各個控制變量,γi是控制變量的系數;provcd 是省份固定效應;εi是隨機誤差項;β 是實數項。方法使用Ols 回歸和Ordered Probit 回歸。
二、實證檢驗
(一)統計分析
簡單從居民數據的統計分析看,居民心理健康均值為3.25,整體上看心理狀態良好;但相對而言,超出健康狀態的1.25 說明存在部分群體心理健康狀況較差。從居民客觀身體健康狀況看,是否有慢性疾病和是否住院的均值數值極低,說明居民的基礎身體素質普遍很高,是心理狀態良好的重要基礎。
(二)基準回歸
表1 是Ols 回歸結果。回歸依次加入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和其他因素,并控制聚類標準差和省份固定效應。總體看模型(1)~ 模型(4),核心變量的系數由0.027 下降到0.022,形狀更加平緩,但始終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互聯網使用強度對個體心理健康狀況存在顯著性影響。控制變量基本都在1%和5%水平上顯著,說明控制變量的選擇較為穩健。
具體看,二次項的核心系數皆為正數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互聯網使用強度和心理健康可能存在“U”型關系,因為Lind 等(2010)[7]認為若數據集某段是單調凸,變量平方項同樣會顯著,但二者并不滿足“U”型關系。因此使用Stata 中的Utest 做進一步檢驗,結果發現p 值在1%水平上顯著,拒絕單調和倒“U”的原假設,二者證實存在“U”型關系。隨著互聯網使用強度上升,初期個體心理健康得到改善,當使用強度達到一定程度,心理健康與強度呈負相關。
表2 是Ordered probit 回歸結果。二次項系數也為正數,互聯網強度和心理狀況概率上呈現“U”型關系。二次項和一次項都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互聯網使用強度顯著影響個體心理狀況。Ordered probit 系數解釋需進一步處理,使用Stata16 求Ordered probit各變量的邊際系數得到表3。由于變量心理健康的數值為“2”“3”時基本是心理健康狀態,為方便解讀便只在4~8 范圍內計算。

表2 Ordered probit 模型

表3 Ordered probit 邊際系數
表3 中互聯網使用強度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相反,說明同時存在概率使得心理狀況改善或惡化,在互聯網使用強度較低時,使用網絡促進心理狀態改善;但當使用強度持續上升,使心理惡化的損害超過心理收益,造成心理健康下降。觀察心理狀態從“4”~“8”各個變量邊際系數的改變,存在系數絕對值遞減趨勢。遞減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心理狀態惡化過程伴隨著對各影響因素的適應過程,對惡化或改善效應產生“耐性”,變量影響概率出現類似邊際效用遞減現象;另一方面,當心理狀態下降到“6”“7”“8”的程度,糟糕心理主導個體狀態,心理惡化程度達到極值。
(三)“U”型機制解釋
社會支持理論認為人處于社會關系網絡中,通過與關系網互動維持個人身份地位,獲得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分為工具性支持和表達性支持。個體通過互聯網找尋健康咨詢服務,高價值信息給予個體協助支持;個體困難如看病步驟、目標找尋等,可尋求網絡關系指引支持等。表達性支持方面,個體中青少年在社交中表達個人思想獲取存在感和價值感支持;互聯網幫助實現老年群體再就業,社會網絡認可老年群體價值從而獲得尊嚴支持等。因此,互聯網使用強度較低時,互聯網“功能性”作用更強,為個體創造更多社會支持條件,獲取高質量資源和條件,促進個體心理健康良好發展。
個體獲取社會支持過程并不純粹,互聯網使用強度越大,面臨落后文化和行為內容的沖擊越嚴重。個體挖掘互聯網程度更深,容易接觸到互聯網監管缺失位置。依據社會濡染機制,個體與互聯網高強度的互動過程中,不良內容濡染機制更容易發生。信息心理群體效應強調群體會影響個體行為和改變個體思想,健康心理在互聯網高強度使用情況下更易被違法互聯網平臺或內容引導走向消極墮落。投入互聯網時間過長,導致身體健康變差,自身脫離現實關系,忽略“人”本身的現實價值,是出現心理問題的重要原因。因此,合理控制互聯網使用時間,才能預防個體心理狀況進入“U”型曲線的惡化階段。
(四)異質性分析
表4 是性別差異回歸。模型中女性的核心系數都大于男性系數,“U”型圖表現為同一階段女性曲線比男性曲線斜率更大,說明隨著互聯網使用強度改變,女性心理狀態受到的沖擊超過男性。可能由于女性相對男性更加感性,容易與互聯網內容共鳴。

表4 性別差異
表5 面對不同年齡群體進行回歸,年少群體的核心系數大于年長群體系數。年長群體“U”型線較年少群體更加平緩,說明隨著互聯網使用強度改變,年少群體心理狀態受到的沖擊更大。年長群體世界觀穩定,互聯網使用時間較少,互聯網對年長群體影響較小。而年少群體是網絡空間最活躍、接受信息最駁雜的群體,獵奇心理使他們易受到網絡浸染。

表5 年齡差異
(五)穩健性檢驗
選取2018 年CFPS 中“每月郵電通訊費”作為上網時間的替代變量,郵電通訊費和上網時間相關,但和個人心理健康沒有直接關系。同樣取對數化使用兩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見表6)。除第三個未控制省份固定效應,其他模型都至少在10%水平上顯著,互聯網使用強度顯著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狀況。因此,實證結果較為穩健。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實證發現互聯網使用強度和心理糟糕程度呈“U”型關系。觀察Ordered probit 模型,發現邊際系數絕對值存在類似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接著理論闡述“U”型機制原因。異質性分析表明,女性和年輕群體更易受到互聯網內容的沖擊。結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三條建議。
第一,鼓勵正向積極健康內容傳播,拓寬網絡空間監管寬度與深度,加大負能量內容打擊力度。研究認為互聯網使用強度上升,增加個體接觸網絡空間灰色和黑色地帶內容的可能性,優秀互聯網作品傳播通過群體效應可以幫助更多群體改善心理狀況;同時,通過更加全面深入的網絡監控機制,針對網絡空間各個角落,結合政府打擊、社會自律和群眾舉報聯動,清掃網絡空間,為個體獲取社會支持的過程創造更加清正的環境,減少互聯網內容對個體施加的負面影響。
第二,合理安排個體互聯網使用時間,正確對待現實關系網與網絡關系網之間的關系。短時間使用互聯網可以迅速擴展個體關系網,使個體獲得強烈存在感和社會融入感,獲得心理快感。但互聯網使用時間不加控制,沉溺虛擬關系網絡尋求心理慰藉,脫離現實關系網反而會使個體關系網不健康,與社會脫節影響心理狀態。對于個體而言,互聯網只能是現實關系網的延伸而不是替代,以正確態度對待來自互聯網的內容。
第三,針對女性和年少群體做出必要措施。現代女性仍是社會弱勢群體,互聯網深深嵌入女性群體發揮效用,積極引導互聯網發揮為女性創造心靈港灣、解決現實問題和實現價值與再就業的作用;為女性打造專門化互聯網平臺和生態,既有利于促進女性心理和身體健康發展,也能促進社會公平的繼續進步。針對年少群體,尤其《“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強調關注解決青少年的健康問題,互聯網使用管控更要合理,一刀切和放任都違背客觀規律;要鼓勵青少年借助互聯網開闊視野、獲取知識并表達思想,但嚴格控制內容和時間,科學把控青少年常見困惑和情緒,特別關注青年女孩,及時疏導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