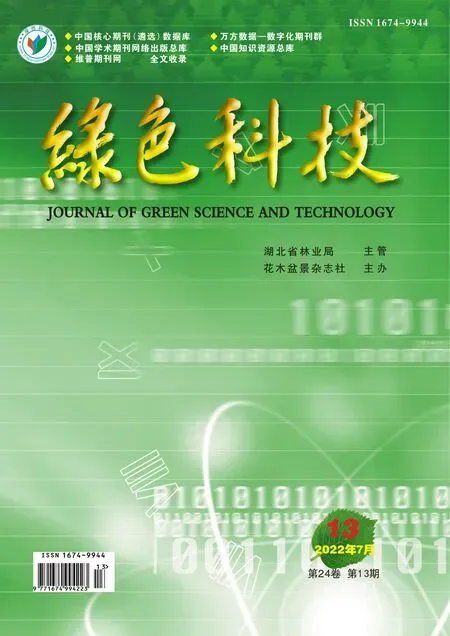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及障礙因子研究
——基于DPSIR模型和相對熵TOPSIS模型
卓瑩瑩,翁異靜,來越富
(1.浙江科技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2.浙江科技學院 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1 引言
城市化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隨著新常態下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的不斷優化調整,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面臨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而新型城市化的建設憑借其在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和推動產業升級等方面的巨大潛力,成為新時期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前驅力量和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重要載體[1]。但在“輕質重速”的城市化發展模式下,城市功能不完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等問題也不斷凸顯,從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城鎮化必須進入以提升質量為主的轉型發展新階段”。那么在高質量發展理念下,城市化建設成效如何?是否符合高質量發展標準?城市化高質量發展進程中存在哪些障礙?這些是高質量推進新型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科學問題。
新型城市化的高質量發展以內涵和效益提升為重點,主張在數量、規模有序擴張的同時,兼顧整體的長期均衡和系統化協調[2]。部分學者對新型城市化建設問題已進行了初步探索,主要集中于新型城市化內涵解讀[3,4]及實證測度[5~7]等方面,方法上則多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對新型城市化水平進行綜合測度[8,9]。隨著我國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相關議題也逐漸受到關注,但極少數文獻對新型城鎮化與高質量發展的關聯性進行了分析[10,11],且目前尚未具體到新型城市化發展層面。而新型城市化作為一個動態復雜系統,需要從系統性角度進行擴展,同時,關于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因素研究稀少,對障礙因素進行研究對于推進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基于此,本文首先基于“驅動-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模型,從復雜系統角度構建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采用相對熵優劣解距離(TOPSIS)法對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動態評價,并利用障礙度模型分析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因子,最后根據實證結果給出促進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以期為新型城市化發展戰略的實施及調整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和決策依據。
2 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2.1 指標體系構建及權重計算
新型城市化具有明顯的復雜系統特征,受人口、經濟、地域、生活等諸多因素影響。新型城市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市化,堅持城市化發展的可持續性,強調走集約型發展道路,進而推動新時期中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12]。因此,構建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需從復雜系統角度綜合考慮,本文依據新型城市化內涵,結合考慮指標選取的科學性、數據可獲得性等原則,從人口、經濟、地域、生活等廣義角度,基于DPSIR模型,從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和響應5個層面選取36個指標建立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將指標分為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正向指標數值越大,評價結果越好;負向指標數值越小,評價結果越好。其中,驅動力子系統(D)是指使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系統發生變化的原因,即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壓力子系統(P)是指在經濟發展的驅動下,社會發展面臨的壓力;狀態子系統(S)是指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雙重作用下,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所處的城市社會發展狀態;影響子系統(I)是指驅動力、壓力及狀態子系統對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整體作用;響應子系統(R)是指為了改善由驅動力及壓力造成的影響,而進一步采取的措施。具體的指標構建及權重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2.2 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國2009~2018年10年的時間序列樣本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經濟年鑒》《中國城市環境衛生行業年度發展研究報告》《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等官方資料。

表1 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
2.3 研究方法
2.3.1 相對熵TOPSIS模型
優劣解距離(TOPSIS)模型是統計決策學科中比較重要的評價模型,被廣泛應用于經濟、環境、工業等管理決策研究中,隨著近年來對TOPSIS模型研究的不斷深入,TOPSIS模型中定義的歐式距離已不能滿足決策者的要求,若評價對象與正理想解的距離和評價對象與負理想解的距離相同,則無法判斷評價對象的優劣性,從而導致TOPSIS評價模型失效。而相對熵TOPSIS評價模型在TOPSIS模型基礎上進行改進,用相對熵值替換TOPSIS模型中定義的歐式距離值,通過相對熵來判別2個方案的差別程度,彌補了原有TOPSIS模型的缺陷[13,14]。相對熵理論通過定義Kullback-Leibler[15]距離進行判別2個系統的差異程度,若兩個系統分別表示為ai和bi(i=1,2,…,m),則兩者的相對熵d為:
(1)
利用式(1)計算評價對象與正理想解的相對熵d+及評價對象與負理想解的相對熵d-,d+越小,評價指標與正理想解越接近,新型城市化發展質量越好;d-越小,評價指標與負理想解越接近,新型城市化發展質量越差。最終,計算評價對象與理想解的貼近度:
(2)
式(2)中,Hi值越大,表明第i個指標貼近度越高,其發展情況越好。
2.3.2 障礙度模型
障礙度模型由影響因子貢獻度、評價指標偏離度、障礙程度3部分構成,影響因子貢獻度Gi是各項評價指標對評價系統的權重;評價指標偏離度Sij是各項評價指標與評價系統理想目標的差距程度,即各項指標與1之間的差值;障礙程度Lij是各項指標對評價對象阻礙程度[16]。計算方式如下:
(3)
式(3)中,Gi=wkwki,wk表示DPSIR模型中第k個系統的權重,wki表示DPSIR模型中第k個系統所對應第i個指標的權重(k=1,…,5,i=1,2,…,m)。
3 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評價結果與分析
基于構建的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相對熵TOPSIS模型對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進行綜合評價。根據上述相對熵TOPSIS模型評價步驟得到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用H驅動力、H壓力、H狀態、H影響、H響應分別表示DPSIR模型中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5個子系統的貼近度,用H綜合表示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值,最終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3.1 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分析
通過計算得到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并繪制相應趨勢圖,如圖1所示。從圖1可得,2009~2018年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相對熵d-值呈遞增趨勢,從0.49038上升到2.87870,逐步遠離負理想解;相對熵d+值呈遞減趨勢,從0.17410下降到0.05131,表明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狀況越來越好。貼近度H綜合由0.73799上升到0.99906,即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值逐年上漲,趨近于1,2011年后緩慢增長,但增長態勢較為穩定。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中國政府對城市化建設的高度重視,黨“十六大”以來,從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到新型城鎮化全面指導“十二五”規劃,到2010年新型城市化成為中國避免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戰略安排,再到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正式出臺,逐步明晰了新型城市化的發展思路。

圖1 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值變化趨勢
3.2 基于DPSIR模型的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子系統分析
根據表2結果,進一步分析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DPSIR模型的5個子系統。
(1)驅動力子系統:2009~2018年驅動力子系統的貼近度逐年上漲,2018年達到了0.99999,接近1。這得益于穩定增長的城鎮人口數量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口數量由2009年64512萬人增長到2018年83137萬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09年17175元增加到2018年39250.8元,同時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也逐年增加,2018年達到了56076 km2。
(2)壓力子系統:壓力子系統中的負指標一直是阻礙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因素,從本文得到的壓力子系統貼近度可發現,2009~2018年壓力子系統貼近度逐年下降,從2009年的0.09226下降到2018年的0.0017,壓力子系統整體上處于較差水平。隨著城市化進程推進,能源資源高消耗和“三廢”高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破壞。同時,由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帶有明顯的政府主導特征,地方政府收入對土地的依賴一直是彌補收支缺口的重要途徑,國家雖采取了一些積極應對措施,但環境污染、土地財政仍不可避免。
(3)狀態子系統:狀態子系統是驅動力子系統和壓力子系統共同作用的結果,2009~2018年狀態貼近度持續增長,2014年貼近度實現質的飛躍,達到良好狀態。這得益于國家積極實施就業政策,如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崗位、拓寬就業渠道、完善就業援助機制等措施,使得2013年城鎮新增就業1310萬人,完成全年任務的145%。2013年城鎮人口就業數量增幅達到18.85%,比2012年城鎮人口就業數量增幅高出13%,有效遏制了壓力子系統對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4)影響子系統:2009~2018年影響子系統貼近度一直呈現穩定增長趨勢,影響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因素錯綜復雜,人口、經濟、地域、生活等方面為主要影響因素。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使得城市開發成本減少、土地資源消費降低;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逐年增長使得城市建設資金充裕,公共服務提供得以保障;城市綠地建設面積的增加、危險廢物綜合利用量大幅度上升、空氣質量達到好于二級的天數增多擴大了生態空間、減輕環境壓力,從而為新型城市化建設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基礎。
(5)響應子系統:2009~2018年響應子系統貼近度從0.00292增加到0.03225,國家致力于制定促進新型城市化建設高質量發展的積極響應措施,城鎮人口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從2009年的50443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131988元,城市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從2009年的7.15人增加到2018年的10.91人,各項投資性補助從2009年的2938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9884.9億元,危險廢物處置量從2009年的48291萬t降低為2551.56萬t。從財政、人員配備、環境治理等方面采取的積極措施,有預見性的推動響應子系統貼近度穩步上升,表明了新型城市化建設發展能力逐漸增強。
3.3 障礙因子診斷
在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的基礎上,利用障礙度模型進一步探析阻礙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因素。根據障礙度模型計算方法分別對2009年和2018年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各指標及子系統的障礙度進行計算,并根據障礙程度從大到小的順序篩選出排名前十的障礙因素,結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2009年和2018年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主要障礙因素排序 %
從表3可以得到,2009年阻礙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壓力、影響和響應子系統,具體包括土地租金收入(A14)、危險廢物綜合利用量(A25)、城鎮危險廢物處置量(A34)、各項投資性補助(A32)、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A22)、城鎮人口就業人員平均工資(A30)、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A23)、環境污染治理投資(A33)、城市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A31)和城市綠地面積(A24)。到2018年,阻礙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壓力、狀態、影響和響應子系統,具體包括土地租金收入(A14)、危險廢物綜合利用量(A25)、城鎮危險廢物處置量(A34)、各項稅收收入(A11)、城市主要廢物排放總量(A13)、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A23)、城市人均生活能源消費量(A26)、城鎮人口老年撫養比(A8)、城鎮居民主要食品消費量(A19)、城鎮居民消費水平(A16)。
綜合分析發現,雖然2009~2018年指標變化態勢都有一定的波動,但土地租金收入(A14)、危險廢物綜合利用量(A25)、城鎮危險廢物處置量(A34)這3個因素始終處于障礙程度前三甲,由此說明,城鎮危險廢物利用與處置和土地租金收入問題對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較大影響。

表4 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五個系統障礙程度 %
進一步對(表4)DPSIR模型5個子系統的障礙程度進行分析發現,壓力子系統的障礙程度雖然有所下降,但依然是5個子系統中障礙程度最高的,原因在于壓力系統中的因素均阻礙著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該結論和上述通過分析貼近度得出的壓力子系統整體較差的結論是一致的。障礙程度排名第2高的是影響子系統,該子系統包含了幾乎所有影響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因素。排名第3的是響應子系統,其雖包含積極且有效促進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但一旦治理不當,由積極轉為消極,也會引發嚴重的后果。狀態子系統的障礙度經歷了先降后升的“V”字形波動,而驅動力子系統的障礙度經歷了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形波動后,使得其障礙度在5個子系統中排名最低,驅動力因素發揮了積極作用。由此得出,5個子系統障礙程度大小排名為壓力影響響應狀態驅動力。
4 結論與建議
4.1 研究結論
基于DPSIR概念模型,從復雜系統角度構建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相對熵TOPSIS模型對我國2009~2018年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狀況進行動態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利用障礙度模型探析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因子,從而得出以下結論: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綜合貼近度逐年上漲,新型城市化發展質量不斷提高;驅動力、狀態、影響及響應子系統貼近度逐年上漲,壓力子系統貼近度逐年下降,表明新型城市化戰略的實施,對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大促進作用;壓力子系統是影響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系統,其次是影響和響應子系統,驅動力子系統最低,土地租金收入、危險廢物綜合利用量、城鎮危險廢物處置量是主要障礙因素。
4.2 對策建議
為促進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根據實證結果提出以下3點建議:
(1)優化調整土地租金,必要可給予政策支持。土地是新型城鎮化建設必不可少的條件,尤其是在高質量發展理念下,土地開發以及土地合理配置成為了新型城市化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且土地租金的高低也直接影響著城市化建設與土地合理配置。同時,土地租金收入是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首要障礙因素,因此,有必要對土地租金進行優化調整,從而有利于提升新型城市化發展水平與質量,必要時可給予相應政策支持。
(2)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合理利用處置危險廢物。危險廢物綜合利用量和危險廢物處置量是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危險廢物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均會造成不良影響,對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也十分不利,應通過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利用高科技提升危險廢物綜合利用能力,將減少工業廢氣、固體危險物排放,以新型能源代替傳統能源等措施并舉。
(3)注重城市化發展差異性,鼓勵“對號入座”政策。壓力子系統是影響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系統,其次是影響子系統和響應子系統。壓力子系統主要體現在人口福利、經濟環境、城市消費方面,而影響子系統和響應子系統則主要體現在城市人口、環境治理、城市生活、政府補助、城市經濟等方面,子系統間雖有相同之處但仍存在差異,因此需要注重城市化發展的差異性。無論是人口、經濟還是環境,都需要發揮各自的優勢,以優勢促進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從而制定相應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