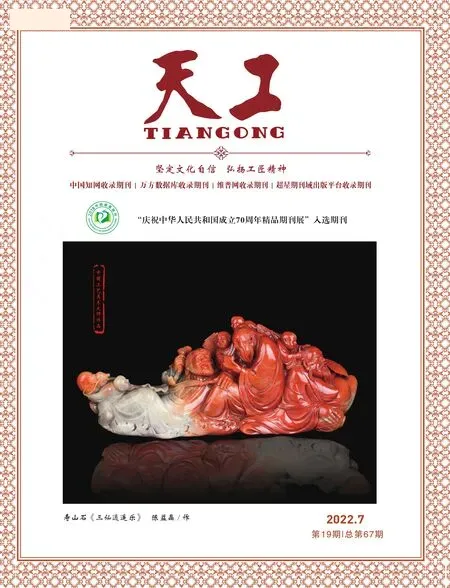古與今的“孿生”
——汴繡在當代繪畫中的傳承與實踐
王 靜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
汴繡又稱“宋繡”,由于承襲了宋畫精致的畫風、沉穩的色彩和高雅的格調,又稱“繡畫”。早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中就有“衣畫而裳繡”①周汛、高春明:《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第4頁。的規定,“畫”與“繡”并用,兩種藝術表現形式相融相合,相互借鑒,互為孿生。
本文以開封市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的《汴繡志》②開封市地方史志辦公室:《汴繡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為主要撰寫依據,以現代汴繡作品《在人間》為實踐研究對象,對當代汴繡藝術的傳承與發展進行創新研究。
當代藝術承擔著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講好中國故事、促進民心相通的責任。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到輸出供給,也對藝術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藝術創作水平的提升,都在呼喚著與傳統文化的融合與新生。通過汴繡藝術與現代繪畫藝術的“孿生”創作,以點帶面,以實踐的方式,探求中國傳統藝術在保留材料、技藝的“古意”的同時,成為中國現代繪畫材料傳承與發展、走向世界的一條出路。
一、“畫”與“繡”
受宋畫的引領,畫種一直是引領汴繡繡法與創作的有效手段,繪畫是汴繡解不開的情結。《在人間》這件作品緣起于2019年北京大學朱青生先生策劃的南宮自然藝術博物館進行的大型動物組圖的創作。筆者長期從事動物寫實創作,以細密筆觸作為刻畫動物的主要方式,通過對不同動物的側面進行組合與重構,再現一個筆者所認知的、觀眾也樂于接受的、與人共生的動物世界。筆者不是動物心理專家,只是相信在相對浮躁的年代,人們更需要一些面對真實自然、講述人間普通情感的藝術作品。機緣巧合,河南輕工職業學院(原河南省工藝美術學校)孫蕊汴繡工作室的孫蕊教授看到了筆者的作品,她提出了創作現代寫實繪畫與汴繡結合的“孿生作品”的建議。
筆者為南宮自然藝術博物館創作的組圖的名稱為《動物的表情》(如圖1),后來也有很多觀者詢問筆者是否在創作一種動物的視角,而筆者更愿意借用動物的面孔進行人類世界的鏡像詮釋。在汴繡制作團隊的選擇上,孫蕊教授邀請了開封汴繡廠的程曼萍大師作技術指導,而筆者也愿意將操持“真刀實槍”的機會交給工作室平均年齡不足20歲的年輕汴繡技師。以此,“畫”與“繡”的結合促成了畫者、傳統大師和青年技術傳承人的技藝融合,傳統技藝被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理解、融合生長、傳承。也有可能提供一種視角,以走出當代汴繡題材依然無法脫離古代名作的現狀。所以,我們將這幅作品稱之為《在人間》,這是在人間的創作,是在人間的技與藝的融合(如圖2)。

圖1 南宮自然藝術博物館動物組圖《動物的表情》展示現場

圖2 《在人間》紙本創作
汴繡以真絲軟緞作為底料,也稱之為繡底。繡底的繪制在當代往往是由電腦輔助完成的,而為了保持對傳統的“敬畏”,筆者堅持秉承古法進行繡底的制作(如圖3)。孫蕊教授通過與程曼萍大師的協商,先后給筆者寄了兩次真絲底緞,第一次沒打漿,第二次打漿后寄給筆者,目的是保持原作的本貌,生怕底緞會產生毫厘變化影響繡品的“孿生”效果。汴繡復制畫作原稿時,無論是尺寸保持統一還是放大、縮小,必須遵從原作比例,而且不可錯位或是添減原作的畫面,這是汴繡藝術的“本真性”表達。

圖3 繡底的制作、在程曼萍大師指導下將繡底上繃
《繡譜》中“繡通”一節,在闡釋繪畫與刺繡的關系時,倡導刺繡者要反復實踐,將書畫知識與刺繡技巧融會貫通,以取得進步。具有“古意”是汴繡的特點,開封汴繡廠的青年技師索曉東說:汴繡的“古意”在21世紀應該稱之為“古里古氣”,這是一種形象的、有意思的解釋,也能表達我們共同創作這幅孿生作品的初衷。汴繡工作室的技師都很年輕(如圖4),相比汴繡廠技師的嫻熟技藝,我們都不約而同地看重這些年輕人較好的繪畫背景和不拘一格的繡法。這些年輕的技師利用傳統絲線對當代藝術作品進行創造性的表達,這種實踐似乎幫我們找到了當代繪畫“民族性”的一種思路。

圖4 年輕的汴繡技師進行《在人間》作品的繡制
二、針與法
以針代筆、以彩線代墨是汴繡的特點,正所謂用針要恰到好處。1979年,開封汴繡廠整理出汴繡的29種針法。1983年,曾任開封汴繡廠美術設計室主任、后調任開封市工藝美術研究所所長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王少卿先生帶領汴繡廠的師傅以純手工的方式制作了《汴繡(宋繡)針法匯編》(如圖5)。書中在前言記述:“汴繡的針法是在運用宋繡針法的過程中,逐步創新、引進而發展起來的。”他們在研究整理的過程中,增加了“疊彩繡”“大亂針繡”“對針繡”“納點繡”“編繡”“小亂針繡”和“交叉繡”7種針法,至此,汴繡針法達到36種。

圖5 《汴繡(宋繡)針法匯編》手工原件封面與前言
與傳統四大名繡相比,汴繡的針法更為單純。選用合適的針法繡制作品,是汴繡保持樸拙本色的關鍵。當然,新的題材必然呼喚新的針法。例如,近年來被普遍使用的亂針繡,就是受西方繪畫影響為表達光影效果應運而生的。在一根針上紉幾條顏色的線,用大小針腳進行作品的繡制,著重于繡品質感的表達。汴繡秉持“一物、一針、一法”,經過數代汴繡人的探索嘗試,產生了諸如滾針繡水紋、練針繡船錨、繩針繡錨繩、別針繡棚席、反戧繡屋瓦、發針繡人物、蒙針繡柳樹等多種針法,形成了“山水得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人情具瞻眺之情,花鳥含綽約之態”的獨特氣質。
不炫技、不驕躁是汴繡針法的氣質所在。汴繡技師往往需要通過與畫師的交流,依循自身的繡制經驗,為畫作訂制“針法”。《在人間》的針法選擇一度成為汴繡技師的爭議點,最終采用了散套繡(如圖6)、亂針繡、平針繡(如圖7),輔以墊針繡、包針繡、悠針繡、滾針繡、齊針繡的針法。作品繡制時,絕大多數采用散套繡,以不同粗細的線股、不同長短的針腳,表現它們毛色的差異和特色。一根真絲繡線劈兩份,每份叫一絨,一絨可以根據需要分成4份、6份、8份、16份、32份……直至分成一絲。

圖6 汴繡的針法表現——散套繡

圖7 汴繡的針法表現——平針繡
為了突出汴繡作品所注重的“空”與“滿”互補的空間關系,占據1/3畫幅的大象采用常見的平繡針法。整體色彩在粉色、黃色兩種色系中細分成25種不同的色線,以達到遠看意境深遠、近看奇妙無窮的視覺效果。
三、傳與承
針法的傳承同時也需要“藝術”的表達,繡法則最為關鍵。在《雪宧繡譜》“繡要”一節中,繡法的工藝美學原理被歸納為“審勢”“配色”“求光”“肖神”“妙用”“慎性”六個要素。其中,作者對“妙用”進行了較為精彩的論述:“色有定也,色之用無定;針法有定也,針法之用無定。有定故常,無定故不可有常,微有常弗精,微無常弗妙,以有常求無常在勤,以無常運有常在悟。”這段話充滿了辯證與哲思,利用彩色絲線與錦緞的結合,在不經意中表現原作寓意,“應物象形”是汴繡針法的“妙用”。
年輕汴繡人從繡底上繃、劈線到針法學習,這個過程就是技法的傳承過程。汴繡常用針法不到十種,學會針法并不難,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反復體會、運用。《在人間》的創作過程中,要能做到根據動物的特點把線順好,把顏色過渡好,把針法用好,從雙手不聽使喚到得心應手,是一個漫長的練習過程。筆者經常與他們談這幅作品的創作心得、邀請程曼萍大師做示范,研究同一塊繡品在師傅的手里怎么表達、能如何深入地表現動物的質感,用相互促進的方法進行學習與創作,是這幅作品創作的日常。“我針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學焉,長而習焉,舊法而已。既悟繡之象物,物自有真,當放真既見歐人鉛泊之畫,本于攝影,影生于光,光有陰陽,當辨陰陽,潛神凝慮,以新意運舊法,漸有得既又一游日本,觀其美術之繡, 歸益有得。久而久之,遂覺天壤之間,千形萬態,但入吾目,無不可入吾針,既無不可入吾繡。”①出自張謇、沈壽共同編撰的《雪宧繡譜》。張謇、沈壽在刺繡藝術實踐中的總結也闡釋了這樣的道理。
在作品繡制的過程中,拆是不可避免的,把沒有繡到位的地方重新拆掉重做也是對刺繡優秀標準的校驗過程。針法并非一成不變,所以拆不單是一針下去沒繡對就要拆,拆也是舊元素新組合,是多樣性的嘗試,是新與舊的重新建構,這就是年輕的汴繡人參與非遺傳承的價值。也是這樣的反復修改,使年輕汴繡人的技藝和心性得到磨礪,他們在找到差距的同時也拓展了新的創作空間。
繡制《在人間》的年輕人從“一花一葉”的技法訓練直接跨越到大作品的繡制,這本身并不符合刺繡傳統傳承方式中師傅帶徒弟的邏輯。對他們來說,這樣的工作充滿挑戰、有許多困難,針法也沒有現成的樣本,需要邊做邊規劃,需要“師生”商量研討,這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創新能力培養與應用脫節的問題,同時傳授者與學習者、師與徒變成了平等的伙伴關系,這對于傳統技藝在當代的傳承有借鑒意義。
歷史上關于“畫”“繡”關系的分析,最終的落腳點都落在繡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養的告誡。在當代,“尋造物之妙巧”②出自南朝梁國人張率的《繡賦》。、安心創作、用一針一線傳承藝德藝馨,是《在人間》創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