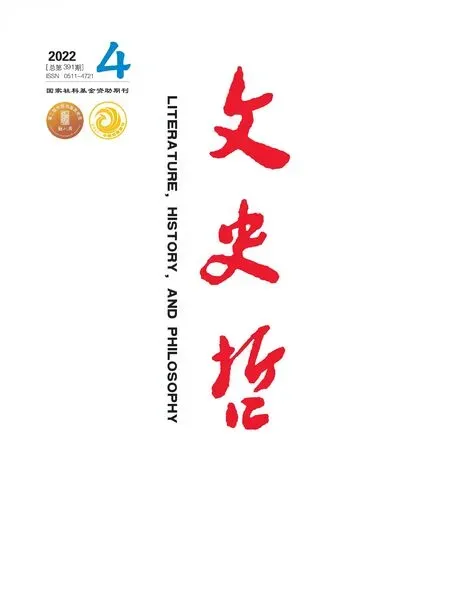漢晉北朝河朔詩(shī)考述
陸 路
結(jié)合漢晉北朝時(shí)的文化傳統(tǒng)、自然地理、行政區(qū)劃等因素,本文所說(shuō)的河朔地區(qū)西抵太行山,東臨渤海,南迄淇水,東南沿黃河、篤馬河(今馬頰河與之大致相當(dāng)),北枕燕山,東北達(dá)遼東。大抵相當(dāng)于西漢時(shí)的冀州、幽州、司隸部河內(nèi)郡的淇水以北地區(qū)。對(duì)于西晉政區(qū)而言,則大致包括冀州大部(不包括平原郡與樂(lè)陵郡大部)、幽州大部(不包括代郡)、平州西部(昌黎郡、遼東郡、玄菟郡),以及司州的魏郡、頓丘郡、廣平郡、陽(yáng)平郡、汲郡北部一角(即林慮縣一帶)。約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大部,北京市,天津市,山東省轄聊城市北部(臨清市、高唐縣等)、德州市北部(夏津縣、武城縣、寧津縣、市區(qū)、樂(lè)陵市、慶云縣等)、濱州市小部分地區(qū)(無(wú)棣縣北部臨近德州慶云縣之地),河南省轄鶴壁市大部(不包括淇縣)、安陽(yáng)市大部、濮陽(yáng)市大部,以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轄赤峰市南部(喀喇沁旗、寧城縣、敖漢旗等)、遼寧省中西部(朝陽(yáng)、阜新、鐵嶺一線以南,撫順、本溪、丹東一線以西地區(qū))等。
河朔地區(qū)是漢晉尤其是北朝文學(xué)的重要興盛區(qū),為中古文學(xué)的發(fā)展、民族文化的延續(xù)等做出重要貢獻(xiàn)。就詩(shī)歌而言,該地區(qū)的創(chuàng)作為五言詩(shī)的成熟乃至日后唐詩(shī)的繁榮提供了某些基礎(chǔ)。本文為河朔詩(shī)做系地研究,認(rèn)定詩(shī)歌遵循屬地原則,河朔詩(shī)即指作于河朔地區(qū)的詩(shī)歌。漢晉北朝政區(qū)有一定變化,西晉居中,政區(qū)較漢要分得細(xì)些,北朝州郡設(shè)置泛濫,故本文在為詩(shī)歌系地時(shí),大體以西晉政區(qū)為綱,兼考慮詩(shī)歌創(chuàng)作時(shí)的實(shí)際政區(qū)情況和文化傳統(tǒng)。同一區(qū)域的詩(shī)歌以創(chuàng)作時(shí)間先后為序。對(duì)漢晉北朝河朔詩(shī)的系統(tǒng)考析,為河朔文學(xué)研究提供地理空間視角,有助于全方位理解河朔文學(xué),也是漢晉北朝文學(xué)地理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漢晉北朝河朔詩(shī)考
(一)司州
1.魏郡
漢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分河內(nèi)郡、清河郡、上黨郡置魏郡,屬冀州。晉時(shí)屬司州,黃初二年(221),東部又分出陽(yáng)平郡,此后魏郡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邯鄲市南部(臨漳縣、魏縣、大名縣)以及河南省安陽(yáng)市之(市區(qū)、蕩陰縣、滑縣)、鶴壁市之浚縣,治鄴縣(今河北臨漳縣鄴城鎮(zhèn))。由于鄴城是河朔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中心,也是河朔詩(shī)歌創(chuàng)作最多之地,故將之在魏郡詩(shī)中單列。
(1)鄴城
東漢無(wú)名氏《皇甫嵩歌》是較早的河朔詩(shī)。皇甫嵩為冀州牧,平黃巾軍后中平元年奏請(qǐng)免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作歌(騷體)頌之。東漢末冀州治鄴縣,是詩(shī)即中平元年(184)作于鄴縣。

劉楨、徐幹為曹丕五官中郎將文學(xué),二人曾在鄴城作詩(shī)贈(zèng)答。劉楨《贈(zèng)徐幹》云:“誰(shuí)謂相去遠(yuǎn),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wú)由宣。思子沉心曲,長(zhǎng)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mén),遙望西苑園。細(xì)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fēng)轉(zhuǎn),飛鳥(niǎo)何翻翻。”所謂“拘限清切禁”正指被拘禁。徐幹《答劉楨》云:“陶陶朱夏別,草木昌且繁。”結(jié)合劉楨與徐幹所寫(xiě)景象,可知亦作于夏季。大約作《公燕詩(shī)》后不久,劉楨見(jiàn)曹丕甄夫人,不拜而平視,因而入獄,在獄中作是詩(shī),徐幹見(jiàn)之而作答詩(shī)。二詩(shī)大約至早于建安十六年夏作于鄴城。劉楨出獄后繼續(xù)任五官將文學(xué),仍有可能參加游宴,所以是二詩(shī)作于《公燕詩(shī)》之前、之后皆有可能。劉楨《贈(zèng)五官中郎將》四首,其二:“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余旬。常恐游岱宗,不復(fù)見(jiàn)故人。”鄴城正是在清漳之濱,清漳河在鄴城西部(今河北涉縣)一帶,可知是詩(shī)約作于鄴城一帶。其三:“白露涂前庭,應(yīng)門(mén)重其關(guān)。四節(jié)相推斥,歲月忽已殫。壯士遠(yuǎn)出征,戎事將獨(dú)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文選》卷二三該詩(shī)李善注:“壯士謂五官也……出征謂在孟津也。《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zhèn)孟律及黎陽(yáng),而無(wú)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wèi),故曰戎事也。”陸侃如先生以為作于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張魯,曹丕出鎮(zhèn)孟津期間。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征張魯,而曹丕鎮(zhèn)孟津時(shí)與吳質(zhì)的書(shū)信中有“元瑜長(zhǎng)逝,化為異物”之語(yǔ),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可知曹丕鎮(zhèn)孟津是在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張魯時(shí)。如果作于建安二十年則劉楨至少是生了兩年病至二十二年卒,但據(jù)《典略》,劉楨是因二十二年的大疫而卒,可見(jiàn)并非卒于多年的疾病,且平時(shí)亦會(huì)生病,生病難過(guò)時(shí)也會(huì)懼怕死亡,并非卒前才會(huì)有類似恐懼。既然是詩(shī)不一定是劉楨卒前兩年作,而曹丕又多次隨曹操出征,如建安十七年十月、二十一年十月曹丕隨曹操征孫權(quán)(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植亦隨行)。也就不能說(shuō)詩(shī)中的壯士出征一定是指建安二十年鎮(zhèn)孟津。故是詩(shī)具體創(chuàng)作時(shí)間未詳,曹丕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間為五官中郎將,是詩(shī)大約作于此期間。
建安十八年春曹植隨曹操征吳北歸,途經(jīng)故鄉(xiāng)譙縣,曹植與夏侯霸子夏侯威交好,離開(kāi)譙縣時(shí),夏侯威一路送行至鄴城。夏侯威離開(kāi)鄴城時(shí),曹植作《離友》二首。序云:“鄉(xiāng)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fēng)。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shī)。”其一曰:“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jì)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lè)康。”追憶夏侯威一路送曹植一行回鄴城。其二曰:“涼風(fēng)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zèng)所思,感離隔兮會(huì)無(wú)期,伊郁悒兮情不怡。”敘離別的傷感思念。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封為魏公,是年七月魏建宗廟,正與序中稱“魏邦”合。曹植還有《侍太子坐》詩(shī)。曹植是詩(shī)稱曹丕為公子,題目很可能是后來(lái)所加,當(dāng)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為魏太子前,約在建安十六年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后。熊清元先生結(jié)合《文選》卷二七王粲《從軍行》五首之后四首(即“從軍有苦樂(lè)”以后四篇)寫(xiě)景之特點(diǎn),指出四詩(shī)作于建安十九年七月隨曹操征孫權(quán)時(shí)。這四首詩(shī)中約有兩篇作于河朔地區(qū)。王粲《從軍行》(涼風(fēng)厲秋節(jié))云:“我君順時(shí)發(fā),桓桓東南征……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則是詩(shī)建安十九年七月從征東吳出發(fā)前作于鄴城。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曹操還鄴,王粲隨曹操用征作《從軍詩(shī)》(從軍有苦樂(lè))。詩(shī)中云“歌舞入鄴城”,則作是詩(shī)時(shí)已回到鄴城。是詩(shī)當(dāng)建安二十一年作于鄴城。
西晉時(shí)陸云曾在鄴城成都王司馬穎幕府,作詩(shī)六首。永寧元年(301)朝廷派太尉王粹至鄴城加司馬穎九賜殊禮,王粹離開(kāi)鄴城前司馬穎為之餞行,陸云作《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祖餞贈(zèng)此詩(shī)》,據(jù)詩(shī)中“歲亦暮止,之子言歸”,可知永寧元年冬陸云已在鄴城,是詩(shī)作于此時(shí)。陸云《與兄平原書(shū)》:“王弘遠(yuǎn)去,當(dāng)祖道,似當(dāng)復(fù)作詩(shī)。構(gòu)作此一篇,至積思,復(fù)欲不如前倉(cāng)卒時(shí),不知為可存錄不?諸詩(shī)未出,別寫(xiě)送。弘遠(yuǎn)詩(shī)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shī),公甚笑。”則司馬穎為王粹餞行時(shí),王粹(字弘遠(yuǎn))、中靜(或曰為郭澄之,字仲靜,姑存疑)、魏郡內(nèi)史張含亦作詩(shī)(三人詩(shī)皆佚)。陸云《歲暮賦》序:“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zhuǎn)大將軍右司馬于鄴都。”則永寧二年夏陸云為大將軍成都王穎右司馬。陸云有《大將軍宴會(huì)被命作詩(shī)》《答大將軍祭酒顧令文》,顧令文事跡未詳,是時(shí)顧令文為大將軍司馬穎祭酒。二詩(shī)大約亦作于永寧二年夏陸云為大將軍成都王穎右司馬之后。陸云《大(太)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shī)》,王羊二公即太尉王粹和侍中羊玄之,詩(shī)云:“飛驂顧懷,華蟬引領(lǐng)。遺思北京,結(jié)轡臺(tái)省。”正指王、羊二公將離開(kāi)鄴城前往臺(tái)省所在的都城洛陽(yáng)。史載:“及(太安元年十二月司馬)冏敗,穎懸執(zhí)朝政,事無(wú)巨細(xì),皆就鄴咨之。”大約太安二年(303)夏朝廷派王粹、羊玄之到鄴城向成都王穎咨詢政事,王、羊離開(kāi)鄴城前,司馬穎為之餞行,命陸云作是詩(shī)。陸云作《(贈(zèng))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hù)軍》,《六朝詩(shī)集·陸士龍集》詩(shī)題作“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hù)軍”,此后有序“奚世都為汲郡太守,客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遠(yuǎn),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悲)此離析,有感圣皇,既蒙引見(jiàn),又宴于后園,感鹿鳴之宴樂(lè),詠魚(yú)藻之凱歌,而作是詩(shī)”。其實(shí)那個(gè)詩(shī)題只是敘述了張彥明由從事中郎出任中護(hù)軍這一事件,并未概括詩(shī)中之意,不像個(gè)詩(shī)題。而現(xiàn)有序文似乎是說(shuō)奚世都之事,與題中的張彥明事無(wú)關(guān)。《古詩(shī)紀(jì)》卷三六將此序文作為《贈(zèng)汲郡太守》一詩(shī)之序文,一是此前版本中無(wú)此用法,二是序文中提及的宴樂(lè)在《贈(zèng)汲郡太守》一詩(shī)中未提及,倒是在“從事中郎張彥明”一詩(shī)中有述及,則此序文當(dāng)與那首詩(shī)有關(guān)。逯欽立先生以為原本詩(shī)題就是“從事中郎張彥明……而作是詩(shī)”,這首詩(shī)是司馬穎為張、奚二人餞行時(shí),命陸云所作。這樣似乎解決了原來(lái)認(rèn)為是序的那部分與原來(lái)認(rèn)為的詩(shī)題以及詩(shī)歌文本中大多不合的疑惑,但這個(gè)長(zhǎng)題終究不像詩(shī)題,且六朝時(shí)還罕有這樣長(zhǎng)的詩(shī)題。頗疑“從事中郎張彥明……而作是詩(shī)”原是序,流傳過(guò)程中原題失傳,而誤以序文中第一句話為題。大約張彥明、奚世都皆為司馬穎從事中郎,太寧二年張入朝為中護(hù)軍,奚出為汲郡太守,司馬穎在鄴城為之餞行,陸云皆作詩(shī)贈(zèng)別,此為贈(zèng)張彥明之作,張彥明答詩(shī)已佚。逯欽立先生以為“客將之官”當(dāng)為“各將之官”,第一無(wú)版本依據(jù),第二詩(shī)中本有“亹亹我王,豐恩允臧。我客戾止,飲酒公堂”,相對(duì)于司馬穎,臣下是客,亦證序中“客”字本不誤。逯欽立先生又以為序中之“非此離析”當(dāng)為“悲此離析”,意義恰當(dāng),今從之。陸云又作《贈(zèng)汲郡太守》與奚世都贈(zèng)別,詩(shī)中之“念我同僚,悲爾異事”,正指二人同在司馬穎幕僚。奚世都答陸云詩(shī)已佚。六首或贊美晉室及司馬穎之功德,或稱頌顧令文等酬贈(zèng)對(duì)象的才德,皆是重大的、嚴(yán)肅的題材,故使用雅正的四言詩(shī)。
十六國(guó)后趙頓丘人徐光為石勒將王陽(yáng)所掠而曾賦詩(shī)(已佚)。前燕慕容儁也曾在鄴城賦詩(shī)。據(jù)載:“(光壽三年359)燕群臣于蒲池,酒酣,賦詩(shī)(已佚)。”“蒲池,在故鄴城外。燕慕容儁嘗與群臣宴會(huì)于蒲池而賦詩(shī)。”東魏魏收、邢劭、溫子昇皆有《大射賦詩(shī)》,僅有魏收詩(shī)存二句,邢、溫之作皆佚。據(jù)載:“靜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shī),收詩(shī)末云:‘尺書(shū)征建鄴,折簡(jiǎn)召長(zhǎng)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guó)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dá)縱橫,我亦使子才、子升時(shí)有所作,至于詞氣并不及之。’”子才即邢劭,子升即溫子昇,溫子昇卒于武定五年(547),天平元年(534)十月孝靜帝即位是時(shí)已非季秋,故諸詩(shī)約作于天平二年至武定四年間某年行大射禮時(shí)。斛律羨(字豐樂(lè))曾在高歡宴會(huì)上作歌,史載:“北齊高祖嘗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樂(lè),武衛(wèi)斛斯豐樂(lè)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guó)計(jì)無(wú)取次。上曰:豐樂(lè)不諂,是好人也。”高歡卒于武定五年,則是詩(shī)當(dāng)此前。高歡當(dāng)是在東魏都城鄴宴群臣。高昂有《贈(zèng)弟季式》詩(shī)。“(高昂)弟季式為齊(濟(jì))州刺史,敖曹發(fā)驛以勸酒,乃贈(zèng)詩(shī)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wú)可比。走馬海邊射游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shí)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出《談藪》)”,“敖曹(即高昂)創(chuàng)甚曰:‘恨不見(jiàn)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jì)州刺史”。大約天平四年春高季式將上任濟(jì)州刺史,其兄高昂在鄴城作是詩(shī)贈(zèng)別。
東魏武定三年,庾信出使北朝,作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將命至鄴》。祖正員指祖孝隱。“(祖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shí)徐君房、庾信來(lái)聘,名譽(yù)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duì)者多取一時(shí)之秀,盧元景之徒并降級(jí)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曹道衡先生指出,蓋迎梁使時(shí),常使兼正員郎之職,疑孝隱當(dāng)時(shí)兼正員郎,故庾信以祖正員稱之。史載:“(武定)三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則是二詩(shī)武定三年作于鄴城。前一首云:“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塍香穗低。”描寫(xiě)鄴城的歷史及農(nóng)業(yè)之豐收,筆力雄健而蒼涼,這也與鄴城歷史、與北朝風(fēng)物對(duì)這位宮體詩(shī)人的感染有關(guān)。后一首云:“交歡值公子,展禮覿王孫。何以譽(yù)嘉樹(shù),徒欣賦采蘩。四牢盈折俎,三獻(xiàn)滿罍樽。人臣無(wú)境外,何由欣此言。風(fēng)俗既險(xiǎn)阻,山河不復(fù)論。”寫(xiě)了抵達(dá)鄴城后的宴會(huì)場(chǎng)面以及對(duì)南北風(fēng)光、風(fēng)俗不同的感慨。祖孝隱贈(zèng)庾信詩(shī)已佚。庾信作有《西門(mén)豹廟》詩(shī)。據(jù)云:“西門(mén)豹祠,在(鄴)縣西十五里。”詩(shī)云:“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窗臨。鶴飛疑逐舞,魚(yú)驚似聽(tīng)琴。漳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菊花”二句可知該詩(shī)作于秋季。“鶴飛”描寫(xiě)祭祀之樂(lè)舞。“漳流”二句描寫(xiě)漳水及鄴城著名古跡銅雀臺(tái)。庾信兩次到鄴城。大同十一年秋代表梁出使東魏,建德元年秋代表北周出使北齊,西門(mén)豹治水有名于史,庾信有可能首次到鄴城即拜謁其祠,故相較作于大同十一年出使東魏時(shí)可能性更大,且詩(shī)中提及銅雀臺(tái),庾信建德元年到鄴城時(shí),此臺(tái)已改稱金鳳臺(tái),亦證作于武定三年到鄴城時(shí)。徐陵亦曾出使東魏。“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具體出使時(shí)間是武定六年九月。其時(shí)裴讓之為中書(shū)侍郎領(lǐng)舍人,設(shè)宴接待徐陵,裴讓之作有《公館燕酬南使徐陵》。詩(shī)云:“嵩山表京邑,鐘嶺對(duì)江津。方域殊風(fēng)壤,分野居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wú)用忝絲綸。”分別以嵩山和鐘山代指南北兩朝都城之形勝,南北山川風(fēng)物各異,分野不同。絲綸代指詔書(shū),正是裴讓之中書(shū)侍郎領(lǐng)舍人之職正負(fù)責(zé)起草詔書(shū)。詩(shī)又云:“方期飲河朔,翻屬臥漳濱。”鄴城正是在漳水之濱。結(jié)合史料與詩(shī)歌文本,可知裴讓之是詩(shī)作于武定六年九月在鄴城接待梁使徐陵時(shí)。該詩(shī)宏闊雄健,體現(xiàn)北朝風(fēng)骨。徐陵答詩(shī)已佚。同樣出使北朝的荀仲舉有《銅雀臺(tái)》詩(shī)。“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于寒山被執(zhí)。長(zhǎng)樂(lè)王尉粲甚禮之。……入館,除符璽郎。”蕭淵明被執(zhí)是在武定五年十一月,荀仲舉此時(shí)來(lái)到北朝,后入文林館,詩(shī)中寫(xiě)及秋日登臺(tái)、歷史的滄桑及內(nèi)心的凄涼,大約作于初來(lái)北朝時(shí)至鄴城后某年秋參觀銅雀臺(tái)遺址而作是詩(shī),下限在天保九年重修銅雀臺(tái)等三臺(tái)并為之改名前。

裴訥之《鄴館公宴》大約作于天保二年(551)夏四月。其時(shí)梁使者出使北齊,裴訥之參與在鄴城接待梁使,作是詩(shī)。裴訥之天保初為太子舍人,奏中書(shū)舍人事。詩(shī)云:“晉楚敦盟好,喬札同心賞。禮成樽俎陳,樂(lè)和金石響。朝云駕馬進(jìn),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tái)映仙掌。當(dāng)階篁筱密,約岸荷蕖長(zhǎng)。”時(shí)節(jié)正與史載蕭繹派使臣聘齊相合。

魏收《贈(zèng)邢劭》(已佚),邢劭答以《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館》。天保九年八月因?yàn)槿_(tái)作賦,邢劭賦不如魏收之作(魏收事先從中書(shū)郎楊愔處得知作賦事而先有準(zhǔn)備),故邢、魏交惡。此年冬邢、魏二人已不大可能唱和,故是詩(shī)作于天保八年冬。天保八年,魏收為太子少傅時(shí),邢劭任太常卿,二人皆參與校訂秘閣群書(shū),故得以詩(shī)歌唱和。是詩(shī)大約即作于校書(shū)時(shí)。邢詩(shī)鋪敘其年老志衰,稱贊魏收之才,依其表現(xiàn)手法而使用晉以來(lái)日益雅化的古體,而未采用當(dāng)時(shí)已傳入北朝的新興的新體詩(shī)。邢劭還有《三日華林園公宴》詩(shī)作于鄴城。鄴城有華林園,始建于石虎時(shí)。該詩(shī)具體創(chuàng)作時(shí)間未詳。
天保十年十月齊文宣帝去世,盧思道、魏收、陽(yáng)修之、祖珽等作有挽歌,今存盧思道、祖珽之作。據(jù)載:“文宣帝崩,當(dāng)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yáng)休之、祖孝征等不過(guò)得一二首,唯思道獨(dú)得八首。故時(shí)人稱為‘八米盧郎’。”《詩(shī)式》所錄盧思道《齊文宣帝挽歌》約即其中之一。祖珽《挽歌》:“昔日驅(qū)駟馬,謁帝長(zhǎng)楊宮。旌懸白云外,騎獵紅塵中。今來(lái)向漳浦,素蓋轉(zhuǎn)悲風(fēng)。榮華與歌笑,萬(wàn)事盡成空。”據(jù)文意,約即為齊文宣帝所作,齊文宣帝在晉陽(yáng)去世,盧思道等前往晉陽(yáng),后來(lái)文宣帝棺槨又回到鄴城,所以挽歌似乎作于晉陽(yáng)和鄴城皆有可能,但聯(lián)系祖珽挽詩(shī)“今來(lái)向漳浦”則大約挽歌為文宣帝棺槨回鄴城后作。
辛德源曾作《于邢劭座賦詩(shī)》。據(jù)載:“辛德源嘗于邢邵座賦詩(shī),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fēng),春色方依樹(shù)。’眾咸稱善。后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風(fēng),春色依樹(shù)。’”“齊尚書(shū)仆射楊遵彥、殿中尚書(shū)辛術(shù)皆一時(shí)名士,見(jiàn)德源,并虛襟禮敬,因同薦之于文宣帝。起家奉朝請(qǐng),后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楊愔,字遵彥,史載:“(天保三年)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tái)辛術(shù)于廣陵送傳國(guó)璽。甲申,以吏部尚書(shū)楊愔為尚書(shū)右仆射……(天保八年夏四月乙酉),尚書(shū)右仆射楊愔為尚書(shū)左仆射。”天保三年辛術(shù)得傳國(guó)璽,征為殿中尚書(shū),楊愔為尚書(shū)右仆射,則《隋書(shū)·辛德源傳》中的尚書(shū)仆射楊遵彥應(yīng)為尚書(shū)右仆射。辛術(shù)何時(shí)遷為吏部尚書(shū),史書(shū)無(wú)明文記載,天保八年四月楊愔自尚書(shū)右仆射遷尚書(shū)左仆射,大約此時(shí)辛術(shù)自殿中尚書(shū)遷吏部尚書(shū)。則楊、辛二人舉薦辛德源約在天保三年四月至八年四月間。辛德源經(jīng)楊愔推薦入朝,與邢劭相識(shí)。王昕卒于天保十年,則辛德源是詩(shī)約天保三年至十年間作于鄴城,其《羌嫗詩(shī)》,作于為散騎常侍時(shí)。
趙郡李愔作《元日早朝》(已佚),李孝貞有《奉和從叔光祿愔元日早朝》。李孝貞作《陪泛玄洲苑應(yīng)令》,詩(shī)曰:“龍導(dǎo)九河通,鰲負(fù)三山出。聲唱云夔動(dòng),棹發(fā)歌船疾”(大約為殘句),魏收于“河清二年,兼右仆射。時(shí)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shū)畢義云長(zhǎng)于斷割,乃虛心倚仗。……帝于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tái)觀之麗,詔于閣上畫(huà)收,其見(jiàn)重如此”。則玄洲苑大約建于北齊武成帝河清間,應(yīng)太子即武成帝子高緯(后為北齊后主)令所作,河清共三年,天統(tǒng)元年(565)高緯即位,則是詩(shī)當(dāng)作于河清間,李孝貞大約河清三年(564)為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則河清間李孝貞為通直散騎常侍,期間與太子一行游新建之玄洲苑,應(yīng)太子令作是詩(shī)。
盧思道《彭城王挽歌》作于河清三年三月高歡子彭城王高浟遇害之時(shí)。《高浟墓志》諱言其遇害,但言“以河清三年歲次甲申,三月己未朔,薨于鄴都邸舍,春秋卅二”。則盧思道挽歌作于河清三年三月己未(初一)高浟遇害后。散騎侍郎裴澤作《詠石榴詩(shī)》(已佚),武成帝以為詩(shī)中有諷諫之義,乃杖六十,髠頭除名,后主即位,以裴澤為清河郡守,則是詩(shī)約河清間作于鄴城。盧詢祖《趙郡王配鄭氏挽詞》,“嘗為趙郡王妃鄭氏制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nèi),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guó),嬪容映趙宮。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fēng)。遂使叢臺(tái)夜,明月滿床空’”。趙郡王指高歡從子高叡,鄭妃為鄭道昭孫女(鄭述祖女),鄭妃卒,高叡又娶鄭道蔭女。高叡天保元年封趙郡王,天統(tǒng)五年太后指使劉桃枝殺高叡,時(shí)年三十六。則高叡生于天平元年,鄭妃約與其年齡相當(dāng)或略小。據(jù)盧思道《盧記室誄》,盧詢祖卒于天統(tǒng)二年七月,則是詩(shī)當(dāng)作于此前。盧思道《贈(zèng)司馬幼之南聘》,天統(tǒng)三年夏四月司馬幼之出使陳朝前,盧思道在鄴城為之贈(zèng)別作是詩(shī)。詩(shī)云:“故交忽千里,輶車蒞遠(yuǎn)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zhǎng)亭。拂霧揚(yáng)龍節(jié),乘風(fēng)遡鳥(niǎo)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wàn)仞清。夏云樓閣起,秋濤帷蓋生。”“晚霞”四句描寫(xiě)送別時(shí)的景象,清新蕭散。“楚山”“吳江”云云想象司馬幼之到南朝沿途所見(jiàn)。可見(jiàn)“夏云樓閣起”,從描寫(xiě)景物看確實(shí)作于夏季。盧思道還有《贈(zèng)劉儀同西聘》詩(shī),劉儀同即指劉逖。“(劉逖)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guó)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fù),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yù)。使還,拜同三司。世祖崩,出為江州刺史。”北齊世祖即武成帝卒于天統(tǒng)四年十二月,則劉逖西聘是在此前,西聘即指出使北周。“天和三年八月,齊請(qǐng)和親,遣使來(lái)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bào)聘焉。”周武帝天和三年即齊后主天統(tǒng)四年(568),是年八月劉逖出使北周,盧思道在鄴城贈(zèng)以是時(shí)。是年十二月齊武成帝去世,正與《北齊書(shū)》敘述順序合。詩(shī)云:“極野云峰合,遙嶂日輪低。塵暗前旌沒(méi),風(fēng)長(zhǎng)后騎嘶。灞陵行可望,函谷久無(wú)泥。”鋪陳想象劉逖出使路上的景象。灞陵、函谷關(guān)正是指代此行將要前往的關(guān)中。盧思道《美女篇》:“京洛多妖艷,余香愛(ài)物華。恒臨鄧渠水,共采鄴園花。”《城南隅燕》:“城南氣初新,才王邀故人。輕盈云映日,流亂鳥(niǎo)啼春。花飛北寺道,弦散南漳濱。”《河曲游》:“鄴下盛風(fēng)流,河曲有名游。應(yīng)徐托后乘,車馬踐芳洲。”曹丕當(dāng)年的“河曲名游”喻陪某王某次鄴下出游。祝尚書(shū)先生認(rèn)為四詩(shī)寫(xiě)及鄴城繁華,當(dāng)作于鄴城,具體時(shí)間未詳。盧思道《后園宴》為雜言歌行體,設(shè)色艷麗,用典繁密,描寫(xiě)歌舞之樂(lè),歌女之美,似受到南朝宮體之影響。后園當(dāng)即張宴之、魏收詩(shī)中之后園。以上諸詩(shī)風(fēng)貌相似,約同時(shí)期作,約作于北齊中后期。在鄴城盧思道還作有《樂(lè)平長(zhǎng)公主挽歌》,樂(lè)平長(zhǎng)公主大約指北齊武成帝子樂(lè)平王高仁邕女,創(chuàng)作時(shí)間未詳。
傅縡的《贈(zèng)和詩(shī)》和薛道衡《答傅縡》是唱和之作。據(jù)載:“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薛道衡)除尚書(shū)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duì)之。縡贈(zèng)詩(shī)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yú)耳。’”“(武平二年九月)壬申,陳人來(lái)聘。……(武平三年)九月,陳人來(lái)聘。”則薛道衡接對(duì)陳使在武平初為尚書(shū)左外兵郎后,則傅縡贈(zèng)薛道衡詩(shī)及薛道衡和詩(shī)(二詩(shī)皆佚)約在武平二年或三年九月陳譴使聘齊時(shí)。魏收卒于武平三年,故該詩(shī)作于武平二年九月可能性更大。庾信《聘齊秋晚館中丞(飲)酒》,詩(shī)中描述鄴城之景:“漳流鳴二水,日色下三臺(tái)。”二水指清漳、濁漳。天保九年在曹操于鄴城所建三臺(tái)指鄴城西魏武帝曹操所立的銅雀、金虎、冰井三座高臺(tái)舊基的基礎(chǔ)上建成新的三臺(tái),改銅爵(雀)曰金鳳,金獸(虎)曰圣應(yīng),冰井曰崇光。大約武平三年秋庾信聘齊作為對(duì)天和六年齊人聘周的回訪,在鄴城作是詩(shī)。《周書(shū)》《北齊書(shū)》皆未有秋季周使聘齊之記載,是詩(shī)可補(bǔ)史書(shū)之闕。
蕭愨的《秋詩(shī)》和陽(yáng)休之《秋詩(shī)》也是唱和之作。顏之推云:“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于篇什。嘗有《秋詩(shī)》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時(shí)人未之賞也。吾愛(ài)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西魏陷江陵,顏之推被徙關(guān)中,據(jù)其《觀我生賦》,丙子歲即西魏恭帝三年(556),顏之推逃往北齊。據(jù)載:“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guó),武平中太子洗馬。”荀仲舉武定五年冬已來(lái)北朝,諸葛潁亦侯景之亂時(shí)逃亡北齊。荀、蕭、顏、盧皆待詔文林館,得以唱和品評(píng),故蕭愨詩(shī)作于待詔文林館的可能性更大。《古詩(shī)紀(jì)》錄是詩(shī)作“秋思”。陽(yáng)休之亦待詔文林館,有《秋詩(shī)》,大約是與蕭愨唱和之作,這也是《顏氏家訓(xùn)》中蕭愨該詩(shī)詩(shī)題不誤的旁證。蕭愨是詩(shī)依然是南朝風(fēng)格,故顏之推、荀仲舉賞之,而北朝的盧思道則不是很能品味。陽(yáng)辟?gòu)櫋肚锿怼?已佚)、蕭愨《和司徒鎧曹陽(yáng)辟?gòu)櫋辞锿怼怠罚?yáng)辟?gòu)櫈殛?yáng)休之子。“陽(yáng)休之子辟?gòu)櫍淦侥┥袝?shū)水部郎中。辟?gòu)櫺允杳摚瑹o(wú)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shí)人嗤鄙焉。”據(jù)詩(shī)題,陽(yáng)辟?gòu)櫾嗡就芥z曹,可補(bǔ)陽(yáng)休之傳之闕。武平三年設(shè)立文林館,武平共六年,則陽(yáng)辟?gòu)櫞蠹s武平六年轉(zhuǎn)水部郎中。楊訓(xùn)《群公高宴》,武平三至六年間蕭愨與陽(yáng)休之、陽(yáng)辟?gòu)櫟仍谖牧逐^,有機(jī)會(huì)詩(shī)歌唱和,武平三年通直散騎常侍楊訓(xùn)待詔文林館,參撰《修文殿御覽》,諸詩(shī)即作于此間期間。
高延宗有《經(jīng)蘭陵王墓感興》詩(shī)。是詩(shī)見(jiàn)于《蘭陵忠武王碑》之碑陰。據(jù)碑可知北齊蘭陵王名肅,字長(zhǎng)恭,《北齊書(shū)》《北史》本傳中高肅以字行,但言蘭陵王長(zhǎng)恭,而未言其名,碑文可補(bǔ)史志之闕。碑文言高肅武平五年五月十二日,葬于鄴城西北十五里。碑陰載:“武平六年九月□王第三弟太尉公安德王經(jīng)墓興感:夜臺(tái)長(zhǎng)自寂,泉門(mén)無(wú)復(fù)明。獨(dú)有魚(yú)山樹(shù),郁郁向西傾。睹物令人感,目極使魂驚。望碑遙墮淚,軾墓轉(zhuǎn)傷情。軒丘終見(jiàn)毀,千秋空建名。”據(jù)此可知高延宗為蘭陵王高肅弟。高肅及妃鄭氏武平四年五月被后主指使徐之范毒死。蕭愨《尋盧黃門(mén)》:“超忽暮涂遠(yuǎn),放曠神襟清”(《詩(shī)式》卷四),是詩(shī)大約只剩殘句。“(盧)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fā),少以才學(xué)有盛名。武平末,黃門(mén)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574-575)盧思道為黃門(mén)侍郎、蕭愨為太子洗馬,蕭愨是詩(shī)大約此期間作于鄴城。北齊后主末年,時(shí)人戲?yàn)殡s言《郭公歌》,預(yù)料北齊將亡。
孫萬(wàn)壽《行經(jīng)舊國(guó)》詩(shī)曰:“蕭條金闕遠(yuǎn),悵望羈心愁。舊邸成三徑,故園余一丘。庭引田家客,池泛野人舟。日斜山氣冷,風(fēng)近樹(shù)聲秋。弱年陪宴喜,方茲幾獻(xiàn)酬。修竹慚詞賦,叢桂且淹留。自忝無(wú)員職,空貽不調(diào)羞。武騎非其好,還思江漢游。”據(jù)“舊邸”二句則離開(kāi)舊居已較長(zhǎng)時(shí)間。“自忝”二句,正與孫萬(wàn)壽“后歸鄉(xiāng)里,十余年不得調(diào)”相合,孫萬(wàn)壽曾為宇文述行軍總管,大約開(kāi)皇九年(589)隋平陳后,萬(wàn)壽歸鄉(xiāng)里至仁壽初復(fù)出,正是十余年不得調(diào)。故是詩(shī)大約作于開(kāi)皇九年至二十年間某年秋行經(jīng)鄴城時(shí)。元行恭《過(guò)故宅》詩(shī)曰:“頹城百戰(zhàn)后,荒邑四鄰?fù)ā④婈颜郏奖巨D(zhuǎn)窮。吹臺(tái)有山鳥(niǎo),歌庭聒野蟲(chóng)。草深斜徑滅,水盡曲池空。林中滿明月,是處來(lái)春風(fēng)。唯余一廢井,尚夾兩株桐。”“(大象二年六月)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fā)關(guān)中兵,即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率軍討之……(八月)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于鄴城,迥自殺,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陽(yáng),其鄴城及邑居皆毀廢之。分相州陽(yáng)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詩(shī)中所寫(xiě)衰敗之景正與楊堅(jiān)令韋孝寬進(jìn)攻尉遲迥而毀廢鄴城之史實(shí)相合。元行恭在北齊時(shí)待詔文林館,建德六年周武帝滅齊后入關(guān)。大約大象二年(580)八月,元行恭聞鄴城被焚毀而痛心,開(kāi)皇間某年春經(jīng)過(guò)鄴城故居作是詩(shī)。與此詩(shī)類似的還有段君彥的《過(guò)故鄴》詩(shī),詩(shī)曰:“玉馬芝蘭北,金鳳鼓山東。舊國(guó)千門(mén)廢,荒壘四郊通。深潭直有菊,涸井半生桐。粉落妝樓毀,塵飛歌殿空。雖臨玄武觀,不識(shí)紫微宮。年代俄成昔,唯馀風(fēng)月同。”段君彥事跡未詳。詩(shī)中亦寫(xiě)鄴城之衰敗,大約亦開(kāi)皇間某年經(jīng)過(guò)鄴城時(shí)作。釋靈裕《臨終詩(shī)》二首,大業(yè)元年(605)正月于鄴縣演空寺圓寂前作。
(2)魏郡其他地區(qū)
作于魏郡其他地區(qū)的詩(shī)歌,東漢時(shí)期有李朝的《張公神碑歌》等。東漢和平元年(150)朝歌長(zhǎng)潁川鄭郴在黎陽(yáng)一帶撰《張公神碑》碑,碑陰處有歌九章,黎陽(yáng)營(yíng)謁者豫章南昌李朝伯丞作。該詩(shī)為七言與騷體的結(jié)合,詩(shī)中除了頌張公之德外還寫(xiě)及張公墓地祠堂畫(huà)像等。無(wú)名氏《岑熙歌》也作于東漢時(shí)期。岑熙尚漢安帝妹涅陽(yáng)長(zhǎng)公主,為魏郡太守?zé)o為而化,民作歌(四言)贊之。岑熙大約安帝時(shí)為魏郡太守,魏郡治鄴城,是詩(shī)即作于此。
曹丕曾作《(于)黎陽(yáng)作》三首,延康元年(220)六月曹丕親征東吳,經(jīng)過(guò)黎陽(yáng)時(shí)作。詩(shī)中所寫(xiě)是用第一人稱,分明是自己親自出征。“載主而征”是用周武王載著周文王木主出征的典故,指自己繼承曹操遺志,征平天下。史載:“(延康元年)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孫權(quán)遣使奉獻(xiàn)。蜀將孟達(dá)率眾降。武都氐王楊仆率種人內(nèi)附,居漢陽(yáng)郡。甲午,軍次于譙。”又據(jù)載:“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shù)萬(wàn)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余,遷魏郡太守。大軍出征,復(fù)為丞相主簿祭酒。……從至黎陽(yáng),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為豫州刺史。”可知此次南征正是從鄴城出發(fā)經(jīng)過(guò)黎陽(yáng),詩(shī)中“朝發(fā)鄴城,夕宿韓陵”“經(jīng)歷萬(wàn)歲林,行行到黎陽(yáng)”正與從鄴城南征經(jīng)過(guò)黎陽(yáng)相合。四言二首作于初到黎陽(yáng)時(shí)。出征到黎陽(yáng),孫權(quán)示好,蜀將孟達(dá)、武都氐王楊仆歸附,這時(shí)曹丕不準(zhǔn)備征戰(zhàn)了,作五言一首,詩(shī)中“追思大(太)王德,胥宇識(shí)足臧”以古公亶父行仁義使旁國(guó)誠(chéng)心歸附自比。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嗣位為丞相、魏王,領(lǐng)冀州牧,二月葬于曹氏政治中心鄴城之高陵,三月改元延康,十月曹丕受禪,是年六月征東吳時(shí)曹丕還未受禪,曹氏政治中心仍在鄴城,所以他南征自然會(huì)從鄴城出發(fā)。
曹丕《雜詩(shī)》其二“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車蓋。惜哉時(shí)不遇,適與飄風(fēng)會(huì)。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huì)。吳會(huì)非我鄉(xiāng),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fù)陳,客子常畏人”。李善注:《集》云“于黎陽(yáng)作”,呂延濟(jì)注:“此詩(shī)帝未即位,尚為漢行征伐也。”或以為黃初六年冬十月曹丕征東吳,至廣陵望大江而興嘆,作《至廣陵于馬上作》乃還。而《雜詩(shī)》其二中“吳會(huì)非我鄉(xiāng),安得久留滯”正與之相合,故亦作于黃初六年征東吳時(shí)。但結(jié)合“(黃初六年)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筑東巡臺(tái)。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余萬(wàn),旌旗數(shù)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二月,行自譙過(guò)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mén)無(wú)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yáng)宮”,曹丕黃初六年從故鄉(xiāng)譙縣循渦水入淮到徐州,十月至廣陵,十二月又到譙縣,再經(jīng)過(guò)梁,黃初七年正月到許昌而未入城,再向西行回到洛陽(yáng)。則此行從出發(fā)到回程皆不經(jīng)過(guò)遠(yuǎn)在北面的黎陽(yáng),所以是詩(shī)非作于此時(shí)自明。建安十七年曹丕隨曹操南征,孫權(quán)早有備,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無(wú)奈撤軍還,曹丕詩(shī)中“吳會(huì)非我鄉(xiāng),安得久留滯”的遺憾與之正合。濡須水入長(zhǎng)江之口,在今安徽無(wú)為縣東南。對(duì)岸即是江東,與曹丕詩(shī)中吳會(huì)亦合。據(jù)詩(shī)中所述當(dāng)是在離開(kāi)吳地后作,則是詩(shī)約建安十八年春征吳回鄴城經(jīng)黎陽(yáng)時(shí)作。與呂延濟(jì)所說(shuō)為漢行征伐正合。王粲《從軍行》(從軍征遐路)云:“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從軍行》另一首“朝發(fā)鄴都橋,暮濟(jì)白馬津”,可知作于從征東吳經(jīng)白馬津(當(dāng)時(shí)為黃河渡口,在黃河南岸與北岸的黎陽(yáng)津相對(duì),屬兗州之東郡,在今河南滑縣東北)時(shí)。可見(jiàn)直至作“朝發(fā)鄴都橋”一首時(shí)剛渡黃河,故“從軍征遐路”一首大約作于“涼風(fēng)厲秋節(jié)”之后,“朝發(fā)鄴都橋”之前,約建安十九年七月隨曹操征孫權(quán)時(shí)作于鄴城至白馬津渡河之間某地。
劉楨曾在韓陵作詩(shī)。“韓陵山在(安陽(yáng))縣東北二十七里。劉公幹詩(shī)云:‘朝發(fā)白馬,暮宿韓陵。’”白馬縣治今河南安陽(yáng)市滑縣舊縣城東,韓陵在今河南安陽(yáng)市韓陵鎮(zhèn),此地有韓陵山。通過(guò)這兩句可知,此行是由南往北走,韓陵距離鄴城已不遠(yuǎn),是詩(shī)大約是劉楨某次隨曹操出征回鄴城途中經(jīng)過(guò)韓陵作。
2.陽(yáng)平郡
黃初二年分魏郡東部置陽(yáng)平郡,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邯鄲市之館陶縣,山東聊城市之冠縣、辛縣等,治館陶縣(今河北館陶縣)。無(wú)名氏《束皙歌》當(dāng)作于陽(yáng)平郡。據(jù)載,西晉太康間陽(yáng)平元城(今河北大名縣東)人束皙為本郡人求雨,鄉(xiāng)人作雜言詩(shī)贊之。
3.廣平郡
漢武帝時(shí)分巨鹿郡置廣平郡,治廣平(今河北邯鄲市雞澤縣東南),屬冀州。曹魏時(shí)治曲梁(今河北邯鄲市永年區(qū)東南廣府鎮(zhèn)),西晉時(shí)屬司州,仍治廣平縣。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邯鄲市大部(不包括館陶縣、大名縣、魏縣、臨漳縣等)、邢臺(tái)市南部(市區(qū)、任縣、南和區(qū)等)等。
漢無(wú)名氏《陌上桑》當(dāng)作于廣平郡。《樂(lè)府詩(shī)集》引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于陌上,趙王登臺(tái)見(jiàn)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則《陌上桑》約即作于邯鄲(今河北邯鄲市)一帶。
隋孔德紹有《送舍利宿定晉巖》詩(shī)。據(jù)載:“定晉巖在(武安)縣西北八十里,高百余仞,懸?guī)r如蓋,松栢森蔚,下有梵宇層建,風(fēng)雨不能侵。”武安縣,治今河北武安縣。后秦皇初三年(396)在武安建有定晉禪院,大約東魏時(shí)高歡因定晉禪院舊址,更建禪果禪院。則孔德紹大約即送舍利宿于定晉巖禪果禪院。詩(shī)云:“仁祠表虛曠,祇園展肅恭。棲息翠微嶺,登頓白云峰。映流看夜月,臨風(fēng)聽(tīng)曉鐘。澗芳十步草,崖陰百丈松。蕭然遙路絕。無(wú)復(fù)市朝蹤。”描寫(xiě)了定晉巖之險(xiǎn)峻,確實(shí)是“高百余仞,懸?guī)r如蓋”。史載:“會(huì)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shū)令,專典書(shū)檄。及建德敗,伏誅。”大業(yè)十三年竇建德稱王于樂(lè)壽;竇建德五鳳元年(618),孔德紹正為景城丞,已替竇建德出謀劃策;五鳳二年,孔德紹為竇建德內(nèi)史侍郎,是年竇建德攻陷洺州(即隋之武安郡),遷都于此;五鳳四年,竇建都為唐所誅。孔德紹大約陳亡后前往長(zhǎng)安,后出為景城縣丞。景城縣為開(kāi)皇十八年改成平縣置(治今河北滄州市滄縣西)。開(kāi)皇十八年改樂(lè)城為廣城,仁壽元年(601)改廣城為樂(lè)壽(治今河北獻(xiàn)縣)。兩地皆屬隋之河間郡。孔德紹從長(zhǎng)安出發(fā)前往景城(當(dāng)在開(kāi)皇十八年后),亦可能經(jīng)過(guò)武安,但由長(zhǎng)安出為景城丞,不大可能帶著舍利。五鳳二年竇建德遷都洺州(治永年,即原曲梁故城所在,今河北邯鄲市永年區(qū)東南廣府鎮(zhèn)),大約為獲得保佑,特派竇建德到永年?yáng)|部武安(亦屬?zèng)持?著名的定晉巖禪果禪院供奉舍利,孔德紹在定晉巖作是詩(shī)。此詩(shī)創(chuàng)作時(shí)間的下限是竇建德五鳳四年失敗前。
(二)冀州
1.安平郡
西漢文帝十五年(前165)分河間國(guó)地置廣川郡,治信都,景帝二年(前155)改稱國(guó),景帝五年改稱信都郡,此后稱國(guó)稱郡及稱廣川稱信都間多有反復(fù)。東漢永平十五年(72)改信都郡為樂(lè)成國(guó),延光元年(122)改樂(lè)成國(guó)置安平國(guó),中平元年(184)改為安平郡。西晉太康五年改成長(zhǎng)樂(lè)國(guó),仍治信都,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轄邢臺(tái)市之威縣、廣宗縣、新河縣、南宮市以及衡水市之市區(qū)、冀州區(qū)、棗強(qiáng)縣、武邑縣、武強(qiáng)縣等。西漢廣川王劉去有《背尊章》《愁莫愁》二詩(shī),這是現(xiàn)可知較早的河朔詩(shī)。因昭信后譖劉去所幸姬陶望卿,去因此怨望卿,而作歌“背尊章”。后昭信為專寵又譖明貞夫人崔修成,劉去憐之,又作歌一首“愁莫愁”。“(劉去)立二十二年,國(guó)除。后四歲,宣帝地節(jié)四年(66),復(fù)立去兄文,是為戴王。”則劉去征和二年(前91)立為王,本始三年(前71)國(guó)除。其作歌約在劉去為廣川王時(shí)作于廣川國(guó)治所信都(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區(qū)),具體時(shí)期未詳。
2.常山郡
秦時(shí)分邯鄲郡北部置恒山郡,漢文帝時(shí)改稱常山郡,治元氏縣(今河北石家莊元氏縣西北),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轄石家莊市中西部(不包括石家莊藁城區(qū)、無(wú)極縣、晉州市、深澤縣、辛集市等)、保定市之阜平縣、曲陽(yáng)縣等。曹魏時(shí)治真定縣(今河北石家莊市正定縣西南),西晉時(shí)亦治于是。
東漢崔骃有《北巡頌》附有騷體歌。據(jù)序是元和三年春北巡時(shí)至北岳作該頌。至北岳是元和三年二月。漢至明祭祀之北岳恒山又稱大茂山,此地有北岳廟(在今河北保定市曲陽(yáng)縣西北),清順治中移祀北岳恒山于太岳山(即今恒山,在山西大同市渾源縣)。漢時(shí)避文帝劉恒諱,改稱常山。是詩(shī)約即元和三年(86)二月作于常山一帶。
3.河間郡
河間郡始置于西漢,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滄州市西部(任丘市、河間市、獻(xiàn)縣、泊頭市)、保定市之雄縣。治樂(lè)成,今河北獻(xiàn)縣東。東漢張衡《四愁詩(shī)》亦是著名的河朔詩(shī),《文選》該詩(shī)李善注已據(jù)《后漢書(shū)·張衡傳》指出張衡順帝初復(fù)為太史令,陽(yáng)嘉元年造候風(fēng)地動(dòng)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詩(shī)序誤為陽(yáng)嘉中。陽(yáng)嘉間張衡正在太史令任上。崔瑗作有《河間相張平子誄》,則張衡永和四年卒于河間相任上,是詩(shī)約永和元年(136)至四年間作于河間,河間郡治樂(lè)成(今河北獻(xiàn)縣東)。
4.渤海郡
渤海郡轄境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滄州市東南部(滄州市區(qū)、南皮縣、東光縣、吳橋縣)、山東德州市之樂(lè)陵市、慶云縣。曹丕有《于清河作》、徐幹有《于清河見(jiàn)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二詩(shī)作于此地。二詩(shī)皆寫(xiě)男女別離,咸以愿如鳥(niǎo)兒成雙作結(jié),曹詩(shī)“愿為晨風(fēng)鳥(niǎo),雙飛翔北林”,徐詩(shī)“愿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亦證二詩(shī)同時(shí)作。如果同一人作內(nèi)容相似的二詩(shī),采用同樣的結(jié)句,意義不大,亦是第二首為徐幹作的內(nèi)證。二詩(shī)皆為樂(lè)府詩(shī)風(fēng)格,從公宴詩(shī)創(chuàng)作即可知,曹丕及其文士集團(tuán)有同題賦詩(shī)的好尚。徐幹此詩(shī)不僅有與曹丕同題作詩(shī)的特點(diǎn),從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上看,已有和曹丕詩(shī)的性質(zhì),盡管當(dāng)時(shí)還罕有唱和詩(shī)。建安二十年曹丕在孟津作《與吳質(zhì)書(shū)》,文中言及昔日有南皮之游,清河正流經(jīng)南皮(今河北南皮縣北),大約曹丕一行南皮之游時(shí)亦曾游清河而作詩(shī),徐幹詩(shī)中有較多秋景描寫(xiě),則此行約在秋季。
5.博陵郡
漢桓帝延熹元年分中山郡置博陵郡以奉其父孝崇皇園陵,西晉時(shí)分博陵郡北部置高陽(yáng)國(guó),此后博陵郡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轄保定市之安國(guó)市以及衡水市之安平縣、饒陽(yáng)縣、深州市,石家莊市之深澤縣等,治安平縣(今河北衡水市安平縣)。
張華有《博陵王宮俠曲》二首,博陵王及此曲當(dāng)與張華岳父劉放家族有關(guān)。詩(shī)中描寫(xiě)游俠與亦作于早年的《游獵篇》《壯士篇》等題材類似,當(dāng)為同時(shí)期作品,或許博陵王亦有燕趙之地慷慨悲歌之氣。東漢建武十八年徙趙王珪為博陵王,“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yáng)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guó)。十三年,降為趙公……(良七世孫珪)建武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侯”。劉珪為劉良七世、孫第八代趙王,徙封博陵王。張華岳父魏方城侯涿郡劉放為漢廣陽(yáng)順王子西鄉(xiāng)侯宏后,《后漢書(shū)·趙孝王良傳》中,劉良及其繼任趙王之子孫未有謚號(hào)為“順”者,劉宏為良曾孫,宏繼任趙王,并非封西鄉(xiāng)侯,宏之父趙王商謚號(hào)為頃而非順,且先祖已有名宏者,劉放父如果為廣陽(yáng)王子孫不大會(huì)再名宏。劉良早已遷趙王,其后代代皆為趙王,假使劉放父為劉良后世子孫,但已早無(wú)廣陽(yáng)之概念,何有仍稱其為廣陽(yáng)王后之理,如果劉放之父為劉良之子倒還有點(diǎn)稱廣安王之理,畢竟良初封廣陽(yáng)王,且其子直接繼承良之爵,時(shí)代亦近還有稱廣陽(yáng)王子的由頭,但從年齡上放父就不可能是良子。劉放似非劉良子孫。據(jù)載:“(本始元年,前73)秋七月,詔立燕剌王(旦)太子建為廣陽(yáng)王。”“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yáng)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shí),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dú)以獻(xiàn)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初元五年(前44)六月封廣陽(yáng)頃王子容為西鄉(xiāng)侯,廣陽(yáng)王建為漢武帝孫、燕王旦之子。廣陽(yáng)王建及其后并無(wú)謚號(hào)為順者,則《三國(guó)志·魏書(shū)·劉放傳》之“順王”約為“頃王”之誤,“西鄉(xiāng)侯宏”約為“西鄉(xiāng)侯容”之誤。涿郡一帶正有西鄉(xiāng)侯國(guó)(治今河北涿州市西北),劉放為涿郡人,則劉放約即西漢廣陽(yáng)王建子西鄉(xiāng)侯容之后。劉放與博陵王珪并無(wú)直接關(guān)系。但博陵王宮畢竟為著名遺跡,又臨近張華故鄉(xiāng),其早年在故鄉(xiāng)時(shí)當(dāng)會(huì)前往參觀并作詩(shī)。
6.趙郡
趙郡始置于漢,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石家莊市之元氏縣、贊皇縣、趙縣、高邑縣等,以及邢臺(tái)市之臨城縣、內(nèi)丘縣等。北魏李謐《神士賦歌》當(dāng)時(shí)在趙郡之作。據(jù)載,趙郡李謐終生未仕,則其當(dāng)居于故鄉(xiāng)趙郡(北魏時(shí)治平棘,今河北趙縣),作有《神士賦》(已佚),唯賦中之歌賴《魏書(shū)》本傳所錄得以保存,李謐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該詩(shī)歌描述頌了隱士?jī)?yōu)游卒歲的生活。《神士賦》應(yīng)作于李謐故鄉(xiāng)趙郡。東魏《凝禪寺三級(jí)浮圖碑》中有元氏縣(今河北元氏縣)居士趙融詩(shī)作:“蟝螻無(wú)夕命,椿柯亦雕零。神飄生滅境,如雀飛空瓶。”該碑立于元象二年(539)二月,出土于今河北元氏縣,該詩(shī)至晚是年初作于元氏縣。
(三)幽州
1.范陽(yáng)國(guó)(涿郡)
漢置涿郡,曹魏時(shí)改稱范陽(yáng)郡,西晉時(shí)稱范陽(yáng)國(guó),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保定市北部(涿州市、淶水縣、易縣、高碑店市、定興縣、容城縣、徐水區(qū)等)、廊坊市西北(固安縣、永清縣)、北京市房山區(qū)等,治涿縣(河北涿州市)。
東漢末靈帝時(shí)范陽(yáng)人酈炎在其家鄉(xiāng)作《見(jiàn)志詩(shī)》二首。酈炎卒于熹平六年(177),時(shí)年二十八,則其生于和平元年(150),劉躍進(jìn)先生以詩(shī)中“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yuǎn)投荊南沙”,認(rèn)為是以賈誼二十四歲為長(zhǎng)沙王太傅自比。以賈誼出為長(zhǎng)沙王太傅之年來(lái)考證酈炎該詩(shī)的作年有一定道理,酈炎一生未仕,則其居于家鄉(xiāng)范陽(yáng),故是詩(shī)約熹平二年酈炎二十四歲時(shí)作于范陽(yáng)。張華早年在故鄉(xiāng)范陽(yáng)方城(治今河北固安縣西南)一帶作有詩(shī)篇。《感婚詩(shī)》作于嘉平元年(249)在方城與劉放女結(jié)婚結(jié)婚時(shí)。《游獵篇》《壯士篇》表現(xiàn)年輕時(shí)之俠義精神,大約婚前或婚后作于故鄉(xiāng)。《勵(lì)志詩(shī)》作于早年游俠之后認(rèn)識(shí)到進(jìn)德修業(yè)重要性之時(shí),則約亦作于早年在故鄉(xiāng)時(shí)。無(wú)名氏《消腸酒歌》,《拾遺記》卷九:“張華為九醞酒……俗謂之‘消腸酒’……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大約早年在故鄉(xiāng)范陽(yáng)時(shí),張華為九醞酒,閭里因之作歌。
盧思道《仰贈(zèng)特進(jìn)陽(yáng)休之》序云:“夫士之在俗,所以騰聲邁實(shí),郁為時(shí)宗者,厥途有三焉,才也、位也、年也。……特進(jìn)陽(yáng)公兼而有之矣。大齊武平之五載,抗表懸車,難進(jìn)之風(fēng),首振頹俗,余不勝嘉仰,敬贈(zèng)是詩(shī)。”則是詩(shī)作于陽(yáng)休之請(qǐng)求致仕時(shí)。史載:“(武平)三年,(陽(yáng)休之)加特進(jìn)。五年,正中書(shū)監(jiān),余并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yōu)答不許。”則是詩(shī)武平五年(574)作于鄴城。該詩(shī)歌頌陽(yáng)休之才德,內(nèi)容正式嚴(yán)肅,使用雅正的四言體。盧思道還曾在故鄉(xiāng)幽州一帶作詩(shī)。據(jù)載:“后漏泄省中語(yǔ),出為丞相西合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后以擅用庫(kù)錢(qián),免歸于家。嘗于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shī)以見(jiàn)意,人以為工。數(shù)年,復(fù)為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mén)侍郎,待詔文林館。”盧思道大約天統(tǒng)三年(567)免歸于家,至武平二年(571)復(fù)為京畿主簿,此期間居于范陽(yáng)家鄉(xiāng),作有詠懷之詩(shī)(已佚)。
2.燕國(guó)
秦置廣陽(yáng)郡,治薊縣(今北京城西南),西漢時(shí)或稱廣陽(yáng)或稱燕,東漢時(shí)稱廣陽(yáng)郡(國(guó)),魏時(shí)稱燕國(guó),西晉時(shí)漁陽(yáng)郡并入燕國(guó),燕國(guó)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北京市大部、天津市大部、河北省廊坊市北部(市區(qū)、大廠縣、香河縣等)等。
無(wú)名氏《張君歌》是較早的燕國(guó)詩(shī)作。東漢建武間張堪為漁陽(yáng)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漢時(shí)漁陽(yáng)郡治漁陽(yáng)縣(今北京密云區(qū)西南),西晉時(shí)并入燕國(guó)。曹丕《燕歌行》二首,建安十二年(207)曹丕隨曹操出征烏桓,此詩(shī)當(dāng)作于此時(shí)。《樂(lè)府解題》曰:“晉樂(lè)奏魏文帝‘秋風(fēng)’‘別日’二曲,言時(shí)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wú)可訴也。《廣題》曰: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于燕,而為此曲。”大約隨曹操出征烏桓途中有感于征人之苦、思婦之怨并受幽燕之歌影響,而作二詩(shī)。同樣的此地之作,毌丘儉有《在幽州》。魏青龍四年至正始九年毌丘儉為幽州刺史,期間作是詩(shī)(僅剩殘句),曹魏時(shí)幽州治薊縣。
西晉末劉琨、盧諶曾在薊縣一帶作詩(shī)贈(zèng)答。建興三年(315)拜劉琨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建興四年十一月劉琨為石勒所敗,十二月奔薊,依幽州刺史段匹磾。劉琨外甥盧諶為段匹磾別駕,盧諶作《贈(zèng)劉琨》,劉琨作《答盧諶》以答。盧諶詩(shī)中云:“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lái)牧幽都,濟(jì)厥涂炭。涂炭既濟(jì),寇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正指段匹磾為幽州刺史,盧諶為其別駕。盧詩(shī)中表達(dá)對(duì)劉琨與段匹磾聯(lián)合復(fù)興晉室的期望。劉琨答詩(shī)表達(dá)深廣的幽憤以及匡復(fù)晉室的希冀,題材重大,皆使用雅正的四言體。劉琨早年為賈謐二十四友之一,深受玄學(xué)清談?dòng)绊懀c《與盧諶書(shū)》中所云“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yuǎn)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相印證。但在經(jīng)歷了永嘉之變家國(guó)喪亂之后,劉琨有深深的黍離之慨。劉琨《重贈(zèng)盧諶》,太興元年(318)劉琨為段匹磾所拘作是詩(shī)。詩(shī)中多用典故,以含蓄的筆法表現(xiàn)了未能復(fù)興晉室卻為段匹磾所害身陷囹圄的憤恨,同時(shí)隱含著對(duì)盧諶匡扶晉室的期望。“琨詩(shī)托意非常,攄暢幽憤,遠(yuǎn)想張陳,感鴻門(mén)、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zé)o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shī)贈(zèng)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陸侃如先生以為盧諶《重贈(zèng)劉琨》《答劉琨》二詩(shī),與琨被拘事無(wú)甚關(guān)系,也許即所謂“常詞酬和”;不過(guò)都有闕文,所以不能遽下斷語(yǔ)。要之,《重贈(zèng)劉琨》“璧由識(shí)者顯,龍因慶云翔。茨棘非所憩,翰飛游高岡。余音非九韶,何以儀鳳凰。新城非芝圃,曷由殖蘭芳”及《答劉琨》“隨寶產(chǎn)漢濱,摛此夜光真。不待卞和顯,自為命世珍”二詩(shī)大約僅剩殘句,由目前所存文本看皆表現(xiàn)對(duì)劉琨知遇之恩的感謝,意思正與盧諶《贈(zèng)劉琨》中“妙哉蔓葛,得托樛木。葉不云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zhì)非荊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騄”之義相似,故二詩(shī)約作于在幽州時(shí)。盧諶《答魏子悌》,詩(shī)云:“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豈謂鄉(xiāng)曲譽(yù),謬充本州役。”《文選》卷二五該詩(shī)呂向注:“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諶同官。”呂向注又云:“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諶、悌往伐之,為賊所敗,奔安次,故云同險(xiǎn)易。”李善注:“王隱《晉書(shū)》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闊遠(yuǎn),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hù)匈奴中郎將,別領(lǐng)戶。’然時(shí)段匹磾為此職,諶在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shū)》曰:‘石勒攻樂(lè)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shù)遣信要琨,欲與同獎(jiǎng)王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jiàn)之,甚相崇重,與琨結(jié)婚,約為兄弟。”結(jié)合上述材料,劉琨是從飛狐口經(jīng)安次前往薊縣的。“飛狐縣,本漢廣昌縣地,屬代郡,后漢屬中山國(guó),晉又屬代郡。……飛狐道,自縣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即古飛狐口也。酈食其說(shuō)漢王曰‘杜白馬之津,塞飛狐之口’此言皆一方之阨也。又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亦謂此道也。”飛狐口在河北張家口市蔚縣東南宋家莊鎮(zhèn)恒山峽谷口北,是太行山脈與燕山山脈、恒山山脈的交界處,是華北平原出入邊郡的交通要道。安次縣在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區(qū)古縣村,西晉時(shí)屬于燕國(guó),正位于自飛狐口至薊縣的途中。“恩由”兩句指共經(jīng)厄難之間恩義更深。“本州役”正指是時(shí)盧諶已為段匹磾別駕。可知是詩(shī)即作于建興四年投奔段匹磾后作于薊縣。魏子悌原詩(shī)已佚。
3.遼西郡
遼西郡始置于秦,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河北省秦皇島市南部(即不包括北部之青龍縣)、唐山市一部分(遷安市、遷西縣、灤州市、灤南縣、樂(lè)亭縣等),以及遼寧省葫蘆島市之綏中縣西部臨近河北之一角。建安十二年曹操征烏桓歸途中作《步出夏門(mén)行》,艷曰:“經(jīng)過(guò)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可知該曲最初作于碣石山望海時(shí),碣石山在幽州的遼西郡,在今河北昌黎,此處東海指渤海。詩(shī)共四解,約非一時(shí)間完成,一解《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sh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fēng)蕭瑟,洪波涌起”,約作于是年秋,為現(xiàn)可知較早描寫(xiě)渤海的詩(shī)歌。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都描寫(xiě)河朔的冬日祁寒,約作于是年冬。四解《龜雖壽》“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歲末亦聯(lián)想到人之暮年,約作于是年冬十二月。曹植《泰山梁甫行》寫(xiě)及冀東邊海地區(qū)民眾生活之苦難,則曹植從曹操征烏桓,該詩(shī)與曹操《步出夏門(mén)行》同時(shí)期作。
(四)平州
1.遼東郡
西晉時(shí)轄境大致相當(dāng)于今遼寧省轄大連市、營(yíng)口市大部、鞍山市大部、遼陽(yáng)市大部、本溪市西部(市區(qū)、本溪縣等)、丹東市(市區(qū)、東港市、鳳城市等)等。治襄平(今遼寧遼陽(yáng)市)。大業(yè)八年四月,煬帝北征,六月至遼東,圍遼東時(shí)隋煬帝及王胄皆作有《紀(jì)遼東》抒發(fā)豪情。無(wú)名氏《長(zhǎng)白山歌》,征遼東時(shí),來(lái)護(hù)兒及其子來(lái)整并善戰(zhàn),當(dāng)?shù)厝烁柙唬骸伴L(zhǎng)白山頭百戰(zhàn)場(chǎng),十十五五把長(zhǎng)槍,不畏官軍十萬(wàn)眾,只畏榮公第六郎。”榮公第六郎正指來(lái)整。在征遼東過(guò)程中,高麗將乙支文德作《遺于仲文詩(shī)》。
二、漢晉北朝河朔詩(shī)的特點(diǎn)

漢晉河朔詩(shī)現(xiàn)可知約81首,現(xiàn)存76首。其中作于鄴城者現(xiàn)可知約43首,現(xiàn)存38首。建安時(shí)期曹操父子及其文學(xué)侍從的創(chuàng)作是河朔詩(shī)歌的第一個(gè)高峰。建安詩(shī)歌主要有征戰(zhàn)、詠懷、公宴、贈(zèng)答、應(yīng)詔等題材。酈炎《見(jiàn)志詩(shī)》以五言詩(shī)述懷,是較早的五言述志詩(shī),提升了五言俗調(diào)的品格。曹氏父子的鄴城詩(shī)以游宴為主,游宴作品往往騁才爭(zhēng)勝,是文人五言詩(shī)技法提高的第一個(gè)重要階段。葛曉音先生指出:“漢魏詩(shī)題材中招隱、公宴、行役對(duì)山水詩(shī)形成有直接影響……建安時(shí)期公宴詩(shī)是最早以山水為審美對(duì)象的詩(shī)篇,寫(xiě)景由比興言志轉(zhuǎn)為觀賞暢情,是山水詩(shī)形成的一個(gè)重要契機(jī)。”其中公宴詩(shī)主要集中在河朔地區(qū),而行役之作也有一部分作于河朔。如上文所引曹丕《芙蓉池作》、劉楨《公宴詩(shī)》、王粲《雜詩(shī)》等已有比較純粹的景物描寫(xiě)。鄴城作為曹氏集圖的政治中心,建有園林池沼,西園等即是曹丕曹植即其文學(xué)侍從重要的宴集地,宴集活動(dòng)中推動(dòng)了游宴之作的興盛。鄴城是公宴詩(shī)的成熟地,公宴詩(shī)的成熟,又對(duì)山水詩(shī)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動(dòng)作用。曹丕、曹植兄弟及其文學(xué)侍從以游宴等為主的鄴城詩(shī)歌創(chuàng)作,大約是五言詩(shī)第一次成為騁才的載體,詩(shī)歌漸重對(duì)偶等技巧,這是文人五言詩(shī)技法提高的第一個(gè)重要階段。而曹植《名都篇》等描寫(xiě)了鄴城的繁華,對(duì)后世的都城之作有啟發(fā)性。這類詩(shī)歌與鄴城游宴之作,共同體現(xiàn)的鄴城的繁盛。贈(zèng)答、感懷亦是建安鄴城詩(shī)的重要題材。如果說(shuō)游宴之作是提升了詩(shī)歌的表現(xiàn)技巧,則贈(zèng)答、感懷之作多抒發(fā)私人化的情感,鄴城文學(xué)正是建安文學(xué)實(shí)現(xiàn)自覺(jué)的重要實(shí)踐場(chǎng)。
公宴之作中的寫(xiě)景更多的是描寫(xiě)人工的園林,行役之作中的寫(xiě)景則主要是自然山川。河朔地區(qū)亦有較多行役之作中提及山水,曹操《觀滄海》,描寫(xiě)登碣石山觀渤海所見(jiàn),雖受四言體以及曹操本人創(chuàng)作特點(diǎn)的限制,用的是簡(jiǎn)筆描繪,但也已是純粹的山水描寫(xiě)。該詩(shī)是較早描繪大海的詩(shī)作,僅此一篇已可奠定河朔行役詩(shī)的地位,與公宴詩(shī)從不同的寫(xiě)景角度對(duì)山水詩(shī)的最終形成起推動(dòng)作用。曹操《冬十月》《土不同》《河朔寒》則不僅通過(guò)行役中所見(jiàn)山川、動(dòng)植物等景物描寫(xiě)河朔冬日祁寒,還從農(nóng)人、商賈、貧士、俠客等社會(huì)生活方面體現(xiàn)河朔冬日下各類人的生活,是較早描繪河朔自然和社會(huì)生活的詩(shī)篇。曹丕《于黎陽(yáng)作》三首、王粲《從軍行》分別描繪從軍南行時(shí)經(jīng)過(guò)華北平原之所見(jiàn),由于是戰(zhàn)亂年代,更多顯現(xiàn)的是凋敝和民生的凄苦,也表現(xiàn)建功立業(yè)的豪情,體現(xiàn)了慷慨悲歌之氣。
北朝(包括十六國(guó))河朔詩(shī)約74首,現(xiàn)存49首。其中現(xiàn)可知鄴城詩(shī)約65首,現(xiàn)存43首。東魏、北齊定都鄴城是河朔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第二個(gè)高峰期。現(xiàn)存北朝河朔詩(shī)中,除去1首七言詩(shī)、1首四言詩(shī)、5首雜言詩(shī),五言詩(shī)現(xiàn)存36首,十句以上者18首。為了更好說(shuō)明北朝詩(shī)人對(duì)詩(shī)歌體式的選取,此處僅以北朝本土詩(shī)人在河朔的創(chuàng)作為例。篇幅較長(zhǎng)的有裴讓之《公館燕酬南使徐陵》(24句),邢劭《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館》(30句),李騫《贈(zèng)親友》(24句),盧思道《贈(zèng)司馬幼之南聘》(16句)、《贈(zèng)劉儀同西聘》(16句)等,大多作于東魏北齊時(shí),可知該時(shí)期河朔詩(shī)歌尤以繼承晉之五古為多。隨著南北交流,新體風(fēng)格詩(shī)雖有增多,但總的來(lái)說(shuō)河朔詩(shī)中北朝本土詩(shī)人所作的標(biāo)準(zhǔn)新體詩(shī)還較少。一些十二、十四句的次長(zhǎng)篇雖然形式上有新體的影子,但在表現(xiàn)手法上仍是古體的鋪敘。如邢劭《三日華林園公宴》:“回鑾自樂(lè)野,弭蓋屬瑤池。五丞接光景,七友樹(shù)風(fēng)儀。芳春時(shí)欲遽,覽物惜將移。新萍已冒沼,余花尚滿枝。草滋徑蕪沒(méi),林長(zhǎng)山蔽虧。方筵羅玉俎,激水漾金卮。歌聲斷以續(xù),舞袖合還離。”其聲律等形式雖略受新體影響,但仍保留古體鋪陳的描述手法。以新體詩(shī)常見(jiàn)的十句以下押平聲韻為特征的體式為例(姑不論黏對(duì)),北朝本土詩(shī)人河朔詩(shī)大致合乎標(biāo)準(zhǔn)的僅有楊訓(xùn)一首(10句)、高延宗一首(10句)、孔德紹一首(10句)、趙融一首(4句)、釋靈裕二首(4句)、盧思道一首(4句)。
北朝鄴城詩(shī)主要有朝聘會(huì)盟、感懷、游覽等題材。東魏北齊時(shí)期鄴城再次成為政治文化中心,公宴詩(shī)再次繁盛,且不像建安游宴詩(shī)以寫(xiě)園林池沼為多,鄴城時(shí)期的游宴詩(shī),游宴范圍擴(kuò)大,多為城內(nèi)和附近的游覽,這或許與東魏北齊時(shí)期鄴城規(guī)模的擴(kuò)大亦有關(guān)。部分詩(shī)好以曹氏鄴城一帶游宴類比實(shí)際的北齊諸王鄴城游宴,如盧思道《河曲游》《城南隅燕》等,這除了是一種創(chuàng)作技法,也顯現(xiàn)出時(shí)人是以建安時(shí)的鄴城及游宴作詩(shī)等風(fēng)雅活動(dòng)等娛樂(lè)為其心中的理想,北齊在曹魏原址基礎(chǔ)上重建三臺(tái),也是這類心理和文化認(rèn)知的體現(xiàn)。由于南北朝后期南北交流更為頻繁,鄴城游宴之作融入了都城元素,增加了會(huì)盟題材,如裴訥之《鄴館公燕》、裴讓之《公館燕酬南使徐陵》述及朝聘宴會(huì)場(chǎng)景及鄴城景象。當(dāng)然東魏北齊時(shí)期的朝聘描繪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游宴詩(shī)中,盧思道詩(shī)贈(zèng)別南聘的司馬幼之、聘周的劉逖,雖為贈(zèng)別之作,內(nèi)容亦與朝聘題材相關(guān)。朝聘會(huì)盟題材重且需鋪敘出使所見(jiàn)及外交場(chǎng)面,故多使用晉宋五古。
河朔詩(shī)歌對(duì)詩(shī)歌體式的探索多有貢獻(xiàn)。建安河朔詩(shī)歌中有對(duì)四言詩(shī)體式的探索。葛曉音先生指出嵇康利用《詩(shī)經(jīng)》的典型句式,找出一種以排比對(duì)偶相結(jié)合的句序,即兩行隔句相同的句子排比,再加一組對(duì)偶的固定程序,如四言《贈(zèng)兄秀才入軍詩(shī)》十八章中其十一:“雖有好音,誰(shuí)與清歌,雖有姝顏,誰(shuí)與發(fā)華。仰訊高云,俯托輕波。”這種句序在民歌中就存在,嵇康大約也是受民歌的啟發(fā)。曹丕的河朔詩(shī)《于黎陽(yáng)作》第三首“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仆夫,載仆載僵。蒙涂冒雨,沾衣濡裳”亦是這樣的句式,曹丕的詩(shī)歌多有民歌之風(fēng),或許亦受到民歌影響。
河朔詩(shī)歌對(duì)七言詩(shī)的開(kāi)拓亦有一定貢獻(xiàn)。張衡《四愁詩(shī)》是第一首初具七言形式的詩(shī)歌。曹丕《燕歌行》為現(xiàn)存較早的完整的七言詩(shī),句句押韻,則河朔是七言詩(shī)成型之地。高昂七言詩(shī)《贈(zèng)弟季式》和溫子昇《搗衣詩(shī)》是現(xiàn)可知十六國(guó)北朝較早的隔句押韻的七言詩(shī),雖然難以判斷高詩(shī)與溫詩(shī)孰先以及溫詩(shī)創(chuàng)作地,但是高詩(shī)作于河朔,至少說(shuō)明河朔地區(qū)是七言詩(shī)押韻體轉(zhuǎn)型的重要實(shí)踐地。
河朔詩(shī)歌對(duì)雜言詩(shī)的發(fā)展亦有一定功勞。如盧思道《后園宴》:“嘗聞昆閬有神仙,云冠羽佩得長(zhǎng)年。秋夕風(fēng)動(dòng)三珠樹(shù),春朝露濕九芝田。不如鄴城佳麗所,玉樓銀閣與天連。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樹(shù)百枝燃。流風(fēng)續(xù)洛渚,行云在南楚。可憐白水神,可念青樓女。便妍不羞澀,妖艷工言語(yǔ)。池苑正芳菲,得戲不知?dú)w。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纖腰如欲斷,側(cè)髻似能飛。南樓日已暮,長(zhǎng)簷鳥(niǎo)應(yīng)度。竹殿遙聞鳳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攜手傍花叢,徐步入房櫳。欲眠衣先解,半醉臉逾紅。日日相看轉(zhuǎn)難厭,千嬌萬(wàn)態(tài)不知窮。欲積妾心無(wú)劇已,明月流光滿帳中。”此詩(shī)為五七言雜言體。首8句七言用一平聲韻。此后繼之以14句五言,前6句五言用一仄聲韻。此后6句五言轉(zhuǎn)為平聲韻。接下來(lái)2句五言與2句七言共用一韻轉(zhuǎn)為仄聲韻。此后以4句五言、4句七言共用一韻轉(zhuǎn)為平聲韻。每一次轉(zhuǎn)韻,第一句不管是五言還是七言皆入韻,此后隔句押韻。整首詩(shī)32句,四次轉(zhuǎn)韻,即共用了五個(gè)韻部,平仄韻交替,低昂互節(jié),錯(cuò)落有致。隋煬帝《紀(jì)遼東》二首,其一曰:“遼東海北翦長(zhǎng)鯨,風(fēng)云萬(wàn)里清。方當(dāng)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后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wàn)里去,空道五原歸。”其二曰:“秉旄伏節(jié)定遼東,俘馘變夷風(fēng)。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洛陽(yáng)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復(fù)道上,先封雍齒侯。”王胄《紀(jì)遼東》二首,其一曰:“遼東浿水事龔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旋歸樂(lè),為聽(tīng)凱歌聲。十乘元戎才渡遼,扶濊已冰銷。詎似百萬(wàn)臨江水,按轡空回鑣。”其二曰:“天威電邁舉朝鮮,信次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迢迢用一年。鳴鑾詔蹕發(fā)淆潼,舍爵有疇庸。何必豐沛多相識(shí),比屋降堯封。”體式上為一句七言一句五言,4句一轉(zhuǎn)韻。4句中首句七言入韻,此后韻腳皆在五言句上。五言一句往往是對(duì)之前七言一句的解答或具體描述,兩種句式間隔參差錯(cuò)落亦增強(qiáng)了節(jié)奏感。這種體式可能是隋煬帝的創(chuàng)造。
總之,河朔是漢晉北朝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繁盛地之一,該地區(qū)以鄴城為主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對(duì)贈(zèng)答、公宴、詠懷、游覽等題材的繁榮有較大貢獻(xiàn),同時(shí)該地區(qū)創(chuàng)作還促進(jìn)了北方四言、七言等詩(shī)歌體式的革新或進(jìn)步。北朝時(shí)河朔詩(shī)以古體為多,在南北交流中亦受到南朝齊梁新體影響,但影響主要在形式方面,而很少接受其宮體詩(shī)風(fēng),以新的形式融合古體詩(shī)的鋪敘等表現(xiàn)手法,展現(xiàn)河朔詩(shī)人剛健質(zhì)樸的風(fēng)格,為南北詩(shī)風(fēng)的融合,最終產(chǎn)生聲律、風(fēng)骨皆備的唐音作出階段性的貢獻(xiàn)。
三、馀 論
與河洛地區(qū)興盛的深受玄學(xué)影響的新學(xué)不同,河朔地區(qū)保留了漢儒舊學(xué)傳統(tǒng)。此地本有經(jīng)學(xué)傳統(tǒng),三家詩(shī)中的韓詩(shī)(《韓詩(shī)》作者韓嬰為燕人)和傳毛詩(shī)的漢河間獻(xiàn)王博士毛萇(趙人)、春秋公羊?qū)W大師董仲舒(趙人)、經(jīng)學(xué)大師盧植(燕人)等即為河朔文士。漢代河朔地區(qū)出文士較多的家族大約是安平崔氏。諸多文士奠定了此地淳厚質(zhì)樸的學(xué)術(shù)文化傳統(tǒng)。東漢永平間整治黃河下游河道后,黃河下游河道經(jīng)歷了一個(gè)長(zhǎng)期安流的局面,免于水患,有利于河朔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東漢末袁紹割據(jù)河北,大量士人投奔袁紹,曹操占河北后,亦多所征召幽冀士人。曹氏父子與其僚屬在鄴城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積極推動(dòng)了河朔地區(qū)的文化。漢代河朔地區(qū)所知作詩(shī)者較少,曹操父子與身邊文士在鄴城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這一地區(qū)文學(xué)的第一個(gè)高峰期,為西晉時(shí)期河朔地區(qū)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chǔ)。河朔地區(qū)在西晉北朝時(shí)期主要繼承漢以來(lái)文化傳統(tǒng)。東魏、北齊的鄴城文學(xué)是河朔文學(xué)的第二個(gè)高峰期,鄴城集中了該時(shí)期最著名的詩(shī)人,河朔籍的有邢劭、魏收、李孝貞、盧思道、祖珽等,北朝鄴城詩(shī)受到南朝詩(shī)文體、風(fēng)格等的影響,部分詩(shī)又能在接受新體裁的同時(shí)保留河朔質(zhì)樸貞剛之氣,是南北詩(shī)風(fēng)融合的重要嘗試。
漢晉北朝在河朔作詩(shī)的本土詩(shī)人占河朔詩(shī)作者的約33%,漢晉時(shí)期在河朔作詩(shī)者25人,本土詩(shī)人3位占12%;北朝時(shí)期在河朔作詩(shī)者47人,本土詩(shī)人18位占38%。與之相較,漢晉北朝河淮本土詩(shī)人占河淮詩(shī)作者約46%,漢晉時(shí)期在河淮作詩(shī)者101人,其中54位本土詩(shī)人占53%;北朝時(shí)期在河淮作詩(shī)者約77人,本土詩(shī)人16位占21%,如果不算占籍洛陽(yáng)的8位元氏文士,則本土詩(shī)人只占總數(shù)12%。從漢晉北朝整個(gè)時(shí)段看,河朔詩(shī)歌作者中本土詩(shī)人比例僅次于河淮詩(shī)作者中本土詩(shī)人的比例。這與河朔地區(qū)是僅次于河淮地區(qū)的第二大文化發(fā)達(dá)區(qū)的地位正相合。但將漢晉和北朝兩個(gè)時(shí)期分別比較,則漢晉時(shí)期河朔本土詩(shī)人占詩(shī)人總數(shù)的比例要遠(yuǎn)低于河淮地區(qū),而北朝時(shí)期河朔本土詩(shī)人占詩(shī)人總數(shù)的比例是河淮地區(qū)本土詩(shī)人占詩(shī)人總數(shù)比的一倍多。漢晉時(shí)期以洛陽(yáng)為中心的河淮地區(qū)為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是文化最先成熟發(fā)展的地區(qū),當(dāng)然是詩(shī)人的聚居地,形成一些世家大族。永嘉之亂中河淮文士大都南遷,中原地區(qū)一度文化衰落,北朝中期北魏遷都洛陽(yáng),中原文化逐漸復(fù)興,北朝時(shí)河淮本土文士占比小,一方面是確實(shí)文士大多已南渡,另一方面是洛陽(yáng)作為漢晉舊都,有其文化象征性,北朝中期再為都城,對(duì)文士有吸引力,雖本土文士已少,但各地文士前來(lái)(尤以河朔、河?xùn)|、關(guān)隴籍為多),再度成為文士的聚居地。北朝后期戰(zhàn)亂東魏遷都鄴城,中原再度凋敝。河朔地區(qū)在漢晉時(shí)亦是重要都會(huì),文化已有一定發(fā)展,安平、常山、河間、廣平、范陽(yáng)、燕等郡國(guó)早在漢代已有詩(shī)歌創(chuàng)作,亦產(chǎn)生一些世家大族,但影響力畢竟比不過(guò)文士聚居的都城所在地河淮地區(qū),本土文士在本土創(chuàng)作比自然低于河淮地區(qū)。永嘉之亂中河朔文士大都留居本土,為北方保留傳承了漢晉文化的脈絡(luò),有河朔世族的文化傳統(tǒng),加之東魏遷都鄴城,河朔成為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河朔文化在短期內(nèi)就趨于繁盛,本土文士在本土創(chuàng)作的比例當(dāng)然遠(yuǎn)高于文士主體早已南渡且又再度衰落的河淮地區(qū)。河淮作為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的時(shí)間遠(yuǎn)長(zhǎng)于河朔地區(qū),河朔在短期作為都城的時(shí)代,文化就有如此發(fā)展,考慮這個(gè)因素,河朔地區(qū)文化的厚度其實(shí)不亞于河淮地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