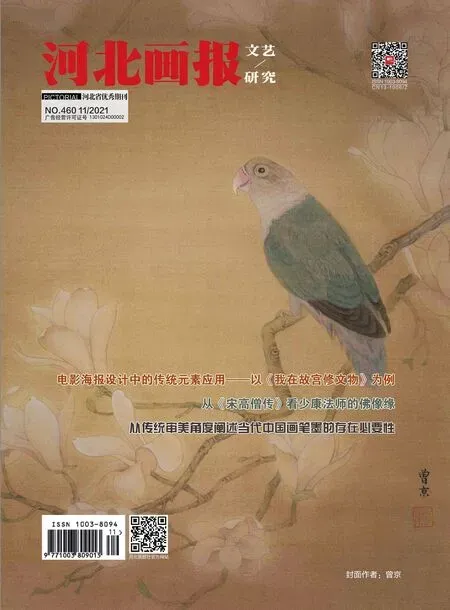當代進化論美學研究述要
宋紅艷
(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進化論美學是運用生物進化論來研究審美和藝術問題的一門新興學科。進化論美學以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和性選擇學說為理論基礎,對于美學基本問題如美和藝術的本質、起源、功能等給出了全新的解釋。它的核心主張是,在人類進化史上,審美和藝術是作為一種適應性行為而產生的,它們的最終功能在于促進個體的生存和生殖成功。[1]
一般認為,進化論美學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進化心理學的出現而誕生并逐漸發展起來的。[2][3]2003年,生物學家Eckart Voland和Karl Grammer主編了《進化論美學》文集,將“進化論美學”這一概念推廣開來。進化論美學的主要研究者是進化心理學家,也有許多美學家、文學理論家參與進來。進化論心理學家主要通過實驗方式開展研究,也有部分進化論心理學家和美學家獨立提出關于藝術的進化適應性假說,例如想象世界說、昂貴信號說等等,另外還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分支是文學達爾文主義。[4]
一、進化論美學的實驗研究
進化論美學大量和專門的研究成果的涌現,主要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進化論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誕生而出現的。其中大部分的研究成果,是由進化論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帶領其研究團隊通過實驗的方式開展。
這些實驗研究傾向于關注人體吸引力和景觀偏好。他們通過實驗力求證明人類先天就具有審美判斷能力。例如,Judith Langlois及其團隊在1987年對于嬰兒注視不同人臉照片時間開展的實驗,他們給6到8個月的嬰兒呈現兩張女性人臉幻燈片,這兩張女性人臉照片已經事先被成年人評定為美和不美的,研究結果發現,嬰兒注視美的女性人臉照片的時間要遠遠長于另外一張照片。[5]人類在嬰兒時期,尚未接受文化及經驗的影響,就已經能夠做出和成年人一致的審美判斷,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人類審美能力的先天性。神經科學家AnjanChatterjee在2009年開展的實驗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給被試呈現不同的人臉照片,要求他們判斷不同照片的人臉相似度,并通過功能性核磁成像技術觀察被試的大腦反應。研究結果發現,即使在被試關注的是人臉照片的其他內容而不是美的時候,與審美反應相關的腦區仍然會被激活。[6]這表明,我們的大腦會自動對美產生反應,審美判斷在某種程度上是先天性的、生物性的。這一類的研究還有許多。
研究人員通過實驗還尋找到了一些普遍客觀的審美標準。在人體美方面,這些標準包括平均性、對稱性、性二態性,相關的實驗有Karl Grammer在1994年對于人臉對稱性吸引力的實驗、Devendra Singh在1993年對于女性腰臀周長比吸引力的實驗等等。[7]這些實驗同時表明,人體美的標準也是健康程度的指標,美和健康是二而一的。在風景美方面,John D.Balling和John H.Falk在1982年開展的實驗表明不同年齡和職業的人對于稀樹草原景觀有一致的本能偏好。[8]稀樹草原是人類祖先誕生的地方,是適宜人類祖先生存和繁衍的環境,這表明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景觀會被認為是美的。
由于這類實驗研究主要是由進化論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開展,不同于傳統的美學家對于美學術語的嚴格使用,他們是在寬泛意義上使用美的概念,并不嚴格區分單純的快感和更為純粹高尚的愉悅。他們在尋找人類審美偏好中普適性的心理模式方面具有積極的貢獻。他們肯定了人類審美能力的先天性,尋找到一些普遍客觀的審美標準,并最終證明審美判斷是一種做出正確適應性決策的適應性行為,美是生存和生殖成功高可能性的承諾。
國內對于西方實驗式進化論美學的研究介紹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郭玉越,他的博士論文《當代西方進化論美學研究》就是對于西方進化論美學實驗研究成果的系統整理,他的其他幾篇論文也都是與此相關,包括《論美感的起源——一種基于達爾文學說的觀點》等等。除此之外,王娟、訾非的《進化美學的起源及其與進化審美心理學的辨析》,朱烜圻的《進化心理美學方法引介——兼論中國傳統審美》等論文,也都對于西方進化論美學的實驗研究做了研究評價。
二、關于審美和藝術的進化適應性假說
除了以團隊實驗方式開展的進化論美學研究之外,還有一些進化論心理學家獨立提出了關于審美和藝術的進化適應假說,其中最為主要的是想象世界說和昂貴信號說。進化論心理學的創始人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2001年發表《美會建立適應心智嗎?邁向美學、小說和藝術的進化》,提出想象世界說,認為藝術是參與虛構和想象世界的能力,在想象世界中可以為以后的生活提供了無風險的實踐。美國進化論心理學家Geoffrey Miller,2001年出版《擇偶心智:性選擇如何塑造人性的進化》,提出昂貴信號說,主張人類的藝術和審美能力是隨著為擇偶服務而被進化的。藝術類似于孔雀的尾巴,是昂貴的信號,展示它們需要力量、活力、智力、技能和創造力,因而藝術是健康的廣告,在進化過程中經由女性選擇而被保存下來。
在進化論美學的研究中,除了進化論心理學家的研究之外,還有不少傳統的美學家參與進來。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Ellen Dissanayake,她分別于1988年、1992年、2000年出版了三本專著(《藝術為了什么》《審美的人》《藝術與親密》),提出使其特殊說,與其他理論家強調藝術隨著個體間競爭而進化不同,她提出藝術隨宗教儀式而進化,藝術具有增強群體凝聚力的功能。1998年,Nancy Aiken出版《藝術的生物學起源》,提出操縱控制說,認為藝術的適應性功能在于操縱與控制他人。美國藝術哲學家Denis Dutton,2010年出版《藝術本能:美、愉悅和人類進化》,認為人類的創造性才能是在更新世進化而來的,講故事能夠使他們不必冒生命危險就解決“如何這樣,結果會怎樣”的問題,同時這種創造性能促進性選擇成功。新西蘭藝術哲學家Stephen Davies在2012年出版的《藝術物種:美學、藝術和進化》中回顧了進化論美學研究中大多數主要參與者的作品,但其本人對于審美和藝術適應性持質疑態度。
國內以生物進化論來研究審美和藝術問題最早見于1986年劉驍純出版的《從動物快感到人的美感》一書,后又有汪濟生1987年的《系統進化論美學觀》、肖世敏2003年的《有動物有美感論——一個大膽的假說》相繼出版。這三本專著討論了動物美感問題、美感所趨方向與進化所在方向問題,但尚未提出完整的審美和藝術適應性假說。魯晨光在2003年出版的《美感奧妙和需求進化》中,提出了需求和美感相互促進模型,認為需求決定美感,合乎需求的就是美的,需求越迫切美感越強烈,美感的意義就是促使人喜愛、接近對象。姜永進在2007年出版的《丑陋的孔雀——人體審美的社會生物學》中,提出美的選擇經歷了從實用到夸張再到實用三層進化過程,審美源于實用,夸張化地美打著實用的幌子獲得與更健康基因結合的機會,從而真的使自己和實用緊緊結合在了一起。除此之外,國內學者郭玉越的《論藝術本能——一種進化論美學的視角》、趙彥芳的《審美的倫理之維——進化論美學的復興和啟示》等論文分別對于Denis Dutton、Ellen Dissanayake等學者的進化論美學思想做了研究介紹。
三、文學達爾文主義研究
在進化論美學研究中,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是文學達爾文主義,主要是由一些文學研究者發起,他們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來解釋文學的起源和目的,并且把進化生物學的概念直接應用于批評理論的建構和對作品的闡釋。文學達爾文主義的首倡者是密蘇里大學圣路易斯分校文學教授Joseph Carroll,他于1995年出版《進化論與文學理論》,2004年出版《文學達爾文主義:進化、人性和文學》,2011年出版《解讀人性:文學達爾文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他豐富和擴充了想象世界說,主張小說的虛構敘事能為現實世界中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提供行為指導,他還著眼于文本批評實踐,運用進化論批評的視角對多部英國經典作品進行重新詮釋。華盛頓與杰斐遜學院英語系研究員Jonathan Gottschall,2005年出版《講故事的動物:故事如何使我們成為人類》。奧克蘭大學文學教授Brian Boyd,2009年出版《故事的起源:進化、認知和小說》。這三位學者是文學達爾文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在2010年合編了文集《進化、文學和電影:一位讀者》。除此之外的研究者還包括,Brett Cooke、Frederick Turner、Robert Storey、Marcus Nordlund、Judith Saunders等人。
國內對文學達爾文主義的研究,最早見于王麗莉和王曉群2007年發表論文《論文學達爾文主義》,此后又有胡怡君的《西方文論關鍵詞文學達爾文主義》、余石屹的《達爾文進化論與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批評》等十數篇論文發表。這些論文主要側重于對西方文學達爾文主義的引進、介紹。還有一類論文側重于進行達爾文主義的文學批評實踐,聶珍釗教授2002年的論文《哈代的小說創作與達爾文主義》是國內進化論批評的開創之作,此后又有王麗莉的《文學達爾文主義與莎士比亞研究》、姜智芹的《文學達爾文主義視野下的〈傲慢與偏見〉》等十數篇碩博學位論文。此外還有不少論文將進化論批評應用于中國經典作品解讀。
四、進化論美學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近四十年來,進化論美學的大量研究成果紛紛涌現。進化論美學是對傳統哲學美學的巨大突破,它們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區別于傳統哲學美學的抽象思辨研究,進化論美學立足于科學的實證研究,以心理學實驗、神經科學實驗、人類學材料為證據支撐。其次,區別于傳統哲學美學把審美當作純粹的精神現象,進化論美學將審美作為精神和身體的復合加以研究,關注人的生物屬性。再次,區別于傳統哲學美學主張的審美無利害,進化論美學力圖突破審美與實用、功能的嚴格界限。
進化論美學是一門正在發展中的學科,它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忽略感官愉悅與美之間的區別、依賴于直覺假設和推測等等[9]。在進化論美學研究中,審美和藝術適應性、審美判斷可變性的原因、美和善的關系等問題也是目前具有爭論性、開發性的問題[10]。進化論美學具有諸多可研究的空間,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