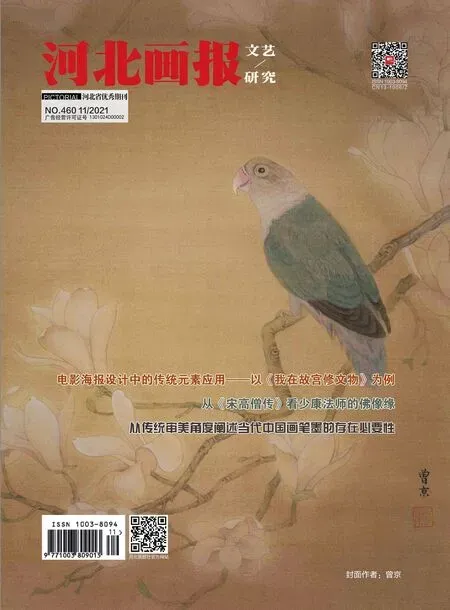維瓦爾第《四季》小提琴協奏曲的美學風格探究
孫萌
(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
《四季》被稱為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珍品,自1752年問世至今,已經成為大眾最喜歡的古典音樂作品之一。它是維瓦爾第結合生命與藝術的感悟寫下的四首協奏曲,“春”“夏”“秋”“冬”四個標題代表著四個季節的景色,也蘊含著深厚的人文價值。
一、《四季》的創作背景
(一)社會背景
維瓦爾第生活在巴洛克時期的威尼斯共和國。在其出生之前,威尼斯已經經歷了千年的發展,積累了深厚的文化與藝術財富。加之作為東西商貿往來的必經之路,其在海上和陸地上還有著廣泛的殖民地,這又使得威尼斯有著富足的社會財富與雄厚的軍事實力。但是,十七世紀末,因為東部土耳其帝國的崛起,威尼斯傳統產業的優勢急劇沒落,政治與經濟的混亂隨之加劇,不得已在1866年解體并入了意大利共和國。曾經的輝煌在并入意大利后,只剩下人文藝術財富,而威尼斯人因為對意大利的政治和外交表現出的漠不關心,使得他們更多地將精力投注到了人文藝術中。在意大利抵御土耳其、奧地利等國家掠奪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矛盾沖突極為強烈的景象,深刻影響了當時藝術與人文的創作旨意。人們把更多美好的情感寄托在藝術作品中,既為了祈求和平,又帶有逃世厭世之意,《四季》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文化背景
威尼斯人對藝術的熱愛是有著淵源的歷史的。上至達官貴族,下至海面漁夫,每一個人都將音樂作為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誠如格羅斯所言:“任何一個穿著工作服的鞋匠或鐵匠哼出的曲調,他的同伴都能準確無誤地與他相和”。人們在音樂中表達情感也接受著心靈的撫慰,重大的祈禱儀式與宗教活動中,音樂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意大利人的音樂修養非常高,為孕育出許多成就非凡的藝術家奠定了基礎。維瓦爾第創作《四季》時,已經年過五十,其對人生的感悟已經成熟,內心也更加的平靜。他把這套作品作為禮物獻給波迪米亞爵士,實際上是當時社會交往的一個重要風俗,再加上制琴工藝的快速發展,讓協奏曲等各種音樂面貌有了展現的平臺,就又足可見得這份禮物的珍貴。
二、《四季》的音樂分析
(一)《春》
《四季》由四首樂曲構成,每一首樂曲包含三個樂章,又都附寫了十四行詩,不僅在當時樹立起了新的藝術風格,即使是在現代社會也可被看作是詩情畫意的代表。
《春》作為第一首樂曲,選取了小鳥、芳草、微風、溪水這些能夠代表春天的景物。其第一樂章以回旋曲的形式出現,五次全奏夾有四個插部,用“春”的主題做串聯,著力表現春意盎然的景象。AB兩個樂段在力度和速度上的反復對比,傳達的是清新灑脫、華麗舒適的美學氣質。在第一個插部描述的是迎接春光的內容。維瓦爾第在這里標注了“鳥兒歌唱”的字樣,第一與第二小提琴此起彼伏模仿的模仿群鳥啼鳴,以此表現春天萬物復蘇的景象。第二個插部描述的是微風輕輕吹拂的景象。小提琴與交響樂隊平行演奏大三度的連續十六分音符,模仿了溪水潺潺的聲音。緊隨其后的第三插部描述了風雨雷電出現的場景,音符也轉成了三十二分音符,在低音區同音反復與小提琴奏出的三連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樂曲也是由此開始了戲劇性的效果。第四次插部的出現,風雨已經過去,一切又都恢復到恬淡的景象。在最后的全奏中,“春天”的主題以華彩性的獨奏完成。
第二樂章是廣板。二部曲式的結構讓旋律線條穩定流暢。維瓦爾第在這個樂章主要使用小提琴和中提琴去表現牧羊人在樹下安睡,牧羊犬忠實依偎在他身邊的田園景象。小提琴模仿風吹樹葉的聲音,大提琴模仿牧羊犬的低吠。二者形成的一種循環徘徊的聲音,增加了立體音響的美感。第三樂章是舞曲風格的快板,回歸曲式。以四次全奏和三次小提琴獨奏的形式表現。描繪了春天的鄉村舞會。仙女與牧羊人在草地上翩然起舞,歡樂的樂曲渲染出盎然的生機,插部中的每一次轉調都與西西里舞曲的旋律相得益彰,讓歡聲笑語的舞蹈場面更加生動。
(二)《夏》
這里的第一樂章用了中庸的快板。3/8拍更見樂曲活潑的節奏,以四次樂隊全奏和三次插部勾勒出慵懶的人們和無精打采的牲畜。維瓦爾第將這一切稱為“烈日令人慵懶”,弦樂的力度降到PP,再加上延長符號和休止符號的不斷出現,生動展現了仲夏季節人們的狀態。這時,小提琴以不間斷十六分音符的形式出現,模仿杜鵑鳴叫打破了沉悶的氣氛。第二次的全奏從3/8拍轉向4/4拍,從節奏上強化了杜鵑帶來的生機,又為斑鳩、金絲雀等鳥兒的出現進行了鋪墊。可是,鳥兒出現不久即被霎時而起的北風所掩蓋,三十二分音符的飛馳、g小調向下屬小調d小調的轉入等,都在強調這場風所帶來的戲劇感。牧羊人顯然被這突如其來的狂風所驚嚇,他擔心自己的命運,也擔心羊群的安危,游曳音型是他的哭泣。
第二樂章運用柔板,曲式結構采用了反復變化的三段體。其仍是由一個個片段所構成的。如狂風暴雨、冰雹、畜群、蒼蠅等。維瓦爾第為了加以區分,每一個樂段都運用了轉調,從g小調轉入關系大調bB,從c小調轉入屬調g小調等,形成了“主調--屬關系調--下屬調--主調”的結構。這是巴洛克后期標志性的調性結構,以強烈的對比展現出作品的戲劇沖突。就《夏》本身來說,它打破了乏味與寧靜,讓生機再次回歸。
第三樂章進入急板。描繪了冰雹摧毀了牧羊人的家。急速的震音與強有力的大跳音程一起展現出冰雹強大的威力和牧羊人惶恐的內心。樂隊的演奏始終保持了狂風暴雨的氛圍,十六分音符的超速演奏悸動人心,給人們留下了刺烈的印象,維瓦爾第在音樂創作技法上的超前性也通過這一樂章得到了充分地展現。
(三)《秋》
第一樂章快板,回歸曲式。五次樂隊全奏中插入了四次小提琴主奏。在整套樂曲的布局上,表現的是十四行詩中“A”的內容--描繪村民們載歌載舞慶祝豐收的場景。淳樸的鄉村氣息撲面而來。對比技法仍被運用到了這一章,高八度的強奏與低八度的弱奏,再配上平行三度雙音程,已經成為維瓦爾第的標志性處理技法。樂章中的幾次全奏都在第一次全奏的基礎上做了縮減,插部出現的三連音與顫音著力的表現了村民們的痛飲。這種旋律上的反復和相承不斷強化著“痛飲”的主題,直到第四次全奏快板轉為較慢的廣板,“痛飲到昏睡”的主題出現,小提琴抒情寬廣的旋律加入,“陪伴”農夫進入了甜美的夢鄉。
第二樂章是柔緩的慢板,歌舞過后,大地重新歸于寧靜。人們經歷了農忙后,終于可以安適的休息。樂章中最富有詩意的片段出現:傍晚的林蔭小路、暮色下的農田,處處都透露出美好與恬淡。維瓦爾第的創作技法從這里開始返璞歸真:小提琴與第一小提琴齊奏,低音樂器以琶音音型協奏,人們在休憩中積蓄著力量。
第三樂章出現了狩獵人,他們在破曉時分,帶著獵狗、獵槍與號角整裝待發,去追趕四處逃竄的野獸,野獸們的倉皇逃竄與獵人們最終的降服之間的六次全奏全部刻畫的都是“獵歌”的主題。唯一不同的是在調性和旋律材料上的變化。具有戲劇性的狩獵場景是對喧鬧氛圍的延申,讓秋季豐收的喜悅更加凸顯出來。
(四)《冬》
《冬》運用了自由回歸曲式,全奏部分使用的音樂材料極力中和了冬天帶給人們的單一乏味的感受。在第一樂章中,四次全奏使用的音樂材料是以交替的形式出現的,第一次和第三次全奏運用相同的音樂材料,第二次和第四次全奏運用相同的音樂材料。而基于渲染藝術氛圍的考量,維瓦爾第又沒有固定于某一種音樂的形式與原則,他的革新精神完全服務于了樂曲。
第二樂章廣板,運用了反復的二段體曲式。人們圍坐在熊熊燃燒的火爐旁,一邊取暖一邊聊天,度過了安靜美好的休閑時光。維瓦爾第在這一樂章運用的情緒色彩、強弱力度、速度節奏,后被人們奉為古典音樂中的典范,小提琴獨奏表現的愜意也讓這一章廣為流傳。
第三樂章展現了人們滑冰的場景。人們在冰上奔跑、滑動、跌倒,場面的歡樂與冷漠的寒風形成了再一次的對比。這時小提琴的出現是在低音聲部,意在烘托寒冷冬季四處結冰的景象,緊接著的全奏讓人們小心翼翼害怕摔倒的心情也得到了表現。維瓦爾第幽默的性格在這里得到了表現。當樂隊最后一次全奏出現時,維瓦爾第對其標注的是“暖風”,冬季雖然是凜冽的,但是全曲還是在熱烈的氣氛中結束,新的希望已經開始孕育。
三、《四季》的音樂美學分析
(一)標題音樂的傳承
對西方音樂歷史的考察可知,標題音樂源于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家李斯特。他認為,標題音樂可以更好地表達作品的創作初衷與內涵。后來,標題音樂又承擔了描述故事具體內容、展現音樂形象等功能,作曲家借助標題完成的創作,在呈現到聽眾面前時,更容易勾勒出清晰的音樂形象。這也是浪漫主義時期標題音樂繁盛的重要原因。但是,維瓦爾第所處的巴洛克時期明明早于浪漫主義時期,其《四季》鮮明的標題音樂特征雖然沒有記錄到西方音樂史料中,卻無疑是一個先驅性的作品。他為標題音樂勾勒出了一個完整嚴謹的雛形,并在標題之下延伸出一首首雅俗均賞的詩歌,以英文字母為詩歌的每一個段落做出標識,讓樂思與文思高度地匹配,甚至是不欣賞音樂只欣賞詩歌,都能給人們帶來美好地享受,足可見得維瓦爾第深厚的文學與藝術修養。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在于,《四季》開創了音樂在表現形式上的革命性運動。近百年之后出現的古典音樂集大成者--貝多芬,在創作《田園交響曲》時,完全承繼了維瓦爾第的創作思路,其第二樂章中對田園各個風光的描述均可一一對照到維瓦爾第的作品中。包括我們在前文提到李斯特,還有交響樂奠基人柏遼茲,他們的作品形式都與《四季》如出一轍。由此可見,維瓦爾第創造的形式獲得了古典音樂的高度認可,他們不約而同地傳承,不僅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形式,也讓向來認為古典音樂生澀的聽眾獲得了親近與了解古典音樂的機會。維瓦爾第建立的通往音樂的橋梁,讓人們實現了“與美同行”。
(二)人文價值的表現
《四季》能夠從維瓦爾第一生創作的五百余首協奏曲中脫穎而出,成為傳世經典,不僅在于其華麗的旋律、絢麗的曲調、巧妙的樂思,更在于維瓦爾第將自己對世間百態的觀察與感悟融入了其中。他觀察自然也親近自然,自然在他的眼里是美妙的詩歌,有著自成一體的運行規律,他以豐富的技法表現著蘊含在其中的奧秘,他善于找到最典型的事物和景態去展現出了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象。其次,他認為,人類在自然界中的生存也應該被自覺地歸入到自然的一部分。他們或是需要順應自然,或是需要融入自然,而不應該去抱著改造自然的態度不遵循既定的規律。這當中蘊含的深刻的哲學思想與當代社會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是高度一致的。即使是在人的主觀意識形態不斷發展的現代社會,“美”已經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有了更豐富的意義之后,這樣的思想也是一個主軸,沒有任何的改變。足可見維瓦爾第的唯物觀是多么超前。從這個層面來看,也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維瓦爾第以及《四季》均能成為經典了。后世的音樂創作者熱衷于對維瓦爾第的創作技法進行研究與臨摹,殊不知,其最深刻的美學內涵早已經蘊含在思想當中,這種對美學里程碑式的推動才是今時今日研究《四季》美學的最大意義。
四、結語
《四季》作為一首連續表現力強烈的音樂作品用旋律線條描摹出了四季的風情,以大自然中蘊含的美感帶來了愉悅的心理感受。維瓦爾第在這個作品中展現出的詩情畫意讓巴洛克音樂的美學特征一下子得到了豐富與拓展,也讓協奏曲走向了巴洛克時期的巔峰。而在其后幾百年的流傳不衰中,更證明了其在古典音樂史上重要的地位與價值。美學意義的研究從來都不會停止,它會蘊含在所有的藝術作品中,并穿越各個時代帶給人們心靈的震顫,這大概是從《四季》美學研究中引申出的最精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