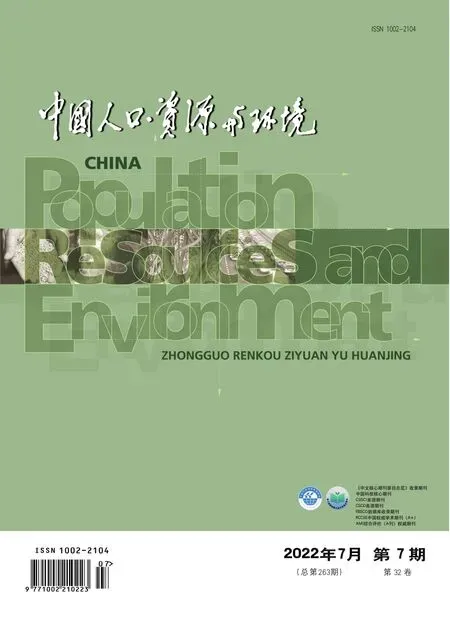數字要素賦能下有偏技術進步的節能減排效應
張思思,崔 琪,馬曉鈺,2
(1. 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46;2. 新疆大學創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烏魯木齊 830046)
技術進步是推動節能減排的重要途徑,內生性的有偏技術進步印證技術進步的非中性,要素稟賦與技術選擇相生相依,納入數字要素的偏向型技術進步重構要素稟賦結構,是影響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因素[1],能源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將會在社會生產中產生節能減排效應。有偏技術進步是指技術進步通過不同比例地改變要素之間的相對邊際生產率,從而對要素使用產生不同比例的節約作用[2]。隨著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數字成為戰略性新型生產要素[3],其廣泛的應用領域能夠快速促進社會生產力提升,激活各領域新動能。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碳排放總量在2019 年達到98 億t 左右。2020 年中國能源產量為40.8 億tce,同比增長2.77%;中國能源消費量為49.8 億tce,同比增長2.16%。2020 年中國煤炭能源消費量占比56.8%;石油能源消費量占比18.9%;天然氣能源消費量占比8.4%;一次電力及其他能源占比15.9%。由此可見,中國能源消費總量較大,但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低,且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等低成本高污染的能源為主。《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約為35.8 萬億元,名義增長15.6%,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7.7%。目前中國在實現“雙碳”目標與保經濟穩定增長的雙重壓力下,如何實現節能減排與經濟穩定增長的雙贏是亟待解決的問題[4]。而數字經濟的騰飛使數字要素賦能有偏技術進步成為必然趨勢。在數字增強型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嘗試驗證有偏技術進步的節能減排效應,并探究其作用機制,對促使中國達成“雙碳”目標、積極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彰顯大國責任擔當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
1 文獻綜述
學界對于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影響的研究主要在行業和區域兩個層面展開。偏向性技術進步是驅動經濟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引擎,當技術進步偏向資源環境要素節約時,能夠帶來綠色低碳發展和經濟穩定增長的雙贏[5]。能源增強型技術進步是中國能源強度變化的重要解釋變量[6]。一方面,不同技術來源的能源強度效應存在非一致性,有學者認為不同來源的技術進步總效應可降低能源強度,有偏技術進步效應大于中性技術進步效應[7]。另一方面,資本與能源間的替代彈性和碳排放強度呈負向相關關系,能源增強型技術進步導致的資本偏向是碳排放強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通過提高資本能源間替代彈性、升級產業結構可以實現碳排放強度下降[8]。
有學者提出不同觀點,董春詩[9]基于偏向技術進步理論框架,判斷2000—2017 年中國各省域的偏向技術進步在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間偏向于使用更多化石能源,且二者之間具有替代關系,這表明整體上偏向技術進步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轉型。這與Unruh[10]首次提出的觀點一致,Unruh認為源于化石能源結構的非清潔技術研發技術更具優勢和持續性,這會阻礙新型低碳技術的發展,甚至會形成技術性碳鎖定而不利于節能減排。此外,技術進步還會促使單位生產成本下降,生產者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及彌補促進技術進步而投入的資本會投入更多的要素來提高產出,碳排放需求上升,反過來又會增加碳排放量,即存在碳排放的回彈效應[11]。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從有偏技術進步的誘發機制和影響機理出發,糅合正反兩方的觀點,提出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在“能源/資本”之間提高能源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節能效應;而在“能源/勞動”之間降低能源效率,表現為能源回彈效應[12]。技術進步能源偏向性與能源強度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系,當生產率效應占優時技術進步能源偏向性降低能源強度,而要素偏向效應占優結果相反[13]。另外,錢娟[14]認為能源消耗、碳排放與能源節約偏向型技術進步之間呈倒“U”型,當前中國工業能源節約偏向型技術進步尚處于倒“U”型曲線左側,邊際效用彈性加劇了能源消耗。
關于數字要素賦能有偏技術進步進而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的直接研究較少。有學者意識到伴隨數字互聯網設備投資的迅猛發展,當前技術進步與資本耦合的趨勢愈加明顯,這種耦合將非對稱地改變要素生產率,影響要素配置和改變對能源要素的需求,轉變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影響[15]。A?ón Higón 等[16]選取了116 個發展中國家和26 個發達國家作為實證研究樣本,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的發展將在前期增加污染物排放,在后期減少污染物排放。Moyer等[17]研究了數字信息技術發展對經濟發展、能源系統和碳排放的動態影響,認為數字信息和通信技術對碳排放的影響有限。關于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影響的傳導機制研究:能源價格[18]、碳排放權交易價格[4]、產業結構升級[8]、有效資本、有效能源和有效勞動的特定要素替代彈性[19]等因素都會成為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影響的傳導機制因素。
綜上,從城市層面分析偏向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和經濟穩定增長雙重目標實現路徑方面的研究比較少,尤其是引入數字要素的具體偏向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的微觀機制方面鮮有探討。文章以數字要素投入為邏輯起點進行機制推導,運用鏈式多重中介模型、分位數回歸模型等方法,驗證了有偏技術進步及其具體偏向型對節能減排效應的影響及作用機制。文章的邊際貢獻可能在于:①嘗試將數字作為生產要素加入生產函數中,用DEA 的非參數Malmquist 指數法測算全要素生產率(TFP)變化,并分離出城市層面的有偏技術進步指數,進而根據要素投入比例判斷技術進步具體要素投入偏向型,劃分出三類偏向型技術進步;②以能源消費結構和經濟規模作為中介變量,利用鏈式多重中介鏈式模型厘清并測度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的傳導路徑、效應大小及異質性差異,嘗試基于數字要素投入對有偏技術進步與節能減排關系進行探討;③從地級及以上城市層面測定有偏技術進步指數和具體偏向型技術進步,嘗試從城市層面挖掘分析有偏技術進步節能減排效應的微觀機制。
2 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數字成為要素的運行機制
數字具備的生產力屬性和數字技術特有的支撐性,使得數據符合成為關鍵生產要素的特征。從運行機制看,首先數據資源、數字虛擬替代、多元共享和推動企業模式創新機制有效提高了組織、交易和生產效率,進行了價值創造,最終實現了數據資產化[3]。其次,數據資源具有空間外溢性和擴散邊際成本為零的特性,有助于實現產業層面的跨界融合,從而有效實現產業融合和產業關聯。最后,數據可以輔助主體來進行智能決策,最終通過數字要素的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數據價值增值[20]。
數字成為生產要素的過程中具有特殊的價值形態。數字本身的傳輸手段對生產效率有不可替代的賦能作用[21],同時數字可與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協同融合實現價值延伸[22]。而后,數據產品通過交換化身數據商品實現了價值。在市場交換過程中數據商品的價值被充分反復利用且邊際生產成本遞減,最終實現了價值倍增的“驚險一跳”,變成了數字生產要素。
2.2 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的影響機制
在數字成為生產要素的基礎上,借鑒Grossman 等[23]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參考錢娟[24]的推導思路,文章引入能源和數字投入要素,構建包含能源投入和數字要素的經濟增長模型。
(1)生產部門。假設生產函數為:

其中:Y代表最終產出,G代表外部生產環境,E代表能源投入量,假定各類中間產品進行數字化生產品質優化程度與常數q成比例,則經過數字化改進的第i種中間產品質量為qεi(q>1,ε為清潔程度),Xεi代表數字化改進后對第i種產品的需求。在此不考慮人口增長因素并將其規模標準化為1。
假設生產部門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均來自中間產品的生產過程,則能源消耗或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中:R代表生產過程中能源消耗或碳排放總量,γ表示碳排放系數或能源消耗系數。
(2)數字運行部門。數字化運行改進新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效率,數字運行部門從產品生產中所獲得的利潤(πεi):

其中:PεiXεi為研發部門獲得收入,φ為邊際成本,φXεi為數字化生產改進的邊際成本。
(3)消費部門。假設在某一時點上社會最終產出完全被用于消費、數字化運行及生產中間產品投入后的值(Y′)為:

(4)三部門實現最優目標。企業目標實現利潤(π)最大化:

其中:P代表能源價格,Pεi代表第i種中間產品經數字化改進品質后價格。此時,企業利潤最大化滿足一階條件為0,則:

數字化運行部門目標最大化壟斷期獲取全部利潤,對式(3)Pεi取一階導數:


由于0 <α<1,壟斷價格高于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價格φ,在此設定φ= 1,則帶入式(6)可得:

滿足消費最大化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式(8)代入(2)可得:

單位最終產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由上述機理推導可見,節能減排效應的影響機制主要包含三部分內容,其中技術進步的綜合效應在文章中重點考察有偏技術進步,文中定義的有偏技術進步主要來自通過改變能源和數字這兩種生產要素與其他要素的配置比率,使得生產前沿面本身發生移動。在給定的生產前沿技術水平下(q>1),技術進步的綜合效應取決于偏向綠色清潔技術進步的程度,技術進步越偏向于能源節約和數字增強則節能減排效果就越突出,說明加入能源和數字要素的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具有直接影響效應。
在能源消費結構的傳導機制中:一方面,綠色經濟發展需求和要素錯配帶來的能源約束,造成能源價格上升,使企業獲得研發動力,新的生產技術提高要素使用效率驅動能源全要素效率增長的基礎動能,通過改變能源消費結構來促進節能減排。另一方面,能源節約型有偏技術進步與數字要素深化出現協同進一步促進節能減排,數字要素促進清潔生產技術應用到能源系統和生產系統,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此外,數字要素以其多元共享性發揮智能監測功能協助政府部門能源政策的實施與監管,提升能源政策效果促進節能減排[25]。
在經濟規模的傳導機制中:一方面,當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與數字要素深化產生協同效應時,企業會研發數字要素增強型的生產技術,數字要素對能源與資本替代的同時,產業數字化會擴大數字化產品的生產規模,總體上社會生產經濟規模會擴大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數字產業化給環保產業帶來發展機遇,數字經濟的平臺優勢為企業帶來了尋求產品創新、發展清潔生產模式、實現綠色發展的機會。通過加快環保科學技術成果的產業化,促進環保產業的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節能減排。但這一時期數字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又會加大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25]。
能源結構效應和經濟規模是對能耗和碳排放產生影響的決定性因素,社會生產中外生性技術進步帶來能源效率的提升和內生性因素能源價格的波動以及能源政策的實施,使得能源結構優化一方面促使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的脫鉤[2],另一方面促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兩方面都說明能源結構效應會帶來經濟規模的變動,進而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然而,在數字要素稟賦發生變動的早期階段,各要素間協同可能并不順暢。甚至在數字要素發揮重大作用的能源互聯網建設前期,數字增強型技術進步推動的能源消費結構的節能減排效應甚微,卻因經濟規模效應擴張造成能耗和碳排放加大[26]。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將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對節能減排的影響更為顯著[25]。
基于上述機理推導及理論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有偏技術進步會通過改變要素間邊際替代效率來發揮節能減排效應。
假設1-1: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的轉化來促進能耗節約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減少。
假設1-2:有偏技術進步通過經濟規模效應來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有偏技術進步會對節能產生正向影響,而在一定時期內對減排產生負向影響。
假設1-3: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推動經濟規模效應的鏈式中介機制,最終對節能產生正向影響,而在一定時期內對減排產生負向影響。
2.3 技術進步的偏向型及來源
Hicks 等[27]將技術進步分為有方向的技術進步和中性技術進步,首次提出技術進步的方向劃分為兩種情況即資本節約和勞動節約。Acemoglu[28]進一步將有偏技術進步定義為生產要素邊際替代率的變動對技術進步不同程度的增進作用,他指出兩種形態的有偏技術進步:一是要素增強型的有偏技術進步,二是要素偏向型的有偏技術進步。
Acemoglu[28]認為,有偏技術進步的要素偏向的來源或者稱為判斷依據是由要素價格效應與市場規模效應決定。另外,Weber 等[29]提出的基于要素投入比例變化以及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指數的大小來判斷制造業技術進步的要素投入偏向。
基于以上論述,文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加入數字要素后,技術進步的不同偏向型對節能減排的影響存在差異。
假設2-1:對于有偏技術進步的偏向,在數字與資本中數字增強型(即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會抑制節能減排效果。
3 模型、變量測算方法與數據說明
3.1 基礎回歸及機制檢驗模型
鏈式中介機制模型用于刻畫存在互相影響的兩個及以上中介變量間的關系,通常會形成順序性特征的中介鏈[30]。借鑒Baron 等[31]、柳士順等[32]、方杰等[33]、吳學花等[30]的方法及思路,繪制了鏈式多重中介模型(圖1)的作用機制,從而刻畫出核心解釋變量通過兩個中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多重多步作用鏈接。按照上文中機制推導,兩個中介變量分別是能源消費結構和經濟規模。在鏈式多重中介模型中,存在三類中介效應:第一種是特定路徑中介效應(a1b1、a2b2和a1a3b2),三者分別代表能源消費結構中介效應、經濟規模中介效應和能源消費結構助推經濟規模中介效應的大小;第二種是總體中介效應(a1b1+a2b2+a1a3b2)即上述三種中介效應大小之和;第三種是對比中介效應(a1a3b2-a1b1,a1a3b2-a2b2和a1b1-a2b2),分別反映上述三種中介效應之間的兩兩差異。除了中介效應之外,圖1 中c代表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的直接效應。

圖1 鏈式多重中介模型
根據有偏技術對節能減排影響的理論機制分析,應用鏈式多重中介模型,文章設立如下基礎計量回歸模型: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地級及以上市i在第t年的被解釋變量具體數值。被解釋變量有兩個,分別為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IBTCit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城市i在第t年的有偏技術進步指數。Z為控制變量,包含了獨立于有偏技術進步水平但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的若干變量,文章選取了6 個控制變量。μi表示不可觀測的地區變量個體固定效應,bi為不可觀測的時間變量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根據上文的理論機制分析,借助鏈式多重中介模型設定如下計量回歸模型。

其中:econit和ecscit為中介變量,分別代表城市i在第t年的能源消費結構和經濟規模。式(15)和式(16)分別模擬兩個中介變量、三條中介路徑推動節能減排的計量回歸過程。Z′和Z″為控制變量,包含了獨立于有偏技術進步水平但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的若干變量。μ′i和μ″i表示不可觀測的城市變量個體固定效應;b′i和b″i為不可觀測的時間變量固定效應,ε′it和ε″it為隨機擾動項。結合式(14)和式(17),通過依次檢驗回歸系數對多重中介效應進行判定,發現能耗強度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和解釋變量有偏技術進步間的相關關系是否存在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若式(14)中系數α1顯著,則表明存在總體效應,該效應在理論上等于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之和。若式(17)中系數θ1顯著,則表明存在直接效應。若特定中介效應β1θ2顯著,則表明在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影響中能源消費結構起到中介作用;同理,若γ1θ3顯著,說明經濟規模效應起到中介作用,若β1γ2θ3顯著為正,說明能源消費結構和經濟規模對節能減排起到鏈式中介作用。上述三者之和為總體中介效應。
3.2 技術偏向型驗證
為了進一步驗證具體的技術偏向對節能減排的影響,借鑒王班班[2]、劉自敏等[4]的研究思路,文章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Yit-j表示被解釋變量的滯后j期。設定三個虛擬變量來表征技術進步的偏向型,若某城市的有偏技術進步在能源與資本中資本增強(即能源節約),則EKb=1,反之EKb=0;若該城市的有偏技術進步在能源與數字中數字增強(即能源節約),則EDb=1,反之KDb=0;若該城市的有偏技術進步在數字與資本中數字增強(即資本節約),則KDb=1,反之EDb=0。μi表示不可觀測的地區變量個體固定效應,bi為不可觀測的時間變量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3.3 異質性檢驗
3.3.1 按照能源強度與碳排放強度分組
考慮到橫向來看不同城市在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降耗和碳排放影響效應的差異性,文章根據各城市歷年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均值將城市劃分成8 組,分別為高能耗組、低能耗組、高排放組、低排放組和高能耗-高排放組、高能耗-低排放組、高排放-低能耗組、低能耗-低排放組。
3.3.2 按照分位數分組
為進一步縱向考察各城市能源消耗強度與碳排放強度在各自不同水平上影響作用的差異性,采用分位數回歸模型來檢驗有偏技術進步對不同水平下的能耗和碳排放強度的邊際影響。根據Powell[34]的研究,分位數模型設置如下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IBTCit為核心解釋變量;Z為控制變量;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bi為時間變量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3.3.3 按照區域異質性分組
嘗試根據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兩種形式的創新成果轉化能力對中國省級單位進行分組,再按照省級歸屬劃分各個城市以進行地區異質性分析[35]。這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測算會在下文做出詳細說明,用各城市的生產總值與能源消費總量(碳排放總量省略)之比衡量創新成果轉化能力。圖2 中散點圖對比展示了中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兩種形式創新轉化能力分布情況(由于數據的可得性,西藏和香港、澳門、臺灣地區除外)。圖3 中展示了中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及其增長水平的情況。考察圖2,按虛線右上方(分組1)和右下方(分組2)大致可將全國各省分為兩組,散點分組1 城市群相較于分組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創新成果轉化能力較強,也為中國經濟繁榮區域。考察圖3,兩條虛線可以將散點大致分為三個組別,第一組(分組3)包含城市群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數字經濟增長發展時間跨度長且有一定基礎而導致增長速度偏緩;第二組(分組4)包含城市群及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勢頭好,但因數字技術基礎較為薄弱起點較低,是未來中國數字經濟崛起的區域;第三組(分組5)包含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增長速度緩慢。

圖2 數字經濟發展與創新轉化能力分布

圖3 數字經濟發展指數與增長水平分布
3.4 變量測算解釋
3.4.1 有偏技術進步指數測算及要素偏向型判斷
參考王班班[2]、劉自敏等[4]、付明輝等[36]的做法,基于DEA 的非參數Malmquist 指數法測算的全要素生產率(TFP)變化,并分離出城市層面的有偏技術進步指數。F?re 等[37]根據Malmquist 指數法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分解為技術進步指數(TC)和技術效率指數(EC),前者指生產前沿面本身的移動,后者指低效率生產要素組合相對于前沿面的移動。F?re 等[38]將技術進步指數分解為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指數(IBTC)、產出偏向型技術進步指數(OBTC)和規模技術進步指數(MTC)。文章采用IBTC衡量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指數,并判斷技術進步的要素偏向型。

該產出距離函數被定義為給定要素投入組合xt時產出yt的最大擴展比例的倒數。該函數用以下方式來表征技術當且僅當(xt,yt) ∈Pt。Malmquist 指數可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指數(EFFCH)與技術進步變化指數(TECH),當產出僅有一種時,TECH可分解為產出偏向型技術進步指數、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指數和規模技術進步指數,即:


其中:規模技術進步指數度量生產前沿面的平移,為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在測算Malmquist 指數時,產出只有一項,如果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則OBTC=1,如果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則OBTC≠1,文章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式(23)表示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它度量技術進步隨著要素投入組合配置而發生變化。IBTC>1,表明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IBTC<1,表明該投入偏向型技術變化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參考Weber 等[29]、付明輝等[36]的做法,來判斷技術進步非中性時要素投入偏向型。假定分別表示t時期和t+ 1 時期的兩種要素投入比,結合式(23)計算出的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指數,判定原則為:當(x2/x1)t<(x2/x1)t+1時,如果IBTC>1,則表示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增加使用x2節約x1,如果IBTC<1,則表示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增加使用x1節約x2,如果IBTC=1則代表技術中性;當(x2/x1)t>(x2/x1)t+1時,如果IBTC>1,則表示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增加使用x1節約x2,如果IBTC<1,則表示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增加使用x2節約x1,如果IBTC=1則代表技術中性。
在測算有偏技術進步指數時選擇的產出變量為各個樣本市的不變價地區生產總值,投入變量選擇勞動、資本、能源與數字要素,具體各變量的解釋見表1。

表1 有偏技術進步指數測算變量選取
3.4.2 數字要素綜合發展指數測算
文章借鑒趙濤等[40]的方法,從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互聯網產出水平、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和數字金融普惠發展指數五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來衡量數字要素的發展水平,具體各指標的解釋見表2。其中,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41]。文章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將數據標準化之后降維處理,最終得到了數字要素綜合發展指數。

表2 數字要素發展指數
3.4.3 中介變量
根據文章第二部分的機制推導,選擇兩個中介變量如下。
(1)能源消費結構(econ)。能源消耗量的計算參照劉自敏等[4]的做法使用各地級市的液化石油氣、煤氣及電力計算,按照《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各能源折算標準煤系數,換算成萬tce 并加總得到。能源消費結構參照錢娟[24]的做法用能源消費中化石能源的比重來表示。
(2)經濟規模(ecsc)。文章借鑒金剛等[42]的做法,使用以2011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換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經濟規模。
3.4.4 控制變量
(1)人口集聚度(poag)。人口的活動和集聚會影響一個城市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各地區的常住人口數占地區面積的比與全國人口占全國面積的比值來衡量人口集聚度。
(2)經濟外向性(ecex)。OFDI對母國碳排放的影響表現出多維性關系,既存在加劇碳排放的直接影響,也有通過中介變量抑制碳排放的間接效應[43]。因此使用各城市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在各省(直轄市)的生產總值占比來表示經濟外向性。
(3)政府科教的重視程度(sced)。政府對科教的重視程度體現了城市為推動技術進步而建立的人才和知識儲備。使用各城市的科教經費支出在公共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來表示。
(4)財政自主度(fiau)。財政分權對碳排放存在正向影響,分權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量的減少[44]。采用各城市財政預算內收入與預算內支出的比重來表示財政自主度。
(5)環境規制程度(enre)。環境規制有利于本地碳排放減少,且其碳減排的作用逐年遞增,而且同期本地環境規制實施可以形成鄰地示范效應,推動相鄰地區碳減排[45]。用二氧化硫排放強度即各市各年二氧化硫排放總量與各年度生產總值增加值之比來表示。
(6)城市優惠政策(fapo)。佘碩等[46]從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特質出發分析低碳試點政策實施效果的異質性特征,實證結果表明低碳試點政策有利于城市經濟綠色增長,有助于節能減排。設置虛擬變量表示樣本城市是否為低碳試點城市,是則取值為1,否則為0。
3.5 數據來源及統計性描述
選擇2011—2019年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作為研究對象,未涉及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同時,由于部分城市存在數據不完整或數據質量不佳等問題,刪除了24 個城市(綏化市、萊蕪市、襄陽市、懷化市、三沙市、儋州市、畢節市、銅仁市、遵義市、安順市、麗江市、普洱市、嘉峪關市、金昌市、天水市、海東市、拉薩市、日喀則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吐魯番市、哈密市)數據,保留了271 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采用插值的方法來彌補少量的缺失數據,變量的相關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各省級統計年鑒、中國宏觀統計數據庫。
基礎回歸模型(14)中有兩個被解釋變量,為能源強度(eci)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coei),分別為各市各年能源消耗量與各年度生產總值增加值之比,各市各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與各年度生產總值增加值之比。城市碳排放的計算借鑒吳建新等[47]的方法,將電能、煤氣和液化石油氣、交通運輸和熱能消耗分別與各自的相應轉化因子以及原煤折算標準煤系數相乘后加總,得到各城市的碳排放總量。
表3中為文章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中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對數處理數據的統計性描述,其中IBTC表示有偏技術進步指數為文章的核心解釋變量,OBIB表示技術進步綜合效應是有偏技術進步指數和規模技術進步指數的交乘積。其余變量均已在上文中做出了解釋。

表3 數據統計性描述
4 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基準回歸結果
經過豪斯曼等一系列檢驗最終選定地區固定效應模型(FE),對于基準回歸式(14)的回歸(表4 列(1)和列(2))可知有偏技術進步指數對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顯著為負,即驗證了加入能源和數字要素投入的有偏技術進步具有節能減排的效應,從而假設1得到驗證。回歸結果還表明人口集聚度、經濟外向性、政府科教的重視程度、財政自主度均對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的影響。城市人口集聚度高有利于能源和公共服務集約利用,反而有利于節能減排。城市經濟外向性程度高,有利于借助外資和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從內生和外生兩個方向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促進節能減排。政府對科教投入力度越大,越能通過提升當地的人力資本和創新能力來實現節能減排。財政自主程度可以反映當地政府對財政分權的掌控力,財政分權程度對碳排放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48],并且財政分權通過正向調節綠色研發投入來提高本地區碳生產率[49]。環境規制程度對節能和減排產生負向的影響,可能是因為環境規制與實質性創新效率和策略性創新效率之間均呈U 型非線性關系,有文獻研究表明中國大部分觀測城市處于環境規制會抑制地區創新效率的階段[50]。而是否為碳減排試點城市僅對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的影響,有研究表明試點城市的碳排放量相對于樣本均值明顯降低,意味著低碳城市建設顯著降低碳排放水平[51]。
表4的列(3)—列(7)回歸中,驗證技術進步綜合效應的鏈式中介效應并不顯著,且加入lnOBIB之后,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的影響變得不再顯著,說明技術進步綜合效應雖然是節能減排影響機制中的構成部分,但在有偏技術的節能減排效應機制中不能作為中介變量。但是表4 的列(3)—列(4)計量回歸結果說明技術進步綜合效應均對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的影響,即技術進步綜合效應對節能減排具有促進作用。
4.2 機制檢驗結果分析
表5的列(1)—列(4)是對式(15)和式(17)的回歸,驗證了圖1展示的鏈式多重中介機制。為了檢驗中介效應在統計上是否顯著,該研究首先對能源消費結構和經濟規模的中介效應分別做Sobel 檢驗,對應P值均在10%的置信水平通過顯著性檢驗。其次,運用Bootstrap方法檢驗是否存在鏈式多重中介效應路徑,檢驗結果表明所有中介效應值對應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說明獨立中介效應1、獨立中介效應2、鏈式中介效應和整體中介效應具有顯著性。
4.2.1 三條中介路徑效應分析
路徑1表示“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來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路徑2表示“有偏技術進步通過經濟規模來對節能減排產生影響”;路徑3表示“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推動經濟規模效應的鏈式中介機制,最終對節約能耗和二氧化碳減排產生正向影響”。從路徑1看,有偏技術進步經由能源消費結構(econ)的中介效應為表4中列(1)中有偏技術進步(lnIBTC)的系數-2.307 4分別與列(3)、列(4)中lnecon的系數0.616 8 和0.159 3 的乘積,這兩個值分別為-1.423 2 和-0.367 6,且這兩個值至少在5%的水平上是顯著的,這說明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這一途徑對能源強度產生了負向影響且對碳排放強度也產生了負向影響,即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對節能減排產生了正向影響,至此假設1-1得到驗證。對于路徑2 計算系數的方式與路徑1 一致,則有偏技術進步經由經濟規模(ecsc)的中介效應分別為-5.404 0 和1.912 8,且這兩個值至少在5%的水平上是顯著的,說明有偏技術進步通過經濟規模這一途徑對能源強度產生了負向影響且對碳排放強度產生了正向影響,即有偏技術進步通過經濟規模會對節能產生正向影響,而對減排產生負向影響。這說明當有偏技術進步出現時減少了能源使用量,從而會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而同時中國的有偏技術進步會促進經濟規模的增長,在兩種效應作用下,節能和減排的效果會受到不同的影響,當前階段加入數字要素的有偏技術進步節能效果較好,而經濟規模效應超過技術進步效果反而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強度,至此假設1-2 得到驗證。從路徑3看,有偏技術進步經由能源消費結構、經濟規模的鏈式多重中介效應為表4 中列(1)有偏技術進步(lnIBTC)的系數-2.307 4 與表4 的列(2)lnecon的系數0.033 8 的乘積再分別與表4的列(3)和列(4)中lnecsc的系數3.976 8和-1.407 6的乘積,這兩個值分別為-0.310 2和0.110 0,且這兩個值至少在5%的水平上是顯著的,這表明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推動經濟規模效應的鏈式中介機制,最終對節能產生有利影響,而對減排產生不利影響,至此假設1-3得到驗證。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假設1-3得到驗證的原因在于,能源發揮要素價格效應,促使生產主體研發綠色生產技術,提高邊際生產率和能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推動產業升級,減少能源使用從而促進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推動能源消費結構優化的同時與當今豐裕的數字要素出現協同創新,生產主體逐利開發數字要素增強型生產技術,促使數字偏向型技術產品的開發與生產規模的擴大,最終產生節能效應。然而,有偏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的市場競爭,與中國市場資源優化配置功能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產生矛盾,中國能源和數字要素仍受到政府監管,要素價格扭曲導致各地區之間要素錯配[52]。能源與數字要素的錯配,加上數字技術進步衍生下的互聯網+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以及數字化基礎設施前期擴建,需要消耗大量的電力和能源[16],在一定時期內,能源消費結構效應推動下的經濟規模的擴大,使得有偏技術進步反而不利于二氧化碳減排。以上結果與Yang 等[53]、Yang 等[54]和Zhang等[55]提出的觀點一致,他們通過系統動力學方法驗證了能源結構優化具有顯著的碳還原能力,但能源互聯網建設過程中會加劇碳排放。
4.2.2 總體中介效應分析
總體中介效應是三條中介路徑效應的加總,對于被解釋變量為能源強度來說總體中介效應為-7.137 4,對于被解釋變量為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來說總體中介效應為1.655 2,且這兩個值至少在5%的水平上是顯著的。這說明經濟規模的擴大為數字基礎設施和技術研發的普及提供了財政保障,使得有偏技術進步促進了能源效率的提升達到了節能的效果,然而隨著數字技術和基礎設施的逐漸普及數字技術帶來的技術革命引發了能源反彈效應[56],此時能源使用量增加提高了碳排放的強度,對碳減排產生了不利影響。
4.2.3 對比中介效應分析
綜上的特定路徑和總體路徑的分析表明,有偏技術進步經由能源消耗結構、經濟規模以及能源消費結構與經濟規模多重中介三條路徑對能源強度的中介效應分別為-1.423 2、-5.404 0 和0.310 2,在總體中介效應中分別占20%、76%和4%;對碳排放強度的中介效應分別為-0.367 6、1.912 8 和0.110 0,在總體中介效應中分別占22%、72%和6%。從對比三條路徑形式在總效應中的占比可以看出路徑2 發揮的作用最大,也再次說明了通過lnecsc的中介效應以及lnecon、lnecsc的多重中介效應,是有偏技術進步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原因。
4.3 技術偏向型結果分析
考慮到內生性、組內自相關及異方差等計量回歸問題,選取差分GMM 和系統GMM 作為固定效應模型(FE)的對比模型。Sargan統計量的P值大于0.05,接受了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原假設,AR(1)和AR(2)的P值均大于0.05,說明存在動態面板的自回歸效應。
加入技術偏向型虛擬變量和技術進步綜合效應變量后,由技術偏向型回歸結果來看(表6),表6 列(1)、(2)的動態面板系統GMM 回歸和固定效應模型(FE)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中,兩個被解釋變量的滯后1~2期滯后變量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都具有時間、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特征。資本增強能源節約和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的影響均不顯著,而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可能是因為在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尚處于萌芽中期向完善初期過渡階段,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和數字經濟的大眾普及正在加速中,在這個時期需要了巨大的能源和資源消耗,數字經濟迅速發展下的信息技術革命引發了能源反彈效應,導致數字增強資本節約的技術進步反而不利于當前階段的節能減排[37]。此外,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容易造成配套政策設置不完善,設備虛設或利用不充分,其運行機制對節能減排的負面影響常常容易被忽略[57]。因此,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促進節能減排的作用在目前階段尚沒有發揮出來。至此假設2和假設2-1得到驗證。

表6 技術偏向型驗證結果
4.4 穩健性檢驗
(1)更換有偏進步指數計算方式。在上文中測算Malmquist 指數時,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則OBTC≠1,這里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則規模技術進步指數OBTC=1,且重新獲得有偏技術進步指數IBTC,代入公式(14)和公式(18)中用固定效應模型(FE)進行回歸。
(2)通過構建系統GMM 模型、盡可能多地增加控制變量、添加工具變量綜合技術效應(OBIBit),并根據在固定地區和時間效應的基礎上估計出的殘差值,再分別計算有偏技術進步指數(IBTCit)、技術進步偏向與殘差(e)的協方差為0.21×10-4和0.24×10-11,非常接近于0,證明模型因遺漏變量產生的結果偏誤被極大降低。
(3)非平衡面板數據。上述基準回歸和技術偏向型驗證回歸采用的是平衡面板數據,為避免部分城市在樣本期間數據缺失影響研究的結論,文章采用樣本期間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進行檢驗。
(4)剔除直轄市。由于四個直轄市獨立受中央直接管轄,行政地位特殊,為了排除行政因素對基準回歸結果的干擾,文章將京、滬、津、渝等四個直轄市從全樣本中剔除后再回歸。
(5)替換被解釋變量。用能源消耗總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替換能源強度和碳排放強度并取對數值之后進行回歸。以上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均與基礎回歸以及技術偏向型回歸結果一致,證明基礎回歸的結果是穩健的(篇幅有限,穩健性檢驗所有回歸結果不在文中展示,備索查)。
4.5 異質性檢驗結果分析
4.5.1 耗能碳排放分組
為考慮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規模異質性及探究技術進步對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影響效應的差異性,將文章樣本劃分成8 組。由表7 的列(1)、列(2)、列(5)和列(6)可知(篇幅有限,耗能碳排放分組完整回歸結果不在文中全部展示,備索查),高能耗-高排放組的回歸結果中顯示有偏技術進步會對節能減排產生負向的影響,可能是因為在高耗高排以及雙高城市組中,要素配置結構與技術進步方向匹配度較差,導致有偏技術的進步起不到節能減排的作用甚至會加劇能耗和碳排放強度,并且相較而言雙高組中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的負向影響最大,高排放組對減排的負向影響最大。此外,高耗能組、高排放組和高耗能-高排放組中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依然是顯著的負向影響,與整體回歸結果一致。由表7 列(3)、列(4)、列(7)和列(8)的回歸結果可知,低能耗-低排放組的回歸結果中,均顯示有偏技術進步會對節能減排產生顯著的正向的影響,說明在低耗、低排以及雙低城市組中,要素配置結構與技術進步方向較為匹配。另外,低耗能組、低排放組和低耗能-低排放組中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和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盡管技術進步偏向數字增強能源節約,但中國目前數字經濟和能源集約利用的適應性機制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尚未協同高效發展,在此階段容易夸大數字經濟的節能效果而忽略適應性機制背后造成的能耗。

表7 耗能碳排放分組回歸結果
4.5.2 分位數回歸模型分析
為分析有偏技術進步指數以及技術進步的偏向型對節能減排的邊際影響,進一步采用分位數模型驗證不同的能耗強度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水平下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的影響。文章通過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分位數曲線,可以大致判斷出將二者的曲線劃分為10%、50%和90%三個分位數,并分組對公式(19)進行回歸(表8)。由回歸結果可知,在10%、50%和總體100%分位數上,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存在正向影響,而且影響的作用先減小后增大近似呈現“U”型。但在90%分位數上,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存在負向影響,這對上文中雙高城市組情況相互印證,再次說明對于高耗能和高排放城市來說,要素配置與技術進步的方向不匹配,有偏技術反而不利于節能減排。

表8 分位數回歸結果
4.5.3 按照區域異質性分組
表9為根據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兩種形式的創新成果轉化能力進行的地區異質性回歸結果。由回歸結果可知(篇幅有限,回歸結果不在文中全部展示,備索查),對于散點分組1 來說,如表9 列(1)、列(2)、列(5)和列(6)所示,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相較而言對于散點分組2 的正向影響作用更大。散點分組2 中所包含的城市相較于散點分組1 中的城市而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創新成果轉化能力弱,多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回歸結果說明這些城市的有偏技術進步水平的提升帶來的節能減排效果更好,也說明加入數字要素后的有偏技術進步水平提升是這些城市實現節能減排、雙碳目標的重要著力點。此外,散點分組1 中,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會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且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僅對節能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可能原因是這些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雖然相對較高,但仍存在巨大發展空間,仍處于數字化擴建的飛躍階段,擴建忽略了數字要素與能源匹配運行機制中的適應性行為的能源消耗。

表9 地區異質性分組回歸結果(部分)
由回歸結果可知對于散點分組4、5來說,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散點分組3這一回歸卻是不顯著的,如表9 列(3)、列(4)、列(7)和列(8)所示,原因可能是散點分組3中包含的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各項指標的風向標,產業結構優化的戰略高地,這些地區節能減排政策執行力度最大,配套政策和措施完善,因此對于這些地區而言,其節能減排的眾多影響因素中內生性的有偏技術進步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并且,散點分組4相對于分組5,有偏技術進步的節能減排效應更為明顯。此外,對散點分組3而言,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均會對節能減排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對散點分組4 而言,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會對節能減排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而對散點分組5而言,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型和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均會對節能減排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可能的原因是相對于4、5 組,第3 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但還需要增強數字與能源要素的匹配度,以實現數字要素賦能能源的消費結構優化。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文章以數字成為生產要素為邏輯起點,將數字要素加入生產函數中,用DEA的非參數Malmquist 指數法測算全要素生產率(TFP)變化,并分離出城市層面的有偏技術進步指數,進而判斷技術進步非中性時要素投入偏向型,劃分出三類偏向型技術進步。借助機制推導與理論分析進行鏈式多重中介效應回歸證實了有偏技術進步通過能源消費結構推動經濟規模效應的鏈式中介機制,最終對節能產生正向影響,而在一定時期內對減排產生負向影響。并且,技術進步的不同偏向型會對節能減排產生不同的影響,具體而言在數字與資本中數字增強型(即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會對節能減排產生負向影響。
在異質性分析中:①高耗能組、高排放組和高能耗-高排放組的回歸結果中,均顯示有偏技術進步會對節能減排產生負向的影響,且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依然是顯著的負向影響;低耗能組、低排放組和低能耗-低排放組的回歸結果中,均顯示有偏技術進步會對節能減排產生顯著的正向的影響,數字增強能源節約和數字增強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②在10%、50%和總體100%的能源強度和碳排放強度分位數上,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存在正向影響,但在90%分位數上,有偏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均存在負向影響。③根據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兩種形式的創新成果轉化能力對樣本進行分組,分組回歸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較慢、創新水平較低的地區有偏技術進步的節能減排效應更顯著。目前在數字經濟發展較快地區,數字增強型技術進步對節能減排會產生負向作用。
結合上述驗證結論,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為政府部門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1)強調數字要素投入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堅實數字生產力的技術基礎,持續拓展數字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融合的廣度和深度。一方面,政府應進一步加大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加快數字中國建設速度。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應鼓勵并引導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58]。同時發展技術和數字要素市場,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
(2)推進節能減排政策工具的市場化。同時,加快能源消費結構調整,充分發揮能源消費結構對綠色轉型發展的促進作用,降低工業行業能源消費中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費占比,提高可再生性清潔能源消費比重,使能源消費向低碳化、清潔化發展[59]。
(3)針對不同地區能耗碳排放以及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現狀制定差異化、動態化的政策措施。首先,鼓勵各城市結合節能減排管控技術水平、自身科創轉化能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要素稟賦,創新性推進內生性的有偏技術進步。其次,針對數字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城市,各地級市應爭取更多的政策傾斜,加快推進數字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數字基礎設施覆蓋面,并推動城市之間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