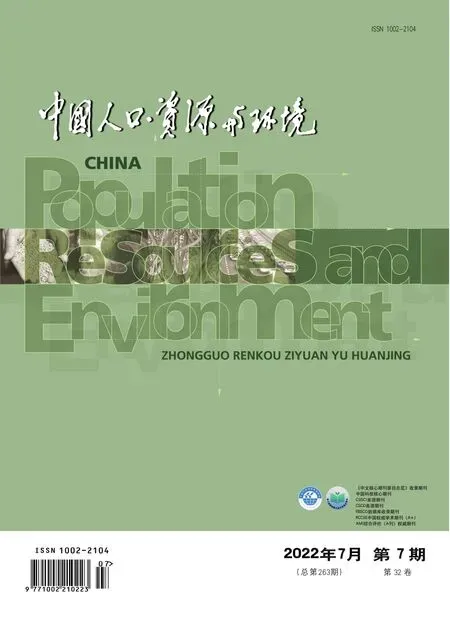RCEP框架下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驅動因素
葛 明,趙素萍
(1.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重慶 400715;2. 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與貿易學院,重慶 400031)
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東盟十國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于2022 年1 月1 日正式生效,標志著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開始啟航。在當下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逆全球化浪潮興起的背景下,順利建成RCEP 對提升區域內市場開放水平和經濟一體化程度,促進中國構建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RCEP 要求成員國貨物貿易立即或逐步取消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其中,零關稅品種數量超過90%,未來增加到95%,中國對RCEP 成員出口占比較高的電氣設備、化工品、通用設備等商品均在優先零關稅產品之列,生效后的RCEP 將進一步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新能源產業貿易往來。經典貿易理論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通過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拓展區域內市場空間,增大區域內貿易規模,為產業發展提供更廣闊的平臺;但同時,由于市場進出壁壘降低,區域內競爭環境更加公平,競爭水平更加激烈,而競爭力不高的企業和產品將可能被淘汰出局。因而,在RCEP 生效后,中國既需要關注貿易自由化措施帶來的需求擴大效應,也需要重視國內產業競爭力面臨的挑戰,特別是關鍵戰略性新興產業。
全球性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和氣候變暖等問題日益突出,積極推進能源革命,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新能源推廣應用,成為各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大戰略選擇。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都已經出臺大規模的新能源發展規劃,將新能源產業作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中國也將新能源產業作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作為推進能源結構調整,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舉措。近年來,由于中國環境治理理念的不斷加強和新能源開發技術水平的提高,中國新能源產業蓬勃發展,逐步形成了涵蓋研發、制造、設計、施工、運行等各環節的全產業鏈體系,風機設備、多晶硅、硅片、光伏電池等生產規模穩居世界第一位,不僅為國內生產生活提供清潔電力,推動能源消費轉型升級和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還通過設備及產品出口,為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降低碳排放、實現“雙碳”目標做出了重要貢獻。自加入WTO 以來,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規模不斷增長,由2002 年的20.83 億美元上升至2019 年的429.10 億美元,年均增速19.48%。其中對RCEP 國家(除中國外的14 國)新能源產業出口額由5.51億美元增加至130.91 億美元,年均增速20.48%,占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6.44%增長至30.51%,在RCEP 國家所占進口份額的增長更加明顯,由2002 年的7.87%上升到2019 年的40.44%,由此可見,RCEP 國家成為中國重要的新能源產業貿易伙伴。
RCEP 正式生效所形成的龐大自由貿易市場,將為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提供新的機遇,而能否抓住機遇,既取決于RCEP需求規模和結構的變化,也依賴于中國新能源產業競爭力水平及其源泉的變動,同時決定于供需規模及其結構是否協同。文章擬基于拓展的恒定市場份額(Constant Market Shares,簡稱CMS)模型三層次分解框架,從總體、國別、產業等三個維度解答中國對RCEP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驅動力。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將有助于在RCEP生效的重要時點上,為中國調整新能源產業發展政策和貿易政策,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出口規模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持。
1 文獻綜述
新能源產業貿易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新能源產業發展重要性與對外貿易效應。當前,全球極端天氣現象頻發,氣候變暖問題日益嚴峻,通過發展核電、風電、水電、光電和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替代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能源成為國際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1]。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既對本國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促進可再生能源消費和經濟可持續發展[2],也能降低大氣污染和碳排放,具有顯著的環保效應和溢出效應[3],還可以通過新能源設備和產品出口減少進口國家化石能源的消耗[4],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也有研究指出,在新能源投資的早期,經濟效應并不明顯,產業發展步入成熟期后,投資效應會顯著增加[5]。二是探討中國新能源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及其國內外原因。羅來軍等[6]總結了中國光電、生物質能、核電、風電等產業發展現狀,指出中國新能源發展面臨三大挑戰:關鍵核心技術落后于國際水平、尚不具備高新技術產業屬性、建設過程存在高耗能高污染問題;除此外,太陽能與風能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7]。史丹[8]認為國際市場萎縮、國內產業發展與市場培育不協調,以及生產力發展與制度建設不協調導致了產能過剩,當然,從中國視角來看,新能源產業國際競爭力不足也是引發外部需求萎縮和國內產能過剩的原因之一。Liu等[9]從價格政策、傳輸能力和裝備制造業結構三個維度分析了風電產能過剩問題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三是分析中國新能源產業對外貿易困境與國際競爭力水平。中國新能源產業對外貿易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曾遭遇到美國“雙軌制反補貼”戰略的嚴重沖擊,陳利強等[10]基于國內主動限權、WTO 限權和擴權、對美積極應訴、對美訴訟和反制的思路提出了應對策略。傅喻[11]認為提高中國新能源產業國際競爭力水平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進而采用貿易競爭力指數分析發現,近些年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競爭力逐步增長,但總體水平仍較低。劉明[12]也認為中國新能源產業國際市場競爭優勢在不斷提升,出口規模受到本國經濟總量、出口對象國消費總量、本國消費總量以及雙邊距離的影響。
如何評估產業國際競爭力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研究的重點。現有文獻在選取指標時一般采用貿易競爭力指數或者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通過貿易變化相對量刻畫某一產品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13],但該指標因不能進一步分解而無法直觀解析影響因素。貿易引力模型常用于影響因素的分析[14],但是研究結果受制于變量的多寡而存在較大差異,且模型的選擇、變量的測度往往依據研究者的主觀判斷,難以獲得準確的結論[15]。恒定市場份額模型通過對一國產業出口變動額的兩層次分解,較為全面而準確地識別出國別和產品需求規模及結構變化,以及產品競爭力變動的影響力大小,成為分析貿易動態變化,探討影響因素及競爭力結構特征的主流模型。CMS 模型最早由Tyszynski[16]提出,將工業制成品貿易增長動因分解為結構效應與競爭力效應兩部分,后由Leamer 等[17]、Richardson[18]以及Sprott[19]等學者引入二階效應,補充定義了結構效應與競爭力效應對貿易額波動的交互影響,從而完成了CMS模型的第一層次分解。Jepma[20]以及Milana[21]將CMS 模型的影響因素進一步細化,其中:結構效應分解為增長效應、市場效應、商品效應和結構交互效應等四部分,競爭力效應分解為整體競爭力效應與具體競爭力效應兩部分,二階效應分解為純二階效應與動態殘差效應兩部分,完成了CMS 模型的第二層次分解。CMS模型的應用十分廣泛,國內學者從多個層面解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波動因素,結論也較為豐富。一是探討中國在多邊貿易組織中的貿易額波動及其影響因素。比如中國對東盟[22-23]、金磚國家[24-25]、絲綢之路經濟帶[26]、歐盟國家[27]等區域經濟體的出口動態及競爭力變化,比較全面地揭示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特點。二是分析中國特定產品出口貿易波動及其影響因素。現有文獻重點關注了中國糧食[28]、高技術產品[29]、機電產品[30]、文化產品[31]的出口貿易波動及其競爭力變化。三是研究能源產業貿易的影響因素。相關研究還比較少,較新的成果涉及到可再生能源產品[32]、光伏產業[33]等領域,因而,對于新能源產業的貿易動態及驅動力的研究仍需進一步拓展。
上述研究為文章選題提供了視角和方法論借鑒,但也存在幾個問題需要拓展。一是新能源產業在實現“雙碳”目標中起到關鍵作用。現有研究多是關心新能源產業的政策效果或單一能源產品的發展特征與趨勢,鮮有文獻探討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波動的驅動因素,特別是國際競爭力水平及其貢獻度。二是采用CMS模型探討新能源產業競爭力效應時,尚未考慮整體競爭力效應是源于出口產品種類的多寡、數量份額的增減,還是相對價格的增減等方面,研究結論缺乏針對性,不利于政策的精準設計。三是關于中國對RCEP 國家貿易變動的研究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RCEP 覆蓋人口眾多,面積廣闊,規模效應巨大,成員國之間貿易互補性強,發展潛力可期,因此,在RCEP框架下分析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波動的驅動因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章做了以下幾點有意義的補充:第一,選取新能源產業作為研究對象,依據HS 編碼與國內慣用標準,將新能源產業細分為核電、風電、光電、水電和生物質能等五大類產業進行結構性研究。第二,采用CMS 模型三層次分解框架,將新能源產業整體競爭力效應按其表現形式分解為價格競爭力效應、數量競爭力效應、種類競爭力效應與競爭力形式交互效應等四部分,從而細化整體競爭力的來源。第三,以RCEP 國家為研究范圍,從整體、國別、產業結構等不同維度分析中國對RCEP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需求拉動力、競爭推動力及其協同效應,希冀在RCEP 協議生效的特殊時點上,深入理解中國對RCEP 國家新能源產業的出口波動特征及其驅動因素。
綜上所述,文章采用CMS模型三層次分解框架,結合2002—2019 年CEPII—BACI 新能源產業HS6 分位數據,從總體、國別、產業等維度分析中國對RCEP 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驅動因素,重點分析進口市場需求和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力大小、結構特征和協同效應,并依據研究結論探討RCEP 框架下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規模和市場份額平穩增長的政策建議。
2 研究方法及數據說明
2.1 CMS模型三層次分解框架
恒定市場份額(CMS)模型假設一國出口競爭力表現為出口產品在進口國進口市場份額的大小,如果市場份額不變,則出口競爭力也不發生變化。由于雙邊貿易額取決于進口需求規模和出口市場份額的大小,那么依據數學上離散變量變化的特征,貿易波動額DEX既取決于進口國需求不變條件下出口市場份額的變化(出口競爭力效應EXE);也取決于出口市場份額不變條件下進口國(區域)需求的增(減)(進口需求效應IME);還取決于進口需求和出口市場份額同時變化的交互影響(供需交互效應EIE),即CMS模型第一層次分解框架具體公式為:

式(1)中:i表示具體產品,j表示單個國家。EX表示中國對區域J產業I的出口額,Qij表示j國家產品i自世界進口總額;Sij表示中國對j國產品i的出口額在j國產品i全部進口額中所占的比重;上標0表示基期指標,1表示觀察期指標,Δ表示觀察期與基期之間的變化量。
當進口對象為多個國家組成的區域和多種產品組成的產業時,依據結構分解分析的思想,進口需求效應IME由兩部分組成,一種是在假定進口國別和產品份額均不變的情況下,單純考慮進口規模波動帶來的影響(進口需求規模效應GIM),另一種是在假定進口總規模不變時,不同國家和產品進口數量此消彼長所帶來的影響(進口需求結構效應SIM)。

式(2)中:Q表示區域J產業I自世界總進口額,Qi表示區域J產品i自世界總進口額,Qj表示國家j產業I自世界總進口額;S表示中國對區域J產業I出口額占J區域I產業總進口的比重,Si表示中國對區域J產品i出口額占J區域i產品總進口的比重,Sj表示中國對國家j產業I出口額占國家j產業I總進口的比重。依據同樣的思路可以將出口競爭力效應EXE的來源分解為整體競爭力效應GEX和結構競爭力效應SEX兩部分,具體公式如下:

在對出口競爭力和進口需求進行整體效應和結構效應識別的基礎上,可以探討供需交互效應EIE的貢獻主要是源自出口市場份額與進口整體規模同時變化的影響(整體交互效應PIE),還是出口市場份額與進口需求結構同時調整的協同影響(結構交互效應DIE)。具體分解公式如下:

上述分析完成了CMS 模型的第二層次分解框架,即對各部分整體效應和結構效應的分解。而需求結構效應SIM還可以依據國別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變動來歸因,一種是假定國別進口數量不變,僅產品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產品需求結構效應PIM),另一種是假定產品進口數量不變,僅國別需求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國別需求結構效應CIM),同樣依據離散變量變化的特征,考慮產品需求結構和國別需求結構同時變動對于出口額的影響(需求結構交互效應CPM)。具體公式如下:

式(5)中,如果研究對象僅有1 個國家,即j=1,則此時CIM=CPM=0,SIM=PIM,即進口需求結構效應僅表現為產品需求結構效應。依據同樣的思路,將結構競爭力效應SEX細分為國別競爭力結構效應CEX、產品競爭力結構效應PEX和競爭力結構交互效應CPX三部分,以在總體上識別不同維度的出口市場份額變化是否有利于出口增長[34]。

式(6)中,如果j=1,則此時CEX=CPX=0,SEX=PEX,即出口競爭力結構效應僅表現為產品競爭力結構效應。但是整體競爭力效應GEX的特征信息并未完全揭示出來。為進一步探討整體競爭力效應的表現形式,參考Hummels 等[35]三元邊際分析框架,以世界市場為參照對象,將中國對區域J產業I的出口市場份額S進一步分解為擴展邊際EM、價格邊際P、數量邊際Q三個部分的乘積,即:

其中:McJ、MwJ分別表示中國c和世界w對區域J的出口額,NcJ、NwJ分別表示中國和世界對區域J出口商品種類的集合,NcJ?NwJ。對 于 商 品i,McJi=PcJi×QcJi,MwJi=PwJi×QwJi。參數?cJi=McJi∑i∈NcJMcJi,?wJi=MwJi∑i∈NcjMwJi分別表示在NcJ類產品中,區域J自中國和世界的i產品進口額所占進口總額的比重。EM測度世界對區域J出口額中,與中國出口產品種類重疊部分所占的份額,該指標越大,說明中國對區域J出口和世界對區域J出口的重疊產品種類越多,當EM=1 時,中國對區域J出口的商品種類覆蓋了世界對區域J出口的所有產品種類,產品廣度達到最大。PQ測度在重疊商品中,中國對區域J出口額與占世界對區域J出口總額的比重,該指標越大,說明中國同類產品在區域J的市場份額越大,產品競爭力越強,即產品深度越大。通過引入時間因素,比較中國針對區域J考察期與基期的市場份額變動,得到整體競爭力效應的分解公式:

式(12)中:整體競爭力效應GEX區分為價格競爭力效應MEX、數量競爭力效應QEX、種類競爭力效應EEX、競爭力形式交互效應MQE等四部分,結合進口需求和出口競爭力的結構效應特征,形成了CMS模型第三層次分解框架,從而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特定產業針對特定區域出口額變動的影響因素、結構特征和優勢來源,各指標具體經濟學含義見表1[36]。

表1 恒定市場份額(CMS)模型指標及其含義
2.2 數據來源與說明
文章基礎貿易數據來源于法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建立的CEPII-BACI數據庫。由于中國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與國際接軌,發生巨大變化;且2002 年以前,RCEP 部分國家新能源產業貿易數據存在大范圍缺失,影響結果的有效性,故而選取2002—2019年HS6分位數據進行分析。參考Wang 等[37]的設定,新能源產業主要涵蓋HS編碼第23章、24章、84章與85章的部分產品,按照產業類型不同,區分為核電、風電、光電、生物質能、水電等五大類產業,每種產業具體包含的HS6 分位產品編碼見表2。

表2 新能源產業分類及對應的HS6分位編碼
3 實證結果分析
基于CMS模型三層次分解框架,本部分從動態特征、國別結構、產業結構等不同維度解析2002—2019 年中國對RCEP國家新能源產業出口波動的驅動因素。
3.1 總體樣本的CMS模型分解
依據世界經濟發展狀況和中國經貿發展重要節點,結合中國新能源產業對RCEP國家出口變動趨勢的特征,文章將樣本期間區分為三個階段予以分別探討,2002—2008 年為中國加入WTO 至美國金融危機發生階段、2008—2013 年為世界經濟緩慢復蘇階段、2013—2019 年為世界經濟動蕩探底以及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階段。
(1)CMS 模型第一層次分解結果(表3)。2002—2019年,中國對RCEP 國家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125.40 億美元,進口需求效應貢獻率15.72%。但在不同時期的貢獻率存在顯著差別,2002—2008 年為28.26%,僅次于供需交互效應,中國加入WTO 初期,依靠低成本優勢迅速打開了更為廣闊的RCEP 市場。2008—2013 年貢獻率升至47.13%,成為主導因素,在金融危機之后,為了刺激經濟復蘇和應對國際環境議題,RCEP 多數國家更加重視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對相關設備和產品的進口需求快速增長。2013—2019 年,受到歐盟對華光伏反傾銷案和此前美國“雙反案”的連鎖影響,中國新能源產業在RCEP國家的出口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疊加世界經濟動蕩下探的影響,RCEP 國家進口需求貢獻率快速下降至-12.39%。進口需求效應的貢獻值也存在相似的波動性,對出口增長的拉動作用并不穩定,但總體而言,RCEP 進口需求擴張對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起到積極作用,但近些年的貢獻率已經不明顯甚至轉為負面影響。

表3 CMS第一層次分解結果及動態特征
2002—2019 年,出口競爭力效應拉動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貢獻率并不顯著,僅為12.24%,但隨時間演進而快速增長。2002—2008 年僅為15.36%,這段時期中國出臺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十五”規劃》,但產業政策、法律法規、激勵機制尚不健全,整體而言處于新能源產業發展的起步階段,國際競爭力尚與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2008—2013 年的貢獻率增至21.23%,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政策,中國新能源產業在各種政策的引導和刺激下發展迅猛,多項指標進入世界前列,出口份額也快速提升。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新能源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核心技術專利較少,依賴政府補貼等問題也日益突出,在經歷歐美等國長期“雙反”調查和懲罰性關稅后,國內新能源產業日益重視核心技術研發、全球產業鏈優化和國內市場開發,進入提質升級的健康發展階段,另外,歐盟在2018年終止了對華光伏產品“雙反”措施,也為新能源產業出口贏得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于是在2013—2019年,中國新能源出口競爭力效應貢獻值與貢獻率大幅提升至20.99億美元和73.85%。總體而言,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快速上升,對出口增長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樣本期間,供需交互效應貢獻率高達72.03%,反映了出口競爭力提升與RCEP 市場需求擴大的協同效應對出口增長起到主導作用。動態來看,雖然供需交互效應的貢獻值和貢獻率均為正值,但是在三個期間的貢獻值依次為21.60、18.56 和10.95 億美元,對出口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步減弱,貢獻率也是相似的趨勢,由2002—2008 年的56.37%下降至2013—2019 年的38.53%。由此可見,雖然出口競爭力和進口需求的交互效應仍然推動出口規模增長,但貢獻程度有明顯弱化的趨勢。
(2)CMS模型第二層次分解結果(表4)。進口需求效應的結構特征顯示,2002—2019年,需求規模效應貢獻率15.92%,前期是出口規模波動的主要因素,而2013—2019 年的貢獻率降為14.85%。需求結構效應的貢獻率比較低,2002—2019 年為-0.20%,但波動比較大,2008—2013 年為6.86%,2013—2019 年大幅降低為-27.23%。上述指標說明RCEP 進口規模擴張對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拉動作用較為顯著,但近些年貢獻率有所降低,而需求結構變化的調節作用也開始呈現負面影響。

表4 CMS第二層次分解結果及動態特征
出口競爭力效應的結構特征顯示,2002—2019年,整體競爭力效應拉動中國對RCEP國家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22.81 億美元,貢獻率18.19%,且動態來看,中國新能源產業在RCEP國家的整體競爭力持續增強,2013—2019年貢獻率達到了81.78%,成為拉動出口增長的主導因素。不過結構競爭力效應在2002—2019 年的貢獻率僅為-5.95%,分階段研究也發現結構競爭力效應持續抑制出口增長,說明中國新能源出口份額結構的變化并沒有契合RCEP市場的需求結構,未能將重心集中在需求規模較大的市場和商品上。
供需交互效應的結構特征顯示,2002—2019年,整體交互效應拉動中國對RCEP 國家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55.61 億美元,貢獻率44.35%,成為拉動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動態來看,整體交互效應貢獻值和貢獻率雖然在各細分區間均為正值,但貢獻程度呈現大幅下降趨勢,至2013—2019 年,貢獻值和貢獻率僅為0.89 億美元和3.04%。結構交互效應對出口增長的貢獻值相對穩定,均在11 億美元左右,但貢獻率有所提升,由2002—2008 年的27.42%增長至2013—2019 年35.49%。因此,從貢獻率來看,結構交互效應逐步成為拉動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
(3)CMS模型第三層次分解結果(表5)。需求結構效應的特征顯示,2002—2019年,國別需求結構效應貢獻了1.31%,產品需求結構效應的貢獻率為-2.81%,需求結構交互效應同樣比較弱,但為正值1.30%。這說明中國農產品出口集中于RCEP進口需求增長較快的國家,但沒有集中于需求增長較快的產品,不過國別需求結構與產品需求結構的同時調整有利于出口規模的增長。動態來看,國別需求結構和產品需求結構變化的負面影響日趨明顯,在2013—2019 年的貢獻率分別達到-16.71%和-35.76%,對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產生嚴重不利影響,不過產品需求結構效應的正向影響也日趨顯著。

表5 CMS第三層次分解結果及動態特征
整體競爭力效應的特征顯示,在2002—2019 年,數量、價格、種類競爭力效應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分別是24.29%、-1.06%、0.17%,意味著中國新能源產業在RCEP 市場的整體競爭力幾乎完全得益于數量份額的大幅擴張,而非價格階梯的攀升,新產品的貢獻度也比較微弱,三者變動的交互效應表現出負面影響。動態來看,由于2013 年遭遇歐美反傾銷調查和加征高額反傾銷稅的影響,中國光伏產業出口數量份額大幅下降而相對市場價格大幅提升,拖累新能源產業出口數量和價格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在2008—2013 年出現方向性逆轉,其余時期對出口增長的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只是貢獻率有所差異,在2013—2019 年,三者的貢獻率分別為110.03%、-25.02%、3.63%,說明當前中國新能源產業在RCEP 市場的整體競爭力仍表現為數量的擴張,此外,參與國際競爭的新產品種類有所增長,而產品的質量階梯所在位置卻有明顯的下滑。因而,中國新能源產業“大而不強”的特征仍未得到有效緩解。
結構競爭力效應的特征顯示,2002—2019 年,國別、產品及二者交互效應的貢獻率與貢獻值皆為負值,顯示出中國新能源產業在出口規模較大的國別和產品市場上,競爭力相對下降;而對于出口競爭力上升的產品和國別,中國的出口規模又比較小,因此,競爭力變化程度與出口規模的配比失調,共同導致國別和產品的結構競爭力效應對總體出口增長起到負面影響。這一特征在不同時期表現相對穩健,只是在2013—2019年,產品競爭力結構效應的貢獻率轉為9.83%,而國別競爭力結構效應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為-15.02%,兩種競爭力結構變化的交互效應有微弱的負面影響,貢獻率-2.74%。因此,如何在RCEP重點國家市場上,提高中國新能源產業競爭力和市場份額是需要重視的問題。
前面提到中國對RCEP 國家的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存在進口需求規模和出口競爭力的國別結構效應和產品結構效應,文章接下來將進一步分析2002—2019 年中國針對RCEP不同國家、不同新能源產業類型的出口增長態勢及其驅動因素。
3.2 國別結構的CMS模型分解
由表6 可知,2002—2019 年中國新能源產業對RCEP各個國家出口額均呈現增長態勢,但國別差異較大,其中,對日本、越南、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增長額都超過10億美元,而對老撾、緬甸、新西蘭、文萊等國的增長額不足1 億美元,下文重點分析中國出口增長額前10位國家的驅動因素。

表6 2002—2019年中國對RCEP國家新能源出口增長的驅動力
CMS 模型第一層次分解結果發現,在日本、越南、韓國、印度尼西亞等中國出口增長額較高的國家,出口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普遍低于進口需求效應;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增長額較低的國家,出口競爭力效應顯著高于進口需求效應,這也解釋了上文整體樣本國別結構效應為負值的結果。從貢獻率來看,供需交互效應在各個市場普遍處于主導地位,說明在考察期間,中國出口競爭力變動和進口需求變化的幅度都比較大,且方向一致,協同促進了中國出口額的增長。
第二層次分解結果表明,針對不同國家,進口需求效應幾乎都體現在整體市場規模的擴大,特別是在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和柬埔寨等國,整體市場規模效應的貢獻率均超過19%。而產品需求結構效應的貢獻率較低,普遍不高于4%,在越南、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等國甚至表現為負值,意味著中國新能源產品未能適應上述四國產品需求結構的調整。整體競爭力水平提高是出口競爭力效應的主要來源,在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貢獻率均超過35%,在韓國、日本、泰國和澳大利亞等國也有不俗的表現。結構競爭力貢獻主要受產品競爭力效應影響,具有明顯的國別結構特征,在新加坡、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表現為微弱的正向貢獻,其中在新加坡貢獻率達到8.72%,顯示出中國新能源產品競爭力的結構調整符合上述國家的市場需求,而在其他國家的貢獻率均為負值。供需交互效應的貢獻主要源于整體交互效應的變化,即出口市場份額變化與進口市場需求變動的協同效應,而結構交互效應的貢獻僅在澳大利亞稍微高于整體交互效應,反映了不同國家在不同產品進口結構上的相對穩定性,但在進口總體規模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新加坡、泰國與印度尼西亞的結構交互效應的貢獻率為負值,說明中國對上述三國的出口產品競爭力變化和進口產品需求結構調整步調不一致,拖累了出口的擴張。
第三層次分解結果表明,數量競爭力效應貢獻率在各個國家均為正值,其中,中國對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的數量份額大幅增加,貢獻率尤為突出。種類競爭力效應在RCEP各個國家的貢獻率均為正值,顯示中國新能源出口產品種類增多,通過產品創新驅動了出口增長,但貢獻率較為微弱,均小于1%。價格競爭力效應僅在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與越南的貢獻率為正值,此時中國出口產品相對價格小幅提高,整體質量階梯有所攀升,但貢獻程度非常低,均不足1%;而在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均為負值,出口相對價格的下降對中國新能源出口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競爭力形式交互效應在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的貢獻率小幅為正,深化了整體競爭力效應和競爭力結構效應的影響;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韓國等國的貢獻值為負,降低了整體競爭力效應和競爭力結構效應對中國出口增長的積極影響。
3.3 產業層面的CMS模型分解
由表7可知,2002—2019 年中國對RCEP 新能源出口增長來源中,光電產業增長最多,達81.78 億美元,占比64.10%,其他產業類型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CMS 模型第一層次分解結果發現,進口需求效應在核電、水電和生物質能產業的出口增長貢獻率均超過30%,特別是生物質能產業,貢獻率高達53.99%,居于主導地位;而在風電和光電產業的貢獻率也分別達到24.48%和8.57%,對出口增長有積極貢獻。近年來,中國新能源產業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參與全球競爭并培育國際市場,雖然光伏產業遭遇多次“雙反調查”失掉部分市場,但仍成為世界能源結構綠色轉型的獲益者,這主要源于中國新能源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不斷增強。各產業出口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均超過10%,其中生物質能產業達到26.20%,表明各產業的出口競爭力都有所增強,推動出口額快速提高。中國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風電產業體系,裝機量和發電量均是世界第一位;中國光電產業占據全球70%以上的市場份額,多晶硅、光伏電池、光伏組件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位,隨著儲能技術和光電轉化效率的提高,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并進一步獲得了進口市場的認可。除生物質能產業外,供需交互效應的貢獻率均占主導地位,進口需求擴大與出口競爭力提高的交互作用,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新能源各產業的出口增長。

表7 2002—2019年中國對RCEP新能源不同產業出口增長驅動力
第二層次分解結果發現,進口需求效應中,各產業的需求規模效應均占據主導地位,RCEP 進口需求規模增長迅速且總體結構穩定,為中國五大類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提供了穩步上升的市場空間;各產業需求結構效應的貢獻率差異較大,核電產業需求結構的變化大幅提升了中國產品的出口,而風電產業和生物質能產業卻輕微抑制了出口規模的增長,其他產業均為正值但貢獻率并不高。整體競爭力效應在五大產業類型的貢獻值與貢獻率均為正值,顯示出五類產業的整體出口競爭力均得到了提高。結構競爭力效應的貢獻,除生物質能外均為負值,表明中國在核電、風電、光電與水電產業的國別和產品份額的調整均不利于出口額增加。五大類產業的整體交互效應貢獻率均處于相對高值,特別是生物質能的貢獻率高達124.09%,顯示出口市場份額變化與總體需求規模變動方向的一致性。生物質能產業的結構交互效應貢獻率為-104.28%,意味著該產業出口市場份額的變化與需求結構的變動方向不一致,在進口需求增長較快的國別和產品市場上,出口市場份額大幅下降,抑制了總體出口額的增長。
第三層次分解結果發現,需求結構效應中,國別需求結構效應也有積極影響,特別是在生物質能、核電、風電和水電產業中影響較大,表明這四類新能源產業出口產品結構較好地適應了進口需求結構的調整;產品需求結構效應則有明顯的差異,僅核電產業的貢獻值與貢獻率為正值,意味著核電出口結構適應了產品需求結構的調整,集中地向需求快速增長的產品種類大規模出口,而其他產業的產品需求結構效應貢獻值與貢獻率均為負值,在這些產業,中國出口結構未能適應進口產品需求結構的調整,對出口增長起到顯著的抑制作用;需求結構交互效應在核電與風電產品上的貢獻率為負值,降低了進口國別與產品需求變化的影響,在生物質能、水電與光電產業的貢獻率雖為正值但促進作用微弱,僅1%左右。整體競爭力效應中,數量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在各類產業中均居首要地位,特別是在光電產業中,貢獻率高達44.94%;種類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均為正值,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產品種類更加豐富,特別是核電產業最為明顯,但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并不高,僅為1.64%;價格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也不高,絕對值在1%左右,其中,在光電產業的貢獻率為負值,意味著中國光電產業出口相對價格有所下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出口質量水平的下降,抑制了出口額增長;而其余四類產業的出口相對價格均實現了提升,對出口額增長起積極作用;競爭力形式交互效應在光電產業的貢獻率顯著為負,其他產業均為正值,但貢獻率比較低。結構競爭力貢獻中,國別競爭力結構效應僅在生物質能產業的貢獻率表現為正值,其余產業均為負值,負向貢獻率意味著出口國別份額結構的調整不符合進口市場需求結構,在具有優勢的國別市場中所占份額下降明顯,從而抑制了出口增長;產品競爭力結構效應在生物質能產業的貢獻率顯著為正,在進口規模較大的產品上所占市場份額明顯增長,促進了出口額的增長,而其他產業的貢獻率均比較微弱;競爭力結構交互效應在生物質能、光電與風電產業的貢獻率為負值,深化了國別和產品市場份額調整對光電產業出口額增長的負面影響,抑制了國別和產品市場份額變化對生物質能產品出口增長的正面影響。
4 出口波動的影響因素
在CMS 模型分解的基礎上,本部分采用計量經濟學模型進一步探討2002—2019年中國新能源產品出口規模EX、出口競爭力S 以及RCEP 國家進口規模D 的影響因素。依據國際貿易引力模型和匯率理論選擇進口國GDP、貿易開放度、相對匯率、進口關稅和中國GDP 作為中國新能源產品出口規模的影響因素;依據國際貿易相似需求理論、貿易自由化理論、匯率理論選擇進口國電力需求規模、人均GDP、匯率水平、進口關稅作為RCEP國家進口總規模的影響因素;依據國家競爭優勢理論選擇中國人均GDP、電力研發投入、金融支持、人民幣匯率、人文服務進出口作為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過程固定年份效應和國別效應,以盡可能消除時間趨勢性因素和國別結構性因素對結果的影響,各變量指標的符號、含義、數據來源、單位、理論基礎、預期影響方向見表8。

表8 出口競爭力影響因素及數據來源
實證結果見表9。第一,中國對RCEP 國家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主要是由國內生產能力提高驅動的,同時受到進口國貿易開放水平的正面影響,特別是降低進口關稅能夠顯著提高貿易規模,但是進口國貨幣相對人民幣貶值卻不利于中國出口增長,上述結果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只是出口規模與進口國GDP的正相關性并不顯著,這反映了進口國生產總值的增長并不必然帶動新能源產業的需求,特別是某些低收入國家,在越過庫茨涅茨曲線頂端之前仍然以傳統能源開發利用為主。第二,新能源進口需求規模與進口國電力總消費量顯著正相關,這反映了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多數國家會將新能源作為電力供給的主要方式,并隨著進口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長,上述結論高度契合了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活質量訴求之間的邏輯關系;另外,進口需求規模還與RCEP國家對華旅游服務出口規模顯著正相關,這反映了人員往來交流與雙邊商品貿易的正向互動關系,但是進口需求規模受到進口國貨幣匯率貶值以及進口關稅上升的抑制,這與貿易成本理論的預期結果完全一致。第三,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市場份額與國內人均GDP、電力行業研發投入規模、資產負債水平、人民幣匯率顯著正相關,因而,緩解新能源產業資金約束、提高企業科技投入、提升經濟發展水平、人民幣貶值均有利于提高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競爭力;此外,出口競爭力還與中國文娛服務進口規模正相關,這從側面反映了雙邊文化交流不但有利于增進人員往來和互信,也有利于增強對雙邊商品的認知和貿易。

表9 實證分析結果
5 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文章基于CMS 模型三層次分解框架,研究了2002—2019 年中國對RCEP 國家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驅動力、結構特征及競爭力貢獻,主要結論有以下幾點。
(1)中國新能源產業在RCEP市場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主要集中在日本、越南、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和光電、水電、核電、風電等產業類型;RCEP 總體需求規模擴大與國別需求結構的變化,拉動了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快速增長;而產品需求結構的調整對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起負面作用;動態分析發現,RCEP 國家新能源產業進口規模不穩定,致使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遭遇較大波動性。
(2)中國新能源產業在RCEP市場的總體競爭力有所提升,較為積極地推動了出口規模增長;但出口份額的結構變化并沒有契合進口需求特征,結構競爭力效應呈負面影響。在菲律賓、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出口規模較大的國家和水電、核電、風電、光電產業等產品市場上,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份額被大幅侵蝕,嚴重抑制了出口規模增長;多重結構變動的交互效應深化了這種不利影響。
(3)中國出口競爭力變化較好地適應了RCEP總體進口規模與進口結構的變化,整體交互效應對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增長的影響居首要地位,這一特征在越南、泰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等市場和生物質能、光電、核電等產業上表現較為明顯。
(4)整體競爭力效應幾乎完全得益于數量份額的大幅擴張,新產品的貢獻度比較微弱,而相對價格的貢獻率則一直下降,這種“大而不強”的出口特征在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日本、泰國和菲律賓等主要出口市場,以及光電等產業中尤為明顯。結構競爭力效應顯示中國新能源產業在出口規模較大的國別和產品市場上,競爭力均相對下降,僅在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和生物質能產業上有所提升。
(5)實證研究發現,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規模與國內生產能力、進口國經濟總量和貿易開放度正相關,與關稅水平和進口國貨幣貶值顯著負相關;而RCEP國家新能源產業進口規模與人均GDP、電力消費量、旅游服務出口規模正相關,但會受到進口國貨幣匯率貶值以及進口關稅上升的抑制;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競爭力與經濟發展水平、金融支持力度、研發投入強度、人民幣貶值幅度,以及與RCEP國家進口的文娛服務規模顯著正相關。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得到如下政策啟示:①用足用好RCEP 便利政策,深入挖掘與RCEP 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相匹配的市場潛力,增強進口市場規模效應的拉動作用;同時密切關注RCEP區域內國別和產品需求結構的變化,通過降低關稅壁壘及時調整出口重點,提高國別需求結構效應和產品需求結構效應的拉動作用。②加大新能源產業科研投入強度,不斷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質量水平,增強價格競爭力水平;加強新能源產業金融支持力度,做強做大產業集群,發揮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優勢,擴大數量競爭力優勢;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持續推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新產品,通過差異化策略,提高種類競爭力水平。同時優化新能源產品出口結構,不斷適應RCEP國別和產業需求結構特征,提升國別競爭力結構效應和產品競爭力結構效應的推動作用。③加強與RCEP 國家的交流與合作,通過擴大人文服務交流、旅游服務開放、貨幣互相兌換等方式,促進雙邊政策溝通、民心相通、資金融通,開發潛在貿易機會、降低匯率波動風險、提高商品貿易效率,尋求更多文化共同點、價值共同點、利益共同點,推進進口需求交互效應和競爭力結構交互效應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