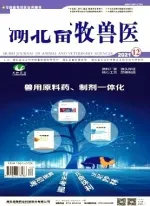村莊規劃的演進分析
向棟良
(廣東中地土地房地產評估與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廣州 510520)
村莊規劃是盤活農村土地、解決“三農”問題、優化鄉村空間結構、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性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然而,中國村莊規劃理論研究相對緩慢,實施與管理尚未到位,無法有效遏止村域內建筑布局混亂、村民建設無序、土地資源浪費等現象[2]。據廣東省國土資源廳2017 年以來開展的第二輪大調研結果顯示,廣東省農村建設缺乏必要的規劃引導和約束,導致村莊布局散亂,及亂搭亂建、土地粗放利用等問題突出。
科學地構建合理、有序的村莊規劃研究體系已成為中國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也是推動宅基地有序利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有效盤活、農用地科學保護等農村“三塊地”改革的重要路徑,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2005 年頒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搞好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村莊、集鎮規劃,引導農戶和農村集約用地”。2016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科學編制縣域鄉村建設規劃和村莊規劃”。2006 年頒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將村莊規劃正式納入各級政府的工作范疇,并要求各級政府加強村莊規劃的資金支持和開展相應的試點工作。2017 年頒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快修訂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大力推進縣域鄉村建設規劃編制工作。”2018 年頒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允許縣級政府通過村土地利用規劃,調整優化村莊用地布局,有效利用農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設用地”。與此同時,學術界從村莊規劃的理論重構、問題與對策、編制與實施機制的創新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3,4]。但仍無法有效地優化鄉村空間結構,平衡村域內的各類“人地”沖突、“人居”沖突、“人人”沖突。尤其是經濟快速發展地區內的村域,受雙重二元結構(靜態的戶籍身份和動態的外來人口與本市人口)的作用,村鎮規劃發揮的調節、約束作用相當有限。以經濟快速發展地區的廣州市為例,其先后在1997 年和2008 年2 次編制了村莊規劃,以緩解城鄉發展之間的各類矛盾,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兩輪的規劃都未能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原有的各種沖突[5]。
結合文獻計量、數據挖掘及統計方法的定量方法,在中國知網數據庫1991—2018 年的文獻數據基礎上,以“村莊規劃”為篇名進行檢索,經數據清洗后,共獲得文獻541 篇,并采用社會網絡分析軟件CitSpaceIII、Ucinet 及統計分析軟件 Spss 進行量化分析,在明晰中國村莊規劃研究時空分布特征的基礎上,探索中國村莊規劃研究的演進規律,及其與村莊規劃政策的協同性,形成村莊規劃研究的發展態勢,進而提出村莊規劃研究的發展要點,一方面為揭示村莊規劃研究的發展動態,構建相對科學、合理的村莊規劃研究體系提供依據;另一方面為規劃學研究提供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新方法思路。
1 村莊規劃研究時空分布特征分析
對村莊規劃研究進行時間和空間特征分析,探討中國村莊規劃研究發展路徑,有利于形成相對清晰的村莊規劃研究認知體系,為構建村莊規劃研究的演變和發展規律體系提供支撐。
1.1 時間分布特征分析
利用 Spss 軟件對 1991—2018 年 28 年的 541 篇文獻數據進行時間分布特征分析,可以發現,28 年來,中國村莊規劃研究呈整體上升趨勢。其趨勢線為y= 1.542 8e0.16x,R2= 0.770 9(R2越接近 1,代表擬合效果越好),具體分為3 個研究階段。
1)1991—2004 年,中國的村莊規劃研究處于探索階段。其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增速平緩,共發表論文68 篇,占總發文量的6.76%。2000—2002 年出現了一個研究小高峰,其原因是受規劃不到位的影響,中國農村地區建房用地粗放問題越發明顯。2000年,農村地區人均住房面積為24.8 m2,遠高于同年的城市地區人均住房面積,比1980 年擴大了近3 倍,而其占用的土地則遠高于這一比例。正因為部分村莊的規劃意識淡薄,未編制村莊規劃或者不按照已編制的村莊規劃進行建設,造成了亂占亂建、占用耕地、盲目建設等問題及空心村(棄舊宅,建新宅)等隱患[6]。村莊規劃問題成為當時社會熱點話題。輿論導向促使學術界對村鎮規劃的共性問題進行宏觀層面的探討。
2)2005—2012 年,中國村莊規劃研究處于全面發展階段。其研究成果相對豐富,增速明顯,共發表論文491 篇,占總發文量的48.81%,平均每年發文量為61 篇。其原因是,2005 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寫進了公報和“黨中央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內。同年,第八個聚焦農業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加強村莊規劃和人居環境治理”。“新農村建設,規劃先行”的理念成為社會的共識。但近80%的村莊尚未編制村莊規劃或編制的規劃不完全符合《村莊規劃標準》,其導致的“臟、亂、差、散”、公共基礎配套設施不足、空心村問題凸顯仍是該階段農村地區的主要問題。由于國家層面對村鎮規劃的重視程度加強和現實中農村地區的規劃亂象,推動學術界對村莊規劃個案性進行微觀層面的研究,使得村莊規劃研究更具針對性和特指性[7]。
3)2013—2018 年上半年,中國村莊規劃研究處于平穩發展階段。其研究成果相對豐富、增速逐趨平緩,共發表論文447 篇,占總發文量的44.43%,平均每年發文量為74 篇。隨著“城鄉統籌發展”“特色小鎮”“城市更新”等新概念的提出,“村莊規劃”研究開始跳出村域的視角,立足于“社會—經濟—自然”的生態系統,從村莊規劃的機制要素出發,探討城市與鄉村、鄉村與產業、村民與鄉村等關系的協調。
1.2 空間分布特征分析
通過Ucinet 軟件對村莊規劃研究的高頻作者進行集群分析發現,村莊規劃研究的高頻作者集群網絡節點為339 個,連接為127 個,密度為0.001 6,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大分散是指在宏觀層面,“村莊規劃”研究的作者相對較多。但大部分作者的研究相對分散、各個作者集群的密切度低,尚未形成一定合作強度和互引關系的核心作者網絡結構。小集中是指部分作者已經發展為固定作者集群,如浙江大學的葛丹東、華晨組成的作者集群、浙江師范大學董魏魏、劉鵬發、馬永俊組成的作者集群等。但集群內的各個作者相對勢力均衡,尚未形成學術領袖的格局。除了鄧柏基、陶修華、彭俊杰、陳軍組成的作者集群,王栗、熊燕、劉賀、褚天嬌組成的作者集群,任朋朋、張丹華、侯愛敏、高菲組成的作者集群外,其余集群內的各個作者雙向密度值均相等。浙江大學的葛丹東、華晨組成的作者集群中,葛丹東與華晨雙向密度值均等于1。印證了村莊規劃研究時間分布特征的分析結果,即中國的村莊規劃研究尚處于發展階段,并沒形成主流的、權威的學術觀點、學術領袖,及完整的、完善的研究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各作者集群之間缺乏必要的學術研究聯系,不利于村莊規劃研究的發展。
通過Citespace 軟件對村莊規劃研究的高頻研究機構集群分析發現,村莊規劃研究的高頻機構集群網絡節點為331 個,連接為72 個,密度為0.001 3,呈現“總體分散、局部集中”的格局。一方面,各個研究機構之間的聯系度較低,不同機構之間的學術交流亟待加強。另一方面,村莊規劃研究以高校和研究院為主。發文量在5 次以上的機構發文數占前40個機構發文數的1/2 以上,這說明村莊規劃研究機構較為集中,不同研究機構之間的科研能力差異并不明顯。同時,研究機構以建筑學、規劃學為基點,展開相關的村鎮規劃研究,如華南理工大學研究團隊關注村莊規劃編制的方法和途徑,浙江大學研究團隊注重探討村莊規劃實施過程中的共性問題,東南大學研究團隊則從新農村建設與村莊規劃協同性的視角探討創新性規劃的編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團隊內的跨學科聯系相對不足。建筑學、規劃學與社會學、管理學等跨學科聯系而形成的村莊規劃研究十分欠缺。此外,研究機構之間,尤其是高校與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網絡已見雛形,如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廣州市規劃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上海市城市規劃協會-上海大學等。但合作機構網絡之間的聯系強度尚不顯著,跨學科的研究機構合作甚少。
村莊規劃研究機構集中在廣東、浙江、江蘇、北京、上海等東部沿海地區,約占研究機構總量的84%。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區和四川、云南、陜西、廣西等西部地區的研究機構相對較少,合計占研究機構總量的16%。這表明,村莊規劃研究可能與研究機構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和工業化推進程度、村落的現代化程度等因素相關。且各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地域性相對明顯,以所在地為研究對象,跨地域研究的現象較少,不同地域研究機構關注的問題存在一定的差異。具體來說,東部沿海地區村莊的發展程度較中西部地區高,其村莊規劃已不僅限于完善基礎配套設施、合理利用土地,已開始關注在編制或實施村莊規劃過程中,公眾參與、鄉村文化傳承、產業培育的問題。中部地區受政策的導向,如“中部崛起”“產業轉移”“新農村建設”等,城鄉差距漸顯。其村莊規劃研究的重心是“協同”,如鄉村內、鄉村與城市的社會關系重構、村莊規劃與新農村建設的協調等。西部地區則由于城鄉差距不大,其村莊規劃并沒有關注過多外部因素,仍立足于各個地區的村域實際情況,探討相對完善的村莊規劃編制方式和實施途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發展狀況不同的地區,其關注的村莊規劃研究內容也不盡相同。
2 村莊規劃演進規律分析
自1991 年起,村莊規劃學科研究的成果主要以村莊規劃作為中心展開,并形成了與之緊密相關的研究體系。在結合村莊規劃時間分析特征的基礎上,研究將村莊規劃研究分為1991—2004年、2005—2012 年、2013 至 2018 年上半年 3 個重要階段,進行關鍵詞主題演進分析。
1)村莊規劃是1991—2004 年的高頻關鍵詞,頻率高達333 次,中心性高達1.26,是整個研究體系的重心,其次是“村莊”“農民”“城鎮建設”,頻率分別為21、11、2。20 世紀 80 年代,受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地區的村民在其收入增加后,進行了大規模的農村建設活動,但由于缺乏科學的村莊規劃,農村建設基本上處于無序的狀態。故此,整個90 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村莊規劃的問題展開。一方面,村莊規劃的先導作用弱,所謂的規劃只是在村域現狀上進行布局、規整,缺乏長遠的產業謀劃,也與經濟發展速度不相匹配;另一方面,村莊規劃的約束作用不強,在執法不嚴的情況下,部分村莊的規劃形同虛設,盲目建設、隨意建設等現象屢禁不止。21 世紀初期,部分學者留意到村莊規劃的先導性與約束性較弱,是源于規劃的建設與管理不足。大部分地區重規劃編制工作,輕管理與監督的現象嚴重,部分地區不嚴格按照規劃要求建設,政府部門充當“守夜人”的職責,只負責發證登記,建設、監管全由村集體負責。在熟人社會、血緣體系內,村集體對村民建房的約束效力相對較弱,既不會過多干預村民的建房行為,也有可能加劇“批房”不透明等“尋租行為”[8]。
2)2005 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對村莊規劃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村莊規劃除了規定村容整潔、基礎設施配套等社會建設外,還著眼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層面,既要合理規劃村社工業園區,為產業發展提供載體,也要合理布局文化設施、保護村域的古建筑與傳統鄉風文明。“新農村建設”“新農村”“新農村規劃”分別成為 2006 年、2007 年、2009 年的高頻熱點詞,頻次為 45、2、2 次,中心性為 0.11、0、0。其后,部分學者總結了村莊規劃實施程度低的原因,即過去的村莊規劃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型規劃,側重于“物的規劃”,但不同村域的經濟狀況、個體特征不同,個體對于村莊規劃的訴求也不一致,且大部分村域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文化特性,村民對村莊的發展有一定的認識,是“個體訴求的規劃”,也是內生秩序型的溝通規劃。村莊規劃更應以村民的實際需要為要旨,從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構建科學的規劃機制。村莊規劃應注重事前咨詢與調研,設立助理村莊規劃師崗位,了解村民的意愿[9];應定期進行事中公開,提高規劃編制的透明性,降低村民個體對政策風險的預期,鼓勵村民團體參與規劃編制論證。注重事后監督與評估,支持村民團體對規劃實施狀況進行監督,鼓勵村集體定期開展規劃效益評估。“公眾參與”“編制工作”“規劃管理”分別成為2009 年、2010 年、2012 年的高頻熱點詞,頻次為 17、4、2 次,中心性為0.06、0.07、0。
3)2013 年,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確定全國28 個村莊成為規劃示范村。“試點工作”成為當年的高頻熱點詞。其后的村莊規劃研究主要以“村莊整治”和“傳統村落保護”兩大主線展開,分別是在2013 年“試點工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新型城市化建設”主題(2015 年的高頻熱點詞),引申到村莊的有機更新環節,包括從“省-市-縣-鄉”的層級,對村莊規劃提供具體的目標,形成目標明確、職能清晰的空間規劃體系。同時,研究熱點還包括避免大規模的拆建,以及加強對原居民區進行控制和引導,對村落內部的建筑進行“微改造”,即不改變建筑的主體結構,注重立面的裝飾和美化,道路、水體、街巷等路徑的優化,進一步尊重鄉村發展的歷史脈絡,保存村域的人文氣息和鄉村文化。研究熱點的興起是源于學者們發現鄉村建設不應等同于規劃區內的社區建設,鄉村建設不應一味追求規整,而應該保留傳統村落的文化,而鄉村文化很大程度是以建筑、街巷、水體等為載體。進行村莊規劃,應對能體現歷史文化的建筑予以保留和修繕,對于質量較好,但與環境不協調的建筑物予以整治,對于質量較差或違規違章建筑予以拆除。
3 討論與思考
1991—2018 年中國村莊規劃研究發展相對穩定,整體的研究成果數量呈現指數性增長,并形成了主線相對明確,分支相對豐富的高頻關鍵詞網絡。且部分研究成果對村莊規劃的相關政策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相對不足的是,研究成果尚未形成一定合作強度和互引關系的核心作者網絡結構,研究成果的多學科共同發展態勢不明顯,定量分析應用程度低。21 世紀的村莊規劃是產業規劃、文化規劃、生態規劃等多維度的體系,但村莊規劃與經濟學科、文化管理學科、生物學科等交流、合作相對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村莊規劃研究的多維度發展。第二十個聚焦“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鄉村振興,規劃先行”理念,其核心是通過規劃提升鄉村的形象、改善鄉村的落后面貌,為鄉村的產業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載體保障。而實現上述目標,既需要加強多學科的交流,也需要進行相對應的統計學分析,以客觀的數理分析,明確影響村莊規劃實施、管理、監督以及產業培育、人居環境優化、生態環境保護等主導因素。
已有研究對于國外村莊規劃的一系列研究關注度不足,尚未形成一個突出的演進聚類。中國的城市化推進、土地國情、法律體系、村域特點、村民心理特征等與國外不盡相同,但借鑒國外的研究理論,能夠彌補中國村莊規劃理論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且以中國本土情景,解讀國外的研究理論,更有可能推動該理論的創新。
小部分研究成果滯后于現實的需求,只是對過去成果的簡單歸納與總結,對規劃政策的推進作用尚未明顯。部分以探討各個試點案例為主,側重于分析案例的存在問題,并提出對應的策略,或依據政策,結合時政熱點進行規劃調整探討,提出相對應的完善規劃編制工作的建議。其研究思路使得村莊規劃研究偏向于應用性研究,導致村莊規劃的開創性理論研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