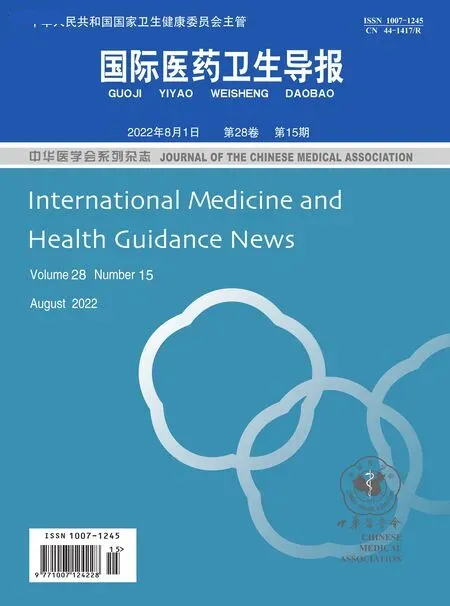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淋巴瘤4例并文獻復習
楊彩紅 李婉君 蕭韻健
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東莞市人民醫院風濕科,東莞 523000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種多系統多器官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臨床表現多種多樣,病程發展與轉歸具有較大的個體差異,與一般人群相比,SLE患者并發淋巴瘤等血液系統疾病的風險增高[1]。
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結或淋巴組織的惡性腫瘤,也可累及全身各器官,主要表現為無痛性淋巴結腫大、肝脾腫大,常伴有發熱、消瘦、盜汗等全身癥狀。當SLE 合并淋巴瘤時因二者臨床表現相似,鑒別困難,增加了疾病診治的難度。本文報道4例SLE合并淋巴瘤的患者,對兩者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希望為今后臨床實踐提供經驗,避免漏診和誤診,并及時給予正確的治療。
臨床資料
1、例1
患者女,54 歲,因“左上腹陣發性隱痛10 余天”于2018 年6 月就診于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既往史:7年前因“顏面紅斑”確診SLE,長期于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門診隨診。入院時抗風濕方案為“甲潑尼龍(輝瑞制藥有限公司,4 mg×30 片)6 mg qd、羥氯喹[賽諾菲(杭州)制藥有限公司,0.2 g×10片]0.2 g qd、來氟米特(欣凱制藥有限公司,10 mg×10 片)10 mg qd”。入院查體:全腹軟,左上腹及臍下有壓痛,無反跳痛。入院前外院查上腹部CT 提示:腹膜后多發占位,不除外淋巴瘤。入院后行超聲引導下腹膜后腫物穿刺活檢,病理提示非霍奇金淋巴瘤,B細胞來源,分型符合彌漫大B 細胞淋巴瘤(圖1)。2018 年 6 月 19 日 起 予 R-CHOP[ 美 羅 華(Roche Diagnostics GmbH,100 mg/10 ml)500 mg 、環磷酰胺(山西普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0.2 g)1.0 g、表柔比星(輝瑞制藥有限公司,10 mg)70 mg、長春地辛(杭州民生藥業有限公司,1 mg)3 mg、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90 mg 方案化療 8 期,過程順利。2018 年 9 月 12 日、2019年9月18日復查PET/CT 示病灶較前縮小,糖代謝未見增高,治療有效。化療后予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10 mg qd 控制SLE,隨訪至今(3 年余)病情穩定。

圖1 例1 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淋巴瘤患者腹膜后腫物穿刺組織光鏡所見(HE ×400):淋巴濾泡結構破壞,見異型淋巴樣瘤細胞彌漫增生,細胞中等偏大,核呈圓形或稍不規則,可見核仁,核分裂相易見
2、例2
患者女,47 歲,2008 年因“顏面蝶形紅斑、關節痛、脫發”于外院診斷為SLE,予激素[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30 mg qd]及中成藥治療。2013 年5月因雙下肢浮腫于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住院,行腎臟穿刺活檢術,腎臟病理符合局灶增生性狼瘡性腎炎伴基底膜增厚,Ⅲ(A)+V 型,AI=2、CI=1。先予激素+環磷酰胺[(山西普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0.2 g)累積劑量23.4 g]抗風濕治療,病情緩解后改為激素+嗎替麥考酚酯(湖北濟安堂藥業有限公司,0.25 g×40 片)維持治療。2015 年患者因“右乳腫物”于外院確診為“右乳淋巴瘤(彌漫大B 細胞)”,停用免疫抑制劑,予放化療治療,具體方案不詳,過程順利。目前予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5 mg qod 及羥氯喹(上海上藥中西制藥有限公司,0.1 g×14片)0.2 g bid控制SLE,隨訪至今,病情穩定。
3、例3
患者女,61 歲,因“關節痛 1 月余,發熱 2 h”于 2016 年7月就診于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入院查體:淺表淋巴結未及腫大,雙膝關節、踝關節腫脹、壓痛,雙下肢中度凹陷性浮腫。入院后完善相關檢查提示抗核抗體(ANA)1∶320(顆粒型),抗SSA/Ro60、抗心磷脂抗體免疫球蛋白(Ig)G、抗心磷脂抗體IgM 陽性,補體C3 低下(0.49 G/L),輕度貧血(110 g/L),coomb’s 試驗弱陽性,診斷SLE,予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甲氨蝶呤(上海上藥信誼藥廠有限公司,2.5 mg×100 片)、羥氯喹(上海上藥中西制藥有限公司,0.1 g×14片)改善病情抗風濕治療,病情穩定出院。2016 年10 月患者于當地診所拔牙后出現創口愈合不良,反復牙齦腫痛,2016 年11 月至外院行“左側牙齦切除術”,術后病理符合彌漫性大B 細胞淋巴瘤,Non-GCB 亞型。遂再次入住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完善PET/CT 示左下頜高代謝腫塊,左頸部、頜下、頦下及胃小彎側多發高代謝腫大淋巴結,胃體大彎側多發高代謝結節,均考慮為淋巴瘤;肝右葉高代謝結節,不除外淋巴結累及。骨髓涂片:粒、紅、巨三系增生活躍,個別見幼淋巴細胞。2016 年 12 月 10 日起予 R-CHOP[美羅華(Roche Diagnostics GmbH,100 mg/10 ml)500 mg、環磷酰胺(山西普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0.2 g)1.0 g、表柔比星(輝瑞制藥有限公司,10 mg)60 mg、長春地辛(杭州民生藥業有限公司,1 mg)3 mg、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100 mg]方案化療8 期+美羅華(500 mg)單藥維持治療 2 次。2017 年 11 月 22 日復查全身 PET/CT 原左下頜高代謝腫塊,左頸部、頜下、頦下及胃小彎側多發高代謝腫大淋巴結,胃體大彎側高代謝結節均已消失,肝右葉片狀高代謝灶,多考慮為炎癥,建議密切復查。化療后予羥氯喹(上海上藥中西制藥有限公司,0.1 g×14 片)0.2 g bid 控制SLE,隨訪至今病情穩定。
4、例4
患者女,56 歲,因“雙下肢浮腫、關節痛 1 周,發熱 1 d”于2016 年4 月29 日入住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風濕科。入院查體:體溫36.9 ℃,心肺聽診未及異常,腹軟,無壓痛及反跳痛,雙下肢輕度凹陷性浮腫。既往確診SLE 10年,長期服用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10 mg qd、復方環磷酰胺片(天津金世制藥有限公司,50 mg×24 片)100 mg qd 控制病情。入院后體溫最高39.0 ℃。完善相關檢查;血常規:白細胞0.4×109/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0.3×109/L,淋巴細胞絕對值0.04×109/L,紅細胞2.63×1012/L,血紅蛋白 94 g/L,血小板 146×109/L。ANA 1∶100 陽性;IgM 0.14 G/L,IgG、IgA 正常;補體正常。感染性疾病篩查均陰性。當時考慮環磷酰胺所致粒細胞缺乏,停用環磷酰胺,予升白細胞、預防性抗感染治療,患者無發熱,復查血常規,白細胞4.1×109/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2×109/L,紅細胞2.59×1012/L,血紅蛋白90 g/L,血小板158×109/L。病情好轉,于2016 年5 月13 日出院。出院后口服強的松(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5 mg×100 片)10 mg qd 及羥氯喹(上海上藥中西制藥有限公司,0.1 g×14 片)0.2 g bid 控制病情,門診隨診,分別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及 2016 年 8 月 26 日復查血常規正常。患者于2016 年10 月28 日因“咽痛、咳嗽、咳痰、發熱2 d”再次入住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風濕科。入院查體:體溫37.5 ℃,雙肺可聞及少許濕啰音,雙下肢輕度凹陷性浮腫。多次查血常規提示三系減少:白細胞(0.40~2.14)×109/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0.1~0.3)×109/L,淋巴細胞絕對值(0.1~0.2)×109/L,血紅蛋白60~90 g/L,血小板(3~14)×109/L;白蛋白20.9 g/L;肌酐145.8 μmol/L;降鈣素原1.70~4.57 μg/L;補體 C3 0.81 G/L,補體C4 0.27 G/L;IgM 0.06 G/L,IgG、IgA正常;ANA 1∶100陽性;抗SSA/Ro60kD 抗體陽性,抗SSB/La 抗體陽性;鐵蛋白>1 500.0 μg/L;淋巴細胞免疫分析:B 淋巴細胞0.73%[5.0~18.0],自然殺傷細胞 8.08%[7.0~40.0],T 淋巴細胞(CD3+)90.23%[50~84],輔助性/誘導性 T 細胞(Th)18.26%[27~51],抑制性/細胞毒性 T 細胞(Ts)70.60%[15~44],Th/Ts 比值0.26[0.71~2.78]。痰培養銅綠假單胞菌陽性。肺部CT:雙肺上葉尖后段、雙肺下葉多發炎癥,右肺中葉內側段及右肺下葉背段少許纖維條索灶,右肺上葉多發點狀小結節狀高密灶,雙側胸膜增厚,雙側胸腔及右側斜裂積液,心包腔少量積液,雙側鎖骨上、縱隔內、主動脈弓旁多發淋巴結,部分增大。患者于2016 年11 月1 日完善骨髓穿刺活檢,骨髓涂片提示骨髓增生活躍,成熟淋巴細胞形態不規則,個別見嗜血細胞,易見體大,核不規則、核仁不明顯的分類不明細胞。骨髓病理符合T 細胞淋巴瘤累及骨髓(圖2)。患者確診T 細胞淋巴瘤,轉血液淋巴瘤科進一步治療,因合并肺部感染,全血細胞減少,血小板極度低下,化療風險高,患者及家屬放棄搶救治療,于2016 年11 月19 日呼吸心跳停止,宣告臨床死亡。

圖2 例4 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淋巴瘤患者髂后上棘骨髓穿刺活檢病理結果(HE ×400):骨髓增生大致正常,造血組織約占50%,骨髓腔內見大量大細胞增生,細胞胞漿較少,核大,圓形或不規則形,可見腎形核,淺染,核仁明顯,核分裂象易見。粒系細胞可見,偏成熟階段粒系細胞明顯減少,紅系以中晚幼階段細胞為主,巨核系細胞易見,以分葉核巨核細胞為主,并可見單核細胞增多
討 論
SLE 是一種臨床表現多樣、累及多個系統和臟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許多研究均證明其可增加淋巴瘤的發病風險,是正常人群的3~40倍[2]。SLE 與淋巴瘤關系密切,SLE可在發病前、診斷時及發病后多年被確診為淋巴瘤,后者也可以模擬前者的臨床表現而造成誤診。例1、例2、例4患者均是在SLE診斷、治療多年后確診淋巴瘤。例3患者雖然按照標準可診斷為SLE,但這些指標缺乏特異性,SLE 較為特異性的抗體(如抗dsDNA 抗體、抗Sm 抗體)均正常,臨床表現方面僅有關節炎、發熱這些非特異性表現。據文獻報道,淋巴瘤患者亦可出現多種自身抗體陽性,如ANA(陽性率31.5%)[3]、抗磷脂抗體(陽性率40.3%,其中抗心磷脂抗體陽性率11.6%,抗糖蛋白I抗體陽性率32.6%)[4],Coomb’s試驗陽性(霍奇金淋巴瘤陽性率為9.9%)[5]等。該患者診斷SLE后3個月確診淋巴瘤,考慮為淋巴瘤模擬SLE的臨床及實驗室表現可能性更大。
SLE 合并淋巴瘤的發病機制目前尚不明確,推測可能與免疫功能紊亂、狼瘡病情活動、感染、遺傳、年齡、藥物等因素有關。⑴SLE 患者存在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缺陷。SLE 患者發生腫瘤的高風險可能與自身免疫監視功能受損有關[6]。⑵持續的病情活動、補體低下是發生淋巴瘤的重要危險因素。研究認為,SLE 活動時由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IL)-6,能夠促進T細胞和B細胞的增殖及分化并減少其凋亡,而低補體血癥能導致B淋巴細胞長時間生存,從而發生癌變的可能性增加,這些在惡性淋巴瘤的發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7-9]。⑶病毒感染。淋巴瘤的發病與EB 病毒感染相關,主要機制是病毒感染對機體局部抗原造成慢性刺激,引發免疫反應,從而誘發了惡性淋巴瘤[10-11]。SLE 治療過程中因長期應用免疫抑制劑導致免疫功能異常,增加了EB 病毒感染的風險,從而增加了淋巴瘤的發生。⑷遺傳因素。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相關基因可能與SLE、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發病均相關,可能是二者共同的遺傳易感基因[12]。⑸年齡。Bernatsky 等[13]的一項國際多中心研究顯示,年齡≥65 歲是SLE 發生腫瘤的危險因素(HR=2.22,95%CI1.38~5.24)。郭金燕等[14]研究也顯示,年齡、診斷 SLE 時年齡、SLE 病程長是患者發生腫瘤的危險因素。⑹藥物。Bernatsky等[13]的研究發現,雖然免疫抑制劑(環磷酰胺、硫唑嘌呤、甲氨蝶呤)的應用與總體腫瘤發生率無相關性(HR=0.52,95%CI0.50~1.36),但增加了血液系統腫瘤的發生風險(HR=2.29,95%CI1.02~5.15)。韓國的一項研究也發現,使用免疫抑制劑環磷酰胺及使用的劑量對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的發生有一定影響[15]。Sliesoraitis 等[16]曾報道 1 例 48 歲 SLE 男性患者使用甲氨蝶呤后誘發霍奇金淋巴瘤,而停用甲氨蝶呤后霍奇金淋巴瘤病情發生逆轉。本文中的例2、例4 均在應用了大劑量環磷酰胺后發現淋巴瘤,不排除淋巴瘤的發生與環磷酰胺的使用相關。而目前一些研究發現,作為治療SLE 的基礎藥物羥氯喹似乎對腫瘤具有抑制作用。有研究證實,羥氯喹對一些腫瘤相關通路的活性具有一定影響,且與傳統藥物聯用能增強其治療活性,但具體應用仍需進一步研究探索[17]。Ruiz-Irastorza 等[18]的一項 SLE 隊列研究顯示,使用羥氯喹治療的患者中有2例發生腫瘤(2/156),而未使用羥氯喹者中11例發生腫瘤(11/79),提示羥氯喹可降低SLE 患者發生腫瘤的風險(P<0.001)。國內學者郭金燕等[14]的研究也顯示,SLE者既往使用羥氯喹的比例高于SLE合并腫瘤者,羥氯喹可能是保護性因素。但仍需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證實其是否可以降低SLE患者的腫瘤發生率。
綜上所述,SLE 患者增加了罹患淋巴瘤的風險,其發病機制目前尚不明確。當SLE 患者出現不明原因發熱、淋巴結腫大、血細胞減少等情況,特別是對于治療效果不佳的,需警惕并發淋巴瘤的可能,盡早行骨髓細胞學檢查或淋巴結活檢,以獲得早期診斷和治療,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及預后。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