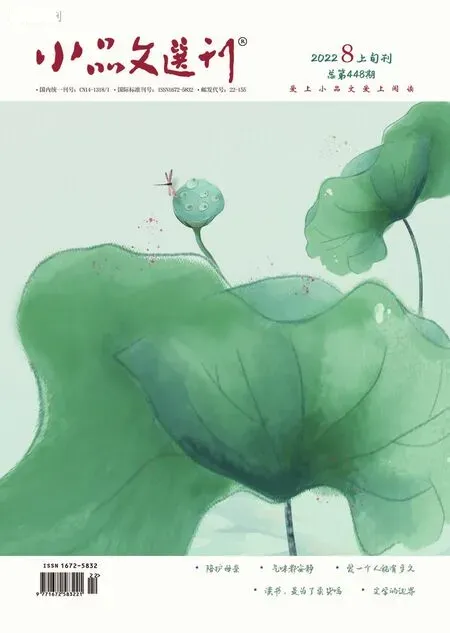空 鏡
□聶還貴

空鏡,影視畫面中只描寫自然景物而不顯象人物的鏡頭:或高山流云,或蒼鷹翔空。或藍浪白帆,或綠松翠冬。以空為實,化實為虛。營造和釋放暗示、象征、隱喻等藝術效果。
以藝術表現手段耐人尋味的空鏡,與詩意的留白同工異曲,鴻影相照。
春風寫意潑彩墨,山眉水波花千色。忽見留得一段白,一樹梨花一樹雪。這首舊日拙作,是早春盛景一影攝照。那一樹梨花,恰以一景留白、空鏡之搖曳,令花團錦簇、姹紫嫣紅的畫面,翼然鮮靈生動起來。
中國書法、金石治印,講究疏可走馬,密不透風,計白當墨,奇趣乃出。黑為實,白為虛。留白是載體,虛空是墨意。筆斷意不斷,墨空意不空。非墨之墨,無色之色。中國戲曲藝術動作虛擬,聽取弦外之音。中國繪畫“畫魚不畫水”“畫山不畫云”,《寒江獨釣圖》:一葉舟,一漁翁,于無水處,江天一色,煙波浩渺。齊白石的蝦圖:那里分明一幕空白,卻又覺漾漾然水靈透明,蝦兒栩栩鮮活。以及圍棋、建筑,都以留白、空鏡為美學追求。
一節綠竹,吹不出曲調,惟掏空內容,方可笛音爛漫飛揚。中國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抖空竹”,竹盒旋飛空中,發出奇特惟妙的聲音,“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堪稱是天籟。鼓掌,是生活中常見常用的一個手勢,掌心虛空,方可拍出熱烈響聲。石頭木頭捶打不出美樂,空心鼓卻可以敲擊出萬馬奔騰、暴風驟雨的聲動場景。中國有民族樂器名曰“空靈鼓”,起源于中國古代西周樂器編鐘。茶道、香道、琴道文化,以及太極、瑜伽、漢服、詩歌、舞蹈、禪修、冥想爭相與之相融會,生發出“妙處難與君說”的奇效。
一日,蘇東坡閑步郊外。時值吹面不寒楊柳風的早春,路邊杏花褪卻了殘紅,露出毛澀澀的青杏。紫燕巧尾如剪,裁出楊柳岸滿眼嫩枝細葉。沿著曲溪綠水,迎面是一戶院墻圍合的人家。一陣女子的笑聲從墻里飛出,打在他身上,儼然沾衣欲濕的杏花雨。東坡脫口而吟:“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好奇心驅動著,東坡隔著院墻,抑或是貓著腰透過門縫,與里面的佳人作了詩意的對話。可惜這對話效果差強人意,東坡無奈留下一聲千年感慨:“笑漸不聞聲漸消,多情卻被無情惱。”東坡究竟說了什么,里面又是作出怎樣的回應,原本火辣辣的歡笑,緣何驟然熄滅……蘇東坡留一方空白,讓讀者看官去縱情播種。
虛實輝映,有無相生。留白、空鏡,恰是審美主體情感注入切口,遂有心境合一、情景交融藝術之效。事實上,所有門類的藝術,都需要呈現以“輕盈態”與“飛動感”。詩忌太實,而繪畫即使工筆畫,即使“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也要寫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之“意”。無論思想內容多么深刻厚重,落在藝術層面也一定是承受之輕。
一位書畫收藏家,看上唐寅《川上圖》:畫面里一人牽一頭驢過橋,橋下流水洶涌,澎湃作響。小毛驢恐懼,收蹄扭頭,牽驢人卯足勁拉拽韁繩。然而,畫里并無韁繩筆墨。買畫者按捺不住心頭之喜,當即向賣主預付定金,約好次日來取。買主走后,老板作想:這幅畫好在哪兒,竟值一百兩銀?驀然,他發現人和驢之間并未畫有韁繩,慶幸這一“硬傷”未被買主看出。于是趕緊找來筆墨,在人與驢之間平添一條韁繩。第二天,買主看畫后,扼腕搖頭,要求退還定金。見賣主一頭霧水,買畫人說:此畫之妙,妙就妙在沒有韁繩……
曾看到一個外國鋼琴藝術家的故事:登臺,鞠躬,走到鋼琴前落座,鋼琴家開始演奏自己的新曲《4分30秒》。聽眾座無虛席,眼睛里閃爍著星光熠熠的期待。鋼琴演奏家清風淡云地打開琴蓋,卻未伸手去彈動琴鍵,卻是盯著手腕上的表,仿佛與聽眾同樣在期待什么。靜靜過了4分30秒,鋼琴演奏家起身,向臺下聽眾謝幕說:新曲演奏完畢。
臺灣大學有一口大鐘,為紀念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臺大第四任校長傅斯年而建。該鐘每天只敲21下,而不是24下,以吻合傅斯年說過一句話:對臺大學生來說,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3小時凝神靜思,便是一段珍貴留白。
太極陰陽圖,一白一黑兩條魚。知白守黑,奧秘無窮。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老子:“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戶牖即一室之留白,因其空,陽光進矣。因其無,虛室靈也。甚至,佛家不留文字,以心傳心,拈花微笑,都與留白藝術脈息相通。
山于麗日高時峻,月在青峰缺處明。老子:“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一月之內,惟有十五滿月,余日皆為留白。彎彎的月牙,翹翹的嘴角,留白人間多少美好遐想。留白是更豐富的色彩,無聲是更強烈的聲音。詩意就在留白的地方,留白原來是一片播種詩的雪野空曠。
人生是空靈的藝術,留白的藝術,距離的藝術,空鏡的藝術。泰戈爾溫情提示:“不要試圖填滿生命的空白。”閉合眼睛,屏蔽所有打擾,包括拒絕即使一絲光線的流照,一抹落霞的飄影。靜靜品讀自己,會發現,原來生命就是一首詩,生活與人生都是一首空靈的詩。乘著空靈的翅膀,生命就會帶動生活與人生飛翔。即使人生某些缺憾,恰是人生的留白,是光照進來的地方。那里有詩意,那里有藝術,那里有余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