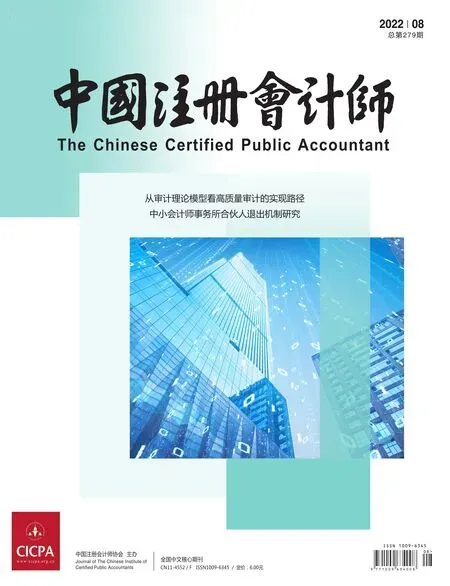關于VIE架構重大影響問題的探討
| 謝 岷
一、案例情況
我國境內C公司(以下稱為“被合約安排公司”)計劃在香港聯(lián)交所申報上市。根據(jù)適用的法律法規(guī),外國投資者被禁止于從事某項技術的開發(fā)及應用的國內C公司中持有股權。因此,在開曼群島成立的擬上市公司(以下稱為“開曼公司”)無法收購及持有C公司的股權。開曼公司通過合約安排搭建VIE(Variable Interest Equity,可變利益實體)架構,通過一系列協(xié)議控制被合約安排公司,避開法律法規(guī)中對于某些行業(yè)不能接受外資的要求,達到被合約安排公司在香港聯(lián)交所上市的目的。《合約安排》由開曼公司在境內的全資子公司(以下稱為“外商獨資企業(yè)”)、被合約安排公司的股東(以下稱為“登記股東”,包括“國內A公司”、“國內B公司”)及被合約安排公司訂立,包括簽署的《獨家咨詢及服務協(xié)議》、《股東表決權委托協(xié)議》、《獨家購買權協(xié)議》、《股權質押協(xié)議》等文件。國內A公司、國內B公司通過簽訂《合約安排》,將持有的國內C公司的股權質押給外商獨資企業(yè),授予外商獨資企業(yè)獨家購股權,同時將股東表決權授予外商獨資企業(yè)。外商獨資企業(yè)通過簽訂《合約安排》協(xié)議控制國內C公司。《合約安排》簽訂前后公司架構變化見圖1、圖2。

圖1 《合約安排》簽訂前的公司架構

圖2 《合約安排》簽訂后的VIE架構
《合約安排》簽訂前,國內B公司持有國內C公司30%股權,對國內C公司派出董事,進行權益法核算。《合約安排》簽訂后,香港全資子公司與開曼公司簽訂《認購協(xié)議》,認購開曼公司30%股權,并派出兩名董事,股比與國內B公司持有國內C公司的股比一樣,派出的兩名董事也與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派出的兩名董事相同。下文將對《合約安排》簽訂后需要解決的相關重大問題進行討論。
二、案例分析
(一)《合約安排》生效后,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是否仍具有重大影響?國內B公司是否需要對國內C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
筆者認為,國內B公司應該區(qū)分合并報表層面和個別報表層面來考慮。在合并報表層面,雖然國內B公司通過合約安排將股東表決權、購股權、股權質押給外商獨資企業(yè),但國內B公司仍可以通過香港全資子公司持有開曼公司30%股權,從而間接擁有國內C公司30%的權益。因此,在合并報表層面,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仍具有重大影響,國內B公司需要對國內C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在個別報表層面,《合約安排》生效后,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不具有重大影響,但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不進行權益法核算的時點,應取決于香港全資子公司對開曼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的時點,這兩個時點應該一致。因為,我們判斷《合約安排》及《認購協(xié)議》等VIE架構及協(xié)議屬于一攬子交易,應該按照一攬子交易進行會計處理。
(二)若判斷合約安排生效后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不具有重大影響,則不具有重大影響的時點如何確定?
1.《合約安排》及《認購協(xié)議》等VIE架構及協(xié)議屬于一攬子交易,應該按照一攬子交易進行會計處理。《企業(yè)會計準則第33號-合并財務報表》(2014年修訂)第五十一條規(guī)定:“處置對子公司股權投資的各項交易的條款、條件以及經濟影響符合下列一種或多種情況,通常表明應將多次交易事項作為一攬子交易進行會計處理:(1)這些交易是同時或者在考慮了彼此影響的情況下訂立的。(2)這些交易整體才能達成一項完整的商業(yè)結果。(3)一項交易的發(fā)生取決于其他至少一項交易的發(fā)生。(4)一項交易單獨考慮時是不經濟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慮時是經濟的。
通過簽訂《合約安排》及《認購協(xié)議》,國內B公司失去國內C公司30%股權,通過其香港全資子公司擁有開曼公司30%股權(開曼公司合并了國內C公司報表,為空殼公司),這相當于國內B公司對香港子公司的資本性投入,即國內B公司將對國內C公司的投資換成對香港全資子公司的投資。《合約安排》及《認購協(xié)議》顯然是在考慮彼此影響的情況下訂立的,這些交易整體才能達成一項完整的商業(yè)結果,《認購協(xié)議》的發(fā)生取決于《合約安排》的簽訂,單獨看《合約安排》是不經濟的,但《合約安排》與《認購協(xié)議》一并考慮時是經濟的。《合約安排》及《認購協(xié)議》等VIE架構及協(xié)議完全符合一攬子交易的特點。《上市公司執(zhí)行企業(yè)會計準則案例解析(2020版)》提示:“一攬子交易的特點的第(3)項指出:一項交易的發(fā)生取決于其他至少一項交易的發(fā)生。例如,交易雙方可能約定,如果后面的交易步驟無法完成,則取消之前的交易步驟。在這種情況下,在整體交易完成之前,不應該對已經完成的交易步驟進行會計處理。” “在實務操作中,應當結合具體情況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進行判斷。”
因此本案例中,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不進行權益法核算的時點應該與香港全資子公司對開曼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的時點一致,中間不應有空窗期;在香港全資子公司未對開曼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的時點之前,國內B公司不應該終結對國內C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
2.股份交割完成日應該成為香港全資子公司對開曼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時點,在該時點相應國內B公司不再對國內C公司進行權益法核算。
《上市公司執(zhí)行企業(yè)會計準則案例解析(2020版)》指出:“企業(yè)會計準則中并沒有對取得重大影響的判斷時點做出明確規(guī)定,但是給出了明確的關于企業(yè)合并中‘購買日’的判斷條件。購買日是購買方實際取得對被購買方控制權的日期。假設合同生效的前置條件已經滿足,在判斷購買一項聯(lián)營投資的購買日時,也可以參考準則對于企業(yè)合并‘購買日’的判斷條件,并結合聯(lián)營投資的特點具體分析”。 《企業(yè)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yè)合并(應用指南)》規(guī)定:“同時滿足下列條件的,通常可認為實現(xiàn)了控制權的轉移:(1)企業(yè)合并合同或協(xié)議已獲股東大會等通過。(2)企業(yè)合并事項需要經過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審批的,已獲得批準。(3)參與合并各方已辦理了必要的財產權轉移手續(xù)。(4)購買方已支付合同價款的大部分(一般應超過50%),并且有能力、有計劃支付剩余款項。(5)購買方實際上已經控制了被購買方的財務和經營政策,享有相應的收益并承擔相應的風險。根據(jù)第(4)項條件,購買方要取得與被購買方凈資產相關的風險和報酬,前提是必須支付一定價款。該條件主要是從風險和報酬的角度進行分析,一般而言,在非關聯(lián)方交易的情況下,交易雙方的風險報酬轉移常常會與價款支付同步進行,因此,價款的支付情況常常能夠體現(xiàn)風險報酬的轉移情況。香港全資子公司認購股權要同時滿足上述5項條件,特別要滿足第(4)項條件,時間點只能是支付股權款日。香港全資子公司與開曼公司簽訂的股權認購協(xié)議“該股份交割的條件”規(guī)定:“各認購方必須在收到本公司的通知后10個工作日內以立即可用的資金將其代價部分電匯至本公司指定賬戶。”即規(guī)定香港全資子公司支付股權款后,該股份交割才完成。開曼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出具注冊資本繳款通知單,通知香港全資子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前將實繳資金撥至指定銀行賬戶。2021年3月31日,香港全資子公司完成開曼公司股份認購款的劃轉,將實繳資金匯款至開曼公司在香港的銀行賬戶。香港全資子公司支付股權款后,該股份交割完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四條規(guī)定:股東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分取紅利;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優(yōu)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但是,全體股東約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或者不按照出資比例優(yōu)先認繳出資的除外。《上市公司執(zhí)行企業(yè)會計準則案例解析(2020版)》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四條規(guī)定可以理解為,股東按實繳出資比例分紅是基本原則,按認繳比例或其他方式分紅是例外,該例外的情況應該有公司章程或投資協(xié)議的特別約定支持。倘若股東之間沒有關于分紅的具體約定且公司章程也沒有約定,那么股東之間的分紅應當按照實繳比例進行。”實務操作中,權益法核算也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四條規(guī)定進行核算。因為開曼公司的章程及認購協(xié)議沒有關于分紅的具體規(guī)定,因此,香港全資子公司的權益法核算應當按照實繳比例進行。
(三)若判斷合約安排生效后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不具有重大影響,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的長期股權投資應如何進行會計處理?
在個別報表層面,合約安排生效后,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不再具有重大影響,但同時國內B公司的香港全資子公司取得了開曼公司30%股權。這相當于國內B公司對香港全資子公司的資本性投入,即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的投資換成了對香港全資子公司的投資。國內B公司個體報表的長期股權投資的會計核算由權益法變成成本法。由于該交換不具有商業(yè)實質,以賬面價值為基礎計量。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合約安排》、《認購協(xié)議》等VIE架構及協(xié)議屬于一攬子交易,不能夠僅憑《合約安排》是否生效,國內B公司對國內C公司是否還具有重大影響來判斷是否進行權益法核算,而應該將《合約安排》、《認購協(xié)議》等VIE架構及協(xié)議多次交易事項作為一攬子交易進行會計處理。如果后面的交易步驟即香港全資子公司認購開曼公司股權無法交割完成,則會取消之前B公司通過合約安排將股東表決權、購股權、股權質押給外商獨資企業(yè)的交易步驟。在這種情況下,在整體交易完成之前,不應該對已經完成的交易步驟進行會計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