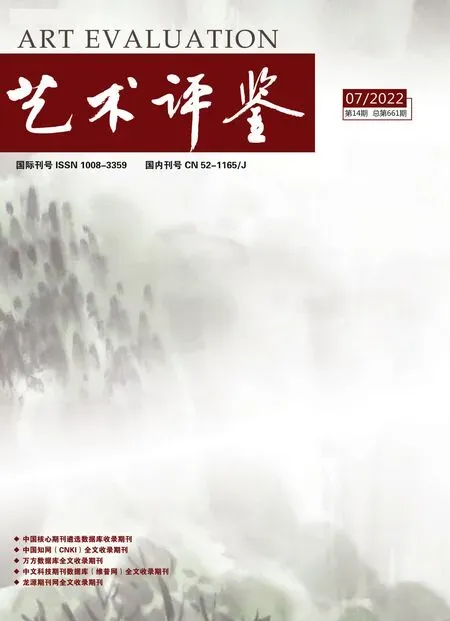對我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構建的思索
沈思雨 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
話語與權力這兩個詞聯系在一起,筆者最初是在管建華教授的文章《音樂話語體系轉型的研究》中看到的,管建華教授提到了關于米歇爾·福柯的權力理論,他將“話語”作為音樂領域的一種分析工具對話語體系轉型進行研究,并將福柯的理論歸結為“話語是權力的關系”。米歇爾·福柯的權力理論對20 世紀中后期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具有深遠影響,筆者原先對“話語—權力”關系的理解,是將其理解為字面表達對話語權的闡釋,而福柯的理論并非是簡單的表達話語的權力,而是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含義,要弄清楚其所傳達的真正意圖,就必須厘清這些概念。對此,筆者深入地了解后,對于福柯“話語—權力”中表現的關系有了以下全新的認識。
一、話語與權力的關系
米歇爾·福柯是處在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過渡時期的法國哲學家,他的研究從最初的知識考古學到權力的譜系學研究或后期對于倫理學研究,對全世界的學者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汪民安教授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與福柯相提并論,他認為福柯是一個哲學家,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歷史學家或批評家,甚至是社會理論家。福柯的思想影響了史學、政治學、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采的影響,被稱為“20 世紀法蘭斯尼采”。福柯的一生贊揚非理性、反對理性和任何形式主義的教條,他的思想充滿啟發性,批判現代性、批判理性、批判知識甚至批判傳統的道德觀念,以及關注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福柯關注到知識與權力的關系——權力怎樣通過話語表現出來,并配合各種規訓的手段將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細節中。他認為,話語構成過程受制于“一組匿名的歷史規則”,它決定著語言、觀念如何相互交換等話語活動,潛在的規范要求話語如何實踐。
福柯的思想對當代社會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當伽利略發現地球圍繞太陽轉時,使一直以人類處于宇宙中心想法的人們感到震驚,也讓曾經圍繞這個觀念建立的整個信仰體系開始變得不同。而福柯的理論出現在文化方面可以說也是一種伽利略式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福科對西方思想產生了強烈沖擊,可以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他的關注點與之前研究者們的不同,在他關注的瘋癲史、監獄史等不同的觀察角度中,一直在追問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呢?關注這些問題的背后,呈現的是福柯對人的主體的關注,他在追問我們或如今的我們是如何形成的。從伽利略時代以來,人們習慣認為,在各方面上,人類都處于中心位置,是人類創造了這一切。而福柯否定了這一點,他認為不是主體創造了文化。
在1971 年福柯出版了《話語的權力》,在這本著作中,他首次將權力理論引入話語理論,提到話語與權力,他指出“在任何社會里,話語一旦產生,即刻就會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防范它的權力和危險,把握不可預料的事件。”三在“若干程序”即權力的形式中,話語籠罩在權力之中,人們使用的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已設置好,人們是有言論自由的,但所用話語在權力范圍之內,就使得話語代表了權力。福柯對權力的進一步認識后,意識到權力的兩面性,一方面是權力會制約我們的話語,另一方面是權力也在不斷地創造話語。他從歷史發展的緯度,關注話語與權力的關系,權力是如何通過話語表達出的,“若干程序” 如何相互配合滲透話語。權力不是在抹去一種主體,而是創造一種主體。對主體的考察,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方式:在經濟學中,主體被置放在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中;在語言學中,主體被置放在表意關系中;而福柯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將主體置放于權力關系中,主體不僅受到經濟和符號的支配,還會受到權力的支配,主體與權力之間的交融,可以讓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筆者認為,福柯所說的話語與權力不可分割,二者相輔相成,是一個共生體,權力創造了話語,話語效力于權力。生活中相關的話語幾乎都由權力關系中的“若干程序”的維護和發展而形成,權力建構出的話語為權力體系服務,話語體系也成為了權力關系的符號。在我們接受生活中的種種話語的設定時,實際上就是接受了背后的權力。例如,1961 年,福柯出版的《瘋癲與文明》,這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的書,它討論了歷史上瘋癲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的。福柯講的瘋癲史是主流研究忽略的方向,福柯并不是精神分析學家,他也不是要對精神病進行分類,更不是為了研究瘋癲,而是思考瘋癲與正常之間的話語。在他的《瘋癲與文明》一書中,處在文藝復興時期和古典時期又或是在現代時期對瘋癲的理解和處置不同,而從一開始區別瘋癲和正常的知識話語表達就是權力創造的,就像鑒定一個人是否瘋癲時,會存在一系列的標準,在這個標準之下,似乎可以科學地進行區分,但這些標準的產生似乎也是權力對主題的一種構建。在福柯的這些思想中,筆者認為他表達的不是認識主體的活動產生了話語,而是權力關系構造了話語的形式和范圍。
目前,國內的一些文獻中雖然提到了權力與話語之間的關系,但大多從哲學、文學、政治學等方面進行分析,而“話語—權力”與音樂的研究上較少,筆者認為關注音樂話語以及音樂話語實踐可以成為建立我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突破口。如同管建華教授所說:“音樂話語是音樂思維活動邏輯推理的表現,音樂話語知識不僅表達人們的思想,也是人們的一種實際活動,與其他的實踐處于一種關系網絡中。”為了更好地認識與構建音樂理論話語,筆者希望通過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的進一步反思,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的發展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二、對“話語與權力”關系的反思
20 世紀90 年代,我國開始廣泛介紹和系統研究福柯,至今已近30 年,他的話語分析、權力解構等概念及時地為我國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討論視角,并在福柯“話語—權力”思想的基礎上解讀全球化多元音樂視域下面臨的許多問題。福柯理論的意義不僅提供了一個視角,還闡釋了對“話語”產生與機制的解讀。音樂絕不是簡單的語言形式因素構成的,自古以來對話語的爭奪在人類歷史中就從未消停,包括個人的、政權的、國家的,在不斷斗爭中關系著最終對話語的掌握,“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與《1984》中提到的“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也不謀而合。在人類社會出現后,話語始終都是歷史的、不斷變化的,話語自形成以來就是動態的、發展的。這種權力是一種泛化的權力,福柯認為人的主體性規范存在于整個話語機制中的權力,文化體制規范了個體的話語,賦予了個人話語的權力范圍。而權力是不斷產生的,在整個話語機制中,不斷發展并充分融入我們的日常中。
話語作為后現代哲學和文論中的重要概念,很多人都把話語理解為“話語權”,但其實話語權指的是說話的權利,這是和義務相關的概念。而本文所說的話語并不等同于“說話”,每個人都可以說話,但我們所說的話語是否還是在權力建構下的結果呢?管建華教授借用福柯的觀察,提出“我們需要正視西方話語所帶來的體制性實踐,以及話語與權力的緊密關系。西方工業文明的音樂話語體系以及其認知方式權威化和正統如何壓抑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分類方式、認知方式、倫理主體話語,并獲得了音樂文化發展的話語權。”早在20 世紀初,我國許多學者就提出了構建中國音樂話語體系,這是一個極其龐大且復雜的工程,但也是每位音樂人必須面對的。
經過了近百年醞釀,對于重構中國音樂話語體系的聲音和嘗試愈來愈高漲,特別是在如今世界音樂發展的大環境下,東西方音樂頻繁交流,建立和完善我國話語體系相當必要,一方面,出于對我們自身音樂發展的考慮;另一方面,對全球化背景下音樂文明的互識、互動與交流的考慮。重新審視我們已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音樂可謂是一路相伴,從賈湖骨笛開始甚至更早時,我們社會生活中始終都有音樂的存在,歷朝歷代的發展中音樂與政治、音樂與社會、音樂與文化以及思想緊密相連。如今,我們要重建音樂話語體系,或許可以借鑒福柯的譜系學研究,追溯到源頭尋找背后的意識形態力量,找到左右話語的權力關系,從而幫助我們了解過去,以便更好地應對未來。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只有當我們真的挖掘到它的“真身”,才能去瓦解被權力支配的話語體系。
筆者認為,在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中,對音樂話語的構建也是對音樂知識話語的構建。值得一提的是,福柯認為知識話語在其發展中可能會形成一種“真理的制度”,在《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中提到:“我的目的不是要寫一部有關禁忌的社會歷史,而是要寫一部有關‘真理’的生產的政治歷史。”他認為真理是不會獨立于權力關系的,并且福柯對“真理的制度”是警惕的,一旦一種知識在社會中形成了“真理的制度”,就會產生一個確定什么才是真理、如何區分真假話語的標準機制,從而使得“那些長期被人們忽視的、邊緣化的歷史知識,以及那些處在知識等級體系的下層、地方性知識、特殊性知識”可能淪為被剝奪了正統資格的“被壓迫的知識”。而我國音樂知識話語的構建也需要面對這一問題,話語產生的客體就是知識,而現實社會就是由各種的知識構成的。這里并不是說知識控制了現實社會,而是我們在權力之下只能通過知識建構我們認知的社會。因而,話語機制生產出我們確認為常識的真理,主體學習知識的過程中,明確了何為真、何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這就是被話語機制所規制,需要學者們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進行分析,敢于反思和質疑固有的“真理”。這樣對發展音樂學科和整個藝術門類都極為珍貴。面對“真理”話語,需要跳出權力范圍,直面權力對知識話語的影響,努力從“同一的邏輯”中解放。學者們有責任、有義務去做這件事,需要擔起這份批判性反思的擔子,拆解那些廣為熟悉和被認可的事物,不斷審視已有的知識體系,進而推動音樂學科不斷向前發展。
當然,在探索的同時,北大學者陳平原提出的觀點也非常值得關注,他認為:“九十年代以后,我們懂得了福柯,動不動往權力、往陰謀、往宰制方面靠,每個人都是火眼金睛,看穿你冠冕堂皇的發言背后,肯定蘊藏著見不得人的心思。不看事情對錯,先問動機如何,很深刻,但也很無聊。”如今社會中“話語—權力”結構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球化多元音樂的大背景下,“話語—權力”結構與我們的社會、政治或人之間構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也有其積極的一面。無論是福柯將它提出,又或是后來人的反復追問,歸根到底都想要尋求某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對我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構建的思索
在不斷有人提出要重新構建我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后,筆者有兩個疑問,一是,“為什么一定要構建中國的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二是,“中國有形成過一套像西方音樂一樣完整的音樂話語體系嗎?”這兩點問題,筆者認為在上述對“話語—權力”的關系的梳理中已大致表達了筆者的觀點。對于第二點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古代的音樂理論事實上在歷朝歷代都有發展,并不僅是音樂理論方面,傳統的民歌、戲曲和儀式音樂等都用著自己的一套系統進行傳承,但如果將這些歸類為音樂話語體系,筆者認為又不完全恰當。發展到近代,我國的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似乎得到建立,但是在放棄很大一部分傳統音樂的基礎上得以發展至今,我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非常西化,導致部分人并不認同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但由于不同的歷史語境和社會生產結構之下,必然會得到不同的結果。20 世紀,中國傳統音樂主流斷裂,音樂發展按照西方歷史的全球化進程標準,將中國音樂史分成了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部分,但我國音樂歷史發展同西方的音樂歷史發展截然不同。由于種種原因,造成我國音樂話語不夠完善,導致音樂在如今的發展中受到一定阻礙,要改變現在的狀態構建話語體系,還要梳理和挖掘我國音樂歷史發展的內涵,在我國的語境中提煉建構音樂話語。
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中西之間雖然存有共性,但我們更應把眼光放在我國音樂的個性之處,這更有利于構建我國的音樂理論話語體系。近代中國經歷了數次歷史變革,我們或是主動或是被動地接納了西方音樂體系,事實上,西方體系也為我國的音樂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推動力。時至今日,西方音樂在中國近百年的融合發展中,也已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音樂文化,對我們影響至深。與此同時,由于早期對西方音樂理論話語的廣泛接納,給我國的傳統音樂也造成了劇烈沖擊。新時代下,構建我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十分必要,同時,構建話語體系是我們能否重新定位中國音樂文化在世界音樂文化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
縱觀歷史,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和融合中共同創造出的瑰寶,在我們的文化內涵中一直都有“和”的基因,秉承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待人之道,即使在文化十分繁榮的唐宋時期,中國也敞開大門與他國廣泛進行溝通交流,這樣的氣度對當代我國中國音樂文化今后的發展也有著啟示作用。在音樂話語體系構建中,我們也應學習和借鑒他國優點,吸收優秀的音樂文化。但與此同時,發展中也應注意不要隨波逐流,要真正地做到“以己為主、為己所用”。正如法國漢學家皮埃爾·夏蒂埃教授對西方學者的告誡,同樣也提醒著我們,他說道:“要把中國與世界隔絕開來,將自己禁錮在僵化的、成了鐵板一塊的‘真誠’之中,那也是危險的。因此,理論上與‘他者’相遇時,也要靈活掌握:加強自己的穩定性,接受對方的碰撞。”值得欣慰的是,我國研究者對構建音樂理論話語體系表現出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希望通過“話語重構”,為我國的音樂發展提供話語支撐和有效表達,同時也有助于中國音樂話語研究的演進,不斷在碰撞融合中完善自我。
四、結語
綜上所述,福柯的“話語—權力”思想提供了一個觀察和理解音樂話語理論體系的視角,對構建中國音樂話語理論體系有著重要作用。筆者認為,話語總處在流變的狀態,沒有誰能徹底掌控話語,也沒有誰是處在“話語—權力”之外。在構建音樂話語體系時,一方面,要在歷史中尋求解答;另一方面,要把握當下,時常停下腳步進行反思,在否定中前進,排除重重障礙,立足于新時代,直面世界音樂話語體系。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簡單地對西方唱衰或排斥可能會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初衷也不是為了將西方中心論轉為中國中心論。對音樂話語實踐研究并不是為了去定義一個學科或解釋一個名詞,而是體驗、感受與理解中國五千年文化底蘊下的精神內核,由內而外的輸出。構建我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工程巨大,需要在不斷發展中吸納、總結并繼續完善,在這條道路上我們仍要不斷思索、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