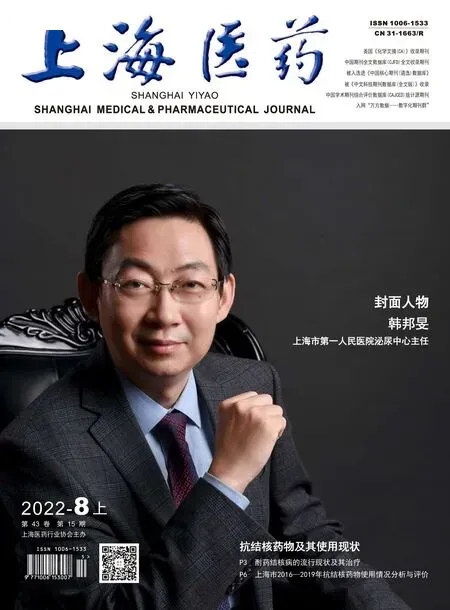1例呼吸罕見病EGPA服用硫唑嘌呤致嚴重骨髓抑制
葉曉芬 呂遷洲 李曉宇 金美玲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1. 藥劑科;2. 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 上海 200032)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45歲,80 kg。因“診斷嗜酸性肉芽腫性多血管炎半年,服用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2周后出現外周血粒細胞缺乏[白細胞計數(WBC)1.45×109/L,中性粒細胞(N)0.9×109/L]伴全身皮疹加重,顏面部紅色、中央破潰結痂伴疼痛的豆大丘疹,于2021年11月25日就診于我院門診。門診復查血常規示粒細胞進一步下降伴血小板下降[紅細胞計數(RBC)3.67×1012/L,血紅蛋白(Hb)120 g/L,血小板(PLT)119×109/L,WBC 0.86×109/L,N 0.4×109/L]; C-反應蛋白(CRP )93.8 mg/L;肝腎功能、出凝血指標無明顯異常;自身抗體無明顯陽性指標。診斷為粒細胞缺乏伴皮疹。
2年前(2019年11月),患者出現反復咳嗽、氣喘,診斷為支氣管哮喘、過敏性鼻炎,長期吸入糖皮質激素聯合長效β2受體激動劑及口服孟魯司特片,癥狀有所緩解。1年前(2020年12月),出現外周血嗜酸粒細胞明顯增高(ESO 2.27×109/L,28.3%)。胸部CT示兩肺多發支氣管腔增寬,管壁增厚,伴有斑點、片絮影,局部肺實質內見斑片狀模糊陰影(提示兩肺支擴、呈樹芽征)。當時紅細胞沉降率(ESR)20 mm/h;CRP 5.9 mg/L;免疫球蛋白E(IgE)343 IU/mL;D-二聚體0.17 mg/L;自身抗體無陽性指標。臨床懷疑嗜酸粒細胞性肺炎可能,予口服糖皮質激素治療(強的松15~20 mg qd),治療后咳嗽、氣喘癥狀有所緩解,血嗜酸粒細胞明顯下降,激素減量后癥狀明顯反復且嗜酸粒細胞復又上升(表1)。半年前,患者開始出現全身多發皮疹伴瘙癢,口服依巴斯汀、奧洛他定對癥處理后有好轉,但反復發作。結合患者多次胸部CT影像表現,多學科討論后考慮嗜酸性肉芽腫性血管炎(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EGPA)可能。于2021年11月,調整治療方案為強的松(15 mg qd)聯合AZA治療,AZA劑量方案為25 mg qd×7 d(11月8—15日),患者無明顯不良反應,查血常規未見明顯異常,遂增加至50 mg qd(11月16—23日),逐漸出現皮疹加重及粒細胞明顯降低。

表1 糖皮質激素治療期間血常規隨訪
根據患者病情及其用藥史,考慮AZA引起粒細胞缺乏可能性大,予停用AZA;皮下注射人粒細胞刺激因子300 μg qod(11月25日—12月2日),升粒細胞治療后,血常規逐漸恢復正常(表2)。皮疹破潰處給予復方多黏菌素B軟膏外涂處理并全身抗感染治療后好轉。

表2 AZA治療前后及升粒細胞治療后血常規隨訪
2 討論
患者長期使用吸入性糖皮質激素(ICS)+長效β2受體激動劑(LABA)+白三烯受體拮抗劑(LATR)治療過敏性鼻炎及哮喘,強的松治療EGPA,間斷依巴斯汀、奧洛他定抗過敏治療,并未出現骨髓抑制、嚴重皮疹破潰等情況,因EGPA服用AZA2周后出現粒細胞降低等骨髓抑制表現,并有面部皮疹破潰伴疼痛。根據實驗室檢查及用藥時間考慮骨髓抑制可能跟AZA存在相關性,皮疹破潰疼痛考慮為EGPA相關性皮疹感染導致。根據WHO化療藥物性骨髓抑制分級標準,該患者WBC 0.86×109/L、N 0.4×109/L,為Ⅳ級,屬于嚴重骨髓抑制。根據諾氏不良反應評分量表[1],患者的骨髓抑制與服用AZA為很可能有關。EGPA屬于呼吸罕見病,是一種多系統疾病,表現為變態反應性鼻炎、哮喘和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顯著增多[2-5]。最常累及肺臟,而肺外器官的血管炎是導致EGPA相關病況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全身糖皮質激素是EGPA的主要治療藥物,劑量一般為0.5~1 mg/(kg·d)[5]。但往往單一激素治療不能完全緩解病情,聯合其它免疫抑制劑(如環磷酰胺、甲氨喋呤、AZA)可以減少激素劑量。該患者擬使用強的松聯合AZA。AZA起始劑量25 mg/d使用1周,無明顯不良反應。但第2周增加劑量至50 mg/d后出現嚴重骨髓抑制。
AZA為臨床治療風濕性疾病常用的免疫抑制劑。AZA口服吸收后在肝臟通過谷胱甘肽S-轉移酶代謝為6-巰基嘌呤(6-mercaptopurine,6-MP)。而后進一步轉化:主要途徑為經次黃嘌呤鳥嘌呤磷酸核糖轉移酶轉化為活性產物6-硫鳥嘌呤核苷酸(6-thioguanine-nucleotides,6-TGNs)起作用,再經核苷焦磷酸酶15(nucleoside diphosphate-linked moiety X-type motif 15,NUDT15)轉化為無活性的6-TG單磷酸鹽;經黃嘌呤氧化酶和硫嘌呤甲基轉移酶(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ase,TPMT)分別轉化為無活性的6-硫脲酸和6-甲基巰嘌呤。其常見的不良反應為粒細胞減少,甚至急性造血功能停止等。當然,嚴重的骨髓抑制臨床上較為少見。早在1980年代,就已發現關于TPMT酶的缺失[6],之后多項研究報道發生骨髓毒性往往與TPMT酶的缺失或活性低下有關[7-10]。后續又有很多研究發現,NUDT15基因多態性與硫嘌呤誘導的骨髓抑制亦密切相關,特別是在亞洲人中[11-16]。真實世界的研究也表明AZA相關的骨髓抑制與TPMT酶和NUDT15的基因多態性相關[17],可以通過基因檢測結果進行風險預測和劑量調整。臨床藥物基因組學實施聯盟(Clinical Pharmacogenetics Implementation Consortium, CPIC)指南[18]更是基于TPMT和NUDT15的基因型給予了硫嘌呤類藥物的推薦給藥劑量,在AZA使用前測定TPMT和NUDT15基因,若檢測結果為正常活性,則提示使用AZA標準劑量時風險較小,若活性低下,則提示根據病情選擇其他適宜藥物或相應減少劑量從而避免嚴重的不良反應:①TPMT:若TPMT正常,AZA可按正常起始劑量如2~3 mg/(kg·d)使用,然后根據具體疾病診治指南調整AZA劑量,一般于2周達維持劑量;TPMT缺失或活性低下,根據具體病情選擇非硫嘌呤類免疫抑制劑替代治療或從大幅減少劑量(每日劑量減少10倍,3次/周)開始,并根據骨髓抑制程度和具體疾病診治指南調整AZA的劑量,一般4~6周達維持劑量。②UNDT15:若NUDT15正常,AZA可按正常起始劑量如2~3 mg/(kg·d)使用,然后根據具體疾病診治指南調整AZA劑量,一般于2周達維持劑量;NUDT15突變,根據具體病情選擇非硫嘌呤類免疫抑制劑替代治療或從大幅減少劑量(每日劑量減少10倍)開始,并根據骨髓抑制程度和具體疾病診治指南調整AZA的劑量,一般4~6周達維持劑量。
隨著AZA相關性骨髓抑制及藥物基因型研究越來越深入,TPMT和NUDT15的基因檢測已廣泛用于臨床,很多醫療機構都開展了該檢測項目,在使用AZA前建議進行檢測以評估用藥安全性及劑量選擇。
本例EGPA患者需要在激素治療基礎上聯合AZA治療,用藥前未進行藥物基因型檢測,經驗性以25 mg/d[0.31 mg/(kg·d)]小劑量起始,血常規未見明顯異常。小劑量使用7 d后增加至50 mg/d,7 d后查血常規即發現明顯骨髓抑制,以粒細胞降低為主。經停藥并升粒細胞治療后逐漸恢復。該病例也給了我們一個警示,在應用AZA前應盡量進行藥物基因型檢測,以提高用藥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