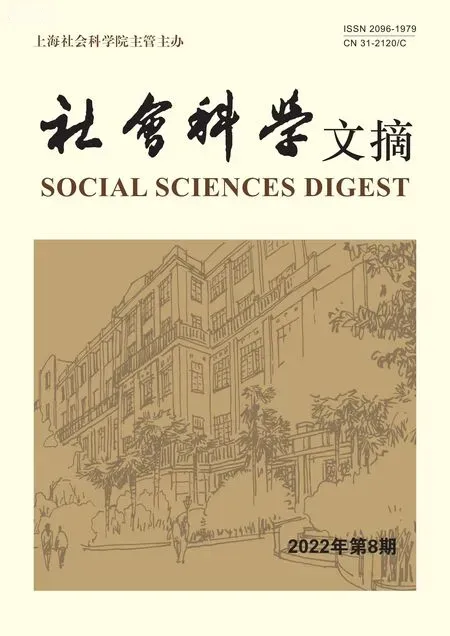在“世界”中的中國科幻小說
文/宋明煒 譯/汪曉慧
中國科幻小說作為一次新浪潮運動,引發(fā)了引人注目的“全球”影響。本文引用大衛(wèi)·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xué)”概念,以及伊斯塔范·西瑟瑞-羅內(nèi)有關(guān)“全球科幻小說”的論點,借用“世界”這個詞的動詞意義來探討三種情形:科幻小說自身形式中的世界建構(gòu),科幻小說進入世界文學(xué)的過程,科幻小說將一個原來不可見的中國呈現(xiàn)給世界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科幻文學(xué)與世界建構(gòu)
在《三體》發(fā)表前幾個月,劉慈欣發(fā)表了中篇小說《山》。《山》名不見經(jīng)傳,但它所建構(gòu)的想象世界和文明故事不但是隱喻科幻文類本身的“超級文本”(mega-text),而且仿佛映照出隨著劉慈欣步入國際舞臺,中國科幻進入世界文學(xué)的歷程。
世界建構(gòu)(world-building)對科學(xué)小說敘事至關(guān)重要。幾乎所有圍繞世界建構(gòu)過程而展開自我反思式情節(jié)設(shè)計的作品都可以被解讀為“超級文本”,即關(guān)于科幻小說本身的科幻小說。借用羅伯特·肖勒的話來說,這類科幻小說代表了一種結(jié)構(gòu)性想象,其中充滿“對作為系統(tǒng)之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之結(jié)構(gòu)的宇宙本質(zhì)的意識自覺”。像《山》這樣的作品,體現(xiàn)出科幻小說的母體情節(jié):與未知的相遇,及為理解這種相遇而做出的自覺努力。它反映出科幻文類的結(jié)構(gòu)性成規(guī),也指向通過對知識的科學(xué)化集合與處理而驅(qū)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情景。
通過《山》的故事,我試圖引入“世界中”(worlding)這一概念;在海德格爾的意義上,這個動詞意味著世界打開的狀態(tài),即一種不斷展開、不斷生成的過程。它與海德格爾哲學(xué)中另一個關(guān)鍵概念有關(guān):“居于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王德威將這一概念借用至文學(xué)史語境中,認(rèn)為“‘在世界中’的概念不但可以作為將‘世界帶入中國’的手段,幫助我們在更廣泛的‘文’的觀念中理解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更重要的是,能夠作為一個媒介持續(xù)不斷地打開世界新格局”。除了強調(diào)文學(xué)的詩性力量外,他還暗示了文學(xué)的生產(chǎn)與生成,和文學(xué)具有情動力打開中國“居于世界之中”的視野,以及與世界文學(xué)的協(xié)商與融和。
我將“在世界中”的概念延伸至新浪潮科幻的詩學(xué)建構(gòu)中,以說明科幻敘事模式作為一種世界建構(gòu)過程的特點:揭示“不可見”之物,創(chuàng)造世界的虛擬形式,并表達文學(xué)想象的詩意拓?fù)洹M瑫r,我用這個動詞來描述歷史語境中三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運動:中國科幻創(chuàng)造獨特文學(xué)世界的歷史,與世界文學(xué)的協(xié)商與融合,向世界再現(xiàn)中國現(xiàn)實之“不可見”部分。
新浪潮
達科·蘇文以一種謹(jǐn)慎的樂觀主義和持久的烏托邦沖動來描述科幻文類,這種沖動可能同時產(chǎn)生烏托邦和惡托邦敘事。科幻小說作為一種能與另類世界形象對話的“選擇性傳統(tǒng)”享有精英特權(quán)。對于中國科幻新浪潮而言,更是如此。中國科幻文學(xué)長期以來默默無聞,但自從20世紀(jì)80年代末以來,思想界對啟蒙和革命的反思、主流文學(xué)以大體上歸于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的手法面對現(xiàn)實瞬息萬變的滯后感、新型科學(xué)理論和新興技術(shù)對日常生活產(chǎn)生影響、互聯(lián)網(wǎng)的興起、類型小說市場的成熟,以及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繁榮等原因,都促成科幻小說的異軍突起。由韓松、王晉康、劉慈欣等人開創(chuàng)的中國科幻的新潮流繼承了來自80年代倡導(dǎo)啟蒙與充滿希望的精神遺產(chǎn),迅速促生中國科幻的黃金時代,并創(chuàng)造了具有顛覆性的“新浪潮”。我借用英美科幻小說歷史上的“新浪潮”(new wave)一詞,以此強調(diào)其先鋒性的文學(xué)實驗和顛覆性的文化/政治意義,同時也用“新浪潮”一詞來標(biāo)識科幻小說在整體上正對當(dāng)代中國主流文化范式產(chǎn)生的“新浪潮”般的沖擊。
新浪潮科幻是烏托邦與惡托邦的雙身同體,用后人類形象挑戰(zhàn)人文主義傳統(tǒng)觀念,反思諸如進步、發(fā)展、民族主義和科學(xué)主義等中國現(xiàn)代性的關(guān)鍵問題。與包括奇幻文學(xué)在內(nèi)的其他流行文類相比,中國科幻新浪潮作品更嚴(yán)肅地切入社會、政治以及哲學(xué)話題。劉慈欣與韓松等作家創(chuàng)造的世界圖像試圖照見現(xiàn)實中“不可見”的域界,在現(xiàn)實表象之下尋找更深層的真實,以及我們的世界在精神和心靈上的幽暗層面。當(dāng)劉慈欣、韓松、寶樹、郝景芳和陳楸帆等人的作品被譯成英文后,展現(xiàn)了一個非同尋常、折疊起來的中國圖景。中國科幻昭示了我們的生活世界之外還有無限豐富的另類可能性。中國科幻的新浪潮代表了一種改變現(xiàn)狀的新希望,一種對更廣大世界的好奇心,一個為中國讀者帶來更多奇觀和啟示的承諾。
中國科幻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圍內(nèi),劉慈欣的《三體》是來自中國的有史以來最熱門的暢銷書。“三體宇宙”憑借20多種語言的譯本改寫了世界科幻小說的版圖。正如大衛(wèi)·達姆羅什根據(jù)跨越民族文學(xué)界限的流通和閱讀來定義的世界文學(xué),劉慈欣的小說也因此很快作為“世界文學(xué)”而獲得新生。在中國之外,劉慈欣的作品在跨語際狀態(tài)中不斷獲得新生,這種情景距離達姆羅什所說的“全球英語”(global English)的勝利已經(jīng)不遠。“全球英語”的策略性使用可以引發(fā)具有社會意義的文學(xué)實驗,但它同樣突出了一個事實,即在用英語(重新)書寫后,沒有什么還能保住“原汁原味”。
達姆羅什主張以跨文化可譯性和跨國界流通為基礎(chǔ)建立的“世界文學(xué)”新概念,同時也清醒地指出:“外來文化在接受國有固有的形象,一個外國作品如果不符合這個形象就難以進入新的競技舞臺;進而,如果它對當(dāng)?shù)氐男枨笠矡o所用處,這種困難就愈發(fā)巨大。”讓中國科幻文學(xué)“走進世界文學(xué)”變得更為復(fù)雜的是,科幻文學(xué)對于劉慈欣和韓松等中國作家來說,原本就是一種“外來”文化。
科幻文類在100多年前通過日本首次被引入中國,并在中國現(xiàn)代史的幾個關(guān)鍵時期經(jīng)歷過幾次短暫的繁榮期,但始終沒有形成連續(xù)發(fā)展的歷史。盡管晚清科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五四之后興起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其主流幾乎完全轉(zhuǎn)向現(xiàn)實主義,與此同時,科幻文類漸漸失去生機。劉慈欣、韓松和陳楸帆等當(dāng)代作家不得不重新創(chuàng)造科幻這個文類,他們從英美、日本、蘇俄和歐洲科幻文學(xué)傳統(tǒng)移植,同時也超越有關(guān)話語、意象、觀念和世界體系,并對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表現(xiàn)模式加以改造試驗。對于中國以及來自世界其他部分的作家來說,選擇創(chuàng)作科幻這一自誕生之日就是“全球”文類,并在其中注入自己的想象力,這本身就是參與“世界文學(xué)”的行為。
“全球科幻小說”及其在后殖民/后人類語境下的再書寫
與其他文學(xué)類型相比,科幻是一種很晚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文類,它有兩種創(chuàng)造現(xiàn)代社會的前瞻性愿景:其一是烏托邦,它起源于大航海時代的游記,托馬斯·莫爾賦予其政治意義;其二是人類會持續(xù)進步的思想,它是隨著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而逐漸成形的一種敘事,在世界范圍內(nèi)對現(xiàn)代思想產(chǎn)生影響。這兩種強調(diào)普世性的愿景,都主要是由現(xiàn)代歐洲知識分子發(fā)明的。
瑪麗·雪萊于1818年創(chuàng)作的《弗蘭肯斯坦》是第一部“全球科幻小說”,它承載了上述兩種愿景,既表達正題,也提供反題,堪稱一場科學(xué)和心靈的雙重革命。在逾越界限和跨國界想象上,《弗蘭肯斯坦》超越了許多后來的科幻小說。相較而言,盡管凡爾納和威爾斯的世界觀相對狹隘,但“人類是一個整體”的傳統(tǒng)在他們具有跨國的視域和立場中得以延續(xù)。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到劉慈欣和其他中國科幻作家的作品中。《三體》在氣勢宏大的敘事中,呈現(xiàn)了全球性末日事件:從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到毀滅地球文明的游戲終局,繼而是太陽系的隕滅,最終是整個人類文明的終結(jié)。
從全球角度看,自烏托邦到惡托邦的轉(zhuǎn)型始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末期,成為現(xiàn)代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科幻的文類基因決定了即使是最黑暗的惡托邦想象,也同樣來自對現(xiàn)實秩序之外理想制度的追求,而正是這樣的沖動,最初啟發(fā)了烏托邦主義。
伊斯塔范·西瑟瑞-羅內(nèi)通過將“全球科幻小說”置于對歐洲霸權(quán)的委婉批評中進一步解釋了它的概念:“歐洲殖民擴張時期的頂峰,即是將西歐文化的主導(dǎo)理所當(dāng)然地視作‘普世性’。‘宇宙’的概念來自神學(xué)霸權(quán),并帶有明顯的非唯物主義思想的學(xué)者認(rèn)為人類處在宇宙中心地位的觀點。……但是,地球不斷從內(nèi)部擴大,它的未來前景是整個人類物種的智力解放、不受限的交流和物質(zhì)發(fā)展。”這段話將“全球科幻小說”的概念歷史化,追溯到它的發(fā)源地歐洲,策略性地指出人類中心觀和歐洲人文主義及其科幻再現(xiàn)的虛幻性和局限性。而如今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非洲、南美洲、阿拉伯世界科幻小說的崛起,都有助于抵抗此前歐洲霸權(quán)將科幻小說納入“一個世界”的牽引。后殖民科幻小說正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旨在解構(gòu)那個在種族和性別意義上對“他者”排斥的世界。
而關(guān)鍵問題在于人是什么。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科幻小說的“世界性”開始偏離歐洲中心論的人文主義,轉(zhuǎn)而強調(diào)差異的多樣化集合體。諸如雪萊的弗蘭肯斯坦的怪物、恰佩克的萬能機器人、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米切爾的克隆人等世界科幻中的知名角色,為此后興起的后人文主義理論框架帶來生機。他們告別歐洲中心論的單一人文主義觀念,在階級、性別、種族、性取向、意識形態(tài)取向和自我身份認(rèn)同等方面拓展延伸了人類形象。后人類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結(jié)合更好地表達了新浪潮的烏托邦愿景,同時關(guān)于“人”的定義也在“全球科幻小說”的新話語中得到了新的回答,即后人類時代將有可能建立所有生命平等的希望。
中國潮
《荒潮》是陳楸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展現(xiàn)了貿(mào)易流動、國際談判、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以及國家、宗族和企業(yè)的權(quán)力整合。它的英文譯本的出版為“全球科幻小說”增加了一部中國作品。《荒潮》中的世界形象將關(guān)于虛擬、擬像理論與中國的真實體驗策略性地聯(lián)系起來,使中國現(xiàn)實成為科幻敘事,揭示大家習(xí)以為常的現(xiàn)實之下隱藏的“真實”。小說中女主人公的人格分裂指向了政治經(jīng)濟的全球突變與地方權(quán)力的全面腐敗所導(dǎo)致的無人性的狀態(tài),而她也是中國科幻中第一個引人注目的賽博格形象。在這部獨特生動的小說中,敘事的高潮是強調(diào)了一種地域性的感傷主義,在賽博格的意識中注滿了人性。
同時,《荒潮》也是一個關(guān)于“回家”的故事。盡管小說有大量對傳統(tǒng)父權(quán)社會的現(xiàn)代性批判,但其中也充滿了懷舊哀傷的鄉(xiāng)愁。中國科幻小說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將中國科幻新浪潮在全球語境中樹立的世界形象帶回國內(nèi)。科幻的成功喚起了中國人在世界上閃亮登場的雄心,也同時也喚醒一種鄉(xiāng)愁,讓中國人來思考何為正宗的中國性——即提問中國科幻有何中國性,決定了它的海外成功;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只在中國語境中有意義,《三體》的海外成功,恰恰因為它在文體上的全球性。
鄉(xiāng)愁的情緒表達也呈現(xiàn)在由小說《流浪地球》改編的電影中,它將一場太空奧德賽改編成了一個回家的故事。出于商業(yè)考量,電影強烈突出了與家庭和家園相關(guān)的價值觀,將劉慈欣在他過去的作品中努力把一個內(nèi)向封閉文明推向外向開放空間的作為,重新演繹成為一個有關(guān)“鄉(xiāng)愁”的回歸旅程。中國科幻文學(xué)再次崛起,為國內(nèi)外更廣泛的讀者所知的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中國夢”的理想。“中國夢”作為一個全新的口號,指向更為傳統(tǒng)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結(jié)合的思路。中國科幻文學(xué)走到了世界文學(xué)的舞臺中心,與此同時,中國科幻在大銀幕的首次亮相具有一種達成國內(nèi)文化敘事的策略,講述了一個關(guān)于家園、鄉(xiāng)愁和回家的故事。
當(dāng)中國科幻文學(xué)登上舞臺中心,還有什么是看不見的
與此不同的是另一種世界形象:它抵制與“回家”相關(guān)的情感,并對與“家”和“(家)文化”有關(guān)的價值觀提出深刻質(zhì)疑。作為中國當(dāng)代科幻代表作家之一,韓松的大部分作品仍不為大多數(shù)中國讀者所知。與劉慈欣刻畫的崇高宇宙形象形成對比,韓松的小說經(jīng)常描寫孤立幽閉的空間,這些空間意象可被視作現(xiàn)代版本的“鐵屋”。
魯迅是20世紀(jì)初科幻小說的倡導(dǎo)者,他敢于直面中國傳統(tǒng)的黑暗面;魯迅將“鐵屋”變成象征中國傳統(tǒng)邪惡性質(zhì)的核心隱喻,并通過刻畫生活在鐵屋中的人們的掙扎和死亡,發(fā)出吶喊以喚醒民眾來一起拆掉舊制度、舊傳統(tǒng)和舊家園。韓松的創(chuàng)作隔了一個世紀(jì),依然在回應(yīng)魯迅的批判。《看的恐懼》是其早期作品,表明科幻小說本身可以作為一種“裝置”,以揭示那不可見的、令人不安的世界本相,這與魯迅《狂人日記》的主旨不謀而合。韓松科幻小說表現(xiàn)“不可見”真相的獨特詩學(xué),決定了他勇于在故事中昭示一切的敘事倫理。
在中國當(dāng)代主要科幻小說家中,韓松始終是主流的挑戰(zhàn)者。在中國科幻文學(xué)迅速占據(jù)的全球市場中,韓松作品被翻譯的數(shù)量相對少。除了一些短篇小說,他的代表作都還沒有跨越國界,未能進入建立在跨國界流通和跨語言閱讀基礎(chǔ)上的世界文學(xué)中。在某種意義上,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國內(nèi)外主流讀者看不見的科幻世界,一個隱藏在成功故事陰影中的神秘、黑暗、深幽的世界。韓松的科幻愿景和寫作方法也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美學(xué)特征,即賦予不可見之物以生命,揭示世界表象之下隱藏的深層結(jié)構(gòu),并釋放出一種打破所有對權(quán)力和財富盲目樂觀的幽暗力量。當(dāng)中國科幻步入世界文學(xué)舞臺中心的時候,韓松的想象構(gòu)成了中國科幻文學(xué)中不可思議的潛意識,并以此來更深入認(rèn)知科幻小說的倫理承擔(dān)與文化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