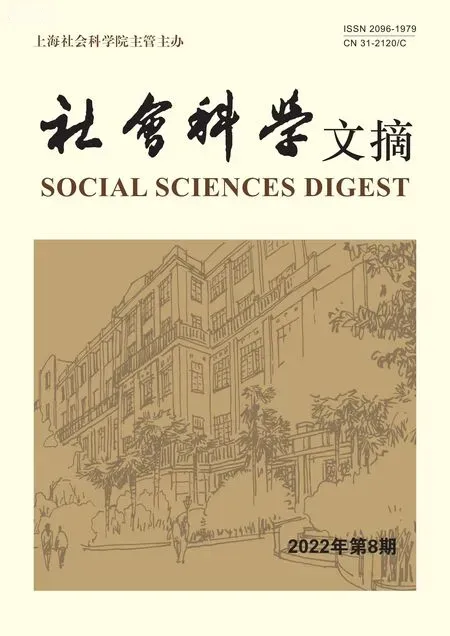論想象
——一種社會學的概念化
文/鄭震
作為一個概念的名稱,想象在社會學的歷史中近乎是缺席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想象不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我們將從社會學思想的歷史中尋找一些重要的切入口,以展現想象如何以某種隱蔽的方式早已存在于社會學的思想之中。當然這并不是對想象本身的直接研究,但思想史的中介作用對于一個尚缺乏概念化的問題而言,無疑具有某種開拓性的間接作用。正是思想史的啟發與反思性的重建,為我們進一步探討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的想象活動的形式化特征和意義提供了出發點。
社會學思想中的想象因素:表象與錯覺
許茨認為那個在原初經驗中的活生生的主觀意義的世界從不是陌生的匿名存在,這意味著任何客觀化的把握都有可能錯失主觀意義的豐富性。然而看似悖論的是,日常生活世界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這確保了人們之間的某種意義上的理解和溝通的可能性,即當作為社會化建構的主體間性的共享知識能夠有效地為面對面互動提供支持的時候,人們似乎并不急于去探究那個黑箱式的主觀意義的世界本身,而是停留于對這個世界的某種類型化的想象,這就是主體間性的文化或意義結構。許茨理論的焦點就在于“類型化”,它首先是排除各種獨特性的具有社會客觀性的常識構造,而社會科學的類型化建構則是基于此種常識構造的更高層次的客觀性建構。如果日常類型本身就已經包含著一種想象的維度,那么科學的解釋就可能意味著對想象的想象。畢竟,類型化是基于許茨所謂的主觀意義世界的不透明性,我們無法確切地了解支撐他人行動的那個意義的變幻不定的獨特方面,類型化僅僅是一種強加的一般性構造,它用類型來取代活生生的經驗現實,它的普遍主義的效率是以犧牲特殊主義的生動性為代價的,它將經驗的不確定性還原成對一種確定性的想象。
許茨所追求的那個基于常識經驗的構想而建構起來的科學概念的構想,在加芬克爾的眼中也只能是一個想象的世界,它以科學的偏見想象了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結構,而這兩者本來是不可通約的。與此同時,我們不難推論出,日常行動者對主觀意義的類型化解釋也同樣無法得到加芬克爾的認可。在加芬克爾看來任何客觀化都將導致意義的喪失,也就是導致對現實的想象和歪曲,唯一不同的也許只能是,社會科學由于其客觀化的程度更高,從而更加徹底地導致了現象的喪失。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常人方法學并不宣稱提供一種有關其對象的高度概念化的命題陳述,拒絕采用一種相對客觀化的方式來概念化(類型化)其所研究的現象,因為這只能導致現象或細節的喪失,從而無法真正地理解其所研究的現象。我們甚至不能將此種做法視為是通常意義上的研究,因為“常人方法學的成果與根本的秩序現象是同一的”,研究只是對現象的展現,或者更確切地說只是去實踐現象本身。這一做法的消極色彩是顯而易見的。它放棄了對社會現象本身的反思和批判的立場,它在拒絕想象社會現象的同時卻沒有意識到,成為“對象”本身也就意味著接受對象所存在的問題,以這樣的方式理解“對象”也就意味著像“對象”一樣誤解自身,從而以其自身的實踐而重現了社會現象自身的想象,因為這個想象也許正是社會現象所無法回避的構成。
布迪厄所謂的誤識恰恰是加芬克爾所堅持的自然態度中的錯覺,似乎現實從來就是如此,在所有人的相似的實踐中進行著一種社會的實驗驗證,作為結果的可重復性正是這一實踐繼續進行的動力本身,反復的實踐證明了實踐自身的合法性,這是社會邏輯中最荒謬的邏輯之一:循環論證。然而這種自然態度并不像它看起來那樣理所當然,它的自然表象完全可能成為最隱蔽和堅固的枷鎖。對誤識的揭示可以視為是對現象學保守主義的一種批判,而加芬克爾則無意之中陷入這種保守主義的陰影中。誤識意味著對自身的行動和處境采取一種理所當然的立場,從而拒絕反思這一行動及其處境的合法性,這也就是胡塞爾所說的將生活世界的信念視為是前科學的原初自明的真理。然而誤識正是想象所制造的錯覺,即想象中的幻想因素(不是有意識的幻想),當人們以類型化的方式來想象他人的形象時,卻誤以為抽象的類型即是他人的形象本身,從而無視這一形象的社會歷史性建構及其所可能隱含的暴力。在布迪厄的語境中,想象的不言而喻性超越了意識哲學的狹隘視角,在一種無意識的錯覺中揭示了社會暴力最深層次的基礎。由此,人們無需將想象理解為行動者有意識所進行的某種形象化或表象化活動,因為社會表象的生成就其最隱蔽的機制而言,恰恰是一種沒有被意識到的身體現象,也正是因此表象并沒有被視為是表象。一種作為社會歷史建構的表象被誤以為是社會的實在本身,仿佛它是客觀給定的事實,獲得了某種自在的規律性或自然性的特征。然而這一切都僅僅是一種觀念的游戲(自證預言),那些被誤以為是實在的現象被賦予了一種符號化或象征化的特征,從而為其存在帶來了某種虛構的穩固性。
社會學思想中的想象因素:表象與真相
在類型化的運作中不只有誤識與暴力,與所謂真相的不一致也并不一定意味著對生存的壓迫與剝奪。我們甚至不能將此種不一致一味地視為是完全消極的現象,戈夫曼有關印象管理的討論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讓我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向表演失誤時的觀眾舉措,這一舉措揭示了表演并非只是一種單向度的演出和接受,而是表演者和觀眾共同投入的情境互動,正是在此種共同投入的互動實踐中社會結構的秩序特征才得以被生產和再生產。觀眾也同樣投入到印象管理之中,也就是去捍衛那個表演者所制造的假象。與其說人們在此所捍衛的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錯覺,還不如說人們是在捍衛一種理想化的社會秩序。表演的偽裝和觀眾的得體都是為了維持或建構一種理想化的互動形態,想象與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反倒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動力所在,這其中自然有合乎各方生存的現實利益的左右。真相成為人們避之不及的可怕之物,觀眾期待著表演者的適當性,盡管已經意識到這也許只是一場表演。這充分揭示了社會現實并不是什么客觀給定的絕對的事實,也不是邏輯上完全統一的單一形態,而是存在著多重的面孔或不同的建構。有的時候人們更熱衷于尋求所謂的真相,厭惡那種被欺騙的感覺;但有的時候,人們卻更樂于沉浸在想象之中,似乎真相是可怕的,唯在想象中方能生存。
社會學思想中的想象因素:想象力
米爾斯為我們提供了想象的另一幅面孔:想力。想象力是一種有助于縮小認知與現實之間的不一致性的創造性能力,盡管這并不意味著它將帶來絕對的真理,但它有助于超越傳統的掣肘與局限,從而推動邁向對現實的更加充分的認知。由此可見,想象或想象力也可以成為一種打破幻覺的束縛、推動創造性認知的力量。歸根究底這是因為想象是一種不確定性,它并不遵循工具理性化的科學邏輯,不是嚴格執行的程序法則,而是不被現實所束縛的創造性的力量。如果我們不僅僅局限于科學思維的意識層面,我們會發現這種由不確定性所主導的創造性彌漫于想象的各種面孔之中(我們用想象力來命名此種創造性)。在日常生活的類型化想象中,它促使人們忽略了那些難以把握的變化不定的直接經驗,從而在一種類型化的想象中構造出日常生活世界的圖像。這種創造性也同樣可以在一種理想類型的意義上捍衛某種道德的秩序,即將一種社會歷史性的道德要求想象成特定情境中理所當然的秩序,即便是一種具有欺騙性的表演也還是在事實上捍衛了這一想象的表象。進而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說,想象的創造性產物既可能成為阻礙合理認知的科學的錯覺,也可能成為顛覆這種錯覺與暴力的創新的力量,這正是想象的奇妙之處,它的不同面孔向我們揭示了想象那不容忽視的社會歷史意義。
結束語:想象的社會學分析
我們的分析已經表明,想象幾乎是社會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現象,其存在的原初根源是直接經驗世界的不透明或半透明及其變動不居的狀態。正是基于此種不透明和不確定,想象成為社會行動的一般性特征之一,我們甚至可以以一種略顯夸張的口吻說,人類正是生活在他們自身所想象的世界之中。這并不總是一種有意識的算計,甚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以一種不言而喻的過程為其特征。
因此,人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非有意識地展開一種表象化的活動,以此來扭曲現實的形象,相反人們常常沒有意識到,他們自身的偏好與視角、理想與好惡在無意之中已經作為一種想象的要素而存在于他們的行動之中。當人們以相似的方式在實踐之中去想象現實的時候,這種未經籌劃的共謀使得想象的現實仿佛就是那個被想象的現實本身(行動之間的相互印證,但其實質不過是一種循環論證),因為不會再有所謂的真相與想象的碰撞,這種自證預言式的處境更加強化了對想象的執著。
在一種缺乏高度對象化的意識活動介入的情況下,想象的世界仿佛就是那個真實的世界本身。當人們以共同的想象投入到共同生活的建構之中的時候(這當然是一種偏重主觀視角的分析),想象與真相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人們把表象視為真相,把暴力當成法則,在一種非反思的盲從中被自身所參與建構的想象所奴役,這恐怕是想象最消極的意義所在了吧。但正如我們的研究所表明的,在社會暴力與壓迫偽裝成受害者的自我想象而實施奴役的同時,想象也可以成為一種共存的積極力量,對于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類而言,想象出一種道德的模樣,這看似消極卻蘊含著積極的力量。當人們共同為了一種情境的道德定義而努力維持的時候,這種被各方視為理當如此的適當性與所謂的真相又有什么區別呢?即便類型化的想象偏離了它們本來試圖把握的直接經驗本身(例如那個表現出道德模樣的人其實采用了非道德的表演),但當人們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中不斷地以這種類型化的方式來生產和再生產生存的過程,那么它又何嘗不是一種社會歷史性的真相呢?
我們將想象與現實的此種轉化關系稱為是想象的辯證法,它從一個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世界的高度復雜性,那種將社會歷史現實想象成客觀給定的事實的做法,充其量只是為這個復雜性增加了一個辯證的因素,當然這取決于這一想象被信仰的程度。事實上,那些被想象所遮蔽的“真實的經驗”其實還是一種社會歷史性的建構,只是與那個試圖把握它的類型相比,它構成了一種更具原始性的事實(這種原始性僅僅意味著類型化的常識運作的相對缺乏)。我們并不否認認知上的扭曲的確是一種社會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對立面就是所謂的永恒絕對的事實,它們只是在不同層次建構的事實之間所做出的一種比較。因此,我們不應當將想象僅僅視為是對事實的偏離,想象的實踐及其后果也同樣是社會歷史性的現實存在,它既存在于那個想象化的過程之中,也存在于那個被想象化的事實之中(區別僅僅是層次性的,是在作為理想極點的完全沒有類型和純粹類型之間的層次變化)。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才可能更具建設性地看待那種對情境中的道德模樣的想象,基于不同場合所采用的得體的行為舉止正是這種想象的展現,至于那些舉止之中是否蘊含著一種投入的信仰,只是在社會行動的層次劃分中具有某種實際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那些與他人共同生活的道德想象在維持著某種基本的社會秩序,這當然是撇開各種消極因素的理想類型式陳述,但它的重要意義卻不可忽視。被想象將以一種道德的模樣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和承認這種想象的合法性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不正是建構一種共同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嗎?
所以,我們不只是在盲從中被想象所奴役,同樣也在盲從中被想象所涵養;我們不只是在想象中誤入歧途,也在想象中理解并積極地生產和再生產著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這一切都構成了一種想象的辯證法。只不過想象很少是以某個單一的面孔出現,它由此才涵括了一種生活的豐富性。正是社會經驗世界的不透明(或半透明)和不確定使得想象成為每一次遭遇的內在構成,盡管想象因此而包含著對明確性的尋求。但因為社會經驗世界的不明確性是無法徹底消除的本體論事實,想象自然也難以通過規律性的方式來獲得其存在的有效性,更何況絕大多數想象本身就是以不言而喻的實踐方式在發揮作用,想象正是其想象的那個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構成因素,它不可避免地帶有不確定性的烙印。日常生活中的人們以不同的方式想象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相同的現實完全可能激發出截然不同的想象),卻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想象本身就增加了這一現實的晦澀性。但這的確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創造性,想象的不確定性無疑為生活增添了多樣化的事實。這種多樣性的能力雖然與科學的創造性在結果上往往大相徑庭,然而它們擺脫成見存在的勇氣卻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只不過科學需要一種強烈的意識介入,需要將打破成見的束縛作為一種明確的對象化需求來加以實踐,而日常生活的想象卻主要在一種前反思的理所當然之中鋪展其創造性的變換能力,這當然也使之更容易陷入各種錯覺與暴力的統治之中。
至此我們可以說,想象是一種有意或無意地制造社會表象的創造性的過程及其結果,它與社會歷史現實之間有一種辯證的關系。但無論怎樣,想象都不能擺脫一種社會歷史性的表象化特征,這正是人之存在的社會歷史局限性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