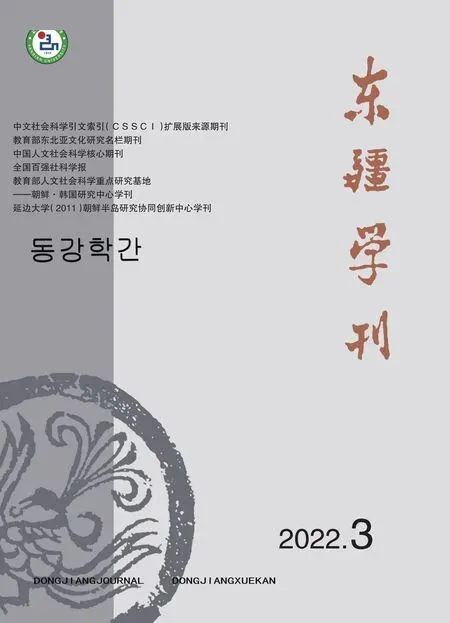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初探
王銘玉,鄒昊平
引言
20世紀之初,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便由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啟。自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日臻成熟,逐漸走向規模化、系統化、專業化。如今,中國共產黨組織開展的翻譯活動已有百年歷史,成績卓然。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的研究成果目前并不豐富,系統、完整的研究更是鮮見。鑒于此,本文從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的體系研究出發,嘗試對其研究內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意義及價值展開初步探討。
一、“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相關概念界定
(一)“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針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翻譯史展開研究,因此這里的“中國共產黨”除組織概念外,還指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中的翻譯主體,即參與由中國共產黨組織或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各類翻譯活動的個人、集體譯者。
(二)“百年翻譯史”:本文研究的“百年翻譯史”既包括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至今的百年翻譯史,也包括中國共產黨建黨準備階段的翻譯史。早在建黨準備階段,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便已開始從事馬列思想的譯入活動。一方面,該階段的翻譯活動為后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另一方面,參與該階段翻譯活動的多數譯者后期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并繼續從事黨內翻譯活動。因此,中國共產黨建黨準備階段的這段翻譯史也屬于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的所指范疇。
(三)“翻譯內容”:本研究中的翻譯內容專指與黨和國家建設、發展緊密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各類翻譯文本。需要強調的是,翻譯內容還涉及到了一些“文藝作品”,但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中“文藝作品”的翻譯內容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藝術)作品,而是特指百年以來與中國共產黨發展建設、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緊密相關的中、外文學(藝術)譯作。
(四)“黨史分期”: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以“黨史”為主線,分期主要依據國內黨史權威專家的界定。2021年2月,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曲青山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一文中,對中國共產黨“黨史”作出最新劃分:“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可以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立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從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這四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完成和推進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1]為保證本文研究的嚴謹性和科學性,我們遵循上述最新黨史階段的劃分,圍繞四個時期的翻譯史展開研究,系統反映“黨史”的整體面貌。
(五)“建黨準備階段”:自辛亥革命爆發至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前身”在這一階段出現、形成,因此我們便將該階段定義成中國共產黨“建黨準備階段”。1942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學習組指導學習研究中共黨史時明確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只從1921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2](402)“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于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后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2](404)可見,黨史研究需要以貫通的視角、歷時的態度,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談起,把該階段視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準備階段”,百年翻譯史研究不能忽視這一時期。
二、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的現存問題
“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是一個重大課題,亟待在百年之際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但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現有研究成果的分析與考察,我們發現尚有許多工作要做:
(一)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零散龐雜,缺乏系統梳理
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零散龐雜,大體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翻譯活動時空跨度大。從時間跨度來看,中國共產黨翻譯史既包括建黨準備階段的零星翻譯活動,也包括建黨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百余年的翻譯活動。早在中國共產黨建黨準備階段,馬列著作的譯入工作便由朱執信、陳望道、惲代英、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愛國知識分子率先展開。他們對先進馬列思想的翻譯與闡釋,為后期自身成為共產主義戰士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后的百年歷程里,為服務于黨和國家各時期建設發展,中國共產黨以個人或者集體身份進行的翻譯活動更是不勝枚舉,層出不窮。從空間跨度來看,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遍及全國各地。例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期,關于馬列著作的翻譯陣地就有“南陳北李”之分。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關于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著作的外譯活動也不乏各級地方政府的組織參與。如《之江新語》(外文版)、《紅船精神:啟航的夢想》(外文版)便都是由浙江省省委宣傳部、中國外文局等多方合作翻譯出版。
第二,翻譯形式多種。最初,中國共產黨建黨準備階段的翻譯形式為譯入,對象主要為馬列著作。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將譯入與外譯兩種形式相結合。除了馬列著作、蘇聯文藝作品的譯入,還有部分毛澤東著作(前期共產國際援助,后期中國共產黨獨立開展)的外譯。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繼續開展馬列著作、蘇聯與歐美文學作品的譯入,另一方面開始加強毛澤東著作、中國文學作品等方面的外譯。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保持馬列著作譯入的同時,加大對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全國黨代會和全會主要文件、“兩會”主要文件、黨史文獻及中國文藝作品的外譯。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翻譯形式基本與前一時期保持一致,既包括馬列著作的譯入與修訂,也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兩會文件等中央文獻與文藝作品的外譯與傳播。
第三,翻譯內容多樣。在中國共產黨建黨準備階段,早期的翻譯內容以馬列著作為主。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譯入馬列著作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著手組織蘇聯、法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如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第四版專為譯載各類外國文藝作品而設立。同時,不論是前期共產國際協助支持,還是后期中國共產黨獨立開展,其翻譯內容均以毛澤東著作為主。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翻譯的內容逐漸豐富。除了馬列著作,還有不少蘇聯、歐美文學作品。除了毛澤東、劉少奇等少數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還包括許多中國文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共產黨組織翻譯的內容中開始出現多語版本。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翻譯的內容顯得更加多樣。在前一時期的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又組織開展了更為系統、全面的多語翻譯,其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全國黨代會和全會主要文件、“兩會”主要文件及黨史文獻等內容。步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在沿襲以往傳統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譯入與外譯的具體內容除了政治文獻以外,還在文化傳播、文明互鑒上有所創新,不斷豐富。例如,中國外文局在這一時期陸續推出了《敦煌》(英文版)、《這邊風景》(波斯文版)、“絲路百城傳”(多語版)等諸多反映中國文學、中國藝術的外譯作品;2019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還專門簽署了“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等。
第四,翻譯主體多元。在建黨準備階段,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的主體(組織參與者)均為追崇馬列思想的愛國知識分子(早期共產主義者),屬于個體譯者。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于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外語人才儲備不足、翻譯經驗欠缺等各方面限制,當時翻譯活動的主體還包括共產國際。1938年,中共中央長江中央局下屬機構國際宣傳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國際宣傳組成立。此后,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便開始由自身組織、獨立領導,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翻譯活動,均由中國共產黨相關的集體或個人作為翻譯主體。
當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缺乏系統梳理。筆者經過詳細的文獻閱讀與分析發現,學界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史料梳理零星散亂,尚未成體系。第一,當前諸多學術論文或專著中有關共產黨翻譯的史料梳理往往局限于特定時期亦或是特定專題。如袁西玲在《延安時期的翻譯活動及其影響研究》中只提及了有關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部分翻譯史史料;邱少明在《民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史(1912-1949年)》中僅梳理了民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馬列著作這一專題的譯入史料;賀團衛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研究》中梳理的僅是民主革命這一時期《共產黨宣言》的譯入史料。第二,國內大部分論文和專著中有關共產黨翻譯的史料梳理還往往局限于特定人物。例如,龐培法的《成仿吾五次翻譯〈共產黨宣言〉》、李曉棟的《翻譯〈共產黨宣言〉第一人》、張俊明的《陳望道第一次翻譯〈共產黨宣言〉》等,以上文章雖對中國共產黨翻譯史史料均有提及,但零星散亂,內容局限,缺乏系統梳理。
簡言之,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時空跨度大、翻譯形式多種、翻譯內容多樣、翻譯主體多元,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的零散龐雜。同時,當下學界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梳理往往局限于特定時期、特定專題或特定人物等,致使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的整理缺乏系統性。
(二)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內部分析不足,考察視角單一
一方面,目前學界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研究成果較少,對其翻譯活動的背景、過程、特征、影響等要素的內部考察相對有限。首先,國內本身關于翻譯史的研究成果就相對欠缺。從柯飛2002年開展的調查結果來看:“上世紀后半葉我們翻譯方面出版的書籍約500多本,其中理論研究占20%以上,而翻譯史僅1%而已。”[3](31)袁西玲曾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指出:“2003年之前,國內的外語類刊物很少刊發翻譯史的文章,零星的翻譯史論述文章被穿插于‘譯論’專欄中。”[4](19)其次,就國內現有的翻譯史研究成果而言,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探討就更為缺乏。當前國內翻譯史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主要與翻譯史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理論等相關;第二類主要與人物史、專題史、時期史、區域史等相關。而人物史研究多圍繞個體譯者,專題史研究多涉及佛經翻譯、西學翻譯、科技翻譯、文學翻譯以及馬列著作翻譯等,而時期史研究暫以民國時期、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等時間跨度較小的斷代史研究為主。因此,目前國內翻譯史研究很少涉及中國共產黨翻譯史,對于其內部分析與考察也就自然相對欠缺。
另一方面,就現有的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研究成果而言,雖然各有千秋,但分析的視角有待擴展和完善。例如,袁西玲在《延安時期的翻譯活動及其影響研究》一文中從翻譯活動的生成語境、譯者主體、翻譯產品及翻譯人才培養視角對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翻譯史進行了分析考察,而從翻譯機構、翻譯流派、社會影響等視角的分析尚有空間。劉科、朱桂蘭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翻譯事業的特點和翻譯成果初探》一文中主要以翻譯事業、翻譯成果為視角考察了中國共產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的翻譯史,我們還可以從背景、翻譯人物、翻譯事件等其他視角展開分析探究。唐榮堂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對外宣傳活動述論(1921-1927)》一文中從外宣途徑、外宣成果視角對中國共產黨早期對外翻譯史展開研究,更廣的視角未予以關注。除此之外,其他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學術成果從各自研究目的出發,多從個體譯者研究、典型譯作研究等單一視角展開探討,暫時還無法形成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的多元視角考察。例如,葛開勇的《1923年-1926年〈新青年〉與蘇聯文獻翻譯》一文從譯作研究這一視角探究中國共產黨1923年至1926年的翻譯史;李永春的《蔡和森翻譯和傳播〈共產黨宣言〉考析》一文以個體譯者及其譯作研究為視角考察中國共產黨有關《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孫玉祥的《〈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翻譯出版》一文,同樣是以某一譯作研究為視角對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史展開考察。
簡言之,目前學界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研究成果較少,客觀上對其分析考察相對有限。而就現有的研究成果而言,考察視角也仍有待擴充。
(三)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的時間跨度受限,“黨史”主線尚未凸顯
第一,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研究的時間跨度不足,百年“黨史”主線無法直觀顯現。根據筆者搜集的資料顯示,目前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研究的時間跨度最短為7年,最長的也僅有數十年。如唐榮堂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對外宣傳活動述論(1921-1927)》一文中介紹了7年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外宣翻譯活動。王璐璐和李飛龍在《全面抗戰期間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翻譯及時代價值》一文中研究了中國共產黨在1937年至1945年8年期間的馬列著作翻譯史。孫嬋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研究(1919-1949)》中,研究中國共產黨馬列思想翻譯史的時間跨度為五四運動爆發至新中國成立。在路軍的《〈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在中國的早期翻譯與傳播》一文中,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時間跨度相對較長,但也僅從20世紀初至改革開放前。在《新世紀以來〈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翻譯研究傳播述評》中,陳紅娟則著重梳理了2000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共產黨有關《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史實。顯然,已有成果大多為“斷代史”,未能完整地體現“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研究”的時間跨度,與百年“黨史”這條時間主線不相吻合。
第二,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研究內容不夠全面,未能完整勾勒百年“黨史”主線。理想的研究應將所有與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程相關的翻譯活動、翻譯人物、翻譯作品等視為研究內容,從而確保研究內容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對應,完整勾勒出百年“黨史”主線。目前國內的學術成果大多屬于主題研究,圍繞翻譯主旨突出對某一譯作、某一人物抑或是某一翻譯專題的探索。例如,劉長軍在《〈資本論〉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及其歷史地位》一文中對中國共產黨關于《資本論》這一著作的翻譯史進行了探討;帥澤鵬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早期譯介者》一文中對中國共產黨翻譯史中的馬克思主義譯者進行考察;又如張傅在《中國共產黨傳播馬克思主義百年回望》一文中對中國共產黨關于馬克思主義這一專題的翻譯史展開了探討。客觀地講,上述研究因為沒有“面”的要求和需求,自然多在“點”上做文章,它們均對百年翻譯史研究構成重要的參考依據,但卻無法與中國共產黨的百年發展歷程彼此觀照,因此難以凸顯“黨史”這條主線。
三、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的研究內容
鑒于目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中的問題與不足,筆者以中國共產黨“黨史”為主線,將百年翻譯史的研究內容按照四個黨史分期對應劃分成四大部分。各部分研究內容主要以所在時期的翻譯大事記及相關重要史料為經,以代表性翻譯人物(機構)及其經典譯作為緯。如此一來,既實現了對各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的梳理、歸納,也為后期對其展開多元分析、多維考察奠定了基礎。
(一)第一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21-1949)
該部分主要圍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展開梳理與分析。然而,“從史學視角來看,不管什么歷史活動,不可能一夜之間突然出現,必然會有一個前期醞釀和認識的過程。”[5](123)為此,筆者在該部分追加了有關中國共產黨“建黨準備階段”的翻譯史研究,一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翻譯史研究追根溯源,二來使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研究更具系統性、史學性。在建黨準備階段(1911-1921),我們主要介紹建黨準備階段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為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先進思想而開展的早期馬列思想譯入活動。筆者具體將其劃分為五四運動前、五四運動后兩個時期,以創建《每周評論》、設立“馬克思主義”專欄、成立京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重要史料為經,以《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即馬克思)之學說》《社會主義精髓》等典型譯作和以朱執信、陳獨秀、李大釗、淵泉、陳望道等代表性翻譯人物為緯,從背景、過程、特征及影響等層面,對早期馬列思想譯入進行全面梳理與多元考察。該階段馬列思想的譯入,為后期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對于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而言意義重大。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除馬列思想、外國文學作品的譯入,還包括毛澤東著作的部分外譯。具體如下:(1)譯入篇包含馬列思想、外國文學作品。首先,筆者主要以成立人民出版社、召開“國民追悼列寧大會”、左翼文化運動,建立延安馬列學院等翻譯相關的大事記為經,以《哥達綱領批判》《列寧主義概論》《哲學的貧困》等翻譯作品和以沈澤民、李季、瞿秋白、李達、吳半農、成仿吾等代表性翻譯人物為緯,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馬列著作的翻譯史展開梳理考察。其次,筆者依據《解放日報》外國文學專欄,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與蘇聯致力和平的奮斗》《中國內部的弱點妨礙了中國作戰努力》《在前線》《小孩與列寧》《上尉什哈優隆科夫》等譯作和以宏毅、柯柏年、陳學昭、岳西、茅盾等代表性翻譯人物為研究史料,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蘇聯、法國等文學作品的譯入展開梳理與分析。該時期譯入的外國文學作品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士氣,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延安的馬列著作譯者、新聞翻譯者和文學作品翻譯者們正是在汲取馬列主義思想和正義力量的‘火種’,來點燃抗戰時期邊區民眾的抗戰意識,他們是知識的傳播者、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文化價值的傳輸者以及社會新文化的締造者。”[4](112)(2)外譯篇主要涉及毛澤東著作。本篇主要以共產國際的支援譯載、第一篇毛澤東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譯介、第一本毛澤東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多語單行本)的出版等重要史料為經,以共產國際、中央長江中央局下屬機構國際宣傳委員會、南方局外事組、國際宣傳處等代表性翻譯機構為緯,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毛澤東著作的翻譯史展開梳理與考察。
(二)第二部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1978)
該部分主要圍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進行梳理與探討。(1)譯入篇包含馬列思想、外國文學作品。首先,筆者以中央編譯局的《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資本論》等譯作為史料,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馬列思想的譯入開展考察。其次,筆者以《牛虻》《復活》《戰爭與和平》《欽差大臣》《巴爾扎克中短篇小說》《日本的黑霧》等蘇、法、日經典譯作及草嬰、巴金、余振、滿濤、蕭乾、劉振瀛、羅大岡、文潔若等一系列翻譯家為線索,展開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史研究。由于這些外國文學作品的譯入,使得國內民眾對世界上不同政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與人民有了更為清晰的了解,更加堅定了對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與信賴。同時,反映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熱潮的文學作品,大大激發了人民大眾的勞動熱情,鼓舞著一批又一批的勞動者投身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把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當作自己學習的好榜樣。”[6](442)因此,上述譯入的外國文學作品均與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息息相關。(2)外譯篇主要包含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全國黨代會主要文件、全國人代會主要文件、文藝作品及其他重要文件。筆者以《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成立、“毛澤東著作翻譯室”成立等大事記為經,以中央編譯局的《毛澤東選集》《劉少奇選集》、中共八大會議文件、全國人代會五屆一次會議文件等外譯本為緯,考察了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全國黨代會和人代會會議文件的翻譯史;以中央編譯局的多語版現代京劇和舞劇《紅燈記》《沙家浜》,多語版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等譯作,中國外文局的多語版《田寡婦看瓜》,英文版四大名著,《中國文學》英文刊創立等史料為線索,探討了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文藝作品的翻譯史;以《詩經》《楚辭》《論語》《老子》《詩經選》《唐詩選》英法版等譯作為基礎,分析了該時期中國共產黨個體譯者許淵沖關于文學作品的翻譯史;最后,基于中央編譯局的《中國軍事博物館簡介》《解放軍管理條例》《評莫斯科三月會議》多語版譯文和中國外文局創立的《人民中國》中俄月刊等史料,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其他主題重要文獻的翻譯史進行研究。
(三)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8-2012)
該部分著重探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各項翻譯活動。(1)譯入篇主要涉及馬列思想。本篇以中央編譯局的《列寧選集》第三版修訂版(一至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資本論》(第1、2、3卷)等譯本為主線,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馬列著作的翻譯史進行梳理、分析。(2)外譯篇內容更加豐富,主要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全國黨代會和全會主要文件、全國人代會主要文件、全國政協會議主要文件、黨史文獻、文藝作品及其他重要文件。本篇以中央編譯局的《毛澤東文稿》俄文版、《陳云文選》多語版、《朱德選集》多語版、《劉少奇選集》多語版、《周恩來選集》多語版、《鄧小平文選》(一至三卷)多語版、《江澤民文選》多語版、《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多語版、習近平《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節選)》英文版等一系列譯本為史料依據,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重要著作的翻譯史進行梳理、探討;以中央編譯局的黨代會(第十一次至第十七次)會議文件、全會(第十一屆至第十七屆)會議文件、人代會(第五屆至第十一屆)會議文件及全國政協(第八屆至第十一屆)會議文件外譯本為史料,詳細分析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全國黨代會和全會、全國人代會以及全國政協會議文件的翻譯活動;以中央編譯局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外譯本為基礎,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黨史文獻的翻譯史進行分析;以日文版《中國地理便覽》、法文版《中國的世界遺產》等中央編譯局譯作、以多語版“熊貓叢書”、中英版“中國文明與文化”系列圖書等中國外文局譯作為重要史料,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對外文化傳播作品的翻譯史進行研究;最后,以《中國宗教》《俄僑在中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等中央編譯局外譯本為真實史料,進一步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其他主題重要文件的翻譯史展開探討。
(四)第四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2012-至今)
該部分主要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翻譯史研究。(1)譯入篇包括馬列思想、外國文學作品。本篇以中央編譯局的《列寧選集》第三版修訂版(第四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等譯本為脈絡,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馬列著作翻譯史深入剖析。同時,以中國外文局的《騎龍游北京》等譯作為主線,研究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文藝作品翻譯史。(2)外譯篇包括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著作和講話文章、全國黨代會和全會主要文件、全國人代會主要文件、全國政協會議主要文件、黨史文獻、《求是》雜志、文藝作品及其他重要文件。本篇以中央編譯局的《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習近平關于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重要論述選編》等譯本和中國外文局的《習近平談“一帶一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三卷)、《之江新語》《擺脫貧困》《紅船精神:啟航的夢想》等多語譯本為基本史料,深入分析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著作和講話文章的對外翻譯史;以中央編譯局的黨代會(第十八次、第十九次)會議文件、全會(第十八屆、第十九屆)會議文件、人代會(第十二屆、第十三屆)會議文件及全國政協會議(第十二屆、第十三屆)文件外譯本為史料,圍繞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全國黨代會和全會、全國人代會以及全國政協會議文件的翻譯史深入探討;以中央編譯局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英文版為史料,探究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黨史文獻的翻譯史;以中央編譯局的《求是》英文版為線索,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政治文章、論述的翻譯史展開研究;以中國外文局的《這邊風景》(波斯文版)、《敦煌》(英文版)、《道德經》(中英雙語·誦讀版)、“絲路百城傳”(多語版)等外文譯作為重要史料,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文藝作品的對外翻譯史進行挖掘;最后,以中央編譯局的《湘江戰役紀念館解說詞》(英文版)、《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英文版)、《“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俄、德、阿文版)等多語譯本,中國外文局的《中國夢:誰的夢?》(英日文版)、“一帶一路”主題圖書(多語版)、《中國關鍵詞》多語版圖書、輕型圖文畫冊《援鄂醫療隊》(英文版)、《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英文版等外譯本為線索,進一步對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其他零星重要文獻的翻譯史展開探析。

四、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思路與方法
首先,完成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的系統搜集、全面梳理。一方面,以文獻學、考據學等方法為指導,將史料搜集線上、線下相結合,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時期劃分,分別對各時期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的史料、史實進行系統搜集。另一方面,在完成上述史料的搜集后,以“譯入”和“外譯”為翻譯形式,以“馬列著作”“外國文藝作品”“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全國黨代會主要文件”“全國人代會主要文件”“全國政協會議主要文件”“中國文藝作品”“黨史文獻”等為翻譯內容,以中國共產黨相關的“個體譯者”和“集體譯者”為翻譯主體,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實現全面梳理。
其次,形成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內部的多元分析、多維考察。基于對史料的系統搜集與全面梳理,筆者以借助歷史分析法、計量史學方法等,實現對中國共產黨翻譯史內部的多維度探究。例如,以歷史分析法為指導,將中國共產黨的翻譯主體、翻譯內容、翻譯形式等要素分別置于不同時期、不同歷史情境中進行研究,探析各要素之間的內在關聯,揭示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活動的背景、過程(翻譯人物、翻譯作品)、特征及社會影響;以文化學方法為指導,重點考察譯者(個人或集體)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探究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對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的影響;運用計量史學方法,對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的翻譯作品類型、翻譯語種類型、翻譯作品數量等指標進行定量分析,考察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翻譯活動的微觀特征;以歷史比較分析法為指導,對四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進行歷時、共時比較,全方位剖析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的宏觀、微觀特征;參照邏輯與歷史統一之法,對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翻譯內容、翻譯人物、社會影響等要素的歷史考察與邏輯分析相結合,揭示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的內在邏輯與深層規律等。
最后,實現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黨史”主線的直觀凸顯、完整勾勒。一方面,從時間跨度上凸顯“黨史”主線。鑒于以往有關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研究時間跨度的不足,筆者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時期為時間跨度,開展了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包括建黨準備階段)至今的翻譯史研究,其“黨史”主線得以直觀凸顯。另一方面,從研究內容上勾勒“黨史”主線。以往國內的學術成果大多只進行中國共產黨關于某一譯作、某一人物抑或某一翻譯專題的翻譯史研究,研究內容局限、不全面,無法與黨的發展歷程完整契合,因此難以凸顯“黨史”主線。鑒于此,筆者將與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程相關的翻譯活動、翻譯人物、翻譯作品等視為研究內容,實現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研究內容與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的緊密貼合。如此一來,透過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研究內容實現“黨史”主線的完整勾勒。
五、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的意義及價值
(一)黨史意義
就黨史研究而言,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的意義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該研究豐富了黨史研究的內容。中共黨史作為一個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它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活動、歷史事件、歷史言論、歷史經驗教訓、歷史發展規律等”。[7](63)其中,歷史活動具體指“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主體的各方面的歷史實踐活動,如政治活動、軍事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科技活動及組織活動等等”。[7](63)由此可見,中共黨史研究應該也離不開關于中共翻譯活動的探討。值得強調的是,中共翻譯活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在屬于文化活動范疇的同時也與政治活動相互關聯。因此,筆者開展的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將豐富中共黨史研究的內容。第二,該研究拓展了黨史研究的視角。“以往中共黨史的研究視角太窄,僅僅局限于中國共產黨本身,沒有把黨的歷史活動放到整個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歷史運動中去研究;也缺乏與整個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等研究的結合。”[8](142)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正是從廣域史學的角度,把黨的成長史、發展史與歷史文化、對外傳播結合起來。同時,通過激活中共黨史學科與人文學科的固有關系,使中共黨史研究邁向跨學科研究。
(二)黨建意義
就黨建工作而言,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對于中共翻譯事業的發展有著重要指導意義。根據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祝靈君教授關于“黨建”的定位與劃分,我們可將其看作一項具體的黨建工作。“作為一項具體工作的黨的建設,它誕生于革命戰爭年代,并在不同時期不斷發展,最終形成了系統化的工作內容、工作慣例及工作方式。”[9](5)從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歷程可以看出,黨的翻譯工作涉及黨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工作的方方面面,它或與黨的萌芽與成長有關,或與革命年代的武裝斗爭有關,或與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有關,或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來的翻譯事業有關等,尤其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共翻譯事業尤其是外宣事業空前發展。可以說,推動中共翻譯事業的發展始終是百年黨建工作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今天進行的百年翻譯史研究是基于對中共百年翻譯活動的全面梳理、多元分析與系統總結,它在加強黨史研究的同時,可以在隊伍建設、理論研究、實踐開展等多方面為今后中共翻譯事業及黨建工作的發展提供重要指導。
(三)史學價值
從史學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的價值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實現史料的鉤沉與梳理,奠定史學研究的基礎。在本文研究中,筆者將采用線上、線下的史料搜集方式,圍繞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中的翻譯活動,對紙質、電子、文字、影像等多種形式的史料進行搜集與整理,真實客觀地展現中國共產黨翻譯活動的歷史原貌,為其相關翻譯史研究的展開奠定基礎。第二,開展史料的分析與考察,加強史學研究的深度。“目前我國的翻譯史研究論文論著大都側重于以文獻記錄為主的史料鉤沉和梳理,這和中國早期的歷史學和文獻學不分家有關。”[10](120)也正因如此,我國的翻譯史研究極少注重史料的分析與考察,其研究深度嚴重受限。而在本文所開展的研究中,筆者通過翻譯活動的背景、過程(翻譯人物、翻譯作品)、特征及社會影響等多維視角,通過對翻譯活動、翻譯主體、翻譯內容等史料的多元考究,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內部展開多元分析,從而進一步加強其史學研究深度。第三,進行史論的概括與歸納,豐富史學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史學研究所得的最新史論可以作為一種科學性結論,直接豐富該項史學研究的現有成果;另一方面,其最新史論還可以實現對前人史論的辨偽糾正,間接豐富該項史學研究的現有成果。
(四)譯學價值
從譯學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該研究為翻譯學的學科發展注入力量。“翻譯學學科之所以能夠具有今日相對獨立學科門類的地位,是翻譯技巧、翻譯理論、翻譯史研究等三方面力量協力推動的結果。”[11](831)因此,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作為中國翻譯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翻譯學科,尤其是中國的翻譯學科建設至關重要。另一方面,該研究為翻譯實踐的組織開展提供指導。中國的很多翻譯實踐活動都是伴隨著中國的革命運動展開的,翻譯實踐讓中國走上共產主義之道,《共產黨宣言》的翻譯使中國人民看到了真理,開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征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研究可以為中國翻譯的走向、中國翻譯學派的形成提供重要的依據,將會對世界翻譯史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