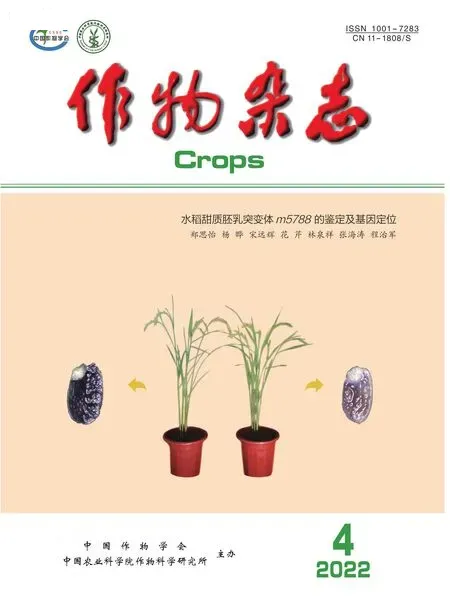基于能值改進模型的紅米與烤煙作物系統可持續性評價
——以貴州省盤州市為例
孫凱梁龍李仲佰
(1貴州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550025,貴州貴陽;2盤州市農業農村局,553537,貴州盤州)
農業作為一個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特性的復雜生態系統,其主要功能是提供食物。但隨著世界人口對食物需求的不斷增長,能源和農用化學品投入增加,在促進作物增產的同時導致農業所依賴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農業可持續發展必須重新審視產量和生態之間的關系。因此,在實際情況中需使農業可持續性可定量化,并使農業生產系統適應經濟、生態和社會系統的可持續發展[1]。
能值分析(emergy analysis,EMA)作為生態學和經濟學之間的橋梁,旨在探索和評價系統的可持續狀況,當前被廣泛運用于農業領域[2-3]。焦士興等[4]運用能值理論,分析河南省農業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與資源環境效益,發現系統過度依賴工業輔助能值投入,且能值內部投入結構存在差異,農業正在遠離生態可持續發展。宋丹等[5]基于區域農業產業協同發展目標,利用EMA法對北京、天津和河北保定農業生態系統進行對比分析,結果表明,天津和河北保定農業系統對環境的壓力要遠大于北京,今后應著重調整津保二市的農業發展方式,以實現京津冀農業協同發展。馬世昌等[6]運用EMA法對安徽省農業生態系統的能值投入、產出及效率進行分析評價,發現安徽省農業系統屬于消費型生態經濟系統,農業生產不可持續,未來需進一步提高能值產出和降低環境負載。
EMA是評價農業可持續性的一種成功方法。但也有學者[7-9]認為,EMA方法忽略了污染排放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因此,通過改進EMA方法并與其他生態環境評價指標和工具組合使用,有可能彌補EMA方法的局限[10-11]。王一超等[9]基于能值與生命周期評價耦合模型,評估了北京市郊區3種(玉米、蔬菜和桃)典型農作系統的生態效率。Su等[12]將農業非點源污染納入能值核算,對中國3種農業生產類型(水稻單作、稻田種養和非糧生產系統)進行了環境可持續性評價。Fan等[13]建議將能值和能量分析結合運用,作為一種可靠的農業生產衡量指標,以便獲得系統更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續生產信息。方一平等[14]將環境污染物(廢水、固廢和CO2)視為非期望產出納入EMA模型,構建了區域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價值度量體系,以檢測西南地區“兩山”價值轉化效率和水平。盡管基于能值改進方法和多指標結合運用的分析文獻不少,但鮮有研究關注農業生態系統的碳源與碳匯。因此,關注并結合“雙重碳”指標,對改進EMA法和進一步探究農作系統可持續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以貴州省盤州市新民鎮為例,在EMA方法框架下,將農業生態系統碳源和碳匯納入相關能值核算指標,并用于評價紅米和烤煙2種典型農作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水平。同時,沿用Wang等[15-16]和王一超等[9]的做法對不同作物系統進行基于彈性系數的靈敏性分析,確定影響系統可持續性表現的環境產出能值流。最后,根據評估結果按照低碳綠色和可持續農業發展原則,提出能兼顧作物生產效率與生態效益的生產優化建議。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概況與材料
新民鎮地處貴州省盤州市東南部(104°48′3~104°58′E,25°17′~25°37′N),下轄 16 個行政村,1個社區,總面積134.5km2,其中耕地面積5770.0hm2,平均海拔1100~1700m,是貴州高原向云南高原的過渡地帶,喀斯特山地特征明顯。太陽輻射量4500~4737MJ/m2,年均氣溫15℃,年均降雨量1135.7mm,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利于作物生長和季節性種植。
新民鎮作為該地區典型農業大鎮,目前主要種植玉米、水稻和小麥等糧食作物,烤煙、生姜、油菜、軟籽石榴和中藥材等經濟作物。過去一直以低效玉米(青貯玉米及籽粒玉米)種植為主,但近年來在玉米價格下行的環境下,地方政府通過不斷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逐步發展出以高原水稻(紅米)為主導,以烤煙、中藥材和精品水果等為特色的多樣化種植模式。為此,本研究根據新民鎮產業發展現狀及規劃布局,選取舊屯村和上乍勒村紅米種植模式代表糧食生產系統,白魚村和五嘎村烤煙種植模式代表大田經濟作物系統(表1),分別分析可持續性,并探究提升空間。

表1 新民鎮2種典型作物種植面積及分布情況Table 1 The planting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two typical crops in Xinmin town
1.2 數據來源
氣象資料來源于中國氣象數據網(http://data.cma.cn/)、貴州省氣象局(http://gz.cma.gov.cn/)和2018-2020年《貴州統計年鑒》。作物種植面積和農產品產量來自《新民鎮“十四五”農業產業發展規劃報告》。土壤侵蝕速率和土壤有機質含量主要參考相關文獻[17-18]。物質投入—產出數據來自2021年9月通過對農業經營主體(公司、合作社和小農戶)進行的面對面訪談和結構式問卷調查的結果。所獲得的農業生產數據包括勞動力、種子、肥料、農藥、農用柴油和農產品產量等,并取平均值。
1.3 農業生態系統邊界
以新民鎮紅米和烤煙2種典型農作物為研究對象,以1hm2單位農田面積的各資源投入和系統產出平均水平為基本計算內容,充分考慮從“搖籃到農田大門”農資生產、農作栽培以及農產品收獲結束過程中的能量流動、溫室氣體排放以及二氧化碳(CO2)固存等細節。其中,根據投入資源的來源判斷,支持系統生產的資源投入可分為自然環境投入和人為輔助投入。自然環境投入包括可更新的太陽光能、雨水化學能、風能(為避免重復計算本文僅考慮數值最大的雨水化學能)(R)和不可更新的表土損失能(N);人為輔助投入包括不可更新的化肥、柴油、農藥、地膜、電力(F)和可更新的有機肥、勞動力及種子(r)。
1.4 研究方法
1.4.1 EMA方法 EMA方法是一種以太陽能為通用單位,以太陽能焦耳(solar emjoules,縮寫sej)為度量標準的生態經濟系統定量評價方法,它通過考慮免費的自然資源投入來評估系統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19-21]。就其分析對象而言,有大到國家或地區的生態經濟系統,也有小到具體產業的生產系統[22]。然而,不同文獻使用的不同能值基準可能導致能值轉換效率的差異[2]。因此,本研究計算使用的能值基準為2016年國際能值學會確定的最新能值基準(1.20×1025sej/a),若涉及所需的能值轉化率,則通過參考文獻的能值基準與最新能值基準(1.20×1025sej/a)的比值來換算。EMA方法一般用以下能量方程式進行計算:

式中,Emergyi表示太陽能值;ei是系統內第i種物質或勞動能量輸入流;UEVi為第i個投入資源的單位能值轉化率,其中自然環境資源投入的太陽能值轉化率采用Odum[20]研究得出的相關參數,人為輔助資源投入和系統產出的能量折算、能值轉化率則選擇具體所投入資源的特定參數[6,20,22-24]。
1.4.2 凈碳足跡法(net carbon footprint method)凈碳足跡法是衡量大氣增暖趨勢和減排潛力的重要方法,它綜合考慮了農業生產各環節的溫室氣體排放與農田CO2固定[25]。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計算:

式中,EE表示農業系統總溫室氣體排放量;GHGEinput表示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量;Gi為各要素投入的數量;βi為相關溫室氣體排放系數(表2);GHGEfield表示施用氮肥引起的農田溫室氣體排放量;N2Odirect為施氮直接釋放的N2O[26];N2Oindirect為施氮間接產生的NH3揮發和NO3-淋失[3];CH4paddy為稻田的CH4排放量(旱地產生的CH4量微小,可忽略不計);1.57和1.33分別是N2對N2O和C對CH4的分子轉化系數;265和28分別是100年尺度上N2O和CH4等量于CO2的全球潛在增溫趨勢[27],t是水稻栽培占全年的時間;α為中國稻田CH4年基準排放系數[28];M為有機肥投入量;0.14是有機肥施用的相應CH4排放參數[29]。

表2 各投入要素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Table 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efficients for each inputs
農田作物CO2固定量計算公式:

式中,ES為農田生態系統植物固定的CO2量,即植物體每積累1g干物質,分別需向大氣吸收1.63g的CO2,釋放1.19g的O2[30];Y為產品產量;θ和H分別為生物體含水率和作物經濟系數[31]。
1.4.3 基于環境產出的能值改進指標(E-EMA indexes) 參照Watanabe等[24]和Wang等[37]的方法,以EMA為基礎,構建包含碳效益的農業生態系統評價模型。具體測算指標如下:
傳統意義上,能值產出率(emergy yield ratio,EYR)是指系統產出能值與人為輔助投入能值的比值,EYR值越高,代表系統的生產效率越好。但是農業生態系統的產出能值不僅只是農產品,還包括生態保育服務(CO2的固定)。因此,理應將農業碳匯視為生態效益產出納入EYR指標進行測算。公式如下:

環境負載率(environmental load ratio,ELR)是指系統不可更新資源與可更新資源能值投入的比值,用來衡量一定生產條件下某一區域或系統生態環境所承受的壓力大小。ELR值越高,代表生態環境承受的壓力越大,一般而言,當ELR<3時,表明壓力小;當3≤ELR≤10時,表明壓力處于中等水平;當ELR>10時,表明壓力很大。與傳統的ELR不同,研究在ELR指數中將農業系統碳排放加以考慮,并理解為生態環境壓力的增加。具體表達方式如下:

生態能值可持續發展指數(ecological emergy sustainability index,EESI)與傳統能值可持續發展指數(ESI)相似,EESI是指生態能值產出率與環境負載率的比值,若生態能值產出率較高而環境負載率較低,則表征該系統是可持續的,反之則是不可持續的。當EESI<1時,表明系統的可持續能力弱,環境負載率高;當1≤EESI≤10,表明系統可持續;當EESI>10時,表明系統資源利用效率較低,整體處于落后階段,可進一步開發[37]。公式如下:

1.4.4 系統靈敏性分析 農業生態系統的靈敏性分析是指通過模擬改變模型內某些能值分量來檢查各項能值評價指標結果的變化,以此探究影響農業可持續性的主要因子[38]。本研究假定系統各資源投入和產品產出不變,設計系統碳排放與碳固定同時減半(減少50%)或加倍(增加200%)的情景,采用基于彈性系數的靈敏性分析方法[15-16],計算各能值指標的變化幅度及波動情況。具體分析公式如下:

式中,E0和E1分別是環境產出能值流變化前和變化后的相應指標結果;ΔC是環境產出增(減)的變動量;SC是靈敏系數,SC>1說明能值評價指標的變化大于能流參數的變化,SC=1表明評價指標與參數同比例變化,SC<1表明評價指標的變化小于參數的變化。
2 結果與分析
2.1 2種典型農作系統的能值投入和產出結果分析
如表3所示,紅米和烤煙系統的總能值投入分別是1.26E+17sej/hm2和1.24E+17sej/hm2,農產品能值產出分別是2.61E+16sej/hm2和6.55E+15sej/hm2,紅米系統的產品產出效率較好。環境能值產出表現為紅米系統碳排放(5.97E+16sej/hm2)遠大于其吸收的碳固定(1.30E+15sej/hm2),是凈溫室氣體排放系統;烤煙系統碳排放(1.95E+14sej/hm2)小于碳固定(3.42E+14sej/hm2),是生態盈余系統,溫室氣體平衡潛力較大。

表3 2種典型農作系統的原始數據及能值結果Table 3 Raw data and emergy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typical crop systems
2.2 2種典型農作系統的能值投入結構分析
2.2.1 自然環境資源能值投入 如圖1所示,紅米和烤煙作物系統更依賴于自然可更新資源的投入,分別占系統總能值投入的89.15%和90.08%,表明當地自然環境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支撐系統自身發展。
2.2.2 人為輔助能值投入 由圖1可知,相比自然環境資源投入,人為輔助能值是人類通過對系統開展間接調控和生產實踐時的各類能量投入。紅米和烤煙作為當地長期保持下來的傳統農作模式,2種系統的人為輔助能值投入差異不大,生產對人為輔助能投入的需要量較少,分別占總能值投入的9.10%和8.15%,但前者的可更新生物有機能投入較多(占8.93%),后者的工業輔助能需求更大(占1.45%),主要表現為烤煙作為經濟作物,其經濟價值相對較高的特點決定了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更偏向于投入較多的工業輔助能值。

圖1 2種典型農作系統的能值投入結構Fig.1 Emergy input structure of the two typical crop systems
2.2.3 人為輔助能值投入構成 紅米生產所需要的人為輔助能包括勞動力、種子、農藥、機械動力燃油和有機肥。其中可更新部分,勞動力和種子投入最多,分別是5.63E+15和5.59E+15sej/hm2,有機肥為1.81E+12sej/hm2;不可更新部分,機械動力燃油和農藥的投入分別是2.08E+14和2.47E+11sej/hm2(表3)。可見,該地區紅米種植仍較為傳統和原生態,而烤煙生產則額外增加了化肥和農膜的投入,使得工業輔助能值投入(1.80E+15sej/hm2)高于紅米。
從2種典型農作系統人為輔助能值投入的內部構成可知,一方面雖然紅米和烤煙同為大田生產,但烤煙屬于經濟作物,所以各農業生產經營者更加重視對烤煙的栽培、管理和收獲;另一方面盡管農用機械已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廣泛應用,但在土地相對零散,以丘陵、坡地為主的新民鎮,其農業機械化程度普遍偏低,生產尤其依賴勞動力的密集投入。
2.3 能值指標評價百分比
傳統和改進的能值評價指標核算結果(表4)表明,紅米和烤煙系統的傳統EYR分別是2.28和0.65,但考慮生態效益產出后,烤煙系統的能值產出率提升了1.5%,為0.66。因此,理論上傳統只關注到社會和經濟效益的EYR核算不足以全面反映生態產出效益較好的農業系統真實貢獻。與傳統的ELR(0.02和0.03)相比,關注了溫室氣體排放產出的ELR改進指標值分別是0.49和0.03。其中紅米系統作為農業溫室氣體排放“源”,其ELR從0.02增加為0.49,指標變化顯著,系統環境壓力明顯增大。在紅米系統中傳統的ESI是116.84,大于10,表明該種農作模式整體處于落后待開發階段。而考慮環境產出后,其EESI出現明顯下降,為4.63。但在碳排放較低的烤煙系統中ESI和EESI差距不大,分別是19.43和19.87。可見,對比傳統和改進的能值指標,對運用能值方法評價農業生態系統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

表4 2種典型農作系統的能值評價指標Table 4 Emergy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two typical crop systems
2.4 靈敏性分析結果
如表5和圖2所示,紅米系統的EYS、ELR和EESI指標變化和相應的SC值結果表明,溫室氣體排放變化對ELR和EESI的影響較大。當系統溫室氣體排放增加一倍后,環境負載率將升高98.18%,生態能值可持續發展指數則會降低49.54%,且ELR和EESI的SC值分別是0.49和0.25;而當系統溫室氣體排放減少一半后,ELR和EESI分別降低49.09%和升高96.42%,同時ELR的SC值是1.96,大于1,EESI的SC值是0.99,接近1,說明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提升幅度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量接近于同比例變化,但ELR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半變化更為敏感,ELR的降低程度遠超過系統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幅度,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能夠減輕系統更多的生態環境壓力。

表5 2種典型農作系統環境產出變化及能值指標波動Table 5 Changes of environmental output and emergy indexes fluctuation of the two typical crop systems

圖2 紅米系統環境產出增(減)后的靈敏性系數Fig.2 Sensitivity coefficients of the red rice system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output increase or decrease
相比紅米生產系統,烤煙系統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圖3),碳排放變化對EYS、ELR和EESI指標的影響較小。但當CO2固定量增加1倍后,EEYR增加5.11%,EESI提升5.11%,相應的SC值都接近0.03。而當系統CO2固定量減少一半后,ELR提高0.60%,EEYR和EESI分別降低2.20%和2.78%,相應的SC值約為0.04、0.01和0.06。

圖3 烤煙系統環境產出增(減)后的靈敏性系數Fig.3 Sensitivity coefficients of the flue-cured tobacco system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output increase or decrease
因此,紅米生產模式的可持續發展水平與系統溫室氣體排放有關,而穩定或增強烤煙生產模式的碳平衡能力可以促進系統生態服務產出、降低環境壓力和提升可持續發展水平。
2.5 確定關鍵投入能值流
從以上的靈敏性測試結果可知,溫室氣體排放是制約紅米系統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子,需進一步減少系統溫室氣體排放。其中稻田CH4減排是重點領域,在擴大紅米種植規模的過程中應特別關注淹水厭氧條件下,稻田土壤中產甲烷菌作用于產甲烷基質產生的CH4排放,可采用覆膜栽培和秸稈合理還田等農藝措施避免溫室氣體過度排放導致環境壓力升高,超出系統承受閾值,降低生產可持續性。
雖然環境產出變化對烤煙種植可持續性的影響不大,但針對現階段烤煙較多依賴不可更新工業輔助能投入(尤其是化肥),產量卻并不高的事實,未來烤煙發展可通過促進良種選育、鼓勵生產經營者選擇對環境影響較小的生物有機肥替代化肥等生產技術,達到烤煙高產和優質,實現不可更新工業輔助能值投入的調控,進而在真正提高作物系統生產效率的同時保證其固碳能力不被破壞,維持系統發展的穩定性。
3 討論
目前,EMA方法已經被用于評價多種農業生產模式的可持續性,但是很少有研究在能值的基礎上關注并考慮農業系統的生態效益和環境排放,使得評價結果缺乏系統性與全面性。因此,考慮了農業碳源與碳匯的能值改進指標體系被用來評估貴州省新民鎮一級紅米和烤煙2種典型農作系統的可持續性,以此兼顧農業生產和生態的雙重功能。
從能值產出率來看,理論上包含生態服務效益產出的EYR改進指標值應高于傳統的EYR核算結果。從環境負載率來看,傳統的ELR核算并未考慮到溫室氣體排放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能導致測算結果低于改進的ELR,然而將其用于分析作物系統中的生態環境壓力有失偏頗。從可持續性指數來看,2種不同指標體系得到的結果存在差異,說明環境產出指標對衡量和評價農業系統穩定性與可持續性具有較大的影響,不能被忽視。
整體上,未考慮農業系統雙碳效應的能值評價指標體系分析結果與改進了的能值評價指標體系分析結果相比,只強調農作系統社會、經濟效益而忽略生態產出(包括生態服務產出和環境損害產出)的傳統能值分析,很可能導致可持續評價結果的高估(忽略農業溫室氣體源排放)或低估(忽略農田生態系統作物碳固定),不能綜合、全面地判定農業生產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未來考慮環境排放與生態服務的多維能值評價指標應是EMA方法運用于農業系統可持續性研究的重點內容。
4 結論
在新民鎮區域內,紅米和烤煙系統對環境造成的壓力雖然都比較小,但紅米系統凈溫室氣體平衡效果不理想,整體表現為碳排放“源”,因此需采取有效的稻田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將碳排放量限制在能夠維持作物生產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可控范圍內。烤煙系統雖然表現為較好的生態效益,但是作物單位面積產量較低,因此提高煙葉產量是今后烤煙種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