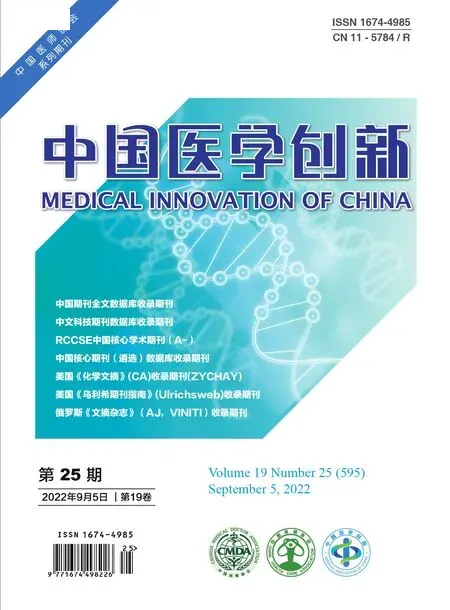中西醫結合治療對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患者血清sICAM-1、SULT2A1水平及肝功能的影響
陳華艷
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是中晚期孕婦常見的并發癥,屬特發性疾病,常引起皮膚瘙癢等癥狀,若不及時干預,將對胎兒及孕婦自身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甚至增加圍生兒病死率[1-2]。目前對于ICP 發病機制暫無明確定義,可能與環境、遺傳、母體激素水平等因素密切相關。西醫在ICP 治療中以降低孕婦體內膽酸表達水平為主,能夠有效控制病情,但需長時間用藥,易產生較多副作用,且停藥后癥狀反復,遠期效果不佳[3-4]。中醫學無ICP 病名,依據其癥狀表現將其歸結為“妊娠黃疸”“妊娠瘙癢”等范疇,認為該病的發生與濕熱瘀、肝膽濕熱內蘊相關,發病時以黃疸、皮膚瘙癢為主要癥狀表現,在中醫治療中應以疏肝解郁、清熱燥濕、利膽化瘀為原則[5]。鑒于此,本研究納入60 例2020 年1 月-2021 年1 月于江西省婦幼保健院接受治療的ICP 患者,采用中西醫結合治療ICP,旨在探究其對血清可溶性細胞間黏附分子-1(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sICAM-1)、硫酸基轉移酶2A1(sulfotransferases 2A1,SULT2A1)及肝功能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 年1 月-2021 年1 月于本院接受治療的60 例ICP 患者。診斷標準:西醫符合文獻[6]《婦產科學》中肝內膽汁淤積癥診斷標準,患者于妊娠中晚期出現黃疸、瘙癢等癥狀,血液檢查可見空腹血清總膽汁酸水平明顯升高(≥10 μmol/L),肝功能檢查提示谷草轉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及谷丙轉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正常或出現升高,妊娠終止后癥狀消失,肝功能恢復正常。中醫符合文獻[7]《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肝膽濕熱型診斷標準,身目黃染,皮膚瘙癢,小便黃染,嘔惡納呆,大便秘結,舌苔黃膩,脈弦數。納入標準:(1)符合中西醫診斷標準;(2)孕前無肝膽疾病;(3)均處于孕中晚期;(4)均為單胎妊娠。排除標準:(1)肝腎綜合征;(2)免疫性肝炎;(3)肝臟惡性腫瘤、酒精性或藥物性肝病;(4)對本研究藥物過敏;(5)病歷資料缺乏;(6)精神疾病,無法配合完成本研究。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研究組(n=30)及對照組(n=30)。本研究獲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家屬均對本研究知情同意。
1.2 方法 對照組行西藥治療,熊去氧膽酸片(生產廠家:武漢普元藥業有限責任公司,批準文號:國藥準字H20123209,規格:0.25 g/片),8~10 mg/(kg·d),于早、晚進餐時分次服用,2 次/d。研究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自擬利膽湯治療,組方如下:梔子、黃芩、地膚子各10 g,茯苓12 g,丹參、茵陳蒿各20 g。若黃疸嚴重,加柴胡、牡丹皮各10 g;若瘙癢嚴重,加澤瀉、荊芥、白鮮皮各10 g。用水煎煮取汁200 mL 服用,2 次/d。兩組均連續治療15 d。
1.3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1)比較兩組臨床療效。依據文獻[8]《中華婦產科學》中療效判斷標準:皮膚瘙癢、黃疸等癥狀全部消失,肝功能明顯改善為顯效;皮膚瘙癢、黃疸等癥狀較治療前好轉,肝功能好轉為有效;上述癥狀均無明顯好轉為無效。總有效=顯效+有效。(2)比較兩組治療前后中醫癥候積分。評估患者身目黃染、皮膚瘙癢、小便黃染、嘔惡納呆、大便秘結各癥狀改善情況,采用0、2、4、6 分評分法,分別表示癥狀無、輕度、中度、重度,癥狀越嚴重,評分越高。(3)比較兩組治療前后肝功能及血清sICAM-1、SULT2A1 水平。采集患者清晨空腹肘靜脈血3 mL,應用日立7600 型全自動分析儀,應用速酶法測定血液標本中AST、ALT及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水平。于治療前后采集空腹肘靜脈血3 mL,將血液標本放置于離心機內以3 500 r/min 速度,離心10 min 獲得上層血清,采用ELISA 法測定血清sICAM-1、SULT2A1 水平。(4)比較兩組妊娠結局,包括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羊水污染。(5)比較兩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包括皮疹、頭暈、便秘、腹瀉。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2.0 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研究組年齡21~36 歲,平均(28.56±3.61)歲;體重指數24.3~29.8 kg/m2,平均(27.16±0.72)kg/m2;孕周32~40 周,平均(36.85±1.29)周;孕次1~3 次,平均(1.52±0.43)次;產次1~3 次,平均(1.05±0.40)次;經產婦9 例,初產婦21 例。對照組年齡22~36 歲,平均(28.67±0.59)歲;體重指數24.4~29.7 kg/m2,平均(27.20±0.70)kg/m2;孕周32~39 周,平均(36.69±1.30)周;孕次1~4 次,平均(1.60±0.47)次;產次1~3 次,平均(1.10±0.42)次;經產婦10 例,初產婦20 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2.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研究組治療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320,P<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例(%)]
2.3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癥候積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中醫癥候積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中醫癥候積分均低于治療前,且研究組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癥候積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癥候積分比較[分,(±s)]
2.4 兩組肝功能及血清sICAM-1、SULT2A1 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AST、ALT、TB、sICAM-1、SULT2A1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研究組AST、ALT、TB、sICAM-1 水平均低于對照組,SULT2A1 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肝功能及血清sICAM-1、SULT2A1水平比較(±s)

表3 兩組肝功能及血清sICAM-1、SULT2A1水平比較(±s)

表3 (續)
2.5 兩組妊娠結局比較 研究組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羊水污染發生率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妊娠結局比較[例(%)]
2.6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 研究組出現頭暈1 例,皮疹及便秘各2 例,發生率為16.67%(5/30);對照組出現頭暈及皮疹各1 例,便秘3 例,腹瀉2 例,發生率為23.33%(7/30)。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417,P=0.519)。
3 討論
中醫學認為ICP 的病機在于濕熱薰蒸,蘊結肝膽,肝氣郁滯,瘀阻脈絡而致脈道不通、營衛不和,從而引發膽汁外溢,或因熱毒入侵,熏灼肝膽,膽液外溢于皮膚。《黃帝內經》中記載:“邪在肝,兩脅中痛”,說明血瘀可引發肝病;《靈樞經》中記載:“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脅滿痛”,提示雖熱從肝生,但下焦也會出現相對應的熱象表現[9]。由此可見,在濕、熱、瘀三者共同作用下,相互搏結而引發ICP,且上述病理產物長時間會對肝、膽造成損傷,當肝失疏泄時,則諸竅不利,膽汁外溢而發黃[10]。因此,中醫治療ICP 應以清熱利濕、理氣寬中為原則。
因妊娠期孕激素分泌量多,孕激素水平急劇上升,致使毛細膽管膜上的酶系統受到明顯抑制,導致膽汁排泄受到障礙,從而引發黃疸[11]。另受到雌激素大量分泌的影響,患者毛細膽管膜的通透性明顯升高,造成膽汁中的水分流入血液中,使得膽酸排泄受阻,嚴重者形成膽栓,危及產婦及胎兒生命安全[12]。故對于ICP 患者給予積極治療尤為重要。現階段,熊去氧膽酸片是治療ICP 的首選西藥,該藥物能夠降低細胞毒性內源性膽汁酸濃度,減輕膽汁酸對肝細胞的損傷及對線粒體功能的干擾,還可減緩肝細胞凋亡過程,穩定肝細胞膜,有助于降低炎癥因子活性[13]。但單純使用熊去氧膽酸片治療ICP 無法有效及時緩解病情,遠期效果不佳[14]。正常人血液中含有一定的SICAM-1,但當發生炎癥、癌癥、移植物排斥時,血液中含量升高,在妊娠晚期時,SICAM-1 表達紊亂,可導致胚胎發生死亡。血清SULT2A1 為膽汁酸硫酸化的關鍵酶,參與機體內類固醇激素的硫酸化過程,當機體疏水性膽汁酸濃度過高時,可增強其水溶性,并可降低其對肝細胞的毒性。妊娠晚期孕婦SULT2A1 水平下降可導致疏水性膽汁酸排出受阻,從而于孕婦體內大量積聚,導致患者肝功能異常,肝細胞受損,形成惡性循環。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治療總有效率為93.33%,高于對照組的73.33%,治療后中醫證候積分、AST、ALT、TB、sICAM-1 水平均低于對照組,SULT2A1 水平高于對照組,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羊水污染發生率分別為10.00%、3.33%、13.33%,均低于對照組的33.33%、26.67%、43.33%(P<0.05),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中西醫結合治療能夠有效緩解ICP患者臨床癥狀,改善肝功能各指標水平及妊娠結局,具有較高的安全性。究其原因可知自擬利膽湯具有清熱利濕、祛風止癢之效,組方中梔子清熱利濕、瀉火除煩;黃芩瀉火解毒、清熱燥濕、止血安胎;地膚子祛風止癢;茯苓滲水利濕、益脾和胃;丹參養血安神;茵陳蒿清熱利濕退黃[15-17]。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黃芩可產生較強的抑制抗體及中和抗體作用,并能夠促進膽紅素排出,起到保肝利膽效果;茵陳蒿提取物有助于肝細胞再生,可加快膽酸及膽固醇的排泄速度,延緩肝細胞壞死,甚至逆轉肝細胞壞死進程;黃芩提取物退黃、降膽酸功效明顯;茯苓可抑制白細胞黏附,利于加快膽汁的排泄速度[18-19]。中西醫聯合治療,可標本兼顧、協同增效,進一步改善肝功能及妊娠結局。
綜上所述,中西醫結合在ICP 治療中療效確切,能夠有效緩解各臨床癥狀,保護肝功能,調節sICAM-1、SULT2A1 水平,有助于妊娠結局的改善,安全性高,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