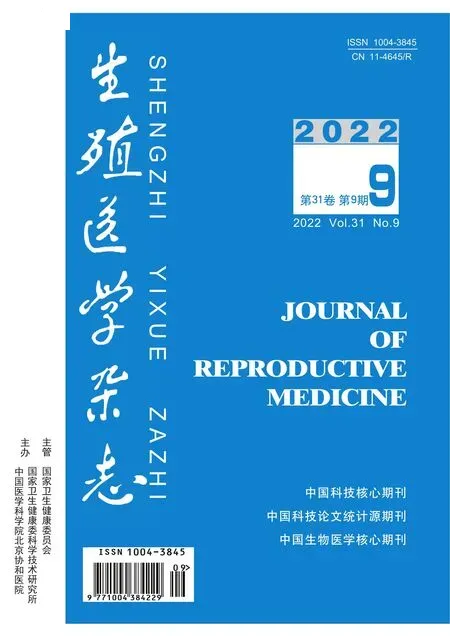中期妊娠引產清宮后胚物殘留致“動靜脈瘺”兩例探討
楊潤喬,鄧姍
(1.盤錦市中心醫院婦產科,盤錦 124010;2,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北京協和醫院婦科內分泌與生殖中心,國家婦產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病例1患者女,35歲,孕3產1(G3P1),因“中期妊娠引產后5月余,發現宮腔占位4月”于2021年12月10日入住北京協和醫院。
初潮12歲,既往月經不規律,5 d/30~90 d,量中,無痛經。2009年自然受孕人工流產1次;2015年因繼發不孕行宮腹腔鏡手術,見宮腔兩側壁中下段內聚,行粘連分離術;2018年 因巨大兒剖宮產1次。
2021年7月1日自然妊娠后孕18周時發生難免流產行引產術+清宮術,術后陰道出血3周,量不多;術后6周余(2021年8月19日)外院復查超聲示宮腔內異常回聲4.3 cm×3.4 cm、子宮肌壁間血流豐富(局部動靜脈瘺?),考慮出血風險大,建議咨詢栓塞的必要性;術后8周左右(2021年8月30日)就診于北京協和醫院,查血激素水平:卵泡刺激素(FSH)6.17 U/L、黃體生成素(LH)4.80 U/L、雌二醇(E2)106.43 pmol/L、孕酮(P)<0.25 nmol/L、β-HCG 1.43 U/L。給予口服優思悅1個周期,同時加用生化顆粒、益母草顆粒。優思悅撤退性出血后(2021年10月11日)外院復查彩超:宮腔內異常回聲1.4 cm×0.7 cm,與子宮后壁分界欠清,宮腔下段索條狀強回聲寬0.7 cm。2021年10月15日開始口服芬嗎通2/10(早紅片,晚黃片)×14 d。2021年11月5日再次月經后復查經陰道超聲(圖1A、B):內膜厚約0.6 cm,回聲不均,內見多處點條狀強回聲,較大者直徑約0.2 cm,后伴彗星尾;宮腔內見中低回聲,大小0.8 cm×0.4 cm,形態規則,邊界清;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CDFI)未見明確血流信號,子宮肌層回聲均。2021年11月15日口服地屈孕酮10 mg bid×10 d,停藥于2021年11月29日出現撤退性出血,持續4 d,量中等,無痛經。2021年12月7日我院復查經陰道超聲(圖1C、D):內膜厚約0.6 cm,回聲不均,宮腔及內膜處見多處點條狀強回聲,周圍見少許無回聲,較大強回聲0.4 cm×0.2 cm;宮腔下段見無回聲,1.1 cm×0.5 cm;子宮肌層回聲尚均。考慮宮腔內疑似“動靜脈瘺”的占位組織雖明顯縮小,血流信號也消退,但宮腔內始終有異常回聲,性質不明,患者仍有生育要求,行宮腔鏡檢查是合理的。
2021年12月13日宮腔鏡術中(圖1E、F)見宮腔深7.5 cm,中下段略內聚,宮底及后壁見片狀疏松淡黃色組織,采用宮腔鏡下刨削器械清除宮腔內上述淡黃色組織后,宮腔形態正常,雙側輸卵管開口可見。術后病理:增殖期子宮內膜及平滑肌組織,局部可見退變物,免疫組化CD138+,符合胚物殘留。術后口服優思悅,月經規律來潮,量中等。

兩次藥物撤退性出血后超聲,A:箭頭示宮腔內中低回聲,大小0.8 cm×0.4 cm,CDFI未見明確血流信號;B:箭頭示宮腔內點條狀強回聲,后伴彗星尾。第3次藥物撤退性出血后超聲,C:箭頭示宮腔及內膜處見多處點條狀強回聲,周圍見少許無回聲;D:箭頭示宮腔下段無回聲,1.1 cm×0.5 cm。宮腔鏡探查,E:箭頭示少許胚物殘留主要位于宮底后壁,與肌層關系密切;F:箭頭示前壁對應部位內膜光滑,繼發粘連的風險小。
病例2患者女,28歲,G2P0,因中期引產后近2月、超聲提示“肌層動靜脈瘺”來診。
既往月經規律。2021年9月因“孕12+周,胎兒NT增厚”行藥物引產,9月17日流產,9月18日清宮;清宮術后出血半月余,因宮腔可疑占位,口服益母草和桂枝茯苓膠囊。2021年10月15日出現陰道流血,前7 d量正常,后淋漓一周。2021年10月29日復查超聲:宮腔上段至前壁肌層可見3.7 cm×2.6 cm×1.7 cm不均質回聲,前壁肌層最薄處0.38 cm,內可見豐富血流信號。予米非司酮25 mg bid × 8 d,期間第3天開始出血量似月經,淋漓不凈近20 d。2021年11月8日復查超聲:同部位不均質回聲區3.6 cm×3.3 cm×2.0 cm,前緣幾乎達漿膜,后緣緊貼宮腔。同期血HCG 4.1 U/L。當地考慮肌層內血流豐富的占位,可能需要子宮動脈栓塞治療,建議轉診來至我院。2021年11月14日查盆腔增強MRI(圖2A、B):子宮前壁下段肌層局限變薄,最薄約0.2 cm;宮腔及子宮前壁周邊及內部可見多發迂曲增粗血管樣流空信號,宮腔內見片狀T1高信號,盆腔內多發迂曲血管影;盆底血管稍迂曲增粗,雙側附件區多發類圓形T1低T2高信號,增強未見明顯異常強化。鑒于患者無活躍出血,予新生化顆粒、益母草、安坤顆粒等藥物保守治療觀察,2021年11月28日月經來潮,前7 d似正常月經量,后淋漓不盡持續20余天,隨后一次月經為2022年1月1日,量中,無明顯痛經。2022年1月4日復查經陰道超聲(月經第3天)(圖2C、D):子宮大小5.5 cm×5.2 cm×4.1 cm,內膜厚約0.9 cm,回聲不均,肌層回聲欠均,CDFI見肌層內較多血流信號;右后壁見低回聲區,范圍約1.8 cm×1.4 cm,邊界不清,內可見點狀強回聲,CDFI見內部及周邊較多條狀血流信號。給予優思悅每天1片口服2周期,月經規律,經期3天,此后間斷偶有少許褐色分泌物,較用藥前明顯好轉。停用優思悅后的末次月經為2022年2月27日,3月1日(月經第3天)復查性激素六項:FSH 23.11 U/L、LH 9.83 U/L、E2109.22 pmol/L、PRL 12.25 ng/ml、T 0.325 ng/ml、HCG(-);2022年3月13日月經后經陰道超聲復查(圖2E、F):子宮大小、形態正常,內膜0.8 cm,宮腔內未見明顯腫塊影像,下段后壁探及約1.4 cm×1.1 cm低回聲區,邊界欠清,CDFI肌壁間未見異常血流信號。考慮局限性腺肌病可能。

引產術后2月余盆腔增強MRI,A:箭頭示宮腔內見片狀T1高信號,前壁肌層似有浸潤;B:箭頭示宮腔內見片狀T1高信號。中成藥保守治療2個月經周期后經陰道超聲,C:箭頭示子宮右后壁低回聲區,范圍約1.8 cm×1.4 cm,邊界不清,內可見點狀強回聲;D:箭頭示CDFI見低回聲區內部及周邊較多條狀血流信號。兩個藥物周期后復查超聲,E:箭頭示宮腔內未見明顯異常影像;F:箭頭示子宮下段后壁1.4 cm×1.1 cm低回聲區,邊界欠清,未見異常血流信號,考慮局限性腺肌病可能。
結合患者目前檢查結果來看,考慮宮腔內無異常占位,但子宮下段后壁低回聲區性質仍不明確,無法明確鑒別是無活性的胚物殘留還是局限性腺肌癥。但目前月經規律,無異常出血,暫不考慮宮腔鏡探查,可停用優思悅監測基礎體溫,觀察排卵情況,并擇期復查性激素六項(因前期檢查提示有卵巢功能下降)。
討 論
一、胎盤植入、殘留等造成的動靜脈瘺的自然轉歸規律
子宮動靜脈畸形(uterine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UAVM)是子宮供血動靜脈間出現不經過毛細血管網的異常“短路”的病理現象,通常伴有血管增生及大量小瘺道形成[1],組織學檢查顯示壁內動脈分支和肌層靜脈叢之間有多個小的動靜脈瘺[2-3],血液從壓力高的動脈血管通過動靜脈瘺道或短路血管直接流入壓力低的靜脈血管,使局部血液循環阻力顯著下降,導致血流速度明顯加速,血流量異常增大,并隨時間的延長逐漸加重,在瘺口部位局部靜脈顯著曲張,引起繼發性出血及腹痛等臨床癥狀。該疾病1926年首次由Dubreuil等[4]描述,當時命名為子宮蔓狀動脈瘤。其后該疾病被冠以不同的名稱,如子宮動靜脈瘺、子宮肌層過度血管化、動靜脈動脈瘤、海綿狀血管瘤、靜脈曲張性動脈瘤等,其中似乎子宮動靜脈瘺最常用。
UAVM可分為先天性和獲得性[5]。先天性UAVM 起源于胎兒血管形成期原始的毛細血管變異[6],是由于胚胎期原始的血管結構發育異常或停止發育而使原始的叢狀結構持續存在所致。獲得性UAVM常繼發于子宮手術(如診斷性刮宮、剖宮產)、多次妊娠、復發性流產、分娩、胎盤植入、妊娠物殘留、宮內節育器置入、子宮腫瘤、滋養細胞疾病、母體己烯雌酚暴露、感染等情況[7],平均發病年齡為33.4歲。有回顧性研究列舉了UAVM患者的既往疾病和手術史,其中62%曾行診斷性刮宮術、26%曾行剖宮產術,宮腔鏡或宮內節育器放 置術、子宮肌瘤剔除術、滋養細胞腫瘤者各占4%[7]。多數學者認為UAVM與損傷過程中的反常血管化或滋養細胞腫瘤及惡性腫瘤的血管侵襲性等有關,另外與高雌激素水平的作用引起血管內皮增殖和子宮內膜的變異、多次妊娠流產病理性的胚胎著床及產后子宮復舊不良及妊娠殘留胎盤血管床復舊不全等都可能相關[8-10]。
胎盤植入、胚物殘留等造成的動靜脈瘺的臨床轉歸受UAVM血管的位置和血管口徑的大小的影響。部分患者可無明顯臨床表現,病灶可隨時間延長在數周或數月內消退;部分患者可因子宮創傷、月經周期或妊娠引起的激素水平變化出現病情進展[11],表現為間斷性的陰道流血、突發大量出血、月經過多等和盆腔痛;少數嚴重的患者在病變部位可觸及或探及搏動感或血流震顫感;極少數患者可因嚴重出血導致休克[12]。
二、胚物殘留的處理時機和策略
胚物殘留(retained products of conception,RPOC)指自發性妊娠丟失(流產)、計劃性終止妊娠或早產/足月產后胎盤和/或胎兒組織殘留于子宮腔內。在足月產后的發生率約為1%[13],自然流產、習慣性流產或人工流產術后的患病率可高達6%[14]。
RPOC的主要危害是異常子宮出血和繼發宮腔或宮體感染,少數情況下,殘留組織仍有滋養細胞活性,可出現HCG下降不滿意并合并月經延遲。
對于RPOC的處理時機及策略需結合患者的癥狀及病情是否穩定來選擇:
1.子宮出血過多而導致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患者:應根據需要補充液體和使用血液制品,并進行緊急手術干預。如清宮術后仍不能減緩出血,可嘗試使用宮腔內球囊導管(如Foley、Bakri等)填塞;如仍無效,則可選擇子宮動脈栓塞(UAE)術。當流產孕周及殘留胚物較大,以及合并流產相關并發癥時,更有可能發生陰道大出血,此時可行UAE術后宮腔鏡下病灶切除[15]。子宮切除術是個別情況的極端搶救手段。
2.伴有膿毒血癥(臨床診斷為感染,同時滿足以下至少2項:體溫>38.5℃或<35℃;心率>90次/min;呼吸>20次/min或動脈二氧化碳分壓<32 mmHg;白細胞>12×109/L、<4×109/L,或未成熟(桿狀核)白細胞>10%)的患者:應給予靜脈廣譜抗生素治療,情況穩定后盡早行清宮術,延遲清宮可能致命。
3.持續出血但生命體征平穩且不伴有感染的患者:可視出血的量及時間等具體情況,選擇期待治療或手術干預。對于自然流產的患者來說,期待治療的成功率在隨訪1~2周時為50%~85%,在隨訪6周時高達90%[16-17]。手術干預用于出血時間長、量較多和/或有繼發感染跡象的患者,具體方式包括刮匙刮宮或負壓吸宮術,或宮腔鏡定向清除術。宮腔鏡手術,具有能同時診斷和治療的優勢[14,18],一項關于宮腔鏡切除RPOC與刮除術清除RPOC的直接比較研究顯示,宮腔鏡操作后的子宮粘連發生率明顯更低,這很可能是因為避免了對子宮內膜的整體造成損傷[18]。從宮腔粘連的發生角度來看,妊娠期(或近期妊娠過)的子宮進行刮宮術是發生宮腔粘連的主要危險因素,尤其在感染的情況下,并且風險似乎隨著手術操作的次數增加而升高。研究顯示,采用宮腔鏡冷刀系統相較于傳統清宮術對內膜的保護性更好、術后宮腔粘連的發生率更低[14],采用宮腔鏡刨削系統清除RPOC相較于宮腔鏡電切,手術時間更短,選擇性更高,對周圍子宮內膜沒有熱損傷及熱效應,內膜損傷更小,術中并發癥及術后子宮粘連的發生率更低[13,19-20]。宮腔鏡抓取鉗治療RPOC也比傳統刮宮術遠期并發癥少,術后妊娠結局較好[21]。因此,在適當的時機,采用定向宮腔鏡,尤其是無能量器械清除RPOC是最佳的處理方法。
縮宮素類藥物、米非司酮和/或米索前列醇常被用于RPOC的治療,但具體方案(包括劑量和時間)均無明確的規范。也有不少醫生愿意采用中藥方法,如益母草、新生化顆粒等促進流產后宮腔的恢復。
本文中兩例中期引產后宮腔及肌層占位,超聲提示動靜脈瘺,考慮為胎盤植入或胚物殘留相關的繼發性動靜脈瘺,癥狀上均沒有明顯的大出血和繼發感染征象,病情穩定,給了我們短期觀察和藥物保守治療的時間。患者最初就診時均有被告知需要子宮動脈栓塞治療的可能,以預防潛在的大出血意外,但我們在處理上既未選擇預防性子宮動脈栓塞,也沒有選擇積極地清宮處理,而是進行了3~4個周期的藥物治療,包括復方口服避孕藥(COCs)、地屈孕酮、人工周期等。根據前人的經驗,胚物殘留最好能在流產后70 d左右或經超聲多普勒顯示無豐富血流信號的情況下再行宮腔鏡擇期手術,也就是說觀察兩個月經周期相對理想。藥物治療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內膜脫落法消除病灶,病例1在每次月經后都可觀察到宮腔內占位的明顯縮小,也沒有異常的子宮出血,于是選擇繼續觀察,后來因超聲還是提示宮腔內有不明確的微小占位,而她還有生育要求,故建議行宮腔鏡檢查和治療。宮腔鏡采用無能量刨削系統定向清除殘留妊娠物,術程順利,術后因患者同時合并有排卵障礙,給予優思悅調整月經。病例2則在經過3個周期的藥物治療后,宮內殘留胚物消失,宮后壁異常回聲雖然仍不明確,但患者無異常出血,病情穩定,暫不考慮宮腔鏡檢查,隨訪超聲即可。
我們借鑒人流術后關懷項目(即人流術后即開始服用短效口服避孕藥)以及COCs廣泛用于異常子宮出血治療的經驗,經激素檢測排除仍有明顯絨毛HCG活性后,給予COCs并無禁忌,而臨床實例獲得的經驗是可行的。當然,需要強調的是,需要跟患者做好風險告知,一旦出血活躍,應盡早急診就診,仍有再次清宮的可能。而如能順利過渡,擇期行宮腔鏡檢查和治療是最理想的。